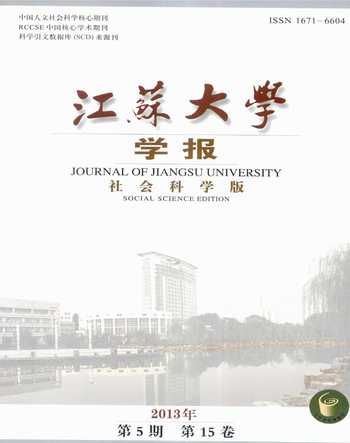从“反动女作家”到文化交流使者
梁志芳
摘要: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是20世纪中关文化交流史上一位重要而独特的人物,其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30余年(1950—1987年)间一度受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控制,长期被误解、误读,甚至被遗忘和抛弃。改革开放后,赛珍珠作品在中国才逐步“解禁”,对赛珍珠的评价也逐渐趋向客观理性。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大地》三部曲;麦卡锡主义;世界文学;以阶级斗争为纲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5—0005-06
1938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年)主要凭借其中国题材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主要以写中国题材作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她被美国历史学家汤姆森(James C.Thom—son,Jr.)誉为“自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赛珍珠一生创作了百余部作品,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题材。赛珍珠的中国题材作品早在1931年便在中国引起了关注,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热议的话题。在中国80余年的赛珍珠接受史中,赛珍珠一度在中国家喻户晓、备受推崇,也一度长期被误解、误读,甚至被遗忘、抛弃。中国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80年代-90年代曾经两度出现过翻译传播赛珍珠作品的热潮。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由于“冷战”与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等原因,赛珍珠作品在中国遭到了否定与全面批判。
目前,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4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两个时期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已有较深入研究,如姚君伟(1994)、刘海平(1998)、郭英剑(1999)、谢天振与查明建(2003)等,而对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中国对赛珍珠的接受情况则分析较少,论述不够透彻。本文以《赛珍珠反动作品选辑》(1959)等第一手赛珍珠研究资料为基础,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对赛珍珠作品在新中国38年(1950—1987年)的译介过程爬梳剔抉、推原本根,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如何控制赛珍珠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新中国38年到底对赛珍珠哪些作品进行了怎样的批判?又是如何评判的?赛珍珠为何会受到“封杀”?有无赛珍珠作品被翻译?赛珍珠作品在中国是何时开始解禁的?其解禁是一蹴而就的,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反复的过程?
一、“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赛珍珠作品的封杀期(1950—1981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冲突等原因,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民间接触几乎完全中断,中美进入了全面对抗的历史阶段。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恐共、反共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盛行,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敌对。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完全沦为政治与阶级斗争的工具,人们习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欧美作家及其作品,海明威、福克纳等作家在中国受到广泛排斥,他们的作品在中国译介极少。而赛珍珠则被视为“反动女作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完全控制了中国对赛珍珠作品的阐释与评价,赛珍珠对中国的描述无法受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与中国官方致力于建设的民族国家背道而驰,因而受到抵制与审判。
1949年后,赛珍珠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列为“禁书”,遭到全面否定与批判。据笔者统计,1950-1981年整整32年间,中国几乎没有出版任何赛珍珠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1959年出于批判赛珍珠的需要,《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作为“内部参考”资料的《赛珍珠反动作品选辑》。该选辑由戈哈(原名李文俊)、董衡巽、柳勤等15人编译,以“内容梗概”、“内容摘要”、“摘译”或“节译”的形式对赛珍珠《大地》(The Good Earth)、《东风·西风》(East Wind:West Wind)、《母亲》(The Mother)、《爱国者》(The Patriot)、《龙子》(Dragon Seed)等21部作品中的“反动思想”一一进行了批判。该书《编者说明》开篇就将赛珍珠定性为“美帝国主义代言人、反动女作家”,编者认为由于赛珍珠作品在美国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都曾大受欢迎,“因此,就有必要搞清楚赛珍珠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在作品中所贩卖的又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其对我国人民生活的歪曲和对中国革命的污蔑等反动思想,也必须予以深刻的批判……其近年来的作品,特别是《北京来信》和《我的几个世界》,内容极其反动……”
《赛珍珠反动作品选辑》的各位编译者在以“内容梗概”或“摘译”等形式介绍赛珍珠作品之前,一般都会通过小段评论文字或《编者按》集中论述该作品的“反动”表现。例如,张佩芬在其为《男与女》(Of Men and Women)编写的“内容梗概”之前,对该小说做了如下评论:“《男与女》一书中虽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以此来掩盖真蒂,赛珍珠企图用男与女的矛盾来遮盖阶级矛盾。这种混淆视听的手段正是赛珍珠用来掩饰她的立场和迷惑读者的”。再如,晓寒、晋浩、史文三人节译的《北京来信》(Letter from Peking)译文之前附有《编者按》,三位编译者认为,小说“内容反动”,“赛珍珠肆意地诬蔑、诋毁、中伤与丑化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后的新中国写成是阴深深的人间地狱,硬说我国有着‘疯狂的反美情绪,不惜用暗杀的手段消灭书中的主人公——一个善良的大学校长——因为他有一半美国血统。这本书就这样倒打一耙,企图在美国人民和西方人民之中培养对新中国的仇恨”。
从编排的角度看,《赛珍珠反动作品选辑》中最有特色的是由戈哈摘译的《我的几个世界》(My Several Worlds)。由于戈哈认为赛珍珠的原文“散漫无章,冗长可厌”,因此他将“书中有问题的段落摘译出来,并依内容粗疏分类”。他大致将有问题的内容分成了15类,这实际是戈哈个人认为赛珍珠在《我的几个世界》中暴露的15条罪状,主要包括“赛珍珠对中国人民的污蔑”、“赛珍珠是怎样‘赞美中国的”、“赛珍珠是美国殖民主义的辩护士”、“赛珍珠是美国在亚洲和中国反共的策士”等。戈哈的译文前还附有“编者按”:
她(赛珍珠,笔者注)的帝国主义立场在这本书里暴露得最为彻底。赛珍珠以前在其它作品中所流露过的各种反动、荒谬、错误、似是而非的观点,在这里也得到了最充分最完全的发挥;她的帝国主义传教士式的伪善手法在这里也益发圆熟,但也越加欲盖弥彰。
1960年初,《世界文学》和《文学评论》连续发表了三篇长文,组织了对赛珍珠的全面批判。此前,北京《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4期刊载了高骏千翻译的苏联人谢尔盖耶娃的文章《破产的“中国通”——赛珍珠》。该文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影响很大,对中国的赛珍珠评论“向左转”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谢尔盖耶娃的文章主要以赛珍珠1949年出版的中国题材小说《亲族》(Kinfolk,现一般译为《同胞》)为例,批判赛珍珠的新作品脱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现实。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章一开始并没有彻底否定赛珍珠,而是对其作品的社会意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赛珍珠是“一个具有无可置疑的才能的作家”,虽然她的作品“总是有一种巨大的缺陷,这就是它企图抹煞正在现代中国发生着的、巨大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变迁”,但是,“她的作品,特别是早期的几部,却并非毫无社会意义”。文章接下来则笔锋一转,指出:
即使在这些早期作品中,赛珍珠对中国现实的表现也是非常片面的。这正是因为她想把阶级斗争和中国的政治生活从读者视线中掩盖起来……她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这国家中正发生着的深刻过程的本质。她不想提到人民革命的发展……而在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战争里,赛珍珠并不是站在他们的一边的。
文章后来的语气逐渐加强,指责赛珍珠的“反动成见”和“反动偏见”使她无法获取中国人民苦难的真正根源。赛珍珠“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是徒劳到滑稽的程度……她竭力想制造一种印象表示人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代表什么”。文章最后得出如下结论:“把自己的笔出卖给帝国主义压迫者的赛珍珠,想逃避这个真理,结果是,她遭受了整个的破产——政治上、文学上和道德上”。
1960年中国内地发表的三篇赛珍珠评论文章分别是:思慕的《猫头鹰的诅咒——斥赛珍珠的<北京来信>》、李文俊的《美国反动文人赛珍珠剖视》以及徐育新的《赛珍珠——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其中,前两篇刊载于《世界文学》1960年第9期,第三篇刊于《文学评论》1960年第5期。《世界文学》1960年发表的这两篇批判赛珍珠的文章当时在美国也引起了一定反响。1960年《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刊登了报道文章《红色中国说:罪恶的赛珍珠》(Pearl Buck Wicked,Say Red Chinese),该文大篇幅介绍了《世界文学》上这两篇文章对赛珍珠的批判。1960年中国的以上三篇赛珍珠评论文章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对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北京来信》、《我的几个世界》等作品进行了种种批判,历数赛珍珠的种种罪状:故意歪曲中国农村的阶级压迫实质;污蔑中国人民革命,支持蒋介石反动政权;歌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反华反苏,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诽谤、中伤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美化封建性,将封建性描写为中国的民族性并使之“永久化”;等等。
例如,思慕的文章开篇第一句即为:“美帝国主义御用文人赛珍珠,是靠着‘中国通的招牌,靠着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污蔑起家的”。该文最后更是将赛珍珠比喻成“青蛙”与“猫头鹰”:至于赛珍珠之流的造谣污蔑,正像在枯草里望天噪叫的青蛙,像不敢站在阳光下面的猫头鹰的咒骂,只不过显出这个反动文人向她的主子讨取残羹冷炙的可耻的末路罢了。李文俊的文章一开篇则宣称“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多年来,它一直处心积虑地豢养了一批走狗文人……在这批无耻的文人中,赛珍珠是最凶狠最恶毒的一个”。徐育新的文章则将赛珍珠定位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大地》“臭名远扬”,是“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文学”。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初,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较之“文革”期间已有所改变,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禁锢并未彻底消除,中国评论界对赛珍珠的评价仍由“阶级斗争”批判占据主导。譬如,张英伦、吕同六等主编的《外国名作家传》(上、中、下册)的下册虽包含“赛珍珠”词条,但该词条的重点却是对赛珍珠的所谓“阶级局限性”进行集中批判:赛珍珠的作品“总的来说艺术价值不高,思想陈腐保守”;其晚年的作品“内容益发贫乏,猎奇色彩更加浓重”;新中国成立后,她写的中国题材作品“都明显地表露出作者对中国的敌对立场”。这些评论实际上与该丛书的编辑方针是一致的,上册“编者的话”指出,《外国名作家传》在简要介绍作家生平的同时,还要“注意指出一些作家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对反动作家则进行必要的、有分析的批判”。
1949年后,不但中国评论界对赛珍珠进行否定与批判,赛珍珠作品不再被翻译与介绍,就是业已流传到民间的赛珍珠作品也被视为“禁书”而没收。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陶洁曾经回忆说,她父亲家藏有的《大地》三部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抄家时拿走。赛珍珠1934年回美国定居后就没有再回到中国,但她一直企盼着能在离世前再次踏上中国国土。1970、1971年中美两国关系逐渐解冻时,赛珍珠曾给中国领导人发电报,希望得到一份邀请和入境签证。但她的签证申请被驳回,这给了赛珍珠致命的打击,她大病一场。1973年3月6日,赛珍珠与世长辞,葬于其美国住所青山农场,墓碑上只有她的中文名字“赛珍珠”。
二、“美国的所谓‘中国通”:赛珍珠作品的解冻期(1982—1987年)
改革开放后,随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逐渐解冻与中美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内地的赛珍珠研究与赛珍珠作品的译介也慢慢开始解冻。但是,中国内地对赛珍珠作品的解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先是逐步放开了对赛珍珠作品的翻译,然后对其评价也逐渐趋向正面。
除1959年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出版的《赛珍珠反动作品选辑》之外,198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林俊德翻译的短篇小说集《生命与爱》是1949年后赛珍珠作品首次在中国内地翻译出版。该小说集收录了海明威、福克纳等作家的作品,并收录赛珍珠的三个短篇小说《少女之恋》、《生命与爱》和《报复》。事实上,该小说集已于1976年由台湾的星光出版社出版,译者林俊德乃台湾翻译名家①。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贵州人民出版社选择台湾译者翻译的赛珍珠作品在内地出版,是力图打破封杀赛珍珠局面的一种可贵尝试,从中可见出版者的良苦用心。
但是,这部译作的出版并不意味着赛珍珠作品在中国内地的全面解禁。例如,1985年,孙坤荣等选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小说选(第二辑)》虽收录赛珍珠的《仇敌》(The Enemy),但该选集选择收录《仇敌》这样一篇日本题材小说,而不收录赛珍珠更有名的中国题材小说,编者的选择可谓耐人寻味。而且,《仇敌》译文前的“简介”对赛珍珠的评价仍然负面,“她(赛珍珠,笔者注)对中国并没有真正了解,她所知道的中国只是触及了中国的一些表面现象……她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格格不入的”。此外,《世界博览》1987年第7期刊登了钱萃翻译的赛珍珠短篇小说《圣诞节的早晨》(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弥足珍贵的赛珍珠作品中译之一。有意思的是,这篇翻译小说作者一栏署名“[美]珀尔·巴克”,而不是通译“赛珍珠”。这是译者由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有意为之,还是译者不知Pearl Buck即赛珍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虽然这一时期赛珍珠作品的翻译已开始解冻,但对赛珍珠的评论仍主要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控制。1982、1986年《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陈艾新、李文俊评论赛珍珠的两篇短文。陈艾新指出,赛珍珠的《大地》与《爱国者》中有不少污蔑中国人民的地方,“实际上这位女作家在我国农村并未深入,观察也很表面,而且是用资产阶级观点来看问题,当然不可能正确了解我国勤苦耐劳的农民,甚至有很大的歪曲”。李文俊的文章《谈谈诺贝尔文学奖》则认为:
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授给一个中国作家,却于1938年授给了一个美国的所谓“中国通”赛珍珠……如果有别的原因把奖金授给赛珍珠甚至授给一个蹩脚的作家,中国人民可以不置一词,可是偌大一个中国仿佛没有一个够水平的写农村生活的作家,竟需要有人来代替,这种行事方式未免过于骄横。
当时一些辞典、传记类书籍中有关赛珍珠的评论与介绍亦仍基本否定。例如,1982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Ⅱ》“赛珍珠”条目简略介绍了她的生平,指出赛珍珠爱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旧文化”,其晚年作品则“更明显地流露出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敌对情绪”。
信德等编辑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传》(1984)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传记之一。该传记“珀尔·S·巴克(赛珍珠)”词条认为,赛珍珠的“主观立场还是站在旧中国的统治者一边的……也就是说她始终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身份来看待中国的一切”,而赛珍珠后期的作品“大都是以陈旧、敌视的情绪来进行描写的,从中也反映出这位巴克女士(赛珍珠,笔者注)顽固而落后的阶级立场”。虽然该传记仍主要从阶级斗争角度出发批判赛珍珠“落后的阶级立场”,但编者同时也明确指出,“如果一概否定《大地》也是不公正的”,并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大地》畅销的原因:
小说之所以能受到美国读者的欢迎,一是作品题材所引起的广泛兴趣,二是它的主题所包含的某些普遍意义,三是作者在描写人物命运时在充满感情的情节安排和内心刻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
如此看来,该传记不但公开宣称不能一概否定《大地》,还对《大地》主题的“普遍意义”以及赛珍珠的“艺术技巧”进行了较正面的肯定。据笔者考察,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内地赛珍珠评论界尚属首次。
三、结语
70多年前,赛珍珠凭借一部有关她对中国认识的作品《大地》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轰动世界。而在中国,有关赛珍珠“丑化”、“侮辱”中国的非议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非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多年中更是一度发展到极端,演化为对赛珍珠的全面“封杀”与完全否定。“美帝国主义代言人”、“反动女作家”、“美国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美国在亚洲和中国反共的策士”、“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美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等,都是给一生致力于填补中西文化沟壑的赛珍珠的“封号”。
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翻译短篇小说集《生命与爱》(内收赛珍珠三部短篇)的出版对中国内地的赛珍珠研究可谓具有“破冰”之效。此后,赛珍珠作品在中国的翻译逐步放开,新中国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评价也逐渐摆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控制,逐步趋向客观、理性。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迎来了赛珍珠作品又一个新的译介高潮,当前赛珍珠研究在中国内地更是蓬勃兴起。200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采纳该社原总编辑、诗人、翻译家屠岸的提议,重新修订出版了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这是中国的国家级出版机构首次出版赛珍珠作品,让赛珍珠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在新世纪为中美(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贡献,赛珍珠天国有知,当含笑矣!
(责任编辑 张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