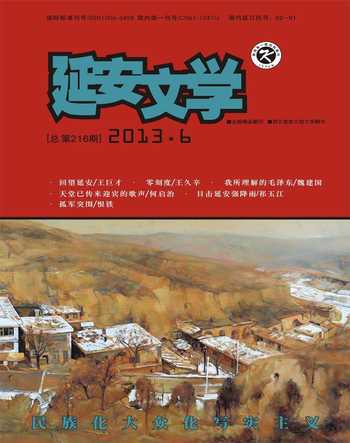石头爷爷
石晓博,陕西户县人。陕西省散文学会理事。
石头爷爷死了,死得十分可怜。
他得的是食道癌。起初还可以喝些流质食物,嫁在本村的女儿常去给他喂些米汤啊什么的。为了增加营养,女儿一次给他端了一碗鸡蛋汤,刚喂到嘴里,石头爷爷“哇”地一声吐出来,嘴里哼哼唧唧地喊着:“你们是想把我往地狱推呀。前年就信佛了,成了居士,再不吃肉了。鸡蛋这么荤腥的东西了,怎么能吃呢?快死的人了,说话要是还不算数,死了菩萨都饶不了我,你们这是害我啊。”
女儿央了许多人,百般劝说但都不管用。蛋汤肉羹是绝对一口不喝的。到了最后,糖开水都咽不下去,喂一口,吐一口,人都瘦成一把干骨头了。石头爷爷是饿死的。他从得病开始到死亡,疼痛再厉害,饿得再难受,从未喊叫过一声。只是听不得人们吃饭的声音和说麻什、面条之类饭食的名字。只要听到这些,他的嘴就不由自主地一张一翕地动个不停,眼睛里马上会渗出两串浑浊的泪珠,滚落到他沧桑的脸膛上,润湿了一片像乱草一样的花白胡子。
石头爷爷的死平凡极了。没有使平静的山村生活荡起一丝波纹,甚至还充当不上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从这个小山村里走出去的我,心田里总是飘荡着那么一丝丝酸楚的回忆和落寞。
剃 头
记得我七八岁时,也是一个淘气包。一天只知道疯跑,脸有时几天也不洗,洗头的次数就更少了,脚是一年洗一回。那时候,人们穷,连热水也很贵重,只是到了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蒸包子的时候,用蒸完包子后的热水,全家大大小小才痛痛快快地洗一次脚。那洗过脚的水,污垢的含量比黄河水里泥沙的含量还高。平时人们是舍不得专门烧水洗脚的。至于洗澡就更谈不上了,一辈子没洗过澡的人多得很。这样,人们身上长虱子也就不足为奇了。我那时身上的虱子特别多,怪不得那时候又瘦又小,这跟虱多吸血恐怕大有关系。不光身上虱子多,头上虱子更多,头发上的白虮子多得就好像头上长出白发一般。那年,我头上生了个黄水疮,不到一月工夫,满头都是。我是惯坏了的娃,不让人看,更不让给涂药,剃头就更不用说了,家里人也就依着我。俗话说:“债多了不愁,虱多了不痒。”虽然身上头上虱子那么多,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的,照样吃饭,照样玩耍。
一天中午,去村西头四婆家玩,她家门口围着一堆人,原来石头爷爷正在那里给人剃头,其他人都是在那里等着。石头爷爷的剃头技术在我们村是拔尖的,夏天收割麦子的时候,有人找他剃头,他是有求必应决不推辞。而且因陋就简,或在路旁的树荫下,或在谁家的屋檐下,撩起脸盆里磨镰刀用过的凉水,将剃头人的头发打湿,随手拿起刚磨过的镰刀刃片,“嚓嚓嚓”就似割麥子一般,三下五除二就剃光一个脑袋,而且被剃头的人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石头爷爷的名声渐渐传到了外村,以至于他去外村串门走亲戚也有人求他剃头。今天剃头的人多,他们一边等着剃头,一边说着闲话,我也好奇地凑到了跟前。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爷爷抓住了我一条胳膊,对石头爷爷说:“老三,今儿给娃也把头剃了!”
石头爷爷笑着说:“大哥,你等一下,叫我把这驴毬弄干净了,就给咱娃剃。”
“我就知道这驴肚子里没好话。”地上蹲着的那人晃了晃半边阴半边阳的头接着说。
石头爷爷刚给那人把头剃完,就走过来用他那又黑又粗满是裂口的大手分开我的头发。
“啊!娃的头发咋长成这个样子了?”
随着他的一声惊叫,众人都围过来,睁着鸡蛋大的眼睛看着我的头。那一个个疮都淌着黄黄的脓水,疮上爬满了正在低头吸食脓水的灰色的、白色的、黑色的、花色的肥大虱子。我挣扎着低头不让人看,想寻个机会一跑了事,可爷爷始终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于是,我就跳着脚哭喊。石头爷爷把他那把锋利的剃刀往嘴里一咬,用那大而黄的板牙咬住刀背,右手拉住我的胳膊,伸出左手按住我的头说:“我娃嫑哭了,爷给你剃头,不剃你的黄水疮就好不了!长短不敢动弹!”
他的声音粗犷沙哑而含混不清,但我听明白了,便立即止住了哭声,服服帖帖任他摆布。
按照辈分,应该叫他爷爷。可我们从未叫过他爷爷,背后总是叫他石头。但当着他的面,我是绝不敢叫他的名字。所以,跟他说话,我们既不叫他爷爷,也不敢叫他的名字。他平时有说有笑,一旦发起脾气来,全村没有不害怕他的。
他十几岁时,就是村子里有名的二杆子。有一年秋收时节,村里的几个喜好恶作剧的小伙子各背了一背篓包谷棒子在路上碰见石头说:“石头,你要包谷棒子不要?”
“当然要哩!”石头不假思索地回答。
“那我们用包谷棒子砸你的头,包谷棒子断成两半截是你的,打不断是我们的。”两个小伙子说。
“行!”石头答道,帮着小伙子放下背篓。
“石头你嫑嫌疼!”几个小伙子抓住包谷棒子的上半截说。
“打吧!谁不鼓劲打谁是孙子!”石头往他们中间一站,昂着头说。
几个小伙子你一下我一下朝他头上猛打,不一会儿,两半截包谷棒子落得满地都是。直到小伙子们打完了各自背篓里的包谷棒子,一个个累得直喘粗气,而石头不慌不忙抖落掉沾到头上的包谷缨缨说:“一点儿都不疼。”头上没起包,黑头皮仍旧是黑头皮。一个小伙子说石头的头比石头还硬,这狗日的真是个铁狼头——民间传说狼是麻杆腿,豆腐腰,铁脑袋。此后人们都知道石头的头硬。伏旱天气和南村争水发生械斗时,他总是一马当先,冲过去一头把南村的领头人撞倒在地,使得那人半天也缓不过气来。他的这一招叫做当头炮,颇具威慑力。正因为有了他,与南村这个大村子争斗,我们村总是占上风。
石头爷爷的头硬,而他的拳头比他的头更硬。那一年他家刚买了头犍牛,那牛浑身黄里透红,没有一丝杂毛,庄稼人都称赞这是一头好牛。那天他套牛车拉土粪,总嫌牛走得慢,其实他的牛车比马车都快了,嘴里大声骂着,扬起鞭子不停地抽打牛,结果,牛惊了。骡子、马容易惊,也容易收拢,而牛轻易不惊,一旦惊了,是很难收拢住的。这时,石头爷爷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牛车是越跑越快,眼看要进村了,石头爷爷只得拉着牛的缰绳跟着跑……情急之中,石头爷爷只得抡起他那木瓜般的大拳头照着牛头砸了两拳,牛车缓缓停住了,牛也卧在那里再也没有起来。他父亲扇了他两个耳光,气得他跑回去扛了一把铡刀往他父亲面前一放,脱了衣裤,全身一丝不挂,滚到铡刀上说,你今天把我不铡了就不是人,后经众人劝说,才算罢了。经此折腾,家境日下,土改时划分了贫农成分,但也是好事。他的这些轶事,我们在夏季打麦场乘凉时,听老人们不知讲过多少遍了。
所以我是知道石头爷爷的厉害的。平时就害怕他,只好硬着头皮不敢动弹,不敢出声。他左手按着我的头,右手从地上的脸盆里撩几把刚换过的热水,扪湿了我的头发,虱子们受到了热的刺激,在我的脸上、脖子上蠕蠕而动,我爷爷一个接一个地将这些肥硕的小动物捏起来扔进那还冒着热气的洗脸盆里,水面立时漂起了一层尸体。石头爷爷右手接过叼在嘴里的剃刀,嚓嚓几下就剃去了多半带有虮子和虱子的头发,剩下的那几撮都是爬满虱子的黄水疮。石头爷爷闪电般地挥舞了几下剃刀,随着我杀猪一样的嚎叫声,那些脓血、头发、虮子虱子的混合物被摔落到地上。我青而亮的光头上顿时冒出了几股殷红的鲜血来,石头爷爷不慌不忙地说:“俺娃嫑哭了,嫑害怕,爷这回可给你把害除了。”说着去四婆家的炕洞里抓了一把草木灰,往那流血处一按,止住了流血。这时候,我真是恨死他了,但也无可奈何。谁知,不几天头上的疮口就长好了。只是再也没有生出新头发来,大而圆的头上从此留下了七八块五分硬币大小的不毛之地,直到现在我总是保持着蓄留长发的习惯,就是害怕暴露那几块不毛之地。
治 病
吃不饱肚子的年代里,石头爷爷成了我们那一方土地上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说他是医生,其实也不会看什么病,他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甚至连农村最常见的的草药名字也说不上来,是那饥饿的年代逼着他当医生的。
那年,村支书的父亲尻蛋子出了个痈,越长越大,直到鹅蛋大小才化了脓破了水,多方求医,总不见好,后来疮口腐烂生蛆,恶臭逼人,疼得支书父亲整天骂骂咧咧,不是骂儿子不尽心给他看病,就是说不知是咱上辈子把人亏了还是这辈子亏了人,得了这难缠病。
石头爷爷一家大小都生得五大三粗,食量如牛,那年月一般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一天他到支书家想求点救济粮。那时候,支书是土皇上,捏着全村五六百口人的命脉,说啥是啥,社员们都变着法儿去巴结他,能巴结上就能得到好处。石头爷爷从哪方面讲,也巴结不上支书,尽管觉得没希望,他还是想试试运气。
进了支书家门,支书没在家,石头爷爷就到支书父亲刘狗子炕边客套一番。难得有人到刘狗子屋里来,刘狗子絮絮叨叨地诉着他的苦处:“老三,我尻蛋子这病就怪了,咋也看不好,到县医院,人家医生把死皮烂肉用剪子绞掉,消了毒,贴了药,说几天就长好了。回来后不几天又化了脓,又生出好多烂肉来。唉!是咱把人给亏了?”
石头爷爷这时已经是前心贴后心了,饿得两眼昏花,心里说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混他支书家一顿饭,把肚子填饱再说。“狗子哥,我有个土方保险能治好你的病。前年娃他姨父和你这病一模一样,也是在大医院看了几回没看好,后来还是让我用这土方治好了。”
刘狗子催着让他快说。石头爷爷说,“先给兄弟吃两馍!”
刘狗子立即命令儿媳妇给石头爷爷取两馍来,儿媳妇虽然满脸不高兴,但还是给石头爷爷拿来了两个白蒸馍。他狼吞虎咽咥了两馍,用袖头擦了擦嘴角的口水说:“狗子哥,你也嫑问啥法子了,我给你治就是了。”嘴上虽是这么说,心里急得跟啥一样,情急之中,忽然想起去年在南村看电影《南征北战》时,前面加演的科教片《农村安全用电》里面,人触电昏迷后,救护人员要赶紧做人工呼吸,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嘴对着触电人的嘴吹气。还演示了人腰疼、腿疼,用拔火罐的方法,能把寒气吸出来。石头爷爷想到这里,心说,管他呢,先试试再说……
刘狗子久病乱投医,欣然应允。石头爷爷让刘狗子趴在炕边上,脱下裤子,只见那干瘪的左尻蛋子中间有一鸭蛋般大小的流着黄脓红血的窟窿。石头爷爷说:“狗子哥,嫑嫌疼,忍着点!”还没等到刘狗子答应,石头爷爷就张开阔口,嘴唇盖住了那个散发着腥臭气味的窟窿。接着他用尽吃奶的力气猛然一吸,咕咕一声,吸满了一大口说不出来味道的脓血混合物。刘狗子疼得龇牙咧嘴。石头爷爷连着吸咂了十来口,吐了多半盆子脓血,出去漱了口,又回到刘狗子屋里,往炕边一坐。刘狗子把身子往炕里边挪了挪说:“老三你这法子就是好,刚才疼得钻心,这会儿受活多了。”随手从炕头拿起上次从县医院开回来的外用药,递给石头爷爷,石头爷爷看也不看胡乱地把药面往那瞎窟窿里一贴。这一切做完,正好赶上吃午饭的时间,石头爷爷放开肚皮,一口气吃了五大老碗捞面条,把刘狗子的儿媳妇气得直瞪眼。这在石头爷爷来说,也算过了一回年。
过了一个多月,刘狗子尻蛋子竟奇迹般地长好了,这在当时,一时间传为美谈。这年,石头爷爷破天荒地得到了八十斤救济粮,熬过了饥荒。此后,村里或邻村的人,腿上、尻蛋上、腰上生个疮啊、疡啊什么的,都请他去看。他还是那个法子,用嘴吸咂出脓水,然后撒上消炎粉之类的药粉。方法就这么简单,而效果却特别好。凡经他看过的疮、疡还没有长不好的。他看病是不带药的,消炎粉、长肉药要由病人准备,所以也就不要钱,但须给他管一顿饭,好坏不拘。在那年月,他拥有这一技之长,肚子少受了许多苦,而且还过了一回吃奶瘾。
那年山娃媳妇生第一个娃时,不知是啥原因,两个奶子的奶水瘀结挤都挤不出来。娃饿得直哭。把奶头塞到娃嘴里,娃吃不到奶水,哭得更厉害。山娃和他妈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那时候,村里人又不知道使用吸奶器,只好将全村的大娃、小娃都叫来,让娃们挨个去吸奶,但没有一个娃能吸出奶来。山娃媳妇胀疼得哭天嚎地。让山娃去吃,还是吸不出奶水来。这可咋办呢?一个是媳妇疼得难忍,再一个奶水瘀结时间太长,还会出大问题。前年,南村建军媳妇奶水瘀结,最后里边化了脓,只得去医院动手术,把整个奶都切除了。还是四婆有主意:不如叫石头老三来给咱咂咂,他的嘴劲大,保险能行,到这时也顾不得体面不体面了。山娃他妈找到石头爷爷一说事情,他二话没说,跟着山娃他妈就来了。
山娃家里围满了女人、小孩。四婆和山娃他妈扶着哭丧着脸的山娃媳妇坐到炕沿上,“咱别嫌怪,就当是给咱治病哩!”一边说一边慢慢地解开她的上衣扣子。山娃媳妇像个木头人一样任凭摆布。石头爷爷一见这场面,浑身不自在,脚手都没处放,不敢睁眼看一下山娃媳妇那雪白的胸脯和鼓胀胀的大奶子。娃把咱叫爷哩,他爷吃孙子媳妇的奶像啥话呢?心里不由得打起退堂鼓。胖嫂子好像看出了石头爷爷的心思,說道:“石头爷!快去,还等啥呢?”连推带拉到了山娃媳妇跟前,硬把石头爷爷的头按到了山娃媳妇的怀里。石头爷爷只能半蹲着身子,额头紧贴着山娃媳妇的白奶子。这时,一股诱人的,久违了的熟悉气味沁入他的心脾,扩散到全身各部位,头脑在瞬间的麻木混沌之后,立刻进入高度亢奋状态,浑身力气倍增,他扬起头一口就噙住了一只奶子,不顾一切地狠命吮吸起来。山娃媳妇先是像触电一般猛地一震,紧接着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感传遍了全身,身子骨似面条一样软,要不是四婆和山娃他妈架扶好,她也许就会倒在炕上。石头爷爷吃空了这只奶,又吃另一只。山娃媳妇此后奶水就顺畅得像溪水一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石头爷爷的称呼也改变了。过去人们叫他“石头”、“石头老三”,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叫他“石头先生”、“三先生”。石头爷爷很高兴人们这样称呼他,哪怕是生气的时候,只要谁叫他一声“石头先生”,他马上就像小孩一样,乐得合不拢嘴。为了能名副其实,石头爷爷也下了一些工夫。先从认字开始,时常怀里揣上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不分时刻,不管男女老幼,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只要碰上,不耻下问,问了就念,忘了再问。功夫不负有心人,石头爷爷终于能够分辨最常用的草药了,也懂得了几种普通西药的功效和用法了,而且还学会了打针。只是他打针时,从不洗手,也不用酒精棉球、镊子之类的东西,随手拿起针剂,放在嘴里用牙一咬,噗噗吐出玻璃渣滓,把药剂吸入针管里,照准屁股的大概部位猛然扎下去,扎得人哎呦哎呦直叫唤,拔出针头,用卫生纸团在针眼上揉两下就行了。他就是这样给人打针的,可是没听过他给谁打针出过问题。不过,求他打针的人确实是越来越少了。那些年,村里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家家户户都养着猪,猪生病的也多,倒是请他给猪打针的人多了。不管是给人打针还是给猪打针,随叫随到,服务态度绝对地好。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