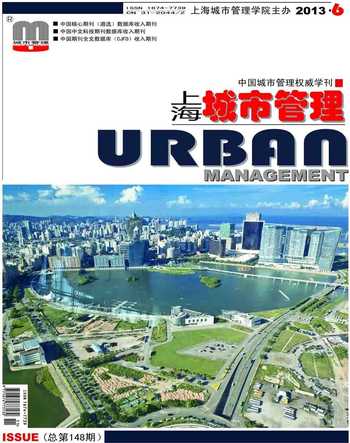城市定位:名声优先还是民生优先?
邓伟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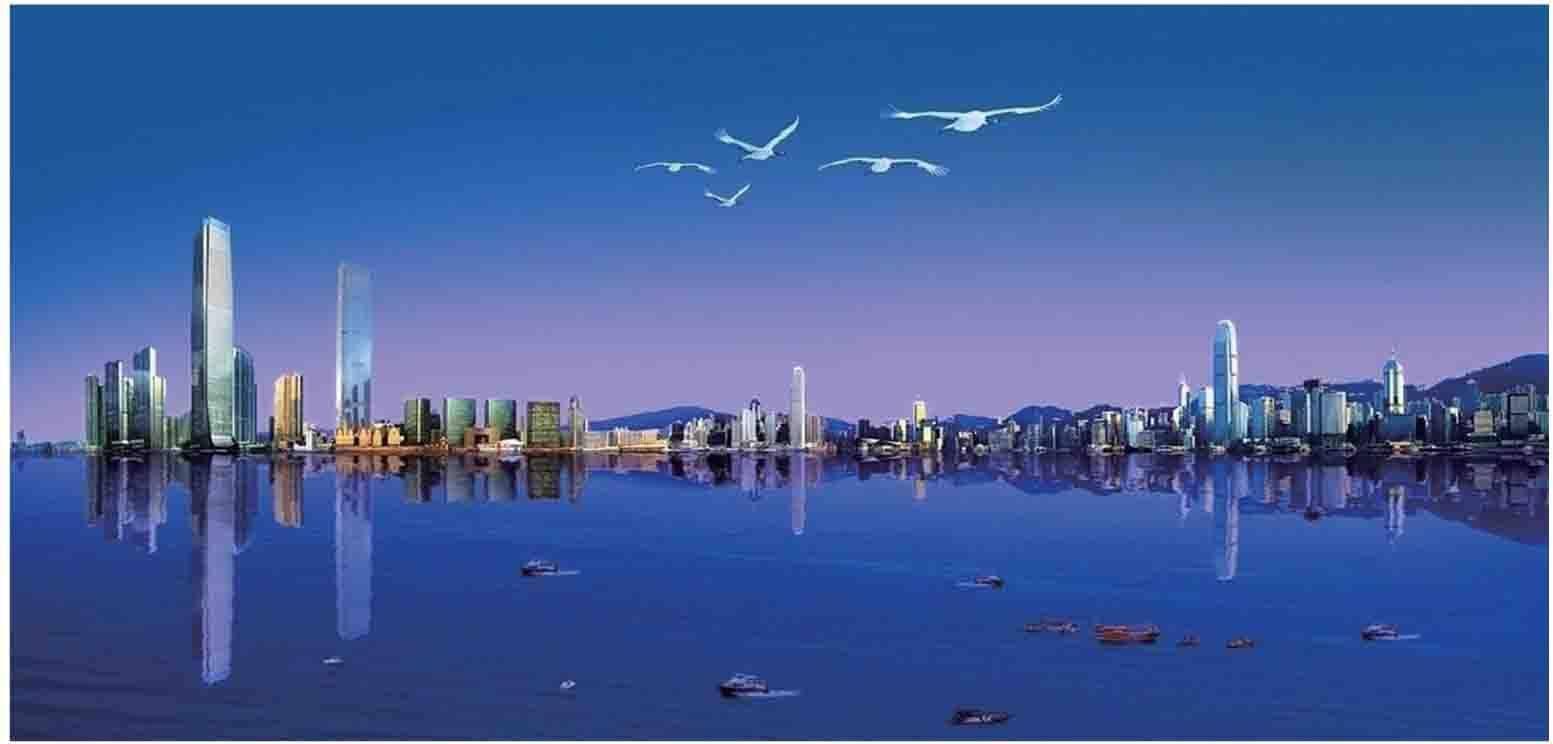
关键词 城市定位 城市规划 理想模式 社会体制
导读:关于城市定位与发展,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其内涵就是根据自身条件、竞争环境、竞争需求、竞争趋势及动态变化,在全面深刻分析有关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复合效应的基础上,科学地筛选城市地位的基本组成要素,并合理地确定城市发展的基调、特色和策略的过程。现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城市定位。城市有战略定位,有发展目标,理所当然是好事,关键是有没有科学地筛选城市地位的基本组成要素,并合理地确定城市发展的基调、特色和策略,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将科学的城市规划合理地、规范地付诸实施。这两者有一个环节出偏差,百姓就将深受其害。
一
叶:关于城市定位与发展,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之所以对它重拾兴趣,源出一个贪官的落马。日前,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被双规,在公示此人“政绩”时,其中有一条就是他喜好搞“城市建设”。比如,为了上马雨污分流等多项城建工程,致使南京古城不断被“开膛破肚”,且城市上空尘土飞扬,民众谓之“秋叶与灰尘齐飞,苍天共黄土一色”。据悉,为完成一个接一个“造福子孙后代的城建项目”,季市长甚至下令不惜砍掉了南京城里几十年、甚至是近百年的法国梧桐。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市长,而且还是有着六朝古都美名城市的市长,这是否属于“太没文化的行为”?
邓:岂止没文化,几乎可被视为是一种无知行为。我臆测他不理解法国梧桐对化解“火炉南京”的作用,所以就无视南京市民对法国梧桐的感情。不说他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至少属于是冒人间之大不韪。
叶:全国六百多座城市中,像季建业这样冒人间之大不韪的的市长还大有人在。有网民说,这种“假建设之名,行毁弃文化之实”的行为,亦属一种犯罪。对此,您作何想?
邓:网民的诟言我暂不评论,我这儿重复我曾说过的一个小故事,以此来作一下对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美国准备轰炸法西斯德国的城市,先是派两架飞机去轰炸德国的科隆,但当两名飞行员在空中看到科隆大教堂是如此精美的哥特式建筑,实在不忍下手。返航后,飞行员的上司也支持了他们不炸文物的举动。消息传到当时的中国,梁思成以此为据,找美国驻华使节理论,提出苏州的建筑比始建于13世纪的科隆大教堂还要早13个世纪(因为此前美国有轰炸日军铁蹄统治下的苏州的打算),美国就此没有轰炸苏州。试想,如果当初美国轰炸了苏州,或许因此就没有了虎丘剑池,没有了寒山寺,没有了拙政园,而一个没有历史古迹传承的苏州,还能享有今日的历史文化名城资格吗?
叶:我记得您说的这个故事曾写在您的文章里过。除了梁思成,您还提到过另一个人,好像是个老革命?
邓:此人是上海以前的一位老领导,叫陈其五,原名刘毓行,是刘少奇为他改的名字。现在年青一代不太知晓陈其五,但此人在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名气很大,他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句名言就出自陈其五之口,是他先用中文、后用英文第一个向中外学生讲出来的。
我提到他,同样也是有关苏州保护古迹的旧事:1949年5月,苏州解放后的第一张安民告示就是陈其五以市长的身份发布的,呼吁军民保护苏州的文物,保护苏州的各类建筑物,保护苏州这座历史名城。布告一出,令行禁止,苏州躲过了当时战火的余劫。有趣的是,陈其五后来虽长期任职于上海,沪苏两地也一步之遥,但他却没有再到过苏州,据说在临终前他对此甚为遗憾。实际上,陈其五只当了一天的苏州市市长(是陈毅亲自任命的),而且也仅是出了这么一张布告,但就是这一日市长的一张布告,却足以永载史册。
叶:苏州现在经济很发达,位于江苏省榜首,在全国范围内也名列前茅,但这座城市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多的还是“历史文化名城”这块金字招牌。我有时与外国友人闲聊,发现他们对中国大陆的城市知之甚少,除了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能说出三分之一的已属于中国通了,但能说出苏州、杭州、西安的却大有人在。我窃以为这些城市之所以能名声在外,主要还是得益于祖先留给他们的文化古迹等遗产。意大利的维罗纳,城市人口30万不到,用我们“量化标准”属于是五线城市,但因为有一个“朱丽叶阳台”而名震寰宇,我亲眼看到,慕名前往的中外游客可以用“蜂拥而至”来形容。文化名胜古迹是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最值得称道的荣耀,这个观念渗透到欧洲人的骨髓里去了。
邓:意大利罗马的繁华地段至今还保留着古罗马的断瓦颓垣,这似乎与繁华很不相称,可是它不仅填补了“繁华的萧条”,物质繁华背后的萧条,而且赋予繁华以文化特色。那断瓦颓垣,是残膏剩馥,是文化遗产,是与繁华相得益彰的宝贵资源。
二
叶:这就进入了我们今天对话的主题。
我曾拜访过制订城市规划的权威,他给了我一个很理论化的城市定位的说法:所谓的城市定位,其内涵就是根据自身条件、竞争环境、竞争需求、竞争趋势及动态变化,在全面深刻分析有关城市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复合效应的基础上,科学地筛选城市地位的基本组成要素,并合理地确定城市发展的基调、特色和策略的过程。
邓:现在全国大中小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城市定位。比如我们上海有七大城市职能:1.中央直辖市;2.我国最大的城市;3.国际化大都市;4.中国最大的商业、金融、经济、贸易、信息、工业中心;5.中国的水陆空交通中心;6.世界十大港口城市之一;7.中国最大的海港城市。刚才说的南京也有七大职能:1.江苏省省会;2.长三角经济副中心;3.副省级城市;4.长江下游最大的城市;5.中国高教、科研中心之一;6.中国七大古都之一;7.国际化开发大都市。
城市有戰略定位,有发展目标,理所当然是好事,关键是你上面说的,有没有科学地筛选城市地位的基本组成要素,并合理地确定城市发展的基调、特色和策略,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将科学的城市规划合理地、规范地付诸实施。这两者有一个环节出偏差,百姓就将深受其害……
叶:说到这,我想起前些日子我了解到的一个讯息,华北某市现有人口不到30万,却在城市规划中决定要在本世纪内将该市建成“华北平原中心城市”、“一个新兴的国际大都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该市决定在近几年建造30余座高楼,其中号称该省、该市的“最高楼”两幢。还有像广西的北海市,现在也只有30万左右的常住人口,但规划却要达到600万,真有一气吃成胖子的雄心壮志!
邓:现在关于城市定位和发展的话题很闹猛,缘于今天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但实际上1949年共和国建立之初,新政权就曾规划过城市的合理布局问题。我还记得1985年,国务院在制订国土布局规划时,也提出过城市布局的4条原则:1.城镇布局与生产力布局,特别是工业和交通建设项目的布局紧密结合、同步协调进行;2.认真贯彻“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以及对城市企业实行技术改造为主的内涵建设方针,正确处理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结合;3.正确处理沿海、中部、西部三个地带的关系,逐步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4.有利于发挥城市的多功能作用,促进城市之间的联系和分工。
从现代社会发展的状况看,因为城市的竞争是多方面的,所以城市定位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城市定位,包括产业定位、功能定位、性质定位等。其中,产业定位是基础,功能定位是核心,性质定位是灵魂。但三者之间,性质定位是最重要的,因为性质决定功能,功能引领产业并决定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所以,找准城市性质,就是找准了城市的本质性特征。
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城市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比如上海,最近在修订自己的城市发展规划时,主动提出不搞单一城市的规划,更重要的是要做区域发展规划,并且要与长江下游发展规划相衔接,有些工业项目要向周边地区疏散,强调区域协调,不再搞小而全、大而全等。郑州也宣布,不再提建大郑州、全国商贸中心、建设国际商埠、“东方芝加哥”之类的不着边际的口号。大连市则提出城市发展“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我个人还觉得成都的定位很富创意,他们提出要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既很好地反映了成都市的本质性特征,也代表了当代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理想模式。
前一段时间,很多城市的决策者都把城市发展定位在一个“大”字上,地域要广、人口要多、产业要全,等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恨不得明天早上就变成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从社会体制的角度去审视,这和价值取向及评价标准直接相关联。
叶:说到城市定位的“大”,我想提一下我曾看到过的一个材料,是关于东京、首尔与北京三个城市大小与经济效益相比较的情况:东京和首尔,城市面积都比北京小,但经济效益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北京城区面积达700平方公里,但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0亿美元;东京城区面积是514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却达5072.9亿美元,比北京高出84.5倍;首尔城区面积是605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是410亿美元,也比北京高出6.8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东京和首尔并不因为经济效益高而自然环境同比下降,妇孺皆知,东京和首尔的的空气质量优于北京。
我想,这个材料向人们显示了两点:1.中国的一些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较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2.认为只有城市空间规模扩大才是城市发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邓:城市定位是城市发展和竞争战略的核心。科学和鲜明的城市定位,可以正确指导政府活动、引导企业或居民活动、吸引外部资源和要素,最大限度地聚集资源,最优化地配置资源,最有效地转化资源,最有效地制定战略,最大化地占领目标市场,从而最有力地提升城市竞争力。否则,城市定位不准,就会迷失方向,丢掉特色,丧失自身的竞争力。
当年上海各区县制订功能定位时,静安区提出建设“文化名区”,杨浦区提出建设“知识大区”,在一个以GDP为考量的社会价值体系里,静安、杨浦有如此城市定位创意,我个人认为难能可贵。当然,静安区名人故居星罗棋布,杨浦区有复旦、同济等一批一流高校,这说明他们具备制订特色鲜明的城市定位条件。
三
叶:以文化定位城市的战略目标,现在是很时髦的。因为时下中国大陆社会有一种现象,一些政府官员、商贾大亨,耻于旁人说他没文化,因为没文化,官再大、钱再多、也不入流,这也是上述两种人竭力想往“文化”一词上凑、竭力要弄一张证明身份的学历证明的原因。据我所知,现在中国大陆大大小小各类级别的城市,用文化来定位城市发展战略的不在少数,但大多是有名无实,苛刻一点说是沽名钓誉,因为你只要查一下那些城市重视文化的实际行为即可做出判断。一些官员造政府机关大楼,造五星级疗养院的热情远高于建图书馆或科普馆,也远高于建设或修缮学校或医院。说到这,我想到日本前首相吉田茂给《大英百科全书》1967年版写的一篇卷首论文,名曰《激荡的百年史》,其中有一段话令我没齿难忘:“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可以看到,小学校的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也表明了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我曾数次在文章中引用这段话,且每次敲击键盘时都让我难抑悲郁之情。
邓:在相当多的国家里,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通常都把图书馆、博物馆、学校等文化教育场所的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而且这些文化教育场所的建筑大都比市政厅大楼更大更好,奥地利总理的家就在图书馆一个楼上。
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影响力、知名度,很重要的一点是文化。文化资源的多寡、文化氛围的浓淡和文化水平的高低,其重要有时不亚于一个城市的GDP总量。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故居在建筑学上有多大价值,恐怕说不上多少,可是因为毛泽东、蔡和森在那里从事过革命活动,却能吸引千百万国内外游客去瞻仰。
现在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之所以重楼房而轻文化,是因为文化有很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城市,十位公民中有几位大学生是很难看得出的;一个城市的市民,人均购书费用是多少也是很难看得出来的;而一个城市的市民,人均阅读量,更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因此,好大喜功者,形式主义者便把文化放在一边,或者是嘴上唱高调应付应付。其实,文化也是可以看出来的。不用说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等等一看便知,就是文化程度也能用肉眼看出几分。我曾在莫斯科大学副校长陪同下到俄罗斯的几个城市转过,在一些社会风貌比较好、人的谈吐比较雅的地方,一问就知道这里整体的文化素质高,大学生比例高;在一些社会秩序比较差、也不大讲礼貌的地方,一问就知道那里整体的文化素质低,大学生比例也低。
叶:当今国际上除了GDP之外,还用HDI作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这就是人均寿命、人均教育和人均收入,这个发展水平指标,和城市定位有直接的关系。
邓:说起定位文化名城,最典型莫过于杭州这个城市了,几乎可以作为大学城市管理专业的教案。历史证明,杭州因为在城市定位决策上失误,致使她几十年来命运多舛。比如1949年政权更替初始,杭州城市定位是旅游参观城市;1953年,建工部和苏联专家认为杭州应该是“风景兼文教和轻工业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性质是以风景疗养为主”;到了大跃进年代,杭州的城市目标定为“建设以重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城市”,杭州钢铁厂等40多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拔地而起,形成了从艮山门到半山的重工业区,所以就有了“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之说;直到改革开放的1979年,杭州城市定位才又回到“重点风景旅游城市”,产业以丝绸和电子仪表等轻工业为主;现在杭州被冠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风景旅游城市”是在1993年,算是在名分上回归了正统。
叶:杭州城有很多别称,因为出龙井,所以被授予“中国茶都”;因为开了西博会,又号称是“会展之都”;因为举办过首届国际动漫节,所以又提出要打造“动漫之都”,还有什么休闲之都、爱情之都、女装之都等等,我不知道還有什么“都”会冒出来,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没想到。
邓:大跃进年代的有句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产多少粮”,嘴大、说话不着边际是我们国家现有的一大陋习。杭州被授予或打造什么“都”都不重要,因为在世人心中,杭州城市是什么定位,早就约定俗成了。一提到杭州,人们首先想到和提到的就是西湖,不会是这个“都”那个“都”的。
■责任编辑:张 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