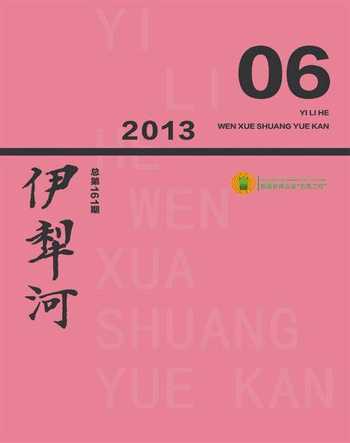穿越时间的足尖之舞
张映姝
大约七八年前,因与黄毅隔墙而坐(共同效力于某时尚刊物),开始零零散散地读他的一些散文。了解一个文人,从阅读他的文字入手,这应该不会有大的偏差和失误,我一直这样想。每每在报刊上读到他的文字,总是让我心动。心动的应该不止我一人,否则我们的党报副刊不会让他的一篇文章铺满弥足珍贵的一个整版。心动完还不够,我定会口齿生津地大肆宣扬,其中就有《新疆四季》、《秋之喀纳斯湖短章》、《不可确定的羊》等。及至2009年天涯杂志第四期推出“新疆散文小辑”,其中节选了《新疆时间》的不少篇幅作为压轴之作,我竟不自量力,自顾自说地妄评了一番,对新疆散文的写作指指点点。现在想来,实在汗颜!近日,听说黄毅要将前几年所写文字结集出版,顿起先睹为快之意。每至编稿校稿疲惫,总会不自主地打开电脑桌面上的“黄毅书稿”,咂摸品读,甚至不舍得多看几页,唯恐早早读完!
一
“进入一个地方,有时不能太认真,也不能太轻率,否则会失去对它的正确判断,当然,更不能听信谁的。”这话是黄毅在《和田叙事》中说的,那么,出生于、成长于、成名于新疆,有着纯正壮族血统的黄毅,眼中、心中的新疆,无疑是客观的,清醒的。他又写道:“我知道在我的内心缺少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缺少的,但为了达到内心的平衡,所有人应该和我一样不断充填内心。”(多年的充沟填壑,让他不吐不快,先为诗,后为散文,现在是双枪并举,同时开火。)那么,他用文字判断、言说的新疆,应该是丰富的,饱满的,独特的,个体的。他还写道:“激发这些深匿于胸壑的飘缈无踪灵感的,一定与我们熟视无睹而又切肤之痛的事物有关。”那么,他笔下的新疆、新疆之事物,注定逃脱不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和庸常,却被他的灵感镀上了亮闪的光圈,呈现出神奇之异相。且看他的笔下:塔里木河边的胡杨林,“是河流的另一种形式,是河接近蓝天白云的一种方式,站立起来的河,哗哗的林涛,让鸟鱼一样游来游去”;无月的禾木夜晚,他想象不出黑暗中的样子,但他“觉得会更真实,就像夜晚卸了装的女人”;听叶尔德什吹响楚儿,他发出感慨“不是每个时代都能诞生民间伟大的乐手,尽管这动作简单到了拿起来楚尔,贴近嘴角”;写在和布克赛尔买书,他“明白一个道理:好书不能买”;写哈密瓜的甜,是因为那些粗粗细细的瓜秧、曲曲折折的藤蔓,总有一头扎在土里,“仿佛是潜入水中的水泵,在我们不为所知的深处,抽取着这块土地的精髓”——于平凡中见神奇,其实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再生过程。就像酿酒,同样的大麦、高粱原材,同样的蒸馏、取萃工艺,可酿出的酒就是千滋百味。写作更是如此。见到黄毅我就会问,可否有新作问世?他大抵支支吾吾,眼神躲闪,顾左右而言他。报刊上也不大能看到他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一直在写,率性而为地写,保持着自己的写作节奏(或习惯),秉承着自己的散文理念,讲结构,谋布局,取文意,达意蕴等。相比而言,他很低产,却篇篇有独到之处、精彩之笔,尤其是近几年,一出手就是大文章、好文章,冷不丁让人半天缓不过神来!“慢工出细活”,的确有些道理。由此,我甚至能嗅闻到那些文字在他头脑中发酵、蒸馏时的蒸腾之气和萃取、凝结后的的馥郁之香。
二
谈及黄毅散文时,我常说一个词:阳春白雪。这多少让别人以为自己很“下里巴人”,上不了台面一样。其实我的本意是,黄毅的散文从容,大气,豁达,且有风骨,与一般的游记散文、行走文学等有所距离。我一直找不到一个词或一句话精准地概括这种感受。前不久,看到赵钧海评价黄毅散文的文字:精美、凝练,还充溢着一股绅士的高雅气度,深以为然!
在大多数人眼里,阳春白雪通常是与曲高和寡并行而生,是远离人间烟火高高在上的,是厌弃尘世放荡不羁的,是苦思冥想故作高深的,是逃避世情孑然独行的,如此等等。统而言之,便是超凡脱俗,与现实众生格格不入。这样的理解放在黄毅的散文上,实在是谬之千里了。黄毅散文立足于新疆博大的地域风土和色彩斑斓的多元文化,取材于杂芜、琐屑、丰富的日常物象,贯之以迷雾缭绕的历史烟云,抒情、写景、记人,纵横捭阖,下笔自如。写景的莫过于《秋之喀纳斯湖断章》,它是第三届“天山文艺奖”获奖篇目,也是作者最中意、自豪的篇什,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出现了野罂粟的暗红的血色,耳边是那句点睛之笔:“野罂粟在我的诗中躲过了秋冬,它一直把伤口裸呈在春夏。”写人的,尤其难忘和布克赛尔最后的女王爷,历经沧桑的情路,王位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都已湮灭,端然而坐的她那头“华贵而典雅的苍然白发,像一蓬燃尽了紫烟的亮丽火苗,”却于不动声色中彰显出内心的隐忍、达观和与众不同的高贵。更多的时候,情、景、人交织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鲜活生动的有机体,流转自如,妙趣横生。我注意到,黄毅散文无论是描摹状物,还是抒情铺排,总是能跳出对物象的惯常思维路数,开掘出常人未及或未能认识的宽度和广度。比如,《不可确定的羊》,其实是要表达人性的贪婪施加于羊的无良之举:为获得更多的奶给母羊带上乳罩,为了获取奖金让本性温顺的羊进入你死我活的决斗场,为让羊吃枯黄的草给羊戴上绿色的眼睛,利用羊群跟随头羊的心理将羊群骗入屠宰场;羊与狼的定律被颠覆,“特殊的事物,必须由特殊的方式才能解决”这一结论就水到渠成了。比如,他从新疆瓜果甜美的常识,探究出了新疆土地的辩证法:用尽了涩苦,剩下的只能是甘甜,有了苦难做底蕴,才能升华出超乎寻常的鲜美。比如,新疆人一日三餐不可缺离的馕,竟被他提纯为“如日月般的馕饼,辉映着多少晦暗的日子”。谷物、瓜果、美酒、佳肴,乃至山水、风土、季节、时序等,寻常的事物总有不寻常的认知在等着你阅读、品味,然后莞尔一笑。我曾打探黄毅是否喜读哲学,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哲学还用学吗,生活中处处都是,关键是你要用心去看、去想。难怪我总能从他的文字中读出辩证、逻辑。
对于艺术创作,老生常谈的是“戴着镣铐跳舞”,舞得沉重、艰难。读黄毅散文,却总有用足尖跳舞的感觉,跳得轻盈、空灵,心灵旋翔,足尖却始终勾紧了大地,汲取着源源不断的大地之乳。这也是他的散文好读、耐读、经读、也难读的原因之一。
三
黄毅以诗成名。他的散文不可避免地带有与诗歌相关的气息:诗情,诗意,诗语等,这让他的书写与一般散文写作者的书写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就说语言吧!诗歌的语言讲究凝练、干净,保有张力和跳跃感。看看黄毅散文中的几句话:
“雪站不住了。”(写春天来临时积雪消融的景象)
“金雕用宽大的翅膀把秋天捎得很远很远。”(写喀纳斯之秋季)
“阳光把天山劈砍得斑斓而辉煌。”(写夜雨过后旭日高照的天山)
“晨光中,一个人和一条狗的格局,被金光描绘成一竖一横的错影,贴在禾木河畔的草地上。”(写晨光中的影子)
“花朵像一串省略号,把春天轻易地隐去了。”
“味蕾的记忆,颗粒状的,埋伏着不屈不挠的情怀。”
尤其要注意动词的运用。惯常的词语搭配被颠覆,营造出新鲜、新奇的动感和意蕴。每当我读到这些语句时,我的头脑都会出现惯常的词语搭配场景:“站不住”,想到的是人或动物东倒西歪的场景;“捎”,浮现的肯定是信件(这里也可理解为“秋的书信”);劈砍,让我想到抡起斧头劈柴;“贴”,不可避免地想起胶水和黏糊糊的手指等。可这些词用在这里,那么妥帖、精准,那么有趣、有味,总让我不忍读过去,总会留恋揣摩良久,好像得到了意外的赏赐。我猜想,黄毅在琢磨他的文字时,每想出一个这样的词,心里是有几分得意的,甚或捻须微笑的。
四
说了诸般妙处,还得说说不满意之处。
客观地说,该部书稿中收录的20多篇文章,大多是2006年以前的几年写就的,文章长短不一,高低也有不同。要求作家的每部作品都能达到大体相当的水平,本来就是苛求。我留意了一下,几篇长文《新疆四季》、《新疆时间》、《味蕾上的新疆》、《高台乐园》等,充分显示出作者的优势:长于结构、布局,熟于跳跃、转换,擅于想象、关联,巧于营造诗意氛围。《野马之殒》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史实、资料的印证与野马之殒的事实叙述,伤痛之慨与理性的思考,似乎缺乏畅通、贯穿之感。《不可确定的羊》、《秋之喀纳斯湖断章》、《蓝马》等不少短文,都是不可不读、读了还会再读的佳作;《沙漠:一阵风等于几十年》、《草原:一种形态》却有滞重之感,或许,用诗歌表达会别有一番况味?
诗人激情迸发时,文思泉涌,情感宣泄扑面而来。这在黄毅散文中也有痕迹。《新疆大地》中那一大段描写新疆风景对立又统一的排比句,句式工整,对比鲜明,却少了耐人寻味的韵味和语言的张力。这一点,可能需要黄毅花些时间再琢磨琢磨!
此种细读,于黄毅散文实冰山一角。自哂!
期待分享黄毅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