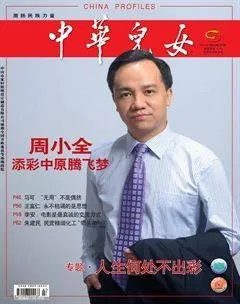金石之美
刘波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因为文字的载荷而绵延至今。发生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故事,随着不断被发现的历史遗迹而扩展、充实。
不算刚刚热起来的微信等最先进的记录和交流手段,单单从普遍的用电脑敲字,回溯到用硬笔写字,再到用毛笔写字,已经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百年”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似乎是遥不可及的过去,但对于“金石”这一特殊学问感兴趣的那一群人,他们的视野,大概不会拘于千年以内,而是唐代以前的古代世界。
那时候的文字除了写在纸绢、布帛上之外,大量的被刻在石碑、摩崖、造像上。特别是一些皇家、大族主持建立的碑刻,更是集一时之选:大文人亲笔撰写的文章先请大书法家亲笔用朱砂手书在碑石上,然后请第一流的刻工镌刻。待到后世,再有第一流的拓工捶拓将之传世。其所附加的人文信息可谓无与伦比:文章可证史志之讹误、可传家国之事功、可赏文风之嬗变、可仰士人之襟怀;书迹可师运笔之枢机、可寻书体之沿革、可究流派之渊薮、可味谋篇之气局;刻工则于游刃中见气韵之流美、于阳刚中寓阴柔之情致、于雕凿间标庄敬之心怀、于起止处显永恒之风神。
而历代拓工,不乏精于书艺之辈,加之后世金石学渐盛,有大学问家直接参与其间,指点引导,更是显示出对于学问精益求精的态度。摩崖险峻,不碍搜奇探丽之士跋山涉水,架梯援壁,张纸摩拓;古碑虽残,不减好古博涉之徒荒山野径,访古寻文,一旦有所创获,则一一记录在册,传之后世。遂使得金石一门学问,蔚为大观。《四库全书》关于金石碑刻的书籍自北宋欧阳修、赵明诚至乾隆朝,已是洋洋数百卷。其间治此学问者,不乏国家之重臣、儒林之旌纛。清朝乾嘉时期更是史无前例的金石学盛期,迄至晚清民国,名家辈出,胜果争攀。近世以来,鲁迅先生、梁启超先生、康有为先生等都是文名、功名显赫之人,殊不知他们还是彼时第一流的金石家,不仅收藏丰富,考证精确,见解更是迥出常人。“厚积薄发”用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形象而贴切的。笔者曾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观赏先生当年用教书所得薪水搜罗来的各种碑拓,从先秦金文、石鼓到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碑刻、造像、墓砖应有尽有。先生不但收藏,更兼亲笔抄录碑文、校勘词句。
看着这些尘封的拓片,观想先生在灯下埋头故纸的痴迷。一个自称“横眉冷对千夫指”永不屈服的斗士,居然能写出那样一笔恬淡雍容、锋芒敛尽的书法,我们不知道先生从古碑中借鉴了多少灵感。这种快乐,绝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所可以带给他的。
广义的“金石”概念,除了权量、钟鼎、兵器、陶文之外,应该还包括殷商甲骨文等。顺着汉字发展衍变的轨迹慢慢上溯,一直推延到甲骨文所记录的年代。从那简约得无以复加的卜辞中,考古学家们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那些已经成熟了的文字,大量来源于自然形态以及据此展开的想象。在造字的初期,就体现出了我们先民非凡的想象力和概括力。对于喜爱书法的人来讲,那些符号可能就是一个个至简至美的图画。
我们不得不承认,历史的风尘会赋予一件器物难以预料的美感。一如古希腊的维纳斯,如果不是双臂断残,一览无余的姿态和动作可能会令观者的想象受到遏制。远古时代的甲骨、钟鼎、碑版,如果一切如新,那一定也缺少了许多那人寻味的意趣,不同时代的洗礼会不断增加它们的内涵,让触摸它们的后人徒生无穷的时空观想。
责任编辑 张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