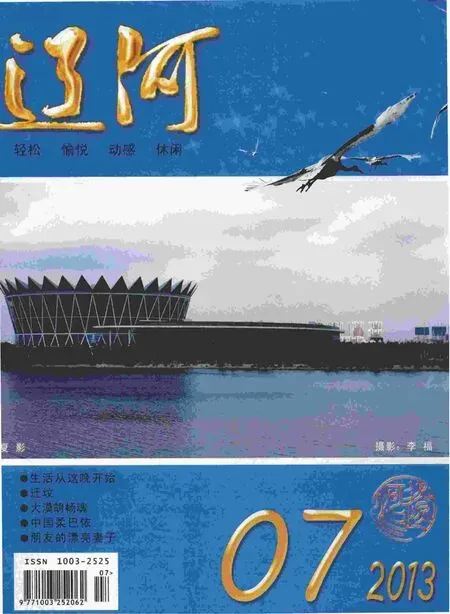炉火边的碎时光(外一篇)
成娜
冬天的阳光穿过枯旧的树枝,再零零落落地撒在地上,像一只裂了纹的瓷瓶,虽说没了完整的容颜,却还能在裂痕里寻得一份回忆。于是一些有关冬天的碎片也便在这充满阳光的冬日里循迹而来,斑斑驳驳地落进记忆的狭缝里。
一
冬天的脚步还没伸进门槛,父亲就开始在奶奶的屋里盘炉子。
盘炉子是个技术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拿得出手,除了要有一定泥瓦匠的基本功外,带点创新的思维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盘出的炉子才能既实用又美观。父亲经常给人盖房子,也算是个“大工”,这方面还是很拿手的,所以盘个炉子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搬砖,和泥,砌砖,经过大半天的工夫,青砖红泥的炉子便盘成了。父亲盘的炉子很大样,像是烧饭的灶台,这样的炉子最大的好处就是省炭,在村里人看来,省炭才是硬道理。盘好的炉子分两个台面,一个专门用来生火,另一个用来放东西,或者说用来炕东西。“炕”字在这儿是动词,就是烤的意思。除了衣服鞋袜可以炕外,发面的大瓷盆也可以放上去,这样就可以节省发面的时间,所以炉台的其他作用也是很明显的。
炉子里烧的不是纯煤炭,那样太奢侈,也没人烧得起,我们一般是用泥和煤的混合物作燃料,我们叫它砟子。砸砟子是体力活,也是由父亲来完成。烧炉子的人家一般都有专门砸砟子的池子,池内放上煤炭,先用带榔头的大木棍把煤砸碎,再加上块状的红泥。红泥是从干涸的水沟里挖来的,这是不需要钱的,所以特别的经济。砸碎的煤炭加上红泥用水调和一下,再用榔头砸一阵,这种半硬半软的东西就是砟子。整个冬天,我们就用砟子来取暖。为了省炭,父母住的屋子里是没有炉子的,所以冬天,只有奶奶的屋里才暖和些。
记忆里是寻不到爷爷的影子的,奶奶一直和老奶奶住在一起,婆媳两个一处便是几十年,倒像是娘俩了。后来有了我们小孩子的加入,便成了真正的老少组合。
奶奶喜欢和衣而睡,无论冬夏,奶奶从来没有一觉到天明的时候,半夜会起来几次,给老奶奶端水端药拿吃的。冬天也一样,奶奶脱掉外套,贴身的棉袄棉裤便是奶奶的睡衣,只要有事,奶奶一骨碌就爬了起来。
早晨,第一个起床的是奶奶。她窸窸窣窣地摸着火柴,嗤啦一下,火柴亮了,一盏老式的煤油灯也便在黑暗里举起了那片昏黄的光。咔嚓!咔嚓!奶奶用火锥把封严实了的炉子叉开,再用火锥在炉眼里这么一阵乱捅,燃了一宿的炉灰就顺着下面的通道落了下来。奶奶再重新添上砟子,然后坐上锅,一家人的早餐也便在噼噼啪啪的炉火上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一切就绪后,奶奶便开始叫我们起床上学。奶奶没文化,不会看表,但奶奶的生物钟特别准,所以我们一般不用担心早自习迟到。在奶奶一声声的呼唤里,我们不情愿地从热被窝里钻出来。奶奶麻利地把烤在炉边的棉袄棉裤递过来,再把烤好的鞋袜拿过来,于是我们的躯体便从一种温暖进入另一种温暖,我们通身便被这种炉火的余温包围着,身上暖暖的,心里也是暖暖的。
在炉火边炕东西也有失误的时候,早上的黑暗还没退尽,迷迷糊糊中,右脚的大拇趾总被一种来自地面的冰冷摩擦着,到了教室才知道,原来我的棉鞋烤焦了一个洞。当然奶奶的自责也来了,唉!咋就把鞋放得离炉火那么近呢!我却为烤焦了的棉鞋暗自高兴,这样我就可以提前穿上母亲做的新棉鞋了。
奶奶与老奶奶两个过早失去丈夫的女人,守着一膛炉火,守着一个残缺的家,她们用特有的勤劳与坚强把一个破落的家庭支撑下来,让家重新有了完整的模样。
二
农闲了,整个冬天,母亲都用针线来打发时间。
母亲是喜欢熬夜的,冬天的夜晚,母亲便围着炉火纳鞋底。锥子与针线在手里交替着,母亲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扎出洞来,再把针线穿过去。嗤啦,嗤啦,麻线一针一眼地从板硬的鞋底里穿过来,又穿过去,像是一首沧桑的老歌,在寒冷的冬夜里充满了浑厚与深沉。母亲把纳好的鞋底挂在墙上,鞋底像是一张精致的蛛网,密密匝匝地排满了虫子一样的针脚,却是密而不乱,横竖有序。
农村的冬夜里寒冷的,透过窗棂,却也有一小撮的温暖在跳动,那是还没熄灭的炉火。“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其实并不是诗人独有的情怀,冬日家庭的温馨也是这样的场景。红砖红泥的火炉倒是真真切切,只是酒却换了内包装,要用茶水来代替了。这样的日子,下不下雪也无关紧要,只要渴了,顺手拿杯子就是了。
母亲把茶杯放在炉台上,一边纳鞋底,一边自斟自饮,倒也是份乐趣。整个冬天,母亲守着火炉,守着一个破旧的茶杯,一家人的鞋子便在这通红的火炉旁有了各自的模样。
其实我们小孩子同样喜欢炉火旁的碎时光。晚自习一下,我们便急不可耐地从学校跑回家,把冻得胡萝卜似的小手伸向炉火边,霎时,一种隐隐的胀痛便在指间蠕动。不过疼痛是暂时的,继而被一种热烘烘的感觉代替了。
“地瓜干烤好啦!”母亲放下鞋底,从炉火旁边取出地瓜干。原先煮过又晒干的地瓜干放在炉火边一烤,一种略微的焦黑覆盖在上面,里面却是金黄酥脆,香味便穿过鼻腔欣然而来。
我们吃着香脆的瓜干,再喝着母亲泡过的茶水,冬夜的幸福便在这种简单而又老式的生活里弥漫开来。我们再顺便搬个凳子,继而挨着母亲写作业。
有时花生和爆米花也会在炉火边派上用场,只要我们喜欢,母亲整个晚上都会守着一膛炉火,烤制我们喜欢吃的东西。
生活并不是因为贫穷就减少了快乐,在没有多少零食可吃的年代,在自家炉火边烤制的小食物照样把快乐填得满满的。
三
冬天的寒冷总在一场雪后变得更加凛冽,炉火的温情也在寒冷里显得愈发可爱。
秋末冬初,姑姑送来了一只小狗,满月多一点,毛绒绒的煞是可爱。只是母亲不同意养狗,在我们这样的家庭,老的老,小的小,口粮总是紧巴巴的,哪儿还能为狗寻找生路!可我却极喜欢小狗那身软软的小黄毛,还是闹着让母亲留下了。
在宠物不盛行的年代,小狗是没有名字的,廉价得就像一片白菜帮子,扔掉也不足为惜。小狗身上的毛是黄色的,我就叫它小黄狗。没事的时候我就抱着小黄狗玩,小黄狗很贴我,总在我身边转来转去。吃饭的时候,我顺便掰下一块窝头或者杂面的卷子扔到它嘴里,它就高兴地在地上转来转去。后来小黄狗也有了点本事,它能表演满地打滚与叼手绢的才艺,这就足以让我很开心。只是每顿饭每个人的干粮是一定的,我喂了小狗,家里可能就有人吃不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用小狗的饥饿来取得家人的温饱。
在冬天的肃杀里,小黄狗瘦弱的身体难以抵挡外面的风寒,所以它很喜欢在炉子旁蹭来蹭去。小黄狗很会找地方,在炉子的下方,有个三四十公分的洞,我们叫它炉倾,那是炉灰下落的地方。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小黄狗就钻进炉倾里,那儿成了它的安乐窝。
在炉倾里的日子是温暖的,只是也有让小黄狗心急火燎的时候。捅炉灰是不定时的,很多时候并不去注意小黄狗是不是在下面,一堆炉灰下去,小黄狗便被烫得汪汪直叫,一溜烟地跑开了。不过小黄狗也不长记性,还是经常往炉倾里钻,时间一长,小黄狗的身上便这儿一撮毛烧焦了,那儿一撮毛烫没了,满身像长了疮,实在难看得很。
烫伤的小黄狗变得越来越难看,家里人都不喜欢它了,我有点为小黄狗伤心。我有时会拿着梳子为小黄狗梳理身上凌乱的毛发,可那些毛发几乎成了一个疙瘩,梳都不开,每梳一次,小黄狗都极不情愿地汪汪直叫。小黄狗身疼,我心疼,所以也就不再梳了,随它去吧。
食物的匮乏还是让小黄狗处在了生命的边缘,尽管我偷偷塞给它食物,但还是改变不了挨饿的命运。两个多月下来,小黄狗瘦得皮包骨头,再加上满身被烫的伤疤,简直就像一只乞丐狗,只落得了别人的奚落。
一个寒冷的午后,我竟然找不到小黄狗了。后来,在西屋的桌子底下,我发现了已经站不起来的小黄狗。受冻挨饿已经让小黄狗无力支撑自己的躯体,它浑身颤抖着,两眼哀怨地看着我。我心痛极了,赶紧给它灌了点玉米粥,它却不张嘴。我想它一家是冻坏了,又赶紧把它放在炉火边。火苗发着微黄的光,热量也慢慢传递到小黄狗身上,可它好像感觉不到,依然没有气力。我把半块卷子掰成小块放在它嘴边,它也没张嘴。我心里凌乱着,不知怎样才能让小黄狗好起来。上学前,我又把小黄狗放进了炉倾里,希望它可以好起来。整个下午我都无心上课,只惦记着奄奄一息的小黄狗。放学后,在堂屋的门口我一眼就看到了小黄狗。它僵硬地躺在地上,已经闭上了哀怨的眼睛,我的眼泪也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知道,错在我,如果不能对一个弱小的生命负责,就不要拿它来玩乐。小黄狗原本该去一个富裕的人家,而我却用幼稚提前结束了它的生命。小黄狗走了,我的心受到了谴责,从此,我再也不养狗。
绿色之外韵味
大巴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一片片绿色的田野不情愿地逃出视线,飞快地向后撤去,我的心情却因这片绿意而飞扬着。
或许是长途颠簸的疲劳,坐在车里,人的精神也像霜打的茄子,蔫蔫的没有丝毫生机。沉静久了,就会有另一种声音来造访,不知谁冷不丁打了响响的喷嚏,那声音之大,仿佛要把车撞起个大包。大家在迷迷糊糊中被惊醒,这才呵呵地笑着,把酸痛的脊背来回晃一晃,伸个懒腰,然后七零八落地打着呵欠,也有人哧哧啦啦地从包里往外拿东西,那份沉默才慢慢退去。
坐在我旁边的是几位年轻漂亮的古筝女教师,阳光随意地穿过玻璃,映着她们恬静而柔美的面容,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优雅与高傲像尊贵的女神一般和着温暖的阳光一起婉约成一道另人眩目的色彩。
对我这个不懂韵律的“门外女”来说,会弹古筝的美丽女子简直让人羡慕的有点嫉妒。有好几次,我都想冲破沉静和她们探讨关于音乐或者近似音乐的话题,可想来想去,总觉自己太浅薄,就像穿了背心再套马甲,怎么遮盖都会露马脚,反而尴尬了自己。但也不能说自己一点音乐细胞也没有,要说能与音乐占点边的话,吼两句流行歌曲还是吓不倒人的。
从乡村的偏僻走进城市的繁华,虽然在地理位置上也算是一个城里人,可我的眼睛还是经常被一片片的土地所诱惑。我喜欢看土地上长出绿绒绒的庄稼,喜欢看一排排庄稼快乐成长的样子,喜欢听一株株庄稼拔节抽穗的声音。换句话说,在骨子里我还是非常乡土的,从小在坷垃堆里长大,那份带土的质地竟不容易改掉,这一点不用别人说,我自己就清楚。
当窗外驰骋的绿树把我的眼睛扯得晕眩,我不得不把视线从窗玻璃上移开,然后扭过头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坐姿。
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又不想让自己懈怠在时间的流失里,于是我打开包,拿出一本《文苑》杂志来打发寂寞的车程。一般在旅途中我都会带一两本杂志来调节自己的心情,一是用来消遣,二是让自己的脑子多装一点东西。长篇大著这个时候我一般是不带的,尽管自己喜欢看长篇,可感觉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太少,就像急急赶路中的一顿大餐,精华是有了,匆忙塞进肚子,消化却不那么容易,说不定还会引起不良,所以短小精悍的文字于旅途中的我来说,欣赏起来更为合适。
我的目光在文字里游弋,可还是不够专注,忽然就感觉视线的边角有一片绿意在移动,我又把视线投向窗外。真得呢!一片片整整齐齐没有丝毫杂质的“绿绒毯”让我的目光生出些许惊喜。远远看去,那是怎样的一种平整啊!就像用压路机把高低起伏的部分给压平一般,竟然没有丝毫的波澜,简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设计。那成片的绿野看上去非常得开阔,睁大眼睛望上半天,视线才好不容易碰到远处模糊的边缘,然后目光再折回来,又会落在那片平整的绿野上。
我兴奋之余,大声地欢呼着:“快看!好平整啊!像绿绒毯,好大的绿绒毯!”我的尖叫声再一次把沉静扯破。优雅的女子抬起头,漫不经心地把目光投向窗外,立马再把视线收回来。“什么绿绒毯!真会想像,不就是庄稼么!那是小麦,要不就是韭菜。大惊小怪,不说了,好土。有人悻悻地驳了我的惊喜,然后继续她慵懒的困倦。
我的兴奋没有引起别人的共鸣,此时我就像一只落单的喜鹊,除了自鸣自唱之外,没有一个人来捧场。我忽然感觉,处在优雅的群落里,一个不优雅的人竟然显得那么的俗不可耐。
其实我也是喜欢古筝的,但我却不懂,我喜欢它,纯粹是喜欢它的声音,喜欢那种清越脱俗的音调,喜欢那行云流水般浅浅低低的韵律。压抑的时候我会在《云水禅心》里倾听“风吹山林兮,月照花影移”的清寂;孤独的时候我会在《高山流水》中体会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的韵韵依依。
试想,在流水一般娇柔清丽的古筝韵律里,在袅袅升腾如梦如幻的烟幕里,一群婀娜的女子,在“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的空灵里,在唇红齿白倩笑嫣然的妩媚里,冷不丁跳进一个布衣布裙素面朝天的女子,还把一曲不入流的乡间叫卖调拨的极高,那阵势,绝对是极其的冷淡与对立。
不是别人的不好,只是自己的不合时宜。在尴尬里我终于明白,有些音调不是可以任意调和在一起的,并非和弦的东西,强加在一起,反而削弱了它的音质。别人不喜欢而自己以为好的东西,还是放在心底不去张扬,只有独享它的美妙了。
我知道,庄稼与我是有特别感情的,我喜欢庄稼,就像父母乡亲喜欢我一样,是不分年代与地域的。庄稼在绿色之外,也是有着特别韵味的,即便单调,即便没有古筝一样的优雅,我也一样喜欢。
(责任编辑/孙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