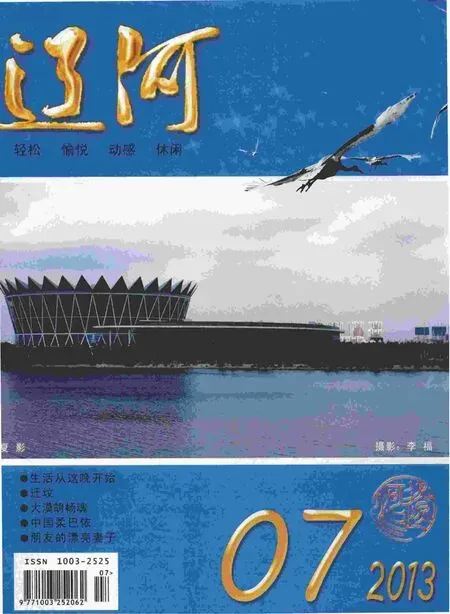福镇故事(三题)
吕品
王箍桶
王青滕的父亲王老箍桶喜欢喝酒,酒让他快活似神仙,也让他在一个冬日的午后命丧南沙渚塘。他的儿子王青滕也喜欢喝酒,大碗喝。王老箍桶死后,王青滕滴酒不沾。从父亲那被人送回来的还散发着浓浓酒气且已发胀的尸体上,王青滕晓得了,这酒有时候也能误人命,就像自己的父亲,身壮如牛的四十二岁生命,就这样说没就没了。
王老箍桶死后的第五天,王青滕就挑起父亲留下来的箍桶担,那箍桶担一头装着小木板和竹篾片儿,另一头里装着箍桶工具,口中吆喝着“箍桶,箍桶”,就这么开始走村坊串街弄地招揽生意了。王青滕的那几声“箍桶”一喊过,就有人手捧着或担着要箍的东西,三三两两地循声而至。要箍的东西大大小小的啥都有——锅盖、水桶、面桶、礼盘、脚桶、粪桶、马桶。好在王青滕平时日积月累的,已将父亲王老箍桶的箍桶技艺学了个八九不离十,因而招揽到的大小活计总能从容不迫地一一箍就。王青滕箍就的木桶或者木盘,板与板之间虽见有缝隙,但由于箍得结实,刷上一遍油漆后,倘若用来盛水,那绝对是滴水不漏的。因而,顾客没一个不竖起大拇指说王青滕的箍桶水平是“神”了的!有的还说你手艺与原来一个姓王的箍桶师傅一样,手段了得!王青滕便停下手中活计,说那是我父亲。对方“噢”了一声说怪不得你手艺这么好,原来是王师傅的儿子。又问王师傅这向可好?王青滕神情黯然,说家父没了,喝醉酒淹死了。听者唏嘘不已,说可惜了可惜了。
就这样,王青滕的箍桶名声渐渐响了起来,比他父亲王老箍桶还响。他不必再走村坊串街弄地招揽生意了,只需在福镇的家里坐等,也没有人再叫他王青滕,而改称他王师傅王箍桶了。
有天上午,王箍桶在家里根据要箍物件的大小正“滋滋”地用篾竹刀将篾青和篾簧削分开来时,有顾客上门来了,见王箍桶正忙碌着,就说王师傅忙着呢?王箍桶头也没抬,说你要箍桶?说着,他左右手各扯着刚削好的竹片一端,再往两头合拢,只听“唰唰”几声响过,就圈成了。王箍桶这一手漂亮的绝活,把个来客看得呆了,直到王箍桶问他要箍啥桶时,这才回过神来。
来客说他是南门江老爷家的,江家的千金下半年要嫁人了,江老爷晓得王箍桶的箍桶手段,就想请王箍桶上江家去箍嫁妆里头的桶啦盘啦之类。王箍桶那会儿正将手头一个篾箍儿往跟前一个锅盖上套,听说是江家的,忙问,你刚才讲啥?江家的小姐要嫁人了?那佣人笑笑说是。
关于江家的底细,王箍桶晓得一二。江家老爷江胖子为人和善,又乐善好施,是福镇近郊的大户,在乡下有良田百亩,在镇上也有店铺数间。
王箍桶说既是江老爷有请,按例说这面子无论如何我得给,你家小姐下半年出嫁,这桶是得赶紧箍了,箍好了还得刷油漆,油漆上了还得除气味。可你看看,我这里实在是抽不开身哪。如我去给你家小姐箍嫁妆桶,那我这眼前的桶啦盘啦要到啥时候才得箍完?哎!实在让我左右为难。江家佣人看王箍桶有点迟疑,便说阿拉(我们)老爷讲了,工钿好商量,还管饭。至于你这里的活计,晚上回家你也可以箍嘛。王箍桶说那好吧。他嘴上说着,手里的活计却没停,对刚套上篾箍儿的锅盖用木楔沿圈儿用力均匀地敲了几下,这篾箍儿就结结实实地圈在了那个锅盖上面。
江家的佣人看王箍桶答应了,就乐颠颠地回江家复命去了。
第二天,一向宁静的江家大院的柴房,开始响起篾竹刀削篾的“滋滋”和圈篾箍儿的“唰唰”声来。这“滋滋”声和“唰唰”声无不在向附近的乡民传递着信息:江家在箍嫁妆的桶类了。只是箍桶的王箍桶没想到,这将要嫁人的江小姐竟会是王箍桶五年前认识的那个小玉莲。
因此,当江小姐与丫鬟慧仙路过箍桶的柴房时,好奇的她们在门口驻足停顿了一下。想不到她俩只一停顿,丫鬟慧仙惊奇地“咦”了一声,江小姐轻声说你叫啥叫,真是少见多怪。慧仙说小姐你看,这箍桶匠有点像五年前救你的那个青滕哥。江小姐说慧仙你别瞎讲。江小姐说着就仔细偷看起王箍桶来。此刻的王箍桶正好抬起头来,与江小姐目光相对。他心里“喀顿”了一下,手上的那把锋利的篾刀就在左手的食指上拉了一道口子,鲜血流了出来。
明亮的大眼,黑葡萄似的瞳仁,王箍桶自己也说不清楚梦见多少回了。
直到江小姐那双柔如无骨的手用她的小手帕给他包扎流血的伤口时,王箍桶还恍然如梦。江小姐边包扎边说青滕哥,真的是你!好欢喜又见到你了。
王箍桶有点不知所措,说,玉莲,我也高兴再见到你。那时你还是个小姑娘,身子也单薄瘦小,想不到五年不见,现在已是大姑娘快做新娘子了。站一旁的慧仙笑嘻嘻地,说青滕哥,你不晓得,小姐那次自从与你分别后,不知道多少次提到你了。江小姐说慧仙你又乱说了,脸上就有了片红晕。王箍桶说玉莲,我还没恭喜你做新娘了呢?一旁的慧仙又抢着说,青滕哥,你不要说小姐的婚事了,好不?江小姐说,青滕哥,你不恭喜也罢,我是不怪你的。今天我有点累,明天再来看你。说着,低着头拉起慧仙抬脚就走。王箍桶一头雾水,不知在啥地方得罪了玉莲!
第二天上午,王箍桶边做活边盼玉莲来柴房,昨天弄破的左手食指的伤口还隐隐作痛。想不到,玉莲他没盼来,等来的却是她的丫鬟慧仙。
于是,从慧仙的嘴里,王箍桶晓得了玉莲为何一提起婚事,就不高兴起来。玉莲要嫁的是福镇警察所长的独养儿子吕强,虽长得高大结实,相貌也看似俊朗,其实一点也不强,是个憨大,用南方话来说,就是个“二百五”或叫“十三点”。江小姐想退婚,可老爷不同意,说是“二百五”有啥不好,你嫁了过去,生出的孩子总不会再是个“二百五”吧,况且,他爸是警察所长,有了这靠山,今后啥人还敢欺负咱江家?可江小姐想好了,她就是死了,也是不肯嫁给那个“二百五”的!
王箍桶听了后,一种彻骨的痛楚从他的心底慢慢地向全身弥漫开来,他好想帮玉莲,不希望玉莲受到伤害,哪怕一点儿!可如今自己没办法,真的毫无办法!这不比五年前,五年前他只是帮助玉莲和慧仙打跑了一条恶狗而已。王箍桶这会儿真有点怕见玉莲了,怕见了玉莲后没一点帮忙的表示给她,这会让玉莲心碎的。
那天以后,王箍桶往桶上箍圈敲木楔的声音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响,“笃——笃笃”声音有点惊心。也许玉莲晓得王箍桶的苦楚,自此后,竟一次也没来过柴房见他。
江小姐的婚期渐渐临近。王箍桶在江家的箍桶活儿也已差不多。
有天午后,王箍桶正在往一只桶上刷油漆,让他想不到的是,玉莲来到了他的柴房,她胸脯起伏,语速急促,说青滕哥,只有你能救我。王箍桶说,玉莲,你说我能用啥法子救你?玉莲双手搂着王箍桶的脖子,把头伏在了他的胸间,说你娶了我就能救我。说着,玉莲的嘴已吻上了王箍桶的嘴。禁不住玉莲的狂吻,王箍桶也回吻起她来,但只过了一会,他还是推开了她,说玉莲,哥这回无能,实在帮不了你。王箍桶想得很实在,警察所长不是他所能得罪得起的,害了自己不说,更害了玉莲。玉莲很失望,就哭了起来,哭着哭着说我走了。可玉莲没走几步,又折回身来,说青滕哥,你要了我吧,这样我即使嫁过去也无憾了。说着她又抱住了王箍桶。王箍桶边推她边说,玉莲,这咋行?这咋行?玉莲见王箍桶心坚如铁,便松开了抱着王箍桶的手,说我玉莲好命苦,没人可怜我。说着头也没回地离开了柴房,留下呆了一般的王箍桶。
第二天,王箍桶刚到江家,还没到柴房,就见玉莲的丫鬟慧仙急急跑来,见了他说玉莲小姐不见了,老爷发脾气让我们找呢?
玉莲不见了?一种不祥之感已在王箍桶的身上弥漫开来。那天上午,王箍桶啥也没做,呆呆地望着眼前的那一只只已油漆了一遍的桶或者盘出神。
中午时分,有人跑来说,小姐找着了,在南沙渚塘淹死了。
王箍桶听罢,觉得天塌地陷了,眼前漆黑一片。他发疯似地拿着把劈木片的小斧子把面前的嫁妆桶盘劈了个稀烂。边劈边说,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然后“哈哈”大笑着跑出了柴房。随后,又在众人惊愕中跑出了江家。待江家发现柴房里发生的一切,王箍桶已不知去向。
第二天,王箍桶却被人发现死于南沙渚塘。尸体捞起来时,与他父亲王老箍桶一样,有股浓浓的酒气。福镇人说,这王箍桶怪了!他酒早不喝了,咋又喝起了这断命的酒?
赵说书
福镇的北门,有家茶馆,叫北门茶馆。北门茶馆店里的茶,好喝又便宜,除了早茶,还卖下午茶。喝下午茶,可一边喝茶,一边听说书人说书。当然。喝茶的钱要比喝早茶贵。
在北门茶馆说书的人姓赵,他说书的水平在全县都有名气,福镇的听众就善意地给他取了个雅号:赵说书。这赵说书高挑个儿,皮肤很白。虽人到中年,但保养极好,乌黑的头发弄做三七分,很有书生气质,是典型的美男子。
都道说书的不容易,倘若你一字不落照搬书上写的说,那肯定是吸引不了听众茶客的。因此高明的说书人就对将说的书上内容进行再创作,多说“弄堂书”。赵说书就属这一类说书人。大凡听过他说书的,都道赵说书——神了!赵说书说书的内容大都是《隋唐》、《封神演义》及《七侠五义》。赵说书每个下午说上两回,他声情并茂绘声绘色,连说带比划,能把书中纸上的人物说得活灵活现。在要紧处,还“啪”地一声,在桌上来一下“惊堂木”,极吊茶客们的胃口,听得他们如痴如醉,身临其境一般,大大地过了一把听书的瘾。往往一回尽了,茶客们的听兴还余犹未尽,直到说书的赵说书收起折扇,说道“要知结果如何?且听下回细说”走下了讲台,这才意识到今天下午的说书已经结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茶馆店。第二天,听兴未尽的茶客又一个不落地到茶馆来听赵说书的“下回分解”。
赵说书喜欢一清早在北门茶馆喝茶,他喝的茶,是茶馆给他免费的。
通常,赵说书在茶馆喝好了茶,就在附近的那条青石板铺成的路上慢慢地踱着方步,边踱边看石板路两旁的老房子,而后,他就车转身子回了茶馆,茶馆早就给他备好了丰盛的中饭,只等他张嘴吃了。
有一回,赵说书从青石板路上散步回店吃饭,从不喝酒的赵说书这回竟向茶馆老板要了一瓶绍兴“古越龙山”。茶馆老板发现,赵说书这回兴冲冲的,好像在散步时捡得了啥宝贝似的。在赵说书酒足饭饱后,茶馆老板就试探着问,说赵老师你散步时看到了啥稀奇事,这么高兴?赵说书“滋溜”喝了口茶后,说神了,简……简直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赵说书有点醉了。接下来,从赵说书醉后的一个个饱嗝声中,茶馆老板知道了这事情的大概。
原来,赵说书散步时,碰上了一个在洗衣服的中年妇女,那妇女的模样竟和赵说书先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要不是赵说书所认识的那人早已逝世多年,赵说书还真当成了那人呢!茶馆老板断定赵说书以前认识的那人是赵说书的未婚妻,要不,在赵说书脑海中的影像咋这样深刻呢?茶馆店老板还发现,自此后,每当在双休日里,赵说书散步回茶馆吃饭总要迟到一点。有一回,茶馆给他备好的中饭都快凉了,还不见赵说书回来。茶馆老板急了,忙叫一个店员去叫,结果那店员在青石板路边看见赵说书与一中年妇女谈兴正浓。店员认识那中年妇女,是福镇中学的语文老师,姓杨,四年前已离异。
茶馆老板就暗里思忖,难道赵说书喜欢上了那个姓杨的语文老师。要是如此,那赵说书倒是蛮有眼光。且不说这杨老师的相貌是如何如何的漂亮,更要紧的是杨老师是个老师,不是一般的福镇妇女。茶馆老板有心要成全这一桩美事。但在这以前,需得了解赵说书的过去。虽然这赵说书在茶馆说书,但对于赵说书的过去,茶馆老板心中是空白一片的。赵说书刚来茶馆时,茶馆老板就对赵说书“背景”有过问号:这赵说书的本事如此了得,咋不在专业曲艺团,反在外跑单帮?现在机会来了,得好好弄弄清楚赵说书这个人。立时有好心人不知从哪里“挖掘”得来了赵说书的“背景”告诉了茶馆老板,据说赵说书原在文化馆工作,后来他辞职不干了。辞职的原因是赵说书在文化馆试图抚摸一漂亮女同事丰满的奶子,女同事死活不从,还杨言要将此事说出去,让大家都晓得晓得赵说书是个伪君子是个大色狼。赵说书知道在文化馆再也没脸待下去了,便辞职了。
茶馆老板知道赵说书这一“真相”后,大吃一惊,原来自己是在“引狼入室”!他想自己的老婆也有点姿色,在福镇是有“茶馆西施”美称的。如此下去,保不定哪天自己也戴起了绿帽子。可茶馆如没有了赵说书,那还有啥人再来吃下午茶。喝下午茶的大都是冲着赵说书,而不是冲他茶馆的茶。虽然自己的老婆也长相不错,但自己老婆毕竟是个一般女人,不像杨老师那样是个知识分子,这赵说书总不至于看上她吧。茶馆老板这样想了后,心里才稍稍安了心。可杨老师咋办?可不能让杨老师这样的知识女性上了这赵说书的当,自己有义务得马上告诉杨老师这姓赵的“真相”!可在杨老师那里,茶馆老板吃了闭门羹,那杨老师死活不相信赵说书是那样的人,说这是有人在瞎说!茶馆老板在回来的路上,想再聪明的女人一旦相信了男人的虚情假意,也就变得愚蠢起来,比如说漂亮的杨老师。
福镇是个小镇,很快,有关赵说书辞职的这个版本在福镇的每个角落里传开了。福镇人恍然大悟似的,暗里说真看不出,赵说书原来是个流氓是个色狼!于是,再遇见赵说书时,就把脑袋避过一边,装做看不见。在茶馆听说书的茶客也少了许多。为此,茶馆老板少不得多听老婆的唠叨“你看你,多嘴!你这是砸自己的生意呀!”茶馆老板想想也有点懊悔,赵说书风流关自己屁事!
一天,茶馆来了个文化人模样的找赵说书。恰巧赵说书不在,去青石板路上散步去了。茶馆老板“旧病”又犯了,说你找赵说书做啥?你知道这赵说书是啥样一种人?来人双眼奇怪地盯着茶馆老板,说晓得,这赵说书是个可怜人!这回轮到茶馆老板吃惊了,说这赵说书是个可怜人,你倒是说来我听听。于是,那人一边喝茶,一边就把赵说书的过去说了个大概。赵说书年轻时是在当时的县文化馆工作,他与文化馆一个唱越剧的沈姓女演员恋爱五年,可双方正要结婚时,赵说书遭人诬陷进了监狱。他的未婚妻却让好色的文化馆造反派头头陆胖子强暴了。赵说书未婚妻羞愤之下,觉得对不起赵说书,就跳河自尽了,据说连尸体也找寻不到。赵说书在监狱里听说了,大病一场。好在一年后,赵说书平反了,但说啥也不愿回文化馆工作。他对几个要好朋友说,我不愿回到能勾起我伤心事的地方。从此后,为了对得起为他殉情的未婚妻,赵说书一直单身。
茶馆老板听后,连拍大腿,说我轻信了谣言对不住赵说书。赵说书这样重情重义的人,杨老师跟了他,不委屈!
来人惊讶地问,杨老师?哪个杨老师?
对,杨老师。你不晓得,杨老师的相貌据赵说书所说生得与他的未婚妻一模一样哩。真有这事?来人有点不相信。难道说赵说书的女友没死,怪不得当时没找到尸体?哎哎,这事实在太像赵说书说的书了!
豆腐阿四
豆腐阿四长得精瘦如瘪谷,相貌也不咋样,他原来不是福镇人,年轻时来福镇做上门女婿,这才成了福镇人。
是福镇的人都晓得,福镇的西寺前有块空地,虽不大,但福镇人把它叫做“广场”。广场的正中有株银杏树,据说有上百年的历史。树冠非常大,状如一把巨伞。福镇人吃过晚饭后喜欢去那里透透气,散散步,用他们的说法,叫做“白相白相”。豆腐阿四也不例外。
有一天傍晚,广场上来了两个打拳卖艺的,一大一小。大的年约四十,是个长得敦实精壮的汉子,小的是个年约十四五岁的少年,长得精瘦。小镇从没来过打拳卖艺的,因此,人们听说后,都早早吃了晚饭,纷至沓来,很快就将广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先是那个精瘦少年打拳,只见他闪展腾挪,指东打西上封下踹,煞是厉害。一套拳打下来,脸不红气也不喘,惹得围观的人们齐声叫好。少年刚打好拳,那个矮壮的中年汉子就上场了。汉子双手一抱拳,说各位,下面我给大家表演硬气功——钢刀刺肚,给福镇人亮亮眼。我这表演还得辛苦两位有点力气的看客帮忙,也就是我拿刀尖指肚,刀柄在上,上来的两位看客用榔头使劲砸刀柄,假若我面不改色,那就请围观的各位捧捧场,让我与徒儿高兴高兴。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嘛。汉子说完,就赤膊躺于地上,拿刀往肚子上一指,单等有人上来砸刀柄。很快,就有两个自恃有些能耐的福镇年轻人上来,只见他俩在那卖艺汉子的面前先是发一声吼,然后各拿起榔头照着刀柄“当”地就是狠狠地一下,躺在地上的那汉子没事一般,那俩年轻人有点发怵了,拼尽全力又朝刀柄砸了二下,那个卖艺汉子仍没事一般。俩年轻人见状,便红了脸丢了榔头退入围观的人群中。这回福镇人没有替汉子拍手叫好。卖艺的汉子翻身跃起,用手拍了拍胸部,大声说,还有人上来试试吗?四周鸦雀无声。卖艺汉子有些洋洋自得起来,说没有人上来一试了?那么请各位看客每人奉献10块钱,要晓得,我刚才的表演那是要冒风险丢性命的,大家说是不是?汉子见大家无异议,正要让少年拿一只纸盒上前向围观的福镇人讨要表演费。只听一个略微沙哑的声音说,我来试一下!大家一看,原是卖豆腐的阿四,都吃了一惊,想,这豆腐阿四今儿这是咋了?昏头了是不,这卖艺汉子也是你能上去试一试的?
他们正疑惑间,豆腐阿四早站于卖艺汉子的面前了。那卖艺汉子也疑惑地看着眼前这精瘦如瘪谷的豆腐阿四,说是你,你能行?豆腐阿四回答说是我,咋了?卖艺汉子有点不相信,说你能行?豆腐阿四说我试一试!况且,试还没试,你咋知道我不行呢?卖艺汉子又仔细地上下打量了豆腐阿四一番,这才说好吧,我信。说罢,他又躺于地上,将刀尖指着肚上,刀柄朝上。豆腐阿四也吼一声,随接抡起榔头朝刀柄重重地砸去。只一下,卖艺汉子身子就一震。豆腐阿四将裤带一紧,牙齿一咬,抡起榔头又要朝下砸。卖艺汉子暗叫不好,急说,好汉放我一马,咱跑江湖卖艺不容易。豆腐阿四说,哪成!你都放大话了,我哪能收手,大家都看着我呢! 卖艺汉子眼看要吃亏,忙一个“鲤鱼打挺”将身跃起,躲过了豆腐阿四的第二砸。卖艺汉子想,这小老头这么不通情理!便恼羞成怒,拉开架子一个“白鹤亮翅”,右手掌猛地朝豆腐阿四裆部撩去。阿四往后一退,便躲了过去。卖艺汉子又上步使右拳击向豆腐阿四胸部,阿四忙一个侧身,又躲了过去。卖艺汉子这一拳便重重地击在了墙壁上,把个墙壁打了个窟窿。汉子这才止了手,然后拉起徒儿,收拾好表演家什,抱拳朝围观的人们拱了拱,说今儿献丑了!随后一声不响朝场外急走。福镇人也默默地目送着他们离开广场,没人喝阿四的彩也没人讥笑卖艺汉子。
于是,豆腐阿四在福镇名声大震。福镇人都在说,想不到北门做豆腐的阿四是个武林高手。那几日,豆腐阿四的豆腐也一下比往日俏了起来,供不应求了。各种传闻也应运而生,有说镇上要办个武术班,让豆腐阿四去当教练;也有说镇里已放话,要推荐阿四当下届的县政协委员。去北门跃进桥下阿四的豆腐店里要拜阿四为师的年轻人也一拨又一拨,非要向阿四学艺不可。豆腐阿四向他们解释说自己没啥功夫,只是年轻时在打铁匠的那里学过艺,因而双臂是很有些力气的。那些想学功夫的年轻人哪里肯信。你阿四师傅越是如此说,他们越是相信阿四藏有真功夫。他们听人说过,说越是有功夫的,却往往说没功夫,而越是没功夫的,却总吹说自己有多少多少的本事。于是三天两头来阿四的豆腐店,说阿四师傅,收下我们吧!这样弄得阿四做豆腐都没法做了,实在没法了。阿四大声说,我没武功就没武功,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你们还要让我咋说才相信呢?那些年轻人这才有些不情愿地回去了。望着走出门去的这些年轻人,阿四大大地松了口气。
想不到第二天,福镇人就有人说,阿四也真是的,你不愿教武功就不愿教吧,对那些年轻人说话那么大声做啥?真是小气到家了!阿四知道后,气得当场说不出一句话来。以后的几天,阿四的豆腐不知为啥?很少有人来买了。于是,从没和阿四红过脸的阿四婶也埋怨起阿四来了,说阿四,你看你,你得罪了人你晓得吗?阿四摇摇头说我哪里得罪人了?阿四婶回答,说你不愿教人家武功。阿四说我没武功我拿啥去教他们,如去教他们,这不是让我哄人嘛,我阿四哪能做这种事情!阿四婶看看话说到点子上了,便说,既然这样,那外来人来咱福镇卖艺,要你出头做啥?阿四说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给福镇人争面子。阿四婶“哼”了一声,说你阿四给福镇人争了面子,福镇人给了你啥?你不晓得,全福镇人都在说咱小气,讲你阿四为福镇做了点芝麻大的事儿,那尾巴就翘上了天。阿四听着听着,手指发抖,喃喃自语着,说咋会这样呢?咋会这样呢?这天晚上,阿四病了,他发着高烧说着胡话,连夜被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说是中风!半年后的一个冬天的早晨,豆腐阿四终因病不治而撒手人世。
福镇终究没人见过豆腐阿四去镇上的啥武术班当教练,以后也没人再敢说阿四曾经当过县政协的委员,这毕竟是传说而已。但有一点却确确实实,那就是,豆腐阿四去火化那天,镇里由文体站出面,给阿四送了个大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