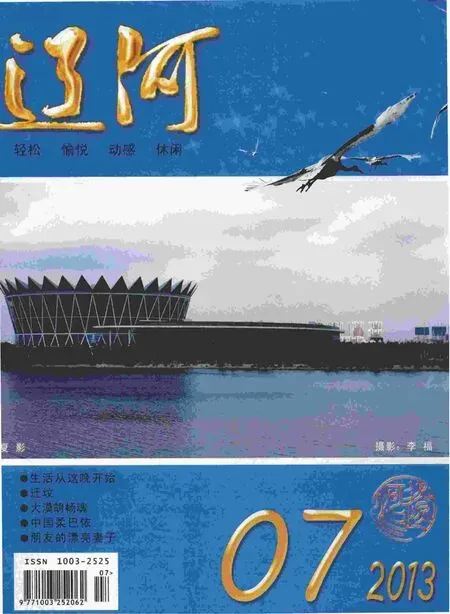背影
秋泥
一
萧长山沿着卫工河走走站站,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在想早晨的事情。早饭后,儿子给他翻换洗衣服的时候,在床箱夹缝里摸出个旧笔记本来,儿子翻开本子看了看,伸到他眼前:
“爸,谁写的呀,这本子上的诗?”
萧长山把本子推远,眯缝起眼睛:粉红色塑料皮儿,摸着硬撅撅的,翻开首页,发黄的纸面上字迹已经褪色,只依稀辨的出 “桃花流水”四个字……萧长山眉头跳了一下,似一道电流“倏”地通到了记忆的深海,他集中心思捋了捋,终于捞出了本子的主人,他拍拍头说:
“哎呀,这个人可不简单,是个舞蹈家。”
“您还认得舞蹈家?”儿子惊讶地问。
“你听他吹吧,”没等萧长山应声,一旁的老伴接住话茬,“和他过了一辈子,就没听说过他还认得个舞蹈家,嘁。”
萧长山白了老伴一眼,没理她。俩人磕磕绊绊了一辈子,一说话就犯相,不知不觉间,萧长山就关闭了和老伴交流的通道。说啥是你的事儿,听不听是我的事儿。儿子怕俩人儿叽咯,也就不问了。晃晃本子说,给我吧。萧长山点点头,他知道儿子爱收集旧东西。
今天是周日,路上的行人不多,空阔的河岸只有一条白色的流浪狗寻寻觅觅地独行。狗儿走的不老实,树根、石凳、栏杆脚,到处支腿儿拉尿。
这八成是条害前列腺的老狗。萧长山想。
这一瞎联系,把自己弄出了内急。忙寻一豁口,捋着护阶一步一蹭下到了河边。四下踅摸,没看见人,就往河里“漓漓啦啦”地撒了一泼尿。末了,打一激灵,险些把帽子抖搂掉。好阴冷的天!萧长山一边系裤子,一边想,狗儿为啥不打激灵呢?他看过狗打哈欠儿,没见过狗儿打激灵。
想不出答案,索性打量起脚下的卫工河。这条河一到冬天,就会有大团的白在河面上翻滚,将岸边的松柳蒸腾的毛茸茸的。人站在河边,就站进了晶莹的童话世界。
多美!谁敢想它过去的样子?萧长山想。
萧长山在这条河边走了四十多年,他当然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四十年前,卫工河两岸林立着无数的大烟筒和厂房,浓墨重彩地凸显着这个北方工业重镇的分量。那时还没有环保概念,工业废水及居民生活污水统统排放进卫工河,使河水终日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儿。那时的河水呈酱油的颜色,水面不时飘过一滩滩的油花。那些油花有的巴掌大小,有的锅盖大小,中间蓝汪汪的,边缘则湿乎乎烂唧唧的,远看,像漂了一河的癞蛤蟆皮。
河水浑浊,河边的植物却长的异常茂盛。蓖麻杆疯长出一人高,叶子大如斗笠;打碗花缠着爬山虎,拧麻花似的爬到几丈高的树冠子上。附近住的孩崽子们,终日在密不透风的蓖麻林子里穿梭。他们网蜻蜓,捉蝼蛄,躲猫猫,或掐着木枪带着草圈,把蓖麻林当成了青纱帐……
令他记忆深刻的是孩崽子们经常玩的“拣儿子”游戏。那时节,从乡下往城里运送农副产品的马车络绎不绝。马铃铛声随风传送,孩崽子们听了立刻雀跃起来,从蓖麻林中鱼贯而出,奔上桥头,自桥栏下整齐地蹲成一排,远看,似蹲了一溜猴子。满载着茄子土豆的马车“嘚嘚”驶来,在十字路口即将拐弯的一刹那,孩崽子们一起大叫:
我儿子是谁呀?
喔!喔!(我!我!)车把式摇鞭收缰,嘴里回应似的吆喝道,一问一答竟衔接得不差分毫。孩崽子们立即夸张地哈哈大笑起来。车把式谙熟城里孩崽子的勾当,大都不作理会,这帮犊子,越搭理越来劲。也有脾气不好的,“嘎”地一声拉死车闸,翻身跳下马车,擎着三米多长的鞭子,大步流星赶来,嘴里吼:
我打死你们这帮小瘪犊子!
这就正中孩崽子们的下怀,他们呼啦下投入蓖麻林,嬉笑声伴着蓖麻林“唰拉唰拉”的摇曳此起彼伏:
哪有儿子打爹的……
哪有儿子打爹的……
车把式怒火中烧,把蓖麻叶子抽打的漫天纷飞,却伤不着孩崽子们半根毫毛。
这些事就像发生在昨天,就一晃的功夫。
他觉得卫工河是认得他的,这样想着,眼见河水响应似的欢快了许多。水面,白蒙蒙的雾气,绵绵不绝,腾空之际,露出许多拧成麻花劲的暗流,暗流激起的水花暴露了这条河的秘密——看似凝滞的河水,其实一直在暗中遒劲地奔流着,不经意间裹走了许多东西。
“你是个贼!” 萧长山瞥着嘴儿说。
仿佛被说中了痛处,细流“唰”地隐进雾里,水草也无声地下潜,河面的雾气更浓了,极目望去,整条河都朦胧起来。
二
走着走着,萧长山忽然想起该听评书了。站住脚,哆哆嗦嗦地掏出收音机,打开开关,把耳机插进耳朵,把收音机装回口袋,继续赶路。
他要听《太平洋战争》。这是新评书,讲的是二战的事儿。过去那些讲古的老段子早听腻了,翻来覆去就那几个。这新评书好,美国鬼子打日本鬼子,打得激烈,打得过瘾。最重要的是,哪一方吃亏他都不跟着揪心。
萧长山十几岁的时候见过日本人,在“奉天驿”,就是现在的沈阳火车站。萧长山那时做些小买卖糊口,冬天卖烧饼,夏天卖凉糕。烧饼是芝麻盐的烤饼,在北市场馒头坊上的;凉糕是芝麻白糖馅的,在西关回回营进的。烧饼、凉糕都是七分钱进,卖一毛钱,一个挣三分。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起来了,进完货,就挎着双层的笼屉盒,沿着马路湾至火车站一线叫卖。那时日本人搞“粮食配给”,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吃大米白面。抓住了,按“经济犯”治罪。所以,萧长山的买卖虽小,却做得提心吊胆。
在这片管区有个外号叫“黑豆皮”的日本巡警,矮趴趴的个头,配上一张长满横肉的黑面皮,人凶得很。萧长山被“黑豆皮”抓住过两次,没收了东西不说,还罚他下跪认罪。当萧长山第三次被抓的时候,“黑豆皮”认出了他,当即暴跳如雷,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破口大骂。大意就是,屡教不改啦,混蛋啦,从重处理啦之类的。骂着骂着,冷不防就踢了萧长山一脚。这一脚踢在了他的肚子上,很重。萧长山疼得上不来气儿,也哭不出声来。“黑豆皮”仍不解气,哇哇叫着把烧饼倒进了垃圾箱,又踩烂了笼屉盒。最后,“黑豆皮”咬牙切齿地说,不看你年纪小,就送你进大和警署法办!
打那以后萧长山再也不敢卖烧饼了,改糊火柴盒了。所以,他特别憎恨日本人。那时大街上经常能看到一些缺胳膊少腿儿的日本伤兵,听说都是在关里给打残的。萧长山想,最好把“黑豆皮”派关里去,把这瘪犊子的两条腿都打折喽!
去年三月,电视上天天播日本大地震的事,说是地震引发了海啸,淹死了不少人。萧长山听了就喊该!说是报应。后来又看到了不少失去亲人的妇女孩子画面,他不落忍了,喃喃地说:早先年造孽的都是些老鬼子,不是现在的这些人啊!
近来电视上天天讲钓鱼岛,讲日本人要把钓鱼岛收为他们国有,呸!这日本人真不要脸,和这样心怀鬼胎的邻居相处真是麻烦。当年,在中国,祸害多少人?一屁股屎没揩净,如今又搞事儿,就他妈的欠揍。后来收音机里说,有人游行,抗议日本鬼子侵占钓鱼岛。萧长山认为很有必要,这样能让小日本子知道下中国老百姓心声,想侵占咱们领土没门儿,咱十三亿中国人不答应!
再后来发生了砸车事件,萧长山觉得不以为然,要砸也得砸日本鬼子的,砸自己同胞的就说不过去了。老百姓使用的很多家电是日本产的,能都砸了吗?日子还过不过呢?年轻人天天喊打,他们是没经过兵荒马乱的年月啊!唉,自己老了,不然……他突然记起年轻时一位夜校老师写的诗:
恨我未生在当年,
持枪跃马守疆边。
洒尽一腔青春血,
斩杀日寇三千万。
这是何等的豪情?萧长山如今读来却没了当年的血脉贲张。日子像水一样的流,自己转眼就步入了古稀之年。打鬼子?枪都扛不动喽!咋过来的?不知道,就一晃的事儿。
同单元一个细溜溜的小媳妇,没事爱牵着一个细溜溜的小丫蛋,遇见他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诉苦:这孩子,啥时候能长大呀,可愁死人了。他抚摸着丫蛋的毛发稀疏小脑袋,认认真真地叮嘱着小媳妇说:
“别盼,千万别盼,一晃儿就长大喽,真的,就一晃的事儿……”
三
卫工河南北走向。往南两站地,是萧长山家居住的小区;往北三站地再向东走一个街区,就是他干了一辈子的铁路器材厂。他在那里工作了近五十年,如今老了,厂子不再需要他这个八级模具钳工了,不再需要他这个“JD钢丝卡”冲压模具的发明者了。
两年前,冲压分厂厂长窦胖子把他送到了厂门口,脸上不阴不阳地笑着,目光游移不定,没事过来转转呗,就当活动筋骨了。
窦胖子是笑面虎,有一天他不笑了。
当他和萧长山在车间安全通道上碰面的时候,没像以往那样点头哈腰地打招呼。而是面无表情地昂首而过,这有些不同寻常……或许人家忙呢?毕竟是领导。
笑面虎不是见谁都笑的,只有上级领导或是值得他恭敬的人,才会获得他那副谦卑温驯的笑容。萧长山显然也在恭敬之列。他清楚,这待遇不是因为他连续三十年获得过厂级先进,而是因为技术。换言之,有他萧长山在,冲压分厂钢丝卡的产品合格率就会保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反之,合格率就会掉在百分之五十以下,等于干一半扔一半。所以,无论冲压分厂换成谁坐庄,都得拿他萧长山当盘菜。
萧长山瞄着笑面虎的背影,胸口突然抽搐了一下,仿佛运行自如的设备突然遭遇低电压,一口气儿滞扭扭地憋在胸腔里,让他难受不已。他捂着胸口想:胃,又闹毛病了?就近坐下来,跟小青工讨口热水,小口小口地润着。终于打出了几个逆嗝,慢慢缓应了过来。
那天下午,厂子召开了重要会议。会上年轻的厂长一脸严肃地宣布了关于产品转型和部分职工下岗分流的决定。对于下岗分流萧长山不感冒。他十年前就退休了,返聘这十年,他被当成弥勒佛一样供着,惬意的很。真正让他感到震惊的是,JD系列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了……
萧长山依稀记得离开厂子时的情景。
晚上,工人们都下班了。萧长山打开床子上的工作灯,坐在床子前端详着自己发明的钢丝卡模具,端详着这个给他带来几十载荣誉的铁家伙:黑不溜秋的,真他妈难看!他笑了,本来就难看啊,土法上马的东西嘛。
抬头望去,一座座巨大的冲床,蹲伏在寂静的黑暗中,像一头头假寐的狮子,似乎在养精蓄锐,等待着天明再展雄风。
打开饭盒,里面装着从食堂买来的炸黄花鱼、肉炒瓜片和一头蒜茄子。又从兜子里掏出一瓶高粱烧,“咕嘟咕嘟”地往搪瓷缸子里倒,他要在机台上吃最后一顿夜班饭。端起缸子的刹那,他想到了自己的师父,那个满面红光、性子刚烈的胡老头。师父十六岁进厂做学徒,那时候厂子叫“满铁电池株式会社”,老板是日本人。
解放后,师父成了新中国第一代技术工人。师父有三牛:技术牛,酒量牛,脾气牛。遇到原则事儿,管他书记、厂长谁的账也不买。虽然扛上,依然备受尊敬,因为技术。八级工,大工匠,在任何企业都是宝贝疙瘩。师父平时言语金贵,喝完酒后就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跟他吼:
“萧长山,你给我记住喽——技术,技术,还是技术!技术过硬,天王老子咱也不尿他!”
萧长山做洗耳恭听状,心里却憋不住想乐。师父说话带口音,把技术说成了鸡术。
后来,师父死于肝硬化,弥留之际跟他嘎巴嘴儿,看口型还是“鸡术”俩字,萧长山扒着师父耳朵喊:
“师父,长山记着呢,‘鸡术过硬,天王老子咱也不尿他!”师父听了,“咔吧”下咽了气。
萧长山记住了师父的话,学习技术更加用心了。他渐渐地发现,过去必须向师父请教的问题,现在自己琢磨琢磨就解决了。他想了想,明白了。这好比他包粽子。萧长山本不会包粽子,每年五月节都是母亲张罗着包粽子,没他什么事,管吃就行了。
母亲过世后,到了五月节孩子们依旧嚷嚷着要吃粽子。媳妇是病秧子,指不上。萧长山只好自己买了江米、红枣、粽叶、马莲,依着母亲的样子泡米,煮马莲、粽叶。开始时他怎么包都包不好,不是包松了漏米,就是掐紧了捏坏了粽叶。他停下来,坐在月影儿地里抽烟。月光飘进窗户,落在地上,在他脚下无声地流淌。他看到母亲一双白净净的手,灵巧地把粽叶围成锥筒,然后放进一颗红枣,然后添米,然后用马莲绕成四角形,那个节打的是双扣,像飘飘欲飞的蝴蝶。母亲的动作轻盈极了,母亲一边包,一边说着包粽子的要领和端午节的一些传说……
萧长山再次坐回米盆边上时,他发现自己会包粽子了。他高兴极了,他想,今后每年都要给孩子们包粽子吃,就像母亲小时候给自己包粽子吃一样。端午节的早晨,他剥了三个白胖胖的粽子放在了母亲遗像前:
妈,尝尝儿子包的粽子,你孙子说好吃,说和奶奶包的是一个味儿,就是没奶奶包的模样精巧。
母亲笑了,母亲说:
你比妈包的劲道,你的手比妈有劲儿。
四
母亲、师父都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人。他们走了,把气脉留在了他的血液里,每逢遇到沟沟坎坎,他们就会不请自来。
接受“JD钢丝卡”冲压模具研制任务时,他把铺盖带到了车间,没日没夜地投入到试制中。模具没搞出来,人憔悴的脱了相。他常常想,如果师父活着会怎样来做这套模具呢?想着想着师父就来了,师父显然喝足了高粱烧,水汪汪的眼睛有些飘飘欲仙,他用少有的温和语气对萧长山说:咱做模具凭的是什么呀?萧长山说,是技术啊。那技术凭的又是什么呀?萧长山语塞……是灵性,灵性知道不?你脑袋现在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得先清一清,得腾出些地方来……
萧长山似乎领悟了师父的意思。他剃了头,刮了脸,洗了澡。又去厂子对面小吃部喝足了高粱烧,然后就驾着云回家睡觉去了。两个星期后,萧长山做出了“JD钢丝卡”冲压模具。尽管是土法上马,但产品合格率基本达标。后来经过调试,合格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件事在当时很轰动,还上了火车头报。
当时车间有个从部队下来的洪书记,不懂技术却喜欢放卫星。他在庆功会上扯着嗓子喊: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要让产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百!并当场让萧长山代表车间表决心。萧长山站起身的时候,觉得血往上撞,他知道是师父胡老头灵魂附体了。萧长山寒着脸,把棍子粗的手指团成钩子,“梆梆”地敲着桌子说:
“产品合格率达到百分之百不现实,技术有它自己的规律,技术不是用来吹牛逼地!”
洪书记丢了面子,尴尬至极。他咽不下这口气,借调了全厂的技术骨干向“百分之百合格率”发起了攻关,唯独不让萧长山参加。结果,试验全部以失败告终,新模具的合格率连百分之五十都达不到。最后,老厂长在生产会上一锤定音:钢丝卡模具不要搞了,劳民伤财!搞模具,哪个能搞过萧大拿?他的东西经住了考验,称为“萧氏定理”都不过分。我们要上报部里,为他申请发明奖。
萧大拿的名头,从此叫响。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令他应接不暇。一年后,他由模具班长提升为车间副主任。
萧长山在车间里坐了一宿,整瓶的高粱烧见了底。天亮了,朝霞从厂房宽阔的天窗上倾泻下来,把这块钢铁交错之地涂上了一片耀眼的金黄色。巨大的冲床披着霞光,似威风凛凛的雄狮。车间里,一排排工具箱、一张张操作台、一堆堆形状各异的冲压件都蒙上了一层迷人的亮色。
萧长山用抹布把模具擦了最后一遍,赶在工人们上班之前默默地离开了车间。他本来想去幼儿园那边转转,去看看那棵老桃树,结果,在车间门口碰到了笑面虎。笑面虎依然客气,只是脸上肌肉做了些许调整,谦卑温驯的笑换成了皮笑肉不笑。
今天,他又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工厂。
一路上急行,赶出了一身大汗。萧长山自己也纳闷儿,大礼拜天儿的,孩子们都在家,自己跑到这个地方干嘛?对了,好像听谁说厂子要拆了,毕竟是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也或许是因为那个笔记本。
尽管萧长山有心理准备,但眼前的情景还是让他目瞪口呆:被纤维布围挡起来的厂区已面目全非,拆去门窗的厂房像巨大的骷髅,空洞洞地在寒风中呜咽。一台爬上瓦砾堆的吊车,甩动着一个硕大的铁球狠狠砸向厂房圈梁,“轰——”的一声巨响,险些把萧长山的心脏震出来。
他不敢看了,顺着小路摇摇摆摆地逃去。逃到厂子东南角他站住了。那里原来是幼儿园,与他原来工作的车间并邻于墙角的两侧,之间隔着一块三角形的空地,空地上长着一株健壮的桃树。
如今房子已夷为平地,那株桃树被剥了皮,光秃秃地伫立在废墟上,像一尊风化的枯骨。
那桃花盛开的时候是相当鲜艳的啊!
萧长山泪光闪闪地自语道。恍惚间,往事如潮,不由分说地将他淹没。
五
当年萧长山走马上任的时候,正值桃花盛开的季节。那时,他才四十多岁。他站在二楼办公室窗前,望着层层叠叠的桃花发呆。桃树巨大的花冠几乎遮蔽了天空,堆在窗前的粉,仿佛一不留神就会破窗而入把他淹没。淹没就淹没吧,那话怎么说,宁愿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呼吸着满室的花香,觉得有些不真实。做了近二十年的模具钳工,凭借着钢丝卡模具一跃就登上了主任的位子……新官上任的喜悦与花香弥合一处,让他陷入忘我的沉醉中。
忽然对面幼儿园的铁门洞开,随着一阵轻快的音乐声,桃树下机里骨碌地跑来一群小孩子,像滚过来一地皮球。小孩子们在女老师的摆弄下很快就站好了队形,并随着音乐节拍翩翩起舞。一排排左右摇晃的小脑袋,像一颗颗饱满的桃花骨朵,可爱极了。女老师身材很好,背对着他做领舞。他的注意力一开始在孩子身上,后来落在女老师身上时就坚定不移了:简简单单的儿童舞蹈,女老师竟跳的异常优美,每一个动作都像飘落的花瓣般轻盈,那胳膊,那腿儿,是水做的吗?
萧长山不懂舞蹈,让他惊叹的是如此好身材的年轻女人,他竟然从来没见过,怎么可能呢?一个单位同事,每天都来上班、干活、吃食堂,就算不熟悉也从总该打过照面的。
音乐停了,孩子们如同来时一样,机里骨碌地消失在对面的铁门洞里。三角园恢复了之前的宁静。只有那女人,依然在萧长山的脑海里轻柔地舞着,宛如轻盈的花瓣儿。
再次见到那女人是在雨后的一天,她手里托着个细脖儿白瓷花瓶,来到树下折桃花。可是那树枝很有韧性,与母体生聚死别般地不肯分离。女人使劲一拽,满树蕴藏的雨水瞬间倾泻下来,将她淋得落汤鸡一般。女人似受到惊吓的兔子般跳开,然后心有余悸地看着桃树发愣。
这一幕让萧长山看得怦然心动,女人和桃花,一起映在树下清亮亮的汪水里,像一幅不染凡尘的水墨画。他伸出头喊道:“别动,等着。”他拿起桌子上剪刀就跑了出去。来到桃树下,他伸手剪下了一株密实的花枝,递给女人说:
“雨后的树枝最有韧性,用手怎么折的断。”
初时,女人听到喊叫声以为是有人责备她。直到萧长山风一般出现在树下,并为她剪下桃枝的时候才如梦方醒。她捋了下滴着水珠的流海,受宠若惊地说:
“谢谢您啊!我叫林茵。”
萧长山如此近地看着她,一下子愣住了:这女子不仅眉目清秀,脸色简直和桃花一样的鲜艳啊!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相见时,林茵总会莞尔一笑,轻声问候:“萧主任好!”这三个字由别人嘴里说出是客套,而由林茵口中吐出,则带着桃花的芬芳,总会令他入心入肺地陶醉上一阵子。他后来想了想,林茵除了说话语气温柔外,发音也非常的标准,甚至可以和播音员媲美。
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每年桃花烂漫的季节,林茵就会托着她的细脖儿白瓷花瓶来到三角园的桃树下等待,直到萧长山给她剪下一支丰美的桃枝。她依然会像初次那样欣喜异常地说:“谢谢您啊!”
有一回,他对林茵说:“你像观音娘娘。”林茵听了,抿着嘴乐:“第一次,我以为你是从树上下来的,你前世一定是桃仙吧。”萧长山不善言辞,只是笑呵呵地望着她。林茵的皮肤很白,白得就像她手中细白瓷瓶;她的眼睛很亮,里边开满了层层叠叠的桃花。
他们之间来往仅限于一些不经意间的相遇,和每年必赴的桃花会。除此之外,萧长山对这个女人一无所知。他是一个从来不听闲话的人,他的品性决定着他不可能挖窟窿盗洞地去打听一个女人的来历。平时他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直到每年三月,窗外粉色遮蔽了天空,他才蓦然想起:
“该给观音娘娘剪桃枝了。”
第四年桃花盛开的季节,林茵黯然地站在树下,仰望着漫天的桃花幽幽地说:“萧主任,我要走了,要回原来的单位去。这个花瓶和笔记本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萧长山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为什么要回去呢?哦,看来你是愿意回去的……那好吧,不过,你要是觉得原来的单位不好,就再回来吧。”她笑着摇摇头。
半个月后,她给他打来一次电话,声音轻柔的近似自语:“萧主任,三角园的桃花都谢了吧?粉莹莹的花瓣还是落得满地都是吧?一定是的……”
后来萧长山听工会干事小黄说,林茵原来是省芭蕾团的国家一级舞蹈演员,曾因成功演出《天鹅湖》、《精卫》受到过文化部领导的接见。因为海外亲属的牵连才下放到工厂的。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因未满足某位团领导的特殊要求而被人整下来的云云……好在都过去了,落实政策后,林茵又重返舞台了。
六
林茵再一次打来电话已经是半年后了,她要送给萧长山她的国庆演出门票,她幽幽地说:“来看看吧,折断翅膀的天鹅涅槃重生了,这一次起舞不为王子,也无关魔咒,只为漫天飞舞的桃花……”
萧长山听得云山雾罩,期间,他正领着工人大干百天,为国庆献礼。他用腮帮子夹住电话,用抹布擦着手上的油污,吭吭哧哧地说:“那个……厂子很忙,天天都要加班……芭蕾舞,说实话,我也看不懂,也没时间……所以,就谢谢你的好意了吧……”
林茵听了,半晌没说话,然后默默地挂了电话。还有一次他值夜班,正在办公室里看报纸,电话突然就响了,他拿起电话刚说了一句:“喂!”就听见电话那边有些慌乱:
“……这么晚,还有人啊?”
“你以为没人?你找谁呀?”他问。
“找你啊,萧主任我是林茵,没事,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没想到你真的在……还好吧?”
“好好,”他一下子不知所措了,“老样子,忙工作呗……”
“我没事,”林茵淡淡地说,“演出完了有点累,洗洗澡,吃点夜宵,夜深人静,一个人在喝茶,忽地就想起咱们单位的桃花了,没想到桃仙也在……”
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也不想用客套话敷衍她,就静静地听着。那是他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此后林茵就杳无音信了。
萧长山也曾认认真真地想过,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上演一幕风花雪月?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自己是个正派人,其次是两人差距悬殊,还有,自己的家庭负担很重:要养活四个孩子和一个寡妇老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萧长山逐渐推翻了从前的想法。他们邂逅于林茵下放期间,那时她是幼儿园教师,他是近千人的大车间主任。所以,差距应该不是问题吧。至于人品或是家庭负担的问题啦,全是借口——其实,自己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萧长山为这个结论沮丧不已。
但他也没啥好后悔的,他萧长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或许这一辈子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但也不会身败名裂。或许林茵看重的,就正是他的正派本分。
他忘不了林茵,尤其在退休之后。
退休之前,他在意的是荣誉,如:厂门口的光荣榜里,年年不落的大头照片;家里墙上,密密麻麻的镜框奖状……
但是离开厂子之后,厂子在他的记忆里只剩下了林茵清澈的笑容和那一树粉莹莹的桃花。这是他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温存。
那个粉色塑料皮的笔记本上写着一首诗: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
落款是:李白·《山中问答》林茵书于1978年3月14日。
很娟秀的钢笔字,是用湖蓝色的钢笔水写的。但萧长山看不太懂,尤其是那个“窅”字,被他念成了窖。萧长山认为桃花流水流到地窖里去是合乎情理的,水往低处流嘛。他小时候没念过书,参加工作后在夜校读的初中。
那个细脖儿白瓷花瓶,他没敢摆在办公桌上。因为它的造型看上去太女性化了,他怕招惹闲言碎语。只有在没人的时候他才会把它从更衣箱中取出来,打开层层的包裹,轻轻地抚摸着……恍惚间心中掠过一丝凄楚:自己出身清苦,注定和林茵这样精致的女人无缘的。
数年后,萧长山在农贸市场遇到了工会干事小黄。当年的小黄已经六十多岁了,一头秀发被岁月的风霜染成了黑白灰,花花搭搭的在风中飘摆。小黄告诉他,林茵死了,是不堪忍受骨癌的折磨跳楼自杀的,死的那年还不到四十岁,一个才华横溢的舞蹈家,可惜了……萧长山听了,胸腔骤然一痛,仿佛里边有根弦“咔吧”下就扯断了。
从市场回来的那天夜里,萧长山梦到了林茵。林茵站在白雪般的桃树下,神情忧郁地望着他,仍是那般梨花带雨,温柔可人……他想上前把她拥进怀里,林茵却向后退去,转眼间隐进了黑洞洞的铁门。萧长山追过去时发现已经无路,那扇门上爬满了葳蕤的青藤,似乎已经封闭了许多年……
萧长山夜半醒来,流了好一会儿的眼泪。
隔年秋天萧长山起夜时摔倒了。他的脑袋“咕咚”下磕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但他没觉得疼……
他被层层叠叠的影子包裹着,喘不过气来。他挣扎着想要出去透透气,这样想着,他就起来了。他来到桃树下看见师父胡老头在喝酒,老人家自斟自饮,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小地桌上摆着酒壶,酒盅;茶壶,茶碗,一碟花生米,一盘樱桃……萧长山小心翼翼地说:师父,林茵呢?
胡老头勃然变色,起身拂袖离去。
萧长山追过去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晦暗的天空下,浩浩荡荡的人群趟着河水,沉默地走向苍莽的远方。萧长山从背影中辨认出了师父,母亲,林茵……他想赶上他们,却怎么也迈不开脚步,他一急,就哭了起来。这时,天空落起了大片的雪花。雪花飘到河上,滚落成一片片粉红色的花瓣随波起舞,天地间瞬时弥漫起泌人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