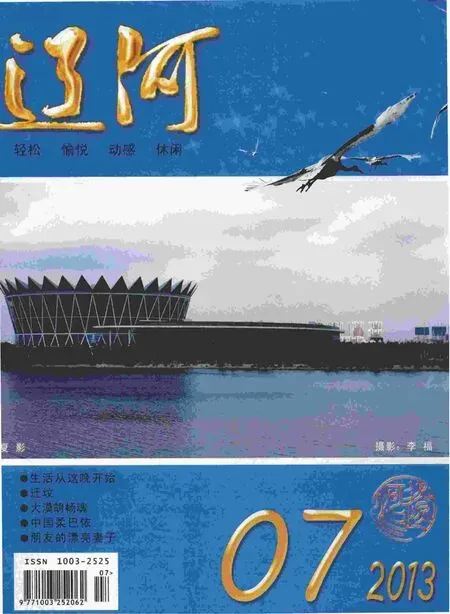朋友
胡发平
医院病床上躺着个女人,病房及走道来了好多人。
女人呼吸有点急促,医生替她插上氧气管。大家目不转睛盯着病人的变化,病人命若游丝,闭着眼睛。女人名叫织梦,病房及走道来看她的是工友。
冷月俯身告诉她大伙都来了,茶花下晚的飞机。织梦隐约听到了冷月的声音,嘴角抽动了一下,迷离之中想起一些事儿。
十五年前,民染厂改制的那晚,她和冷月、茶花像哭丧婆,困坐在她家沙发里,悲悲戚戚。她诅咒她们年纪轻轻偏偏撞在世纪之末,国事家事个人事奔袭而来,让人窒息。那时她们还不到30岁呀,说得这么轻巧,下岗就下岗。你说,俺们从农村到城里容易吗,被一脚踢入社会,算哪一辙?她眼泪簌簌落,一阵呜咽声,天上月亮像扯块遮羞布,也哭没了月光。
她在家歇了半年,天天买菜烧饭。公婆有了异样的目光,老公也似乎少了点以前的温情,她心里不是滋味。做点什么呢?她不相信这么大个城市就没个立身之地。
有一天,她无聊在城里闲逛,无意中见到月薪1000元的“蓝青蜒”招工广告。她在家憋气半年,像是饿牢里放出来的,见了这诱人的苹果,馋涎欲滴,心里顿时痒痒的,于是她走进了“蓝青蜒”。
之后,她在大厅当服务小姐,扫地,端茶,忙得腰酸背痛。她在民染厂时学会跳舞,一般三步四步都能应付。忙时,客人邀请她做伴舞,她也只好勉强上场。过后,客人便给她小费。她弄不清这些男人出手这么大方,基本上天天有小费进帐。她又惊又喜,于是把平时穿着的蓝黑长裙脱下,特意换上了淡青色带小花的素色短裙。
这可让老公急眼了,她每天深更半夜回家,他像警犬似的用鼻头在她身上嗅了嗅,闻她身上有无男人味,生怕别人种了他的自留地。她一上床便大睡。他开始不悦,久之便起了疑心。
有一晚,一位风度翩翩的老板,举止优雅地邀请她与他共舞。她一笑,起身携着他的手入池。舞至一半她明显感到老板有意无意地用力将她往身边揽,她懵懂只当无事儿。正当两个身体逐渐贴拢时,老公突然出现,抓个正着。她的脸热热的,像个做错事的小女孩,什么也回答不出来。
数月后,她离婚被踢出家门。夏天的夜是寂静而温暖的,这一切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天边仍旧呈现着白色,而且让落霞染上了一抹残红。这晚,她徘徊在世纪广场,走了一圈又一圈,又走到姐妹烧烤店,见冷月和茶花鼻头发酸,竟淌下委屈的泪水。她俩邀她入伙,她皮子贱,嗅不惯烧烤油烟味,而且那地方有一张张“伟人头” 的诱惑。
可是命运弄人,两年后她竟然染上了病。那天她站在二十三层楼顶,心想一跳了事,但她不甘心哪,房顶上是一片白茫茫的雪,铅灰色的天空,冷寂的空气,只有她脖子上的红围巾,在白雪的强烈映衬下,像一团火耀眼夺目。她闭眼蝴蝶般飘了下去,飘到了姐妹中间。
这次,她不是来嗅烧烤油烟味。她说,把门牌换了,改成姐妹服装店。冷月和茶花懂得她的心思,便随了她的意。不几年生意红火起来,门牌几经翻换,最后变成了丝织有限公司。
人手不够,她惦记着工友,就一个一个的找回来,工友重新有了一个小小的家。她说,家小不算什么,照样什么都能装下,过去、现在和未来。
织梦回忆到这儿,迷迷糊糊的,她累了也想睡了。
很晚,茶花推开病房。织梦捏着茶花的手,仿佛是在检索这十几年来姐妹间的情意。她似乎很满足,她眼睛睁了一条缝儿,扫描着一张张熟识的脸。
冷月不失时机地说,你瞧,茶花又签订了几宗大单。织梦的情绪出现了反常,她用舌尖艰难地顶出“满好”两字。之后,她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微笑,走了。
第二天,公墓里添了新坟,墓碑上刻有一行字:永远的朋友。落款:工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