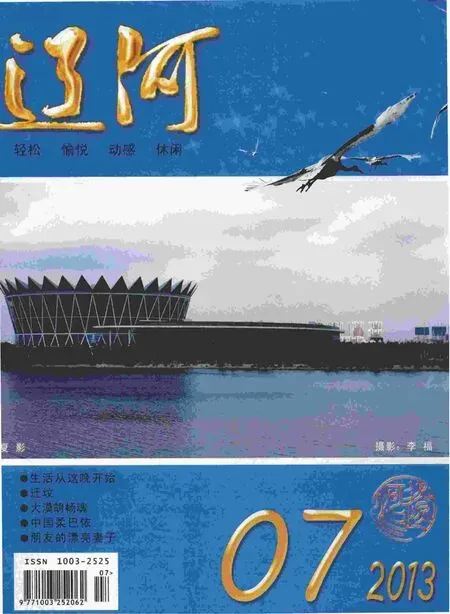大漠胡杨魂(外一篇)
王宝文
中巴车在浩瀚高远的戈壁滩奔驰,映入眼帘的是望不到边际的深褐、暗红、灰黄的色彩。在穿越戈壁大漠的途中,猛见有一片浅绿,那就是我期盼见到的胡杨。
三十年前,岳父从酒泉某试验基地转业到地方工作。他回来时,没带西北的任何特有稀品,只带回一包由他亲手采集的胡杨树种。在我认识岳父后,他为我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胡杨。说他们刚刚进入戈壁大漠,生活条件很艰苦,给养不足没有吃的,他们只好到一片千年的胡杨林中,去围打成群的羚羊和野马,以解决在大漠里的生存问题。这样的传奇故事并没有打动我,倒是那片神秘的胡杨林让我牵挂。它是什么样子?在戈壁荒漠中,它们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后来,岳父又给我讲,在风沙干渴中,胡杨有三千年之说,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烂。这就更加重了我对胡杨的好奇心和神秘感,期冀有一天能亲眼看看心中的那片胡杨林。
这次出行西北采风,将了却沉积在我心底多年的心愿。百里空旷的大戈壁上,在一片浑黄起伏的沙丘之中,突兀出现了一片胡杨林,显得伟大而孤独,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敬畏。远远望去,整个林海黄绿相间,黄的是大片盐碱滩和大自然过早地给胡杨的树干、枝叶带来的秋色,绿的是那秋风还未来得及剥去的稀疏的胡杨叶。我走近胡杨林,细细地观察着每一棵胡杨,他们高矮不一,相互簇拥地生长,棵棵都长得铁干虬枝,粗壮有力,就连每一个细小的枝杈都显得刚劲而凛然。那枝干的树皮纵裂,呈灰白或灰褐色,树冠阔圆如伞,叶子呈灰绿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示着荒原上独有的明艳与旺盛。走进胡杨林深处,我立刻徒生一种肃穆,一棵棵胡杨那巨大的、苍迈的、奇形怪状的形态,仿佛有了灵性。它们有的像龙蛇盘踞,有的像鹰鹤独立,有的像骏马惊立……也有许多站着、躺着干枯的胡杨树干,有的被雷劈过,有的被野火烧过……还有的树看下边是枯死的,断裂出错落有致,抬起头来没被风砍去的边缘部位却奇妙地生长出一截完整的树梢,那树梢的茂盛让人总觉得是一种幻景。稍显完整一些的胡杨树可能左边伸出的是枯枝,右边伸出的却是盎然的绿枝。那些或粗或细的枯枝举着自己或半掩埋在沙土中的姿态,实在是形神兼备。即便是枯死了也像活着,也许是茫茫沙漠对此映衬出的生机吧!它们神兮兮的,鬼森森的,还透着些人气。我把伸出去想折一截枯枝的手又缩了回来,我担心,只要触到那枯枝,它们就会发出尖叫或呻吟,面对这些干枯的胡杨,我的心像被利器尖锐地划过,它们是沙漠的语言!生生死死都在诉说着亿万年的变迁,亿万年的人类历史。它们生长着,繁茂着,遥望苍穹,吞阻洪荒,主宰着整个戈壁,统治着这里的一切生灵。怪不得资料中介绍说:胡杨一生甘居沙漠,凛然地阻挡风沙,抵御寒风,保卫绿洲,维护西部地区的生态。其实细想起来,胡杨的奉献何止是“一生”啊?它的生命经历岁月这么悠久,足见它的根系扎得多么深,躯体和筋骨有多么坚硬。即使生命止息了,倒下了,它生命更多的部分仍然延伸在大地的深层。啊!胡杨,这茫茫大漠造就的生命,浩浩沙风雕镂的塑像,给我提供了宽泛无际的想象。
我站在一棵巨大的胡杨树前,它那拧曲如虬的枝干,倔强地直指苍穹,苍黄、龟裂的树皮热烈地向外张扬着。我用手摩挲着这龟裂的树皮,我触到了洪荒干旱留下的创伤,我摸到了雨雪风霜劈下的刀痕。在这悠远与深邃中,有一股热流从我的手掌传到胸中,在心头涌动着,翻滚着。哦,胡杨的树根植于土地的深处,那里有一种顽强、热烈的原生力正在向地底下延伸,那是一种所有树根的凝聚力,紧紧地拥抱着脚下这片热土。
我取下随身带的矿泉水,向树根倾洒下所有的水,我要让自己的甘露和我的整个心都顺着千年胡杨的树根浸入这西北大地,和所有的胡杨连成一片。
啊!胡杨,你承受了过多的苦难,负载了过多的沉寂,在荒凉的大漠中,兀立起铮铮傲骨,为自己树起了一座丰碑。
小村古地
这里是一片平地,就在燕山余脉的角山脚下,距山海关古城西北六公里。
这里原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踞兵攻打山海关城安营的兵寨。
且行且看,这里没有一座城,也没有一个楼台,真真实实的是坦荡平地的美丽农村田园,真真实实的是一代兵魂呈现绿色生命的地方。在这里要找古战场残留的遗痕是不容易的。历史,变化得很快很惊人!昨天还有人在这里趾高气扬地称帝称威,穷极武勇,今天竟夷为平地,一片寂静,只有庄稼茂盛地长着,只有有情人或可从那摇曳的田禾野草中寻找到历史悲剧的辛酸、无情……用武之地,竟消失得这般快……
然而,在这块土地上真真切切地记载着改写中国历史的史实。即使隔了三百六十余年的历史烟尘,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的生命光芒依然能穿透文字的覆盖,明亮我们的视野。
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农民起义军在闯王李自成的率领下,一举攻陷北京城,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政权。可李自成却无治理天下之能,入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追赃助饷,剥夺高官显宦们的家财,实属狭隘的小农之举。即使对有降顺的关宁总兵吴三桂的家人也不放过,昔日巨富的吴府被搜刮得空空荡荡,就连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掠为李自成麾下“权将军”刘忠敏的人了。
当血气方刚的吴三桂听到从京城逃亡的家人诉说,深感遭到了奇耻大辱,猛然拔出腰间佩剑,将面前的桌案劈成两半,大声喝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
冲冠一怒的吴三桂登上城楼,看到团团围困着山海关的李自成的大顺军,仰天长叹,他紧握着拳头走下城楼跨上马,调转马头向山海关城东的威远城驰去。在那个小小的城池里,他跪在了昔日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清摄政王多尔衮的面前,剃发改服称臣,乞求清军出兵为他报仇雪耻。从此吴三桂永远地背负了历史的重债,成了所谓的“民族的罪人”。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亲率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兵临山海关城下,在城外的石河滩上展开了攻城态势,而老谋深算的多尔衮早已掌握了大顺军的动向。可他为了保存八旗兵的实力,命令吴三桂为先锋冲击敌阵。吴三桂只能从命,就像狗一样地去卖命了。
彭孙贻在《平寇志》中这样描述道:三桂悉锐鏖战,无不以一当百。自成益驱群贼连营进,大呼,伐鼓震百里。三桂左右奋击,杀贼数千。贼多数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贼众(三桂)兵寡,三面围之。自成挟太子登庙岗观战,关宁兵东西驰突,贼以其旗左萦右拂之,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就在这时,多尔衮指挥满清骑兵绕过角山,从大顺军的侧翼发动突然袭击,杀得天昏地暗。大顺军猝不及防,造成了全线大溃退,伤亡惨重。从此一蹶不振,相继退出北京和西安,大顺军残部被追逼得无有藏身之处,后来李自成被困死在湖北九宫山。而清军在吴三桂的引导下,由山海关长驱直入,征服了中原,建立了统一的满清王朝。吴三桂也因献关有功,坐上了平西王的宝座。诗人吴伟业讥讽他是“痛苦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山海关人为纪念这一史实,将李闯王立马观战的山岗称将军台,把他安营退兵的地方叫做——回马寨。
安营攻城、回马退兵——已是遥远的事了,只有破碎的,迷离的梦还留着。而今这裸露着黄色胴体的土地,在和谐风里展现着销魂的新倩姿,那巍峨凝立的燕山山峰,宛如一尊威武的战神,已抖落了血染的战袍,在万山苍翠中显出了和谐宁静的青春气势。没有凄凉,没有忧思,没有荒唐,仅有的是缓缓流淌的石河,仅寻见的是残破的烽火台,只是那时恪守自己命运的沉思。
在这平坦的土地上,古老而神奇的陈述是默默无声的,悲鸣在这里消失了,骄傲也在这里消失了,那时的怅惘只是历史的画面。当然,谁又能不怀思于自己故土的历史呢?从这个意义上,那时捐躯沙场的鬼雄,虽已湮没于荒丘和燕山峡谷的萋萋芳草中,也还可从中山王徐达图置的护城卫队,从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精锐戚家军,从关宁总兵吴三桂的铁骑精兵,看出那古边关的悲怆神情,窥见古人的清泪和温馨的梦。这犹自说明,昨天痛苦,昨天屈辱,昨天的鲁莽的厮杀和士兵的肉墙,终没挽回非正义的湮没和持正义的昌盛之命运,倒是被称为鞑靼的女真人大力倡导民族大融合,实施通婚和亲,减免征税等——在这里辟为一个和谐的村寨,倒是这沉默的燕山山峡,春风中的沃土田禾犹在给历史旁白,犹在给现实解释。
这里,山的平衡,水的平衡,人心中爱的平衡已从历史反思中得到兴亡的诠释。这里,边塞的古战场——回马寨,已满目是新时代的和谐美好的烂漫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