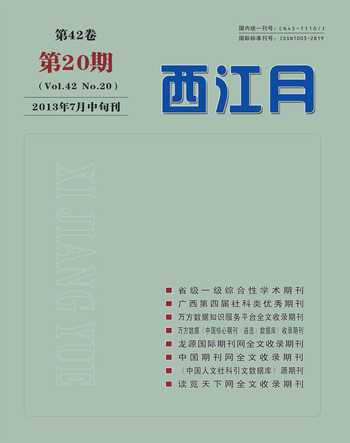林文铮与1928年《中央日报》副刊
畅洁
【摘要】林文铮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恶之花》,这举动有悖于《中央日报》是为国民党和民国政府代言的创刊宗旨。究其根源,首先是由于当时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其次,这一时期上海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出版业的发达和大批文人的聚集使得上海有着较为自由的出版环境;最后,林文铮的法国留学经历和他提出的“亚波罗”精神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林文铮;《中央日报》;波德莱尔;《恶之花》
从目前对《中央日报》副刊的研究现状来看,研究者们大部分都着重于1929年《中央日报》迁至南京后,对这之前的副刊鲜有关注者。这使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央日报》副刊难以全面和客观。笔者通过对1928年《中央日报》副刊整理,发现这一时期的《中央日报》副刊可谓“百花齐放”,各种文艺思想、艺术观念、文学思潮都出现在了这短短的九个月的副刊中,完全颠覆了之前对于受执政党控制的中央机关报副刊的认识。而其中林文铮译述的法国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一、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
何应钦在1928年2月1日《中央日报》发刊词中强调“本报为代表本党之言论机关,一切言论,自以本党之主义政策为依归,不致有倚轻倚重之避……”[1],并说明出版《中央日报》的用意“当此思想繁复,见解分歧之际,中央日报,忽于今日出版,从此党国宣传,有此寄托,我人言论,有所取则,其愉快为何如,惟我人鉴於往昔之历史,应认识宣传之重要,及本党因乏宣传所遭之损失,对此苦心孤诣诞育之中央日报应具无穷之爱护和希望……”。[1] (p2)由此可见,《中央日报》的任务是为国民党及其政府代言,其总体上自然代表了这个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由于各地方势力还没有完全消除,当局又忙于消除敌对势力和巩固自己的势力,无暇顾及其他,特别是在文化控制上,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状态,这给《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者和投稿者提供了相当宽松的创作环境。
二、自由的出版环境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是随着政权的交替,旧的思想道德与礼仪制度迅速地崩溃,另一方面是随着开埠,在各个领域都受到变革如潮的世界经济、思想、文化的猛烈冲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社会的动荡不安果然是不幸的,但新旧交替之际却为他们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实践、时尚和实验在不受官方限制的情况下争奇斗艳创造了条件。”[2]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作为当时执政党的国民党,在1928年将其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从汉口迁移到了上海,由于1926年奉系军阀进京,政治迫害发展为屠杀,迫使激进的新文学家们纷纷南下,来到上海,例如1926年较早来到上海的鲁迅,以及随后南下的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沈从文、丁玲等“五四”运动精英;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革命转入低潮,许多曾经身处现实政治斗争第一线的文人也只好选择从北伐前线退回上海,如郭沫若、沈雁冰、蒋光慈、阿英等;与此同时,还有从国外留学回国的那一批知识精英,如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夏衍、冯乃超、刘呐鸥等。而在这众多文化精英中,有不少都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者或主要撰稿人。例如:作为《摩登》的主编者田汉发表了戏剧《黄花岗》和很多诗歌,沈从文发表了《爹爹》、《卒伍》等作品;《艺术运动》主编者之一的林文铮发表了译述作品《恶之花》;《红与黑》的主编者胡也频,发表了大量他的诗歌作品,丁玲的《素描》、《潜来了客的月夜》等,徐霞村的译述作品。
“报纸和杂志是和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同步发生和发展的,报纸和杂志在政府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言论空间和社会有机体”。[3]这时的上海具有其他城市所无法企及的期刊杂志和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这不但为文人活动和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性,还为文人创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而上海作为全国最具开放性的城市之一,它还能最先、更好地接受新东西和外来思潮,是我国与西方文化接触交流的前沿阵地。
三、“亚波罗”精神的指导
林文铮对艺术方面的批评和艺术思想应该也会对他选择译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产生一定的作用。
回国后的林文铮,看到国内艺坛死气沉沉,而国内大众对于艺术概念的认识又非常狭隘,“我们东方人向来一提起艺术这个名词,在那充满了五千年成见的脑海里,之浮起丹青两个字而已。在人人的心目中,除了渲染以外,简直没有他样艺术存在了。”[4]他希望改变这种现状,于是提出了“亚波罗精神”:“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三千年来精神界完全受两大思潮之支配:一为希伯来精神(Hebreisme),一为希腊精神(Hellenisme),前者是来世主义。后者是现世主义……现世主义是坚认实现生活之价值及自我之存在。前者的立脚点在神人(Dieu-homme),后者的立脚点在人神(Homme-Dieu),前者可以耶稣为代表,后者可以亚波罗为代表。”[5]这种精神和改变在艺术上的体现是多方面的,不单单是绘画、建筑、音乐、雕刻,想要人们的认识和思想发生改变,最直接的就是文学作品,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不论是在法国发表,还是被译述到其他国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波德莱尔于1857年发表了他的伟大作品,诗集《恶之花》。这本书把法国文坛搅个底朝天,而且深深地震撼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对于许多人来说,似乎撒旦的一个精明强悍的使者从地狱的深渊出现了。”[6]林文铮希望利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能改变、颠覆当时国内大众对于艺术的认识和理解。
对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他是这样评价的:“大家都知道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所谓新时代精神(Esprit moderne)是发轫於一部‘恶之华诗集。甚且六十年来西方的诗坛仍然是渲染着这部杰作之余润!……恶之华集是公认为冷酷的绝望之一片呼啸呻吟,波氏毕生之苦痛,冤屈,欢乐,失望,烦恼,悲哀已结晶於这部不朽的杰作……”[3](p23)他认为波德莱尔的内心“纯是耶教内心的冲突,灵肉的冲突——他同时以其无私冷酷的慧眼观察他的心战,以其坚强的理智批评他的内讧!”并且“按法国文学家普尔札对于恶之花的爱情观念略分三要素:‘神秘,放荡,尤好分析一切。而波德莱因为对于自身过于搜罗探讨,逐激醒内心中沉睡的青年,甚至於令他呼号流血。这个青年就是他内心中从未污损的天真,爱与求爱,献身与求生之本性。”[3](p34)对于波德莱尔的情人与其诗歌的关系,林文铮认为“波德莱之情歌已如火焰清涤他一切庸俗的恋史而且光大之,因为他所恋爱过的女子其实没有一个是配得上他的。但是他把他的情人全数化为神女诗娥了;在她们怀抱中他只恋爱他的好梦和幻想;这种幻梦逐酿成他的不灭的真实:他的诗歌是也。”[3](p98)所以“要了解百年来所谓世纪病,要洞悉近代心理之复杂神秘,波氏的情感生活及其杰作‘恶之花是绝妙的研究资料。”[3](p65)
【参考文献】
[1]中央日报(1928)[N].上海: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影印本).
[2]林风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D].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4]杭州市[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1).
[3]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4]林文铮.莫忘了雕刻和艺术[J].国立艺术院半月刊,1928(4).
[5]林文铮.从亚波罗的神话谈到艺术的意义[J].国立艺术院半月刊,1928(1).
[6](法)戈蒂耶(Gautier.T)著,陈圣生译.回忆波德莱尔[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