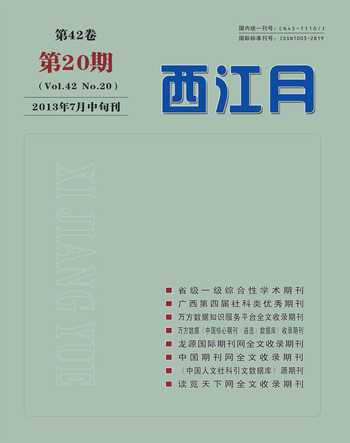《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研究
郑宇

【摘要】《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共二十卷,是南宋薛尚功所著,该书以吕大临的《考古图》和王黼的《宣和博古图》为基础,广泛辑录并依样摹写了钟鼎原器款识,附以释文和考说,是南宋金文著录流传至今的重要著作,也是宋代金石书中铜器铭文资料最丰富的一部。本文将对该书的作者、版本、内容、价值等进行介绍,并与今人王辉编著的《商周金文》的体例、内容进行对比,探讨现代的铭文辑录著作对前代著作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薛尚功;《商周金文》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也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共二十卷,是南宋薛尚功所著。该书以吕大临的《考古图》和王黼的《宣和博古图》为基础,广泛辑录并依样摹写了钟鼎原器款识,附以释文和考说,是南宋金文著录流传至今的重要著作,也是宋代金石书中铜器铭文资料最丰富的一部。本文将对该书的作者、版本、内容、价值等进行介绍,并与今人王辉编著的《商周金文》的体例、内容进行对比,探讨现代的铭文辑录著作对前代著作的继承与发展。
一、作者生平及成书背景
薛尚功,字用敏,钱塘人。南宋绍兴年间为通直郎,后官至佥书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薛尚功精通篆文和籀文,尤其喜好钟鼎书,著有《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另有已佚的《重广钟鼎篆韵》7卷。
作为专门之学,金石之学滥觞于宋代,最早从事古铜器研究的是刘敞和欧阳修,刘敞著有《先秦古器记》一卷,欧阳修著有《集古录跋尾》十卷,对铜器的形制和铭文开始加以考释。此外,吕大临著有《考古图》十卷,李公麟著有《古器图》一卷,王楚著有《钟鼎篆韵》二卷,王黼等著有《宣和博古图》三十卷,黄伯思著有《东观余论》二卷,董逌著有《广川书跋》十卷;赵明诚著有《金石录》三十卷,王厚之著有《钟鼎款识》一卷,王俅著有《啸堂集古录》二卷,张抡著有《绍兴内府鼓起评》二卷。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就是在金石之学盛极一时的背景下形成的。在这些著述中,董逌、赵明诚等所著只有名目,不存图谱;吕大临、王黼等所著则既图形制,又摹写铭文。薛尚功则但以录文为主,不图原器形制,这也开了后世金文著作的通例。
二、《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版本、内容、体例及价值
所谓“钟鼎”,即钟和鼎,上面多铭刻记事表功的文字,《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中就说:“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铭於钟鼎,又图形於丹青。”《左传·襄公十九年》中有:“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杜预注:“彝,常也。谓钟鼎为宗庙之常器。”所谓“彝器”,又叫“尊彝”,是对古铜器中礼器的通称,钟、鼎、樽、罍等都属于彝器;所以,钟鼎彝器就是指钟、鼎等古铜器中的礼器。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古铜器》中说:“所谓款识,乃分二义:款,谓阴字,是凹入者,刻画成之;识,谓阳字,是挺出者。”“款”、“识”二字析言则异,浑言不别,二字同义连用,“款识”即是古代铜器上铸刻的文字,后也指书画上的题名。因此,从书名来看,《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是对当时出土的前代古铜器上所刻写的文字的摹写。所谓“法帖”,写在纸或丝织品上的、篇幅较小的文字都叫帖;宋代有人汇集历代名家书法墨迹并将其镌刻在石或木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卷或册的刻帖,这种刻帖是学习书法的范本,所以又叫法帖,也是使前人书法得以流传的重要媒介之一。曾宏父的《石刻铺叙》中曾介绍,《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薛尚功官定江军之时,在郡守林师说的帮助下镌刻的,当初是石刻本,所以也称“法帖”。
根据《<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研究》一文的介绍,该文作者张唯在上海图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图书馆查阅了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流传至今的版本情况,认为该书流传至今有三个系统,即宋拓本残本、明清木刻本、明清抄本。自宋元以来,一直有两大系统,即宋石拓本及其抄本、刻本,薛尚功手写本及其刻本、抄本。其中,宋石拓本在流传过程中极为罕见,能够流传至今的仅剩19叶残片;薛尚功手写本曾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流传过,但是在清中期后亡佚。在当今传世的刻本中,明代朱谋里刻本、清代阮元刻本和民国古书流通处本流传最为广泛。辽沈书社1985年版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以古书流通处本为底本影印;中华书局1986年版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以于氏影印朱刻本为底本影印,文后附录容庚《<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述评》,这是目前最为便利的两个版本。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以吕大临的《考古图》和王黼的《宣和博古图》为基础,广泛辑录并依样摹写了钟鼎原器款识,附以释文和考说,是南宋金文著录流传至今的重要著作,也是宋代金石书中铜器铭文资料最丰富的一部。该书共收录器物铭文511件,其中包括夏器二,商器二百零九,周器二百五十三,秦器五,汉器四十二。
在内容编排上,该书首先分夏、商、周、秦、汉五代,各代之下又依据铜器的类别排列。卷一有夏代的戈、钩带和商代的钟、鼎共46器,卷二有商代的尊、彝43器,卷三有商代的卣34器,卷四收商代的壶、罍、爵44器,卷五收商代的觚、举、觯、敦、献、鬲、盉、匜、槃、戈44器,卷六、卷七、卷八收周代的钟、磬38器,卷九、卷十收周代的鼎57器,卷十一有周代的尊、卣、壶、舟22器,卷十二收周代的觯、角、彝、匜33器,卷十三和卷十四收周代的敦39器,卷十五收周代的薰、簋、豆、盉22器,卷十六收周代的献、鬲、槃、盂、盦29器,卷十七收周代的戈、铎、鼓、琥13器,卷十八有秦代的玺、权、斤和汉代的钟、甬、钫、鼎18器,卷十九有汉代的鑪、壶、巵、律管、洗、钲、匜14器,卷二十有汉代的鐙、锭、烛槃、献、釜、甑、鋗、弩机15器。
在著述体例上,薛尚功以摹写铭文为主,每篇铭文都加上释文并对铭文中提及的人和事都加以考证,还对器物的年代进行的断定,《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较早的专录并考释铭文的书,开创了后世铭文著录和考释类金石学著作的体例。同时,薛尚功比较重视铭文本身,是较早对铭文进行逐篇研究的人,他采用对照法、偏旁分析法等较为科学的方法对铭文进行考释。如卷一·公非鼎:“按:《史记》有公刘五世孙公非者,考其时正与祖甲相近,则作此鼎者当为公非矣。”,这是与《史记》对照的例子;又如卷一·癸鼎:“右按:《说文》癸之字具四屮,而此鼎之癸则一屮三包,盖癸与丑相次。”卷九·鲁公鼎:“按:鹵字,许氏《说文》云:‘从西省,象鹽形,即鲁字也。”这是与《说文解字》对照的例子;再如卷十二·双弓角:“右铭中作双弓者,弜字也。《玉篇》音渠良切,疆也。作器者之名也。”,这是与《玉篇》对照的例子。
后世对《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其版本的考订,二是对其所录器物铭文的重新考释、对器物年代的考订和伪器的判别等。《四库总目》中对薛尚功此书的评价是“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箱之学,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伪刊误之功,非钞撮蹈袭者比也。”可见一斑。《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收的器物现在大多已经不传于世了,该书虽经过传抄翻刻后会有谬误,但仍保留了当时出土古文字材料的原貌,为当代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可供参考的史料。当然,由于当时金石学尚在草创阶段,薛尚功在书中对器物铭文和器物年代的考订有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四库总目》也说:“其中如十六卷中载《比干墓铜盘铭》之类,未免真伪杂糅,然大致可称博洽。”
三、与《商周金文》的对比
《商周金文》是王辉所著,全书包括凡例、金文及其研究、金文释读、附录和后记。《金文及其研究》叙述了金文的主要内容及其研究概况;正文选取了68篇有代表性的铭文加以注释,上起商末,下迄春秋,其中包括商末4篇,周代57篇,春秋早期7篇。在编排上,正文以时间为序,商及西周以王年为序,春秋只选诸侯国器,以纪年为序。与之相比,《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共收录器物铭文511件,包括夏器2、商器209、周器259、秦器5、汉器42;在编排上也是以时间为序,先分夏、商、周、秦、汉五代排列,各代之下又依铜器的类别排列。两相比较,在收录的器物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广泛且以商周时代的器物居多,《商周金文》则在广泛的铭文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且以西周为主;在编排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以朝代为序并依器物类别排列,《商周金文》继承了以时间为序的排列方法,且因为断代比宋代更为精确,故而能以王年为序排列。
《商周金文》的正文每篇分小引、著录、释文、注释、断代等项。以《利簋》一篇为例,“1976年陕西临潼县零口乡西段村青铜器窖藏出土,现藏国家博物馆。4行32字。”是小引,说明了利簋的出土情况、收藏情况和字数,部分小引还会说明青铜器的别名。“《文物》1977年8期《集成》8·4131”是著录,著录只选择常见书或最早的著录书,不求其全。“珷征商,隹(唯)甲子朝……用乍(作)旜公宝尊彝。”是释文,是对青铜器铭文的转写,铭文多为拓本,个别附摹本。注释中的疑难词语一般采用一家之言,部分列举几种不同说法,如对“岁鼎(贞)克闻,夙又(有)商。”的注释,先对岁、鼎、岁贞、克、闻、夙分别作了解释并引古书或甲骨文字体为证,然后说“此句极难理解,除以上解释外,还有多种不同解释”,并附上唐兰等人的三种不同理解。断代则依据铭文、史书等断定,并辑录了学术界的其他不同说法。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正文右上角为器物名,铭文多为摹写,铭文之下有释文,释文只转写了部分铭文;铭文左边是考释。薛尚功但以录文为主,不图原器形制,开了后世金文著作的通例;同时,他还是较早对铭文进行逐一考释的人。如卷一·庚鼎:“右按:李氏《古器录》云:‘《说文》庚位西方,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此庚乃有垂实之象。许慎记古语虽著其义,今商器多象其形,信汉儒著书自有原本,由科斗法行意,渐与古书相失,况隶话至今,但点画而已,无复本初之意也。”薛尚功不仅考释了铭文的含义,还指出,古文字的字形与本义是相互关联的,而隶变之后简化的文字则逐渐丧失了揭示造字本意的功能。再如卷一·子鼎一、二:“右二铭同,而后一鼎作立戈形,盖子为父作鼎,以铭其有武功耳。”卷一·父甲鼎:“铭曰:‘子父甲。盖子为父甲作此鼎,以追享其父也。故加父於上,以显尊神之意。子字或作立戈,或作横戈,皆所以铭武功耳。”卷二·辛未父癸鼎:“右铭亦子为父癸作宝尊彝,后一字未详,必作器者之名耳。”薛尚功考释铭文的同时还考释了铜器名称的来由。立戈形和横戈形的“子”在书中出现很多次,而据辽沈书社1985版《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序说,《宣和博古图》对父甲鼎的铭文是解释为“立戈父甲”的,薛尚功虽以《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为基础写成此书,却不拘泥于陈说,所以有刊误之功。但《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收录的器物铭文中有许多是只有一两字的,如商鼎中的庚鼎、辛鼎、癸鼎以及商尊中的象尊、父丁尊等。
由以上对比可知,《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开了录文而不图器物形制的先河,也是较早对器物的出土情况、收藏情况以及铭文进行逐一考释的书。《商周金文》继承了《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录文传统和考释传统,但是,在录文方面,《商周金文》采用的是拓本,可以更好地让读者看到器物铭文的原型,比摹写的方式更进一步;在选取器物铭文方面,《商周金文》采用精选的方式,而不是《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的广泛辑录;在考释方面,《商周金文》对铭文的注释更为全面,断代更为精细,因此在铭文的排序上能以王年为序,而不是仅以朝代和器物类型为序。
此外,《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卷一收录了《虎父丁鼎》,铭文是“右鼎铭亚形中著虎象,凡如此者皆为亚室。而亚室者,庙室也。庙之有室,如左氏所谓‘宗祏,而杜预以为宗庙中藏主石室者是也。父丁者,商君之号也。”《左传·庄公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杜预注:“宗祏,宗庙中藏主石室。”“宗祏”就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室,借指宗庙、宗祠,引申可指朝廷、国家。在铜器铭文的研究中,薛尚功是较早注意到亚字形铭文所蕴含的王室宗庙祭祀含义的,后世学者研究时也常引用这段铭文。
图一是虎父丁鼎的铭文,薛尚功的考释是“亚形中虎父丁”。图二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四祀 其卣的铭文,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四祀 其卣又称亚貘卣,器外底有铭文8行42字,盖、器内底各4字,图二就是盖和器内底的铭文。《商周金文》中,图二的铭文为“亚貘父丁”,亚貘是国族名,父丁则是 其之父,是祭祀的对象,丁为其日名,表示在此日祭祀,用日名也是商人的礼俗;在该器的断代上,王辉认为,从器外底的铭文和于省吾的考证来看,此器当为商器。图一和图二都是商代器物上的铭文,时代相同,铭文形状相似,但虎父丁鼎中的“亚形中虎”是否也应考释为“亚貘”还有待考证,此处仅备一说。
【参考文献】
[1][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第1版)[M].辽沈书社,1985(7).
[2][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第1版)[M].中华书局,1986(5).
[3]张唯.《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7(03).
[4]马晓风.简论薛尚功的金石学研究[J].华夏考古,2012(01).
[5]王辉.商周金文(第1版)[M].文物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