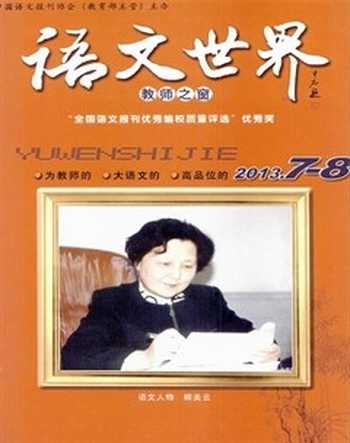积极语用教育观与小学语文教学
潘涌 罗丹红
罗丹红(浙江省绍兴县教研中心教研员,以下简称“罗”):潘教授,2009年前后,您提出了“积极语用”这一语文教育新主张。它一提出就引起了语文教育界的关注,目前已经产生比较广泛的影响。大家知道,一种教育主张的提出一定有它的基本背景。潘教授,您为什么会在2009年前后这个时期提出“积极语用”这一语文教育新主张?
潘涌(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以下简称“潘”):就理论背景而言,积极语用教育观既来自国外语用学又超越之。1977年,荷兰出版《语用学学刊》(Journal of Pragmatics),标志着语用学学科诞生。亦可译为“言语施行论”,主要研究言语行为。语用学是对语言学的新发展,构成言语教学论的理论基础。语用学早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译介到大陆英语教育界,在英语教育界比较流行,在汉语文教育界较少提及,更没有展开本土化的系统研究。语用是言语行为,语用学是结合一定的语境而对言语行为的意图、意义和交际价值所作的动态研究,语境、背景、话题、交际方、话语是其基本要素。我不是简单照搬国外语用学的理论。“积极语用”与国外语用学的区别是:从侧重口语交际行为扩展到综合、立体的“全语用”,以及“自觉语用”“深度语用”等。
就时代背景而言,积极语用教育观的提出是基于对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思政中心论”“语言工具论”“语识中心论”和“语感中心论”等汉语文教育思潮的批判性反思。在汉语文教育实践中,长期以来趋同化输入、共性化输出的基本范式并未得到根本改变,表征为青少年汉语思辨、运用、创造诸能力全面弱化的母语教育的危机,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公共问题”。
积极语用教育观又是在前瞻文化强国的时代发展远景中酝酿而成的。除了有所参考国外语用学外,其理论基础还来自积极心理学、超越论教育学、“表现性目标”课程论以及时间美学等。
罗:就是说,积极语用教育观不是照搬国外的主张,而是中国化了的。那它一般包括哪几个方面的要素?
潘:一般言语行为的表达效果是由三个要素的乘积所形成,就是:言语动机、言语情感、言语能力。言语行为的表达力是由这三个要素的乘积构成而不是它们的机械累加或堆积。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语用方程式:
语用行为=语用动机(0~100)×语用感情(0~100)×语用能力(0~100)
这个语用行为方程式,简洁地说明了从消极语用到积极语用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言语区间,语用主体的动机、情感和语用能力三要素之乘积决定了语用行为的效果。所谓积极语用,是表达主体基于独立人格和自由思维而以个性言说、独立评论和审美表达等为形式特征,因而富于创造活力的主动完整的表现性言语行为。积极语用包含“自觉语用”“全语用”和“深度语用”三个相对独立、有机融合的子概念。
罗:潘教授,您是说,积极语用包括“自觉语用”“全语用”和“深度语用”这三个层面,那这三个层面又有怎样的特点呢?
潘:“自觉语用”是指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受动机支配的,动机驱使着人的言语行为。“自觉语用”对我们语文教师的启示,就是要积极唤醒学生的表达意识,使之能够拥抱母语、享受母语,满足用母语表达自己深思真情的那种愉悦感和成就感。“全语用”是指人的言语行为是一种完整、立体式的言语行为,包括两个层面即“内语用”与“外语用”“输入型语用”与“输出型语用”。“深度语用”就是指言语行为达到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即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之间高度吻合,是思想品质和审美品质两者之间的深度融合,也就是孔子所谓“文质彬彬”。“文”就是言语形式,“质”就是言语内容。当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两者融为一体,就达到了言语行为的极致。
罗:潘教授,听了您的解释,我们渐渐明白了“自觉语用”“全语用”“深度语用”的特点。但是,“积极语用教育观”与传统意义上的“听说读写观”有什么不一样?
潘:第一,“听说读写观”缺少对学生思想能力的必要重视,将语用行为仅仅视为一种外部感官的言语行为。如果片面注重“听说读写”,只能陷入一种技术主义教育的泥淖,是忽视生命主体思维和情意元素的技术主义的狭隘思路。而言语行为从来不是人的感官的简单技术行为,更是一种智慧生命的心灵闪光,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思想和情感能量的释放。所以,传统“听说读写”云云,就是忽视了对学生内在思想力的重视和培养。
第二,将“听说读写”四种能力并置,将输入型语用与输出型语用看作是同等关系,就是忽视了表达力的目标指向,这是片面的误导。久之,必然致使语文课程形态主要以阅读课为主,写作课成为阅读教学的附庸,而口语交际教学则完全缺失。这样一种汉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狭隘格局陷入了接受型、偏废了输出型,最严重的是不自觉地放弃了对基于阅读和倾听的表达能力的培养。输入型语用固然重要,但它无非是为输出型语用作必要的积淀,只有经过长期的语用实践转化为更重要的表达力时,输入型语用才对智慧生命具有意义。否则,人就降格为留声机、电脑软件一类的工具了。“说”和“写”是指向,是语用行为的目的,“听”和“读”是其基础和条件。古往今来,唯有语言的表达力才是实现主体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最后达成人自身价值的最主要能力。
在“听、读、视、思、说、写、评”七字语用能力体系中,外语用包括“听、读、视、说、写、评”,其中的“视”即“读图能力”,看视频能力;而内语用即指“思”。外语用中的“评”很重要,汉语文教育最缺少的是培养学生对外在事物的独立评判能力,尤其是深刻、缜密、严谨的独立评判能力。以前讲“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其实是蒙学教育的一种混沌读书法,这样的混沌读书法,其实湮没了中国历代的思想者,数千年来都出不了善于建构思想体系、撰写体大虑周宏伟作品的思辨性人才。
罗:原来我们往往提到的是“听说读写”这四个方面,潘教授,您又加上了“思”“视”和“评”,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潘:刚才已经提到,语用有内语用和外语用之分。就内语用而言就是“思”。而外部的语用是通过人体感官来实现的,因而输入性语用除了“读、听”外,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无疑需要加入一种“看视频”的能力或曰“读图”的能力,简称为“视”。全球化时代,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图像占据了我们阅读量很高的比例。我们通过“读图”来接受大量信息并在去芜存菁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因此,“视”的能力是全球化时代对每一个现代公民的特殊要求。
在输出型语用能力方面,我特别强调一个“评”字。除了“说、写”,这个“评”尤其显示突出的地位。在中国,在汉语文教育中,大部分的“说、写”能力并不是“评”,因为我们的传统教育更倾向于让学生作出对客观事物的描述、再现、复制,忽视作为独立主体对外在事物的个性、深刻、创新而又缜密的评判。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是重新认识人对外部事物、现象等等的主观印象和评价。人,正是在与各种人物、事物与物象的价值联系中建构自己的评价体系。每个人都可以在源于特殊文化心理基础上而秉持自己的独立原则和立场,从特殊的立场出发去评判这些人物、事件——这就是至为宝贵的“评论”能力。世界的多维性来自主体评论的多元性。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中小学的母语教育乃至大学教育都严重忽视基于自主人格和自由思维的独立评论能力之养成。我反对简单记忆、机械背诵而高度注重“评论”,正是基于对母语教育乃至整个蒙学教育的批判性反思。当然,输入性语用能力与输出性语用能力,两者不可完全分离,更切忌对立。“视、听、读”是输出性语用的一种基础,“说、写、评”是基于输入性语用而超越之的目标指向。
罗:潘教授,听您这样一说,我们明白了积极语用不同于平时我们传统所说的“听说读写”,它还应包括“思、视、评”。
潘:是的,作为积极语用,其实包含着三层意思:其一是唤醒语用行为的动机;其二是构建全面、完整、主动的语用能力体系;三是追求语用品质的卓越,即将深刻、创意的思想内容与清新、鲜活的言语表达形式完美融合。只有这三个方面都达到了,才可以说是积极语用。假如连自觉的表达意识都没有,如果这种意识还陷于昏昏然沉睡之中,学生的语用行为只是停留在复述、再现、描摹层面,那么,充其量就是一种“消极语用”层面,即所谓被思考、被体验、被表达。尽管某个人在说话,其实是别人的思想借其嘴巴而“复述”出来的——学习过程异化成对“他者”思想的复述——这当然是“消极语用”。
罗:目前,积极语用教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汉语文教育思想,正在受到广泛关注,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教育学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课程教材教法》《中国教育报》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中小学教育》《高中语文教与学》《初中语文教与学》等十多家重要学术媒体都先后刊载或转载这方面的文章。积极语用教育观对于日常教学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请问潘教授,一个普通的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如何把这些主张落实到课堂中去?
潘:就组织形式而言必须要进行小班教学。因为语言课,无论是母语还是外语,都是培养学生的言语能力,而言语能力不能通过老师的讲、学生的听来养成。学生必须像学习游泳那样在水里、在惊涛骇浪中学而不是在岸上学。母语教育亦如此,在游泳中学游泳、在表达中学表达。
假如一个大班,50多个人却只有短短的40分钟时间表达(就算教师基本不讲),怎么保证每个学生拥有充足的时间来展开表达?教师又怎么从中协调?怎么及时对学生的表达能力和个性作出到位的发现、评价、引导等等?基于如是考虑,语文课必须是小班化的。
罗:可是潘教授有所不知,是否进行小班教学,这可不是我们一线教师所能左右的。如果是大班,能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吗?
潘:当然也可以。教师可以做的就是在现有大班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怎样把大班进行分解、化整为零、实施小组教学——这就是小班化教学。以小组为单位实施讨论、交流甚至争辩。所有的言语实践活动,首先在小组内进行。小组提供给每一个学生比较充分的表达机会,使其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思想观点,在小组的多边互动中达成思想的分享、情感的融通,并对学习内容有所升华。当然小组内应该有具体的操作措施,比如应该有主持人,主持人掌握小组里全面语用活动,给小组里每个人享有均等的机会并协调交流活动,当然也要对小组活动的时间进行规限等。主持人掌握小组学习的基本规则,确保每个同学都有充分的表达机会。老师在教室巡回、倾听、点评、协调,并且把巡回教学中的问题带入下一个教学环节。这是教师作为课堂总主持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教师可以不讲话,但是他不应该也不可能置身于课堂之外,在积极语用教育的背景下,教师更是一个倾听者、协调者、点拨者和引导者。
这样的小班化就是对大班的语用实践特别是表达活动进行纠偏并回归,即把被颠覆的课堂重新颠覆过来——所谓“课堂归正”。课堂提供每个学习者表达心灵智慧、情感体验和独特观念的契机,使之感受到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颇有成就感地享受母语。“享受”母语而不是简单“使用”母语——“使用”尽管是对的,但是没有“享受”一词那样蕴含丰富的内涵。语文课只有让学生“享受”母语才可能“人”“言”合一、目标到位。因为这里隐含着哲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语用即“我”,“我”即语用。20世纪哲学的一个主流趋势就是通过语用行为去研究并发现心灵的奥秘。所谓人的价值,必然是在语用尤其是表达中体现出来,没有了语用就是失去了“人”的思想现实,就是失去了人自身!因此,积极语用教育观主张通过小班化学习形式去实现学生思想力的发展和表达力的提升。当然,课堂积极语用教育的操作细则有待于教师别具匠心地探索且创造性地付诸实施,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即是。关键是保护好每个小学生的童真和天籁。
罗:听您这么一说,明白了大班可以通过分组活动来开展言语实践活动,唯有这样,才可以让每一个学生享受课堂、享受交流、享受表达。作为教师,在教学艺术或方法上还应该如何探索和创新呢?
潘:就教学艺术而言必须要实施“留白”。“留白”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时间留白”,其二是“思维留白”。留白的艺术,表面上似乎无作为而实际上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大作为,类似于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不教之教”。
首先是“时间留白”。教师要从课堂抽身,让学生通过积极语用填补空白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的成长,恰如马克思所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给学生全面语用的时间,就是把生命成长的自主权还给学生,为其内语用和外语用留足必要的“发展空间”。当然,“时间留白”要针对课型特别是教师特定素养而分别处理,我们并不盲目、绝对地主张“去讲授”,教师精彩的讲解仍然需要;但总的来说,课堂要留给学生热情洋溢地去自觉语用、全面语用和深度语用,教师要自觉保持金子般宝贵的有内涵的“沉默”——这就是山东杜郎口课堂创造的新观念:将“以教代学”转变到“变教为学”(“不教之教”)。
另一个是“思维留白”。这就是给学生留足一个心灵内部语用的思维空间。在全预制、全垄断和全封闭的指令性课程中,当学生展开思维活动之前,教师往往喜欢说一些隐含思想倾向的话语,即使“设问”也由教师精心设计好标准答案。这样的前提下实施启发式教学,其实是让学生“思维入套”,即诱导学生思维亦步亦趋地陷入教师预设的“美丽的思维陷阱”——这是母语教育的大忌。从发展意义上说,学生思维的“出轨”和“犯错”其实远比“入套”要好,唯有保护好学生思维的“出轨”和“犯错”,才能维持学生创意思维的勇气与胆量——如此,那他才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找到正确的思想并逐渐逼近真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课堂学习不是学会对知识的认知,而是学会对既定知识与真理的质疑、批判乃至颠覆,也就是学会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唯有学会学习,才是母语教育乃至一切学科教育的最高目标。
罗:潘教授,您说得很对,通常情况下老师精心设计的问题本身就是个诱饵,答案早已设定。那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呢?
潘:在平时教学中,教师应该改变精心设计问题的“问答流向”,就是变“师问生答”的单一模式为“生问生答”“生问自答”“生问师答”甚至“生问无答”(就像解方程一样,可以暂时没有答案)多维问答形式。这种问答流向的改变,实质就是促进学生思维由狭隘走向开放、由开放走向无疆界。学习者思想的解放比知识的简单认知或机械记忆远为重要。英国著名的课程论专家劳伦斯·斯滕豪斯所倡导的实施“人文学科课程计划”所需遵循的五项“过程原则”,对如何释放课堂教学中学习者的思维活力和表达个性颇有参考价值。劳伦斯·斯滕豪斯教授认为:文科教学的基本内容应该是问题而不是既成的结论;探究问题的主要方式应该是讨论而不是灌输式的讲授;教师应在学生争议中秉持中立立场;教师不该以权威或书本上的观点来封锁学生的思维疆界,问题讨论不一定达成一致意见;教师作为讨论的主持人应对学习质量和标准承担责任。斯滕豪斯的主张无疑是对“思维留白”式教学的完整、深刻的诠释:积极语用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借此才可砥砺学习者的思维品质和语用品质,并以积极、亢奋、昂扬的情感体验来促进其语用能力长时期的可持续发展。
罗:潘教授,您的思考很全面,做法也比较新颖,给了我们一线教师很大的启发。那么,在培养学生积极语用能力时,教师自身需要怎样修炼?
潘:教师要做好角色转换。首先,教师应该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激励者。学习、求知、思考、创造这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情,一个优秀教师的使命在于催生学生尽可能充分地释放生命深处的智性元素和情意能量。打个比方,如果教师是一位颇有匠心的点火者,那么,熊熊燃烧一己生命则是学生自己的事情,释放生命的智性和情意能量是其义不容辞的天然使命。所谓“点火艺术”,就是教师实施积极和激励性的评价。对学生思维和言语行为的评价,应当充满强烈的激励性和期待性。即使面对其稚嫩、偏颇乃至错误的表达,也要从发展和差异的原则出发去鼓励之。保护积极思考和积极表达的主动性、个体性和前瞻性远比简单消极的“指瑕”更有深远的价值,因为前者才意味着创新的可能。诸如教师要鼓励学生打破沉默、纳悦有差异的表达、肯定学生间隔性的沉默(间隔性沉默是表达前一种必要的酝酿期)等等。
其次,教师自身更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语用素养尤其是表达力。真正优秀的语文教师,其口头和书面的表达就是学生学习母语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教师今日语用之修炼,就是学生明日语用之造化。与其说是一本优质的教科书造就了人,不如说是一位卓越的语文教师熏陶并升华了青春生命。即使有一本优质的教科书,充其量它只是教师实施教学的一个小小道具而已,而比道具本身更重要的是教师自身那种超凡脱俗的思想力和表达力。
从这层意义上说,教师要先于学生而努力锻炼自己的思想力和表达力。思想力可以从异质阅读开始,在指令性课程范式中教师自身接受了太多的同质化阅读,导致自己的思想也被高度同质化乃至日益趋向机械化、刻板化、单一化。我们应该非常自觉地展开多元开放的异质阅读,只有经过如此多元阅读的长期砥砺,才能催生每一位教师蜕化出思维精彩、表达个性的新自我!
罗:潘教授,谢谢您对“积极语用教育观”深入浅出的解说。有了您的引领与指导,相信我们的语文教师在培养学生以思想力和表达力为核心的积极语用能力方面将获得根本性的突破。
(罗丹红整理,并经潘涌教授审读)
作者简介:潘涌,浙江省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浙江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高师语文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罗丹红,浙江省绍兴教研中心教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