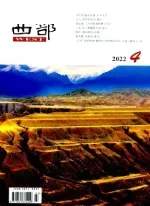当音乐穿过《悲惨世界》
耿韵
在我们这个时代,分歧是出在人性上的,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局限和可能性的描述上。历史学至今没有搞清楚“人性“的局限和含义。
——C·赖特 ·米尔斯
2012年汤姆· 霍珀导演的电影《悲惨世界》,改编自法国音乐剧作曲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一部以雨果的同名小说为原型的音乐剧。雨果或许没有想到现代艺术以综合的形式对他的作品进行了阐释。这是一部非同寻常的电影,它保留了音乐剧的基本形式,将舞台景观的虚拟性置换到电影需要的物质环境中,电影音乐剧对《悲惨世界》的再度创造使这部十九世纪的作品闪烁出经典持久的光芒。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字描写、过于繁复的小说情节被更简洁的音乐化的叙事所取代了,小说式的现实描写或传统电影的再现让位于一种经过人物、故事与冲突的删繁就简之后,获得了一种以音乐形式或音乐形象为审美核心的抒情化的叙述。它在音乐话语所构成的新的审美趣味中,重新激活了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一部常常被束之高阁的经典的理解。
音乐和语言的一个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有一种像水波一样推动我们去感受变化的神秘力量。比起语言,音乐显得更具有感性的直接性。当语言转向歌唱,语言就开始自然地偏离词义单一的意义逻辑,语言中的声音自身的含义就像话语中一直被压抑的能量深深地被释放出来,语言就被带向它自身的极限与临界,它逼近音乐、气息与呼吸,逼近身体和沉默。歌唱不仅是心智的语言,歌唱开始成为身体的语言。这就像歌唱与单纯的说话不同,歌唱须动用整个身体发声,声音,声音的各种形态如停顿、间隔、强弱、连续、沉默,以及气息与呼吸的节奏,都融入了新的语义表征。这种力量激发起暗含在其中一切可能的置换与结合,一系列音调与组合的技艺。与小说不同,音乐剧用唱词和音符去重复、重新解释、返回和修正曾经由语言组成的素材。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几年的历史、建筑、政治、道德、哲学、法律、正义、宗教信仰,现在由音乐、唱词、画面建构起情节、主题、构思和观察,还有光线、对象物,甚至还有去感知它们的观影者的眼睛,通过思想从形象追溯直至感觉。这似乎在人们的内心节拍和所讲述事件的外在节拍之间建立起了秘密的一致性,这是认知与温情交替的场所,由听觉与视觉组成的世界,一个观影时私语的秘密。
正如梅洛·庞蒂说的那样,“历史形式与进程、阶级、时代作为行为的逻辑而存在,它们处在一种社会、文化或象征的空间中。它不比物理空间缺失真实,而且在物理空间中获得支持。因为意义不仅仅生存在语言中,或者在政治或宗教的制度中,而且生存在种种亲属关系、机构、精致、生产的样式中,一般地说,在人类交换的全部样式中。在全部这些现象间产生冲突是可能的,因为它们全部都是象征系统,甚至一个象征系统可以翻译为另一个象征系统”(《世界的散文》,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版)。影片中,同样的象征系统体现在一个旋律永远都在被另一个声部重复的过程里,音符系列携带着“模糊”的意义在无限组合变化。这个系列(或旋律、主题)先由一个声部发声,然后由另一个声部接续,这些声部永远持续和其他所有声部以相反又相成的方式发生着置换。音乐与小说语言不同,它们是小心翼翼的、探索性的和非既定的,不仅是历史,不仅是意义,而且还有声音、韵律、各个部分的和谐。音乐并不直接去澄清、支持或指责任何一种历史或政治立场,它像视觉摄影技术一样,用听觉记录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它在许多隐蔽和出人预料的层面,微妙而自然地将整个社会背景与人物命运联系在一起。如电影中芳汀的音乐主题,就像一台逐渐收缩的观剧望远镜,始终贯穿着冉阿让的一生。芳汀的音乐主题似乎成为冉阿让灵魂中的声音,产生了他们在音乐主题中的结合。
小说和传统的电影叙事形式难以如此表述:这是一个著名的抒情唱段《芳汀的梦》,已沦为妓女的芳汀躺在一个形似“棺材”的小床上,俯视的镜头向着重现的过去深处推进,逐渐聚焦在她的脸上,往日生活随着音乐在回忆中旋转着,她几乎怀疑曾经经历过这段如梦的生活。记忆把芳汀孤立在画面的黑色背景之中,像是另一个人所经历的一段生活那样,镜头中没有任何多余的画面和色彩把她同过去连接起来,过去与未来的间距被冻结了,象征着现时的黑色隔开了整个空间。它是那样巨大和难以抵抗,阻止芳汀感受它后面的一切,它弥漫的阴影吞噬着曾经微弱的温情、青春、憧憬和梦想,只有一双在暗处闪烁的眼睛。这是美与善良的受难。如同一个受难的圣母。芳汀体现的是宗教受难主体在尘世生活中不幸的位移,残留着宗教受难余音的几乎是纯粹世俗的物质苦难下移到那些没有力量承受它,当然也没有能力转换它的最弱小的人的身上。在某种程度上,冉阿让的受苦是一个反抗者的受苦,更是一个宗教皈依者的受苦。这份苦难有着被宗教史或社会史所叙述的指望。然而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不需要女人顶班的。逐渐的,连女人自己也开始相信,她们的语言是流出而不是吼出的,就像芳汀颤抖的声带,带着泪水的、低语般的哀号。她的命运,不只是制度、阶级、经济、历史的抽象概念,而是所有这些因素和现象融合之后掰碎了弥漫在生活细节里的——它们迫使她在张口时总在怀疑有没有忠实于自己的声音。当然,在一个人的各种体验中,似乎不可能存在断裂,在截然不同的境遇中,无论是爱情还是回忆,感情生活还是思辨生活,在影片中都显露出相同的音乐和色彩光影基调。某种自然景色,天空的某种颜色,音符的跌宕都表明了某种精神选择和感情的渗透。缥缈的遐想深深地与最抽象的观念思辨汇合在一起。那些表现最隐秘的私生活,表现对时代或死亡进行思索的主题正是在事件中,在人物中,在感觉、欲望或相遇之中,通过画面及光影以音乐流水般的绵延得到表达。芳汀的生命在女儿柯赛特的身上延续着,她犹如晦暗世界里充满阳光的透明诗篇,这样的诗意在于,即使对最现实事物的描写也是和童话般的感觉交织在一起的, 它讲述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之间的爱情。在这少有的热情与明澈的结合之中,音乐展示了它最原始的魅力。青年革命者马里尤斯和柯赛特的爱情唱段,不再是芳汀般低语的、颤抖的、断续的,而是高音调的、抒情的和跳跃的。
对革命和自由的热爱把马里尤斯这一群策动起义的青年人联系在一起,年轻的革命岁月在四周喧响着,他们幻想和国家一道走向幸福的未来。他们通宵达旦地待在那间拥挤的小房间里,起草宣言。破窗户外,风在黑暗中喧嚣,老鼠顽固地咬啮着地板,桌上的食物就是廉价的酒和几块面饼,但生活却是美好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就像是革命,而革命和对自由的狂热向往就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置身于物理现实和形而上现实之间,忠诚,心胸宽广,饱含着做人的尊严感和正义感。在以《红白黑》为主题的唱段里,男声合唱似乎带着所有的激情从晨雾中喷薄而出,庄严地盛开在阳光之下。镜头从小房间内推向远方直至整个城市的上空,在那里,阳光的影子和坚定、简洁、高昂的音调永远都不会使人产生迷失感和孤独感。合唱预示着一个年轻的群体的力量之集结,预示着一种社会性的反抗情绪的汇合。年轻革命者的合唱意味着一个充满希望的群体对共同情感与道义力量的分享。他们共有一个声音,凝聚一种意志。在合唱中说话的是一个集体灵魂和它的意志的凝聚。这正是这部电影音乐剧的魅力所在,力量的单位不再是句子,而是句子的音乐形式,是音节、音律和唱词,是化为群体情感形式的观念与意志。跳动的音符使我们感受到在一个时代的思想貌似合理的表面下,人类精神的更深层的骚动和变化,以及一个新生的共同体中的自由精神晦暗而不安的孕育期。或许还有,这个集体灵魂为了胜利的获得,暂时还对个性与个人的生活选择表示了它的集体质疑。那些存在着一些微弱但不时充满热忱的异见,使我们感到一些新观念胚胎的逐渐诞生,尽管它受到当时人们的忽略或误解,而正是音乐的节拍、休止、反复赋予了它本质上的不连贯或尚未清晰的表征方式。随着电影主题的深入,音乐已不仅仅是旋律的指尖,它的表达容量由厚厚的和声支撑着,由若干等长的音律组成,这些合声线条带着沉厚的、流逝的历史感和坚实的确定感蜿蜒交织,依循歌剧般的规则挥洒自如。在这显得深远的和声背后,是对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的预示,是一种逐渐被这个年轻的群体灵魂所唤醒、所激发的更大的社会情感所发出的遥远的共鸣。
音乐不仅善于为人的灵魂表达出它自然、最直接的痛苦与欢乐,而且善于表达通过可见之物、通过无生命的自然传递那些最短暂的、最复杂的、最道德的感觉(合唱),不仅有个人感受以外的形象(雨、街道、起义),而且还有它的表情、它的目光、它的忧愁、它的巨大的快乐、它的讨厌的仇恨、它的沉醉或它的恐惧,所有一切具有人性的东西,以及非凡的、神圣的或恶的一切。正是这一切,使我们在沙威的不同唱段里,在他那些自我表露的唱词里,看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独特力量。在影片开始时,它是简短、重叠和具有重量的,即暗示其中有一种客观的精纯和断然的陈述,倾听者情不自禁假定这音乐有一种非比寻常的重要性,似乎能看到每个声部、每一刹那、每个音程都经过充分的衡量。它是法律和真理,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它来自沙威的内心生活、目标和理想,来自他具有的某种观点或观念,来自他的成长和驯化过程。不管沙威身居何职,身居何处,来自什么地方以及在做什么,正是因为他拥有这种内心生活,使他有别于冉阿让、起义者和其他任何角色。这种内心的流变,在冉阿让的音乐主题搅动下,被电影所拥有的技术权利提取、放大和单独呈现,甚至不需要任何唱词。虽然他一再地从既定的社会共同体中证实自己“无罪”,但当他对潜在的激进情感及未来的社会巨变有了一种模糊或尚不完善的直觉感知时,音乐替代了神谕的语言,提供了一个浩瀚的天地,通过音、像和节拍的流动,在沙威看似统一的和安全自主的空间里掀起了波澜。他不再是被因果律的力量所左右的消极而无感情的资料,而进入了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时间的、空间的、物的、与他人的关系或与自我情感的体验)中,他所遵循的“规则”一次次地与冉阿让的“无规则”和终极的善与宽容发生碰撞。法国批评家让·皮埃尔·理查曾说,“ 为什么音乐对于不幸者如此亲切?因为,它以一种模糊的并不伤害自尊心的方式使人们相信亲切的怜悯心。这种艺术把不幸者冷漠的痛苦转变为使人惋惜的痛苦”(《文学与感觉》,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当沙威轻轻地将自己制服上的勋章取下来,戴在死去的小小起义者身上时,整个背景配乐逐渐弱去,在目光的幽灵、窥测和敌对的幽灵中响起只有他一人听得见的音乐,“缄默不语”地将其转化为复杂的同情。
沙威的感情在一种模糊的一致性中流动着,他曾经对起义的孩子们说:“你们投降吧,你们无法成功,巴黎的民众还在睡梦中。”沙威无意识中说出了历史的谜底:起义者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不拥有道义或正当的理念,而是民众尚未觉醒,年轻起义者的血在白流。一个时刻的不幸是,沙威最终成为他自身模糊觉醒的牺牲品。他是一个集中体现了权力、社会与民众的诸种内在冲突的化身,他是信奉政治权威、制度理性又为道德理想所模糊感召着的自我分裂的化身。在名为《星星》的唱段里,音乐在形式上已不再是“连接”的,三连音不断地进行并列和分隔。忧郁是心灵的夜晚,他站在警察局的顶楼望着星空,夜晚提供了某种私人空间的保护作用,它使人回到真实,它逐渐地淹没棱角、混淆残留的确定性。音乐起着感觉的原子作用——水平线上出现的象征正义的雕塑侧影、巴黎圣母院钟楼上时隐时现的星星、他脑海里衣衫褴褛的芳汀——目光成为视觉的回声,触及并依着在上面看似不可分割的、坚硬的“正义”。 假如艺术的作用是“唤醒情感”的话,那么领悟艺术的意识是否包括在这些情感之中呢?他不自觉地寻找某些内在的答案,这是他的内心独白,从夜色中引出的感觉、观念或感情,在朦胧的直接经验中,我们看到沙威冷峻和温情这两种基本气质的在场和混合,以及对确定和模糊这两种中心原则的召唤,它们相互抵触、妥协和挣扎着。宗教说:这样去想!法律说:那样去做!但是宗教不能证明它们是合理的,法律也在历史中不断地迂回和修正着。就像沙威此时的声音,每句唱词都是重浊的,复音线条也欠清晰。语言的剩余物弥漫在远处的地平线上——沉默、空白,无法言传的观念和感情,它们看似被语言所忽视,这是一个语言尚待完成的过程。天色渐亮,在街上,像是有意似的,集中了很多古老的风化了的台阶、挡土墙、常春藤、偏僻的小巷、粗石围墙、窗户上弯曲的百叶窗和残留着枯萎鲜花的小院,怀疑犹似痛苦的幽灵那样从暮色后升起。清晨清除了黑夜,一切解脱都在音乐中汇聚:把“我”同自身结合起来的解脱以及把“我”同他人连结起来的解脱。它谨慎地把“我”交换给“我自己”的命运,同时它使“我“向着人类的同情心敞开。音乐安抚着沙威的痛苦,音符唤起多重、复杂的意义,驱动着沙威去理解生命里的各种力量,三连音伴奏和旋律的意境逐渐舒缓,当沙威的声音在晨曦中从整个城市上空掠过时,它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定。虽然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说,“音乐被视为脱离生活的艺术,一种非模仿、非拟声的直接表达,最大限度上远离对客观事物的描述”,但道德价值或许只有在一个人为它献出生命或把生活托付于它的时候才能在历史中获得实在。沙威的自杀,打破了冉阿让奉行的那个单一的模式,即永恒的爱的智慧。他的犹豫、矛盾和痛苦,就像舒伯特所言,“伟大的作曲家的标志在于身陷一场灵魂的宏大战役,却能在这场激战中头脑冷静地指挥军队”。无限制的强权并不是历史的唯一规律,虽然每个人都用正确的语气为自己创造或提出结束语,但对沙威来说,只是活着并不够,应该有一种命运。他思索着现实中那些无法驯服之物、那些不可弥合的深渊。他的唱段,不再只是实际剧情唱词的陪衬,而成为音乐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敏感性最真实的捕捉,音乐充实了周围的世界记忆中所有的现象,无论它们是崇高的还是渺小的,它消解了语言预设在理解者和被理解之物、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某种裂痕。在这个意义上,《悲惨世界》中的音乐主体可能是世界,可能是个人,或可能是阶级、国家、教会——任何被定义为构成世界最真实的现实的那些存在。它越来越持续地表达着人类内在不可言说的精神——主宰着人类一切想象并推动人们一直探询和行动的内在精神,那个真实、纯正、深刻、虔诚的人类生活。
虽然,人们普遍满足于把雨果的这部原著置于善与恶、宗教与现实的二元性中,还不太注意描述他所采取的各种具体态度,也不太注意描述他的两种相对立的倾向之间能够结合起来的共识与契合。但在音乐的提炼下,在书中可能存在的一切抽象的普世价值内,还有一个流动的、神秘的抒情曲 “回响”着:一个时代、一种文明或文化在漫长的精神变迁中,某些中心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再现着那个时代和文化中人们对自身及其活动的看法。在电影精致的画面、音效、化妆、音乐、唱词的帮助下,它回溯了社会真实经验与记忆,回溯了那种社会情感、社会理念在个人心灵和集体灵魂中的最初的发生,并且如同一种音乐动机一样逐渐在人们的心中、命运与事件中的展开形式。在音乐剧的形式中,如同尼采所说的一种悲剧精神在音乐中的诞生,一种自由精神也开始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音乐中诞生了。可以说,当一种社会理念、当一种个人的和集体灵魂中的诉求获得了其自身的音乐形式时,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的外化了。音乐把一个民族全部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全部内在和外在生命紧紧捆绑在一起,维系成一个能量惊人、极度活跃、生机无限的整体。它提供了另一种陈述和诠释,一种史诗般的和悲剧的宏大结构:它是一场内心的独奏会,是苍白的芳汀,是疾病,是堕落、是羸弱;它是柯赛特和马里尤斯的爱情抒情曲,是永恒的白色光芒、是生活的丰盈、是青春,是神秘;它又充盈着起义者鲜活的色彩和沙威敏锐的目光,澄清着我们在对世界的感知中未经思索的问题,是骚动、暴力、冲突、混沌,是精灵,是狩猎的号角,是对活在当下的渴望,是快乐而天真的乡村牧歌,是对瞬间的喜悦,是对永恒的意识;它还带着对现实到彻底市侩化的旅馆夫妇那令人捧腹的幽默感,是生活斑斓的丰富,是习以为常的视景,是民歌的声景; 它又是至上的宗教和声,芳汀低声部里的上帝,被放置在一个时空遥远的地方。马里尤斯的宗教信仰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合奏曲,一个世俗的天堂,寻求着新的经验秩序;冉阿让则是抒情的慢板,上帝简化为人类爱的一项功能,他对这黑暗世界中人事的兴衰起伏,不怀任何希冀,他不相信一事一物的微光能集成烈火,他那颗质朴的心只知道爱;而沙威的信仰如宏大的奏鸣曲,成为赤裸裸的意志的表达,是暮霭中的古迹,是永久的“家世”,是不可分析的、愿意信守却无法表达出来的旧秩序,他试图命令它、理清它、组织它,而最终,他发现只能对自身、对自己的灵魂具有力量,执着地付出忍耐、谦恭、庄重、冷静,才得以重塑自己的心灵。也许,只有这一点,是沙威唯一能确定的。电影音乐剧是这一切的共鸣:当音乐精神穿过这个“悲惨世界”时,一切都在被改变。
在这宏大的音乐叙事中,聆听者总是知觉到有某种效果在要求他注意,虽然观影处在公共领域,但聆听者却在自己的回忆与联想这个私密领域里,感受音乐解释着世界秘密的本质:它是智慧的解释者,说着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一门语言。这是一种类似阅读的经验,耳朵、眼睛总在不自觉地感受到这种相似性,每人都在各自现实生活的不同领域检索着。当然,雨果给予影片的不仅仅是素材,它质朴的词汇的力量,以及简洁而没有任何修饰的故事的力量是难以表述的。只有借助恰当而又准确的语言,才可能在一部小说中描写出酷刑的阴郁场面,又可以让全部的书页充满鲜花遍野的爱情气息、小鸟的歌唱、夏日细雨的淅沥声和革命无边无际的乐观精神。电影承接了关于人类、关于未来的思考,并把自我的性质、意志、自由、人的同一性、人格和尊严以及它们被滥用、侵害、侮辱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它们不受侵害的恰当边界(无论这些边界如何划定)清晰展现。电影将自由观念在一个多世纪里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兴衰变迁,以音乐的形式传达给观影者,褪去了小说或许存在的“说教”成分,转化为观影者自主的凝视权利:自由不是一种放弃尘世的理想,而是使这个世间更适合人居住。或许,这也是这部电影在雨果原作诞生一百五十年后,在一种音乐精神的阐释方式中,再次引起人们精神共鸣的原因。
栏目责编: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