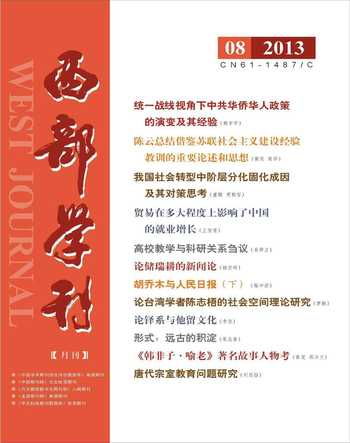高校教学与科研关系刍议
摘要:教学工作始终是高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也是大学教师最根本、最神圣的使命;教师的科研水平、综合实力首先应该体现在课堂上,体现在学生的反应上;对大学老师的考评机制也应该突出教学这个中心。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高校教师更应该把精力放在教学上,把自己的科研体现在课堂上。文学研究的科研性质远不及自然科学技术,文学课教师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教学上,用精妙的语言文学知识充实人,以丰厚的人文素养陶冶人。
关键词:高校教学;科研;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高校纷纷打起了“建立研究型大学”的旗号,甚至一些重在培养基础教育师资力量的高等师范院校也贸然跟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所谓的“科研”在高校突然吃香起来。与之相应,发表论著的多少和书刊的级别就成了考评老师的一个重要标准。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我们的大学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有人指出:“大学教育当然与中小学教育有着很多目标性和功能性的区别,后者更多的是有关知识传输和习得的过程,前者则兼有知识的教学并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创造性潜力的功能。大学教师不仅仅有‘传道、授业和解惑的传统职能,还有着发挥创新能力,在文化、科学技术上直接用理论成果为现代化服务的重要任务。所以,大学需要既能讲好课的传授者,又能够在科研上不断前进的探索者。”[1]
由此看来,高校要求老师既教又研、教研结合无可厚非。但教学与科研在大学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这就是:教学工作始终是高校经常性的中心工作,而科研不是。[2]众所周知,教书育人是教育的根本,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学校是因为学生而存在的,学生是任何学校的第一服务对象。所以,教书育人应是大学的第一功能,也是一个大学教师最本质、最神圣的使命。相应地,对大学老师的考评机制也应该突出教书育人这个中心。但现在的事实是这一中心不仅没有凸现出来,反而成了科研成果一票否决制;所谓的“教学与科研并重的考核体系”,几乎演变成了以申报课题、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为指标的考核体系。
对此作法和现状,笔者不敢苟同、实难恭维。因为:首先,课堂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老师课上不好,必然直接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其次,一位大学老师,在搞好教学的前提下兼顾科研,他的科研水平、综合实力也应首先体现在课堂上,体现在学生的反映上。事实上,学校里科研活动之目的也首先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如果一个教师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就是不会讲课,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来,那么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研究者,但肯定不是一个好教授。正如学生们普遍所言:在评判标准多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我们没有答案,但我们知道,谁是不合格的大学老师。对于时下融入了过多“铜迹”色彩、充满“商品”味道的师风、学风、文风,教师最重要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是体现在课题、论文、职称上,还是体现在学生的认可上?在学校,应该没有比学生更真实可靠、更不带功利色彩的评价了。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全民教育、大众教育,而不再是少数教育、精英教育。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教师越发该把主要精力放到传道、授业、解惑上,应该把自己的研究体现在课堂上。试想一下,没有平时的精心钻研,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得之见,一位教师(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教师)怎么能在课堂上激扬文字;一位不能在自己的课堂上激扬文字的教师,又如何能够赢得学生的尊重;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又如何能够长期“占领”讲台。也就是说,许多优秀的教师没有发表论文并不等于没有进行科研,也不等于没有科研能力。
虽说知识传播不是现代大学的唯一职能,但它却是大学精神最为内核的部分,因为知识创新也好,服务社会也好,如果没有知识传播之地这个内核,大学只会沦为市场经济的奴仆,教师也只能沦为功名利禄的俘虏。在有论文就会有高职称、有高职称就会有好待遇的今天的大学,对那些不为名利盲目跟风“科研”,却一直能够默默坚守在教书育人第一线的教师,人们应该给予大力褒奖。
换一个角度说,国家和社会有那么多专门的科研机构,大学里也有许多专门的研究机构,为什么还非要让专职教师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再承担大量的科研任务呢?应该说,大学里的科研是不同于社会上的专门科研机构的,它具有更多的理论性、虚拟性,所以多表现为平面形式的论文和著作,因而其实际意义也不能与社会上的专门研究机构同日而语。即使说,近年一些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在“知识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成绩不菲,但也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和价值就忽视和抹煞那些在高校长期从事学科基础知识教育的老师们的存在和价值吧!我们的高校管理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区别对待他们的有效机制。据资料:同济大学设置了“教学型教授”聘任岗位,教学型教授享受与科研型教授同样的待遇。[3]武汉大学出台规定,对于教学效果优秀,教学成绩特别突出且任副教授5年以上者,只要其近5年在本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篇(其中教学论文2篇),就有资格升任“教学型教授”。为了给教学一线教师创造晋升“教学型教授”的条件,该校还规定,教学一线教师每工作5年可享受一次“学术假”,用于到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科研、进修学习或著书立说等活动。[4]湖南大学的做法则更灵活、更富人情味:为了调动教师从事教学的积极性,突出教学的重要地位,2004年,湖南大学决定在全省高校率先推出教学型教师职称“指标单列、集中评审”的办法,从而使长期在教学一线工作、教学成绩突出的教师可以优先晋升职称,而且教师的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可以互相转换。这样在教师面前就摆出了两条发展道路,适合搞科研的教师可以潜心科研,擅长教学的教师可以全身心投入教学。[5]矛盾迎刃而解,何乐而不为?
二
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金碧辉的调查报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影响因子排名前10%的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的中国论文,每两年以45%的速度增长;在高被引用论文统计样本中,中国作者独著论文逐年增加。国内一些大学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在惊喜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出色表现的同时,不禁令人担忧——中国80%左右的国际论文分布在低被引区间和零被引区间!繁荣的背后不过是泛滥的泡沫,国家每年大量的科学资源投入和科研经费支出,制造出的竟是些毫无科学价值的“垃圾论文”![6]
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论文的价值尚且如此,那么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文学学科论文的价值又如何呢?我们不妨先来就文学研究的科研属性做一番考量。
“科研”一词是“科学研究”的简称,而提起“科学研究”就一定意味着严肃性、客观性、真理性,甚至是实验性、实践性。应该说,自然科学技术及其研讨、探究活动,才具有上述属性。人文社会学科远不及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更富有科学性,因而关于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尤其是文学学科)里的分析和研究,也就谈不上多少科研的性质。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撰写关于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也被称为“科学研究”了。而且,在高校“褒研贬教”“重课题轻育人”“重论文轻教学”的考评体系下,这一科研势头目前正在高歌猛进。众所周知,文学作为离经济基础最远的社会意识形态,其研究成果(尤其是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的解读结果)之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因为研究者的主观随意性太大、个人情感色彩太强。正如有人指出:“文学研究融注着研究主体浓厚的主观意识”,“加上文学的表意功能是诉诸于形象性的符号系统,而形象在表意上并不是‘能指同‘所指间具有严格意义对应的关系。因而,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解读,不同的研究主体可以作出不同的诠释,所以才能‘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7]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同时也不允许“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科学真理”,或者“有一千个科学家就有一千个真理”。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学及其研究工作的客观真理性和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结论的唯一性。一句话,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科学,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才具有真正的科研属性。我们只听说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专门家被称之为科学家的,还没有见到一个从事人文社会学科的专家被称为科学家的,尤其是搞文学研究的人,哪怕这个人著作丰富、名闻遐迩。一般我们称这样的人为“专家”“学者”。所谓专家,意即某个学科领域的专门家,也就是说比起一般人来说,你掌握着这个学科更多、更系统的知识,但并不意味着你所掌握的知识就是真理,或者说具有科学性,所以不叫科学家;至于学者之称就更是如此了。所谓“学者”,顾名思义就是学习的人。若觉得这一解释不足以与一般的学习者相区别,可以解释为会学习的人并因此学得好的人和有学问的人,但同样并不意味你的所学就是科学真理。相反,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专家学者不管成就大小、成果多少,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科学家。这就像我国有科学院和工程院,也有社会科学院,但前者有院士且被称为科学家,而后者尽管也有科学之谓,但却没有院士,也不叫科学家一样。
按理说,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都有其相应的学术研究,这本无可厚非。但不要忘了,这些学科在高校首先是一门课程;高校教师兴致所至进行一些学术研究,这也未尝不可,但学术研究首先应该服务于你的教学、体现于你的教学。正确地讲,在高校中,教学与科研(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应该是以研促教、以教带研、教研结合、相互补充的关系。但由于目前不恰当地过分强调科研、突出科研,使得教学与科研已经处于严重的脱节甚至对立的状态。表现在:许多教师岗位聘任时争上科研岗而弃选教学岗;万不得已被聘为教学岗,也是整天忙着炮制论文,然后到处参加学术会议、拉关系发论文,一本教案多年不变一个字,教学工作成了副业甚至“劳役”,象征性地带几节课而已;即使勉强走上讲台也不认真备课,讲课缺乏激情、心不在焉,课后不与学生交流沟通,他们想的不是如何取得最佳教学效果,而是如何尽快“完事”。且不说这些人为了多出成果、快升职称、多拿津贴而杜撰抄袭、粗制滥造的学术造假行为,单就其为了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而笼络人际、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也极大地败坏了学风、校风甚至社会风气。现在,高校已经出现了教授不想带课、博士不会讲课、老师讲不好课的问题,这种现状最后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大滑坡、人才质量的大下降。
笔者以为,高校每一位文科教师,尤其是从事文学课教学的老师,对自己所学专业的价值和作用应该有一个清醒和实在的定位,这就是:它首先是一门载负着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和素质教育的课程;其次它并不像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那样具有绝对完全的科学研究的性质;第三,它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或工程技术发明那样会给人类社会即时带来巨大的生产力。笔者这里无意否认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性,只想给那些头脑过热的“专家”和“学者”提个醒,给高校目前高烧不退的“科研”(尤其是文科科研)降降温。据中国知网引文数据库统计:“最新被引文献”“高被引期刊”“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文献”“高被引专题”等栏目,名列前茅的均为自然科学或工程技术方面的文献、期刊、作者和学科。尤其是“高被引专题”栏目指标排名,共分168个学科,“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独占鳌头,“数学”“物理”“生物”“化学”“材料”“机械”等理工学科紧随其后,而语言、文学学科则被远远抛甩于80位之后。众所周知:我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社会科学却没有院士;我国不定期举行的科学大会并不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各种奖项的力度和额度也远不及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即使是诺贝尔奖,也只是奖励给创造作品的作家,并不包括评论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者。人们现在都深深明白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想没有一个文科学者敢妄自尊大地说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并给予有力的证明。并不是说文学研究就不揭示真理,在笔者看来: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探讨容不得半点虚妄和掺假,所以它一般给人们揭示的是绝对真理;人文社会科学与此有所不同,由于主观随意性大于客观真实性,一般给人们揭示的是相对真理;无数个相对真理经过堆积和上升,最后才有可能产生一个绝对真理。这就像修建金字塔,从塔基到塔身最后到达塔尖。不过,由于谬误的普遍存在和过程的漫长无期,人们大都看不到塔尖。加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受到一个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阶段性政策的影响,某些观点或论断很容易突然成为人人都得接受的绝对真理;与此相反,某些绝对真理一时则可能变为相对真理甚至谬误。在绝对与相对的转换中,有些观点和论著一夜之间可能家喻户晓、洛阳纸贵;有些观点和论著瞬间就可能一文不名、成为废纸。如上世纪80年代关于国有企业“姓社”还是“姓资”,多少人写了多少论文和著作,但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英明论断,让他们顿时不值一提。
应该说,文学研究并不具备完全、纯粹的科研性质,至少不具备科研的绝对性质,因此也就不具备有确定的或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因而把对文学作品的解读或评议称之为“科学研究”看来并不合适,倒是称为“学术研究”还说得过去。不过在笔者看来“研究”二字还是去掉为好。因为,所谓“学术”乃学习的方术,并不是知识或学习本身,而是学习的手段方法。重术而轻学实乃本末倒置,若再加上“研究”二字,导向上就更难免舍本逐末。目前,文学学科的学术现状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形式主义相当严重:许多学者不着眼于生动形象、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和生活现象本身,而是脱离生活和文本实际,苦思冥想、闭门造车,观点唯恐不新奇、体系唯恐不庞大、用语唯恐不生僻,从而造成各种奇谈怪论满天飞、大小体系比比皆是、新词僻语应接不暇。
笔者以为,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学科研,应该像文学作品的创作一样建立在有感而发的基础之上。高校从事文学课教学的老师,在平常的读书学习过程中,或在教书育人过程中,读了一部作品或想了一些问题,有了一些感悟和见解,如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时拿起笔来,提升为论题,撰写成论文,发之,则大家分享;不发则应用于教学。这才是一篇文学论文产生的本来面目。而那些为了职称去写论文、为了津贴去写论文,甚至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者,不仅偏离了论文写作的初衷,简直说就是学术的异化、人性的异化。长此以往,科研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下降不说,哪儿还谈得上有力地服务于教学,恐怕只能是有力地误导教学吧。
由于文学研究的科研性质远不及自然科学技术,高校文学课老师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教书育人上,用精妙的语言文学知识充实人,以丰厚的人文素养陶冶人。而科研活动,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所以,发表学术论文要十分慎重。同时应改革考评机制,减轻教师写论文、出书的压力,这不仅有利于教学工作中心地位的回归,也可从根本上减少科研中的注水和造假现象。
参考文献:
[1]李隼.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教师[EB/OL].北京:文摘报,2005-04-10.
[2]薛东前.关于教学工作中心地位的综合思考[C].创新教育:大学永恒的主题.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吴华.上海同济将设教学型教授 高手不立说也可当教授[EB/OL].2005-04-22.http://news.sohu.com/20050422/n22529 3562.shtml.
[4]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深化教师职务聘任改革 促进高校人才队伍建设[EB/OL].北京:学信网,2005-12-14.http://www.chsi.com.cn/jyzx/200512/20051214/273860.html.
[5]张茧,刘爱民.教学名师优先晋升教授 湖大率先出台激励措施[EB/OL].湖南:红网,2006-10-8. http://hn.rednet.cn/c/2006/10/08/997398.htm.
[6]程蓉,王春,罗倩.SCI,是舞台还是羁绊[EB/OL].山东:山东大学(威海)高等教育研究所网站, http://gjs.wh.sdu.edu.cn/show.jsp?aId=220&classID=050320091800675976.
[7]黎跃进.外国文学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吴舜立(1962—),男,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