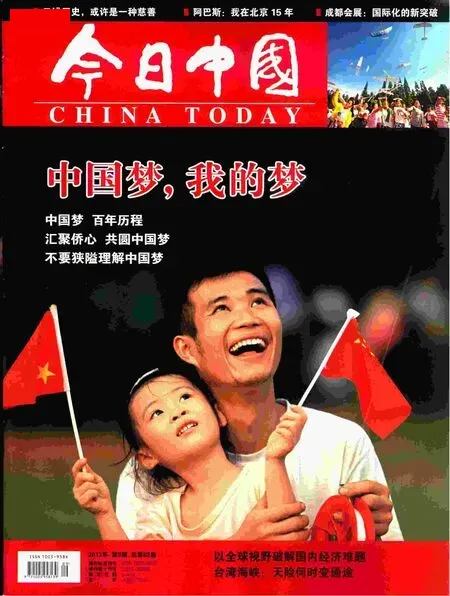“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新解(下)
李荣胜
孟子以三位圣王(尧、舜、禹)为例,来说明农家的谬误和社会分工的深层含义是很有深意的。其一,是针对农家忽视国家管理者(即“劳心者”)的职责而举例,这些圣王主要职责是为天下操心,是无暇亲自种庄稼的;其二,是针对国家管理者(即“劳心者”)的作用而举例,他们作用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是关系到全天下人的,决不像“种庄稼”那么简单:其三,是针对国家管理者(即“劳心者”)付出的是心力、不是体力而举例,他们整日为天下人操心,为天下谋得福祉,则天下人才称他们为最伟大的圣王。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了。
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当做封建帝王制造专制统治的理论来批判,显然是把“劳心者”当做封建帝王了。因为人们痛恨封建专制的黑暗、腐朽、残暴、压迫,因此,理所当然地痛恨封建专制的“劳心者”。而孟子这里讲的“劳心者”又的确包括帝王(但不仅仅单指帝王)。然而从孟子讲完这句话的举例中,我们清楚地知道,孟子指的制帝王是像尧、舜、禹那样的圣王,是为全天下操心的帝王,而决不是指为一己之天下的封建专制帝王。历代封建帝王使用孟子的话维护他们的统治,是他们利用了孟子在民众中的威信,欺骗了民众而已。如果封建帝王都能成为孟子心中的尧、舜、禹那样的“劳心者”,那么,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还会有那样多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吗?儒家始终是把“大同世界”作为他们的社会目标来追求的,而“大同世界”也是需要“劳心者”管理的,而管理“大同世界”的“劳心者”必须是像尧、舜、禹一样道德崇高、勤勉为民的圣王。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千古冤案,还有一个关键字:“治”。断章取义者认为“治”就是“统治”。那么,“治”到底是不是指“统治”呢?“统治”是政治专用名词,是指凭借权力控制、管理国家和地区等。今天的人们更愿意将“统治”理解为“凭借权力的控制”。如果是“封建统治”,那么显然是一个更加令现代人极不愉快的贬义词了。而孟子在这里讲的“治”,极为明白的是指尧、舜、禹这样圣王的“治”。这些圣王为众生教农耕、治洪水、谋福祉,是在“治理”天下,决不是在“统治”天下;这些圣王让众生懂人伦、讲礼义、有秩序,是在“管理”天下,也不是在“统治”天下。最终尧选中了贤明的舜,禅让了帝位;舜又选中了贤明的禹,禅让了帝位,这就更不是为一己之私“统治”天下。把这样的“治”解释为“统治”,强加在孟子头上,孟子的的确确是冤枉的。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按照孟子的本意,应该解释为:“靠心力劳动的人治理、管理人,靠体力劳动的人被人管理、治理。”
以上用了五节的篇幅,解读了孟子记录的那场辩论的全部文字,我们就十分清楚地知道了,孟子这里不是在为专制统治制造什么理论根据,而是在揭示他发现的社会管理的真谛。
孟子与陈相的辩论,实际上就是儒家观点与农家观点的碰撞和交锋。这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是极为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正是在这样的辩论交锋中,各家都在阐述着各自认为的“真理”。或许,孟子意识到他与农家辩论的某种“真理性”内容,所以才将这场辩论整理成文字,收入《孟子》一书。
那么,孟子在这场辩论中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首先,孟子发现了社会是有分工的,而这种分工又由交换联系在一起。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尽管社会还是农耕社会,但各种不同的行业出现了。有种粮的,有织布的,有烧陶的,有打铁的,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行业,便使每个行业都能不断壮大,并以行业间商品的平等交换来达到他们之间的生活互补,从而使社会达到平衡、稳定和发展。孟子发现了这种社会分工的进步性,而农家却不懂得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反而要求国君要跟农民一样种粮食。这种观点在今天谁都知道很荒谬,但在两千多年前,那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见呢!
其次,孟子发现了社会最重要的分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而这种分工靠税赋联系在一起。孟子讲的“劳心者”,我们翻译成“用心力劳动的人”换成今天的语言,就是“脑力劳动者”;同样,“劳力者”就是“体力劳动者”。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就是从全社会劳动性质讲,大的分工就两种:或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孟子进而作了解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告诉我们:脑力劳动者治理、管理人,体力劳动者被人治理、管理。(这里孟子只注意到了社会管理意义上的分工,没有意识到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是脑力劳动者。这大概就是历史局限性吧!)孟子接着又作了一个开诚布公的解释:“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这里“食”读作:si,同“伺”,拿東西给人吃的意思。孟子是在告诉人们:体力劳动者要养活人,脑力劳动者被人养活。靠什么“养活”呢?靠税赋,税赋是社会分工的调节杠杆。税赋制度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里,已经很普遍地使用了。孟子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一理论概括,是前无古人的。直至今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也还在沿用着吗?
再次,孟子发现了社会分工中无论“劳心者”还是“劳力者”,都是“劳动者”,都要付出“劳动”;在社会分工中,没有不劳而获者。这个发现对“劳心者”意义尤其巨大。对于诸侯国的君王,要像尧、舜、禹一样“劳动心力”,为国家臣民去操心,不能整日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对于各级官吏,也要像尧、舜、禹一样“劳动心力”,为国尽忠、为民出力,不能无所事事,更不能搜刮民脂民膏。孟子的这个“劳”字,是不是对今天的社会管理者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呢?我以为是有的。
最后,孟子发现了在社会分工中,无论“劳心者”还是“劳力者”都是“人”,都是平等的人。“劳心者治人”,这个“人”,显然是指“劳力者”;而“劳力者治于人”,这个“人”,显然是指“劳心者”。在这里,孟子把他们都统称为了一样的“人”。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奴隶制残余势力仍然强大,封建等级制度正在构建之时,孟子的这种不顾职位高低、等级贵贱的平等称谓,就是向当时社会的一种挑战。同时,也体现了儒家对“人”的朴素的平等认识一管理者是人,被管理者也是人;缴税赋的是人,享受税赋的也是人。这是儒家学说中难能可贵的人本思想。
在孟子之前的中国古籍中,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社会是必须分工的;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社会的主要分工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治理关系;没有人这么明确地讲过,社会分工中人人都要劳动,人人都是平等的人。孟子在两千多年前的这些极具进步意义的发现是伟大的,强加在孟子头上的不实之词应该平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