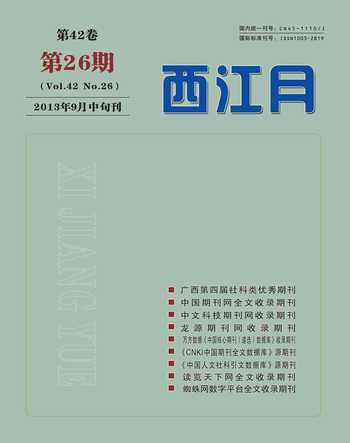博尔赫斯与西川在叙述诗学上的比较研究
朱晓琳
【摘 要】叙述是诗歌言说方式的一种,体现了诗人在处理自身经验时不同于抒情诗人的切入方式。诗人博尔赫斯与西川用它呈现故事、塑造人物、记录日常经验。西川从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处继承了这种言说方式并加以创造性地发扬,创作出了与博氏一脉相承但又个性鲜明的诗歌文本。
【关键词】叙述;博尔赫斯;西川;叙述的所指
“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秘密的营养系统”,它包括他生活成长的背景、经历、知识结构等构成“他”之为“他”的种种因素。尽管诗人自己不能完全说清这个“系统”,但一位有自信的诗人从来不会讳言自己意识到的所受的影响。毕竟,没有一种思想是原有的天生的。
博氏是一个丰富的存在,他的人格魅力、广阔的精神空间、敏感纯净而博大的心灵、渊博的学识等足以构成一个世界。他对于西川的影响是巨大的。当然,西川作为一位优秀诗人,他极强的悟性能帮助他更善于将自身所有的经验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他比一般诗人更急迫、更有意识地想要寻找到自己的声音和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他固然受博氏影响,不过,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事物的区别在于相似之处”,西川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在言及博尔赫斯与西川时,论者总将他们与梦、知识化、形而上这些词联系在一起,这固然不错,但我希望谈论西川在言说方式方面所受到的博氏的影响。无疑这种影响与西川所受的精神上的影响密不可分。下面将从叙述的所指方面谈论这一影响。
在我看来,叙述是目前诗歌中最主要的言说方式。但叙述的内容则取决于诗人自己的思维向度与独特的表达需求。就博尔赫斯与西川的诗歌创作而言,人们因为他们太引人注目的独特性而至少忽视了他们极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即对于事件与日常经验的呈现。他们不希望诗歌仅仅用来表达“情绪、热情、悲伤、幸福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希望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与丰富性。
一、故事进入诗歌
昆德拉说,小说是生活世界中理解人们的具体生活的思想,但诗人如何呈现这些经验与评价似乎是个问题,甚至很多诗人根本没有找到处理这些经验的合适的方法。西川与博氏对于这些经验的处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即用诗歌讲故事与展现人物。但西川与博氏绝不雷同。博氏或以写散文的笔法或以戏剧独白的形式讲述故事与塑造人物。这些作品大多出自偶然与灵机一动。西川则以谋划的姿态创作了这类作品,并且有自己独特的写法。博氏除作为一位伟大诗人,还是杰出的小说家、知识渊博的散文家与评论家。他中年时致力于小说、散文与评论写作,年过六旬重新开始写诗,他似乎不需再刻意用诗歌来展现他那精妙绝伦的编造故事的本领,而热衷于信手拈来的题目。对他而言,诗歌来自世界的赐予。不过,在他的诗集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精炼而令人叫绝的故事。
而西川以诗歌写作为主,他理所当然地要用诗歌去容纳各式各样的经验、进行种种技艺层面的尝试、打磨创造力,带有更多的有意识的形式试验性质。他的方法之一是松动小说与诗歌的边界。许多诗人既不愿意放弃诗歌这种语言的最高形式,又希望在诗中呈现故事与情节,于是诗人的表达需求与对诗歌语言的坚守相互碰撞,产生了“戏剧化的诗”。西川在这方面做得较为彻底。“诗歌只变化,不发展”、“变化意味着多样性的选择”的诗歌观念使他成为具有自觉创新意识的诗人。他深知这些探索与发现并没有成功作为保证。他也承认自己曾经走过不少弯路。
《镜花水月》在呈现一个个场景时塑造了一系列人物:陌生人、熟人、赌徒、天文爱好者……西川在其中寄寓了种种或显或隐的道德评价与思想。《厄运》通过简单的情节、场景和心理刻画塑造了众多模模糊糊但不乏真实感的人物。在西川这里,诗歌不再仅仅是传達个人体验或个人经验的了,他几乎把诗当做可以容纳万事万物的一个容器,在其中进行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的工作。他顺利地呈现了事件、场景、人物、道德评价、哲学思考。
这些诗采用散文式的片段结构成篇,但又保持了极为明显的属于诗歌的形式感,更重要的是,西川新创了属于他自己的形式,它们看似极为放松自由,却包含着许多精心构思,主要表现在对诗的结构进行整体性的构思。“美要依靠体积与安排”,当作家们写散文或小说时,由于作品篇幅较长,他们只能看到自己写作的局部,但创作诗歌时,他们能统揽全局。这也许是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融合时能够发挥的优势之一。西川在借鉴小说的写法时使诗歌在语言和整体性方面的优势都得以充分发挥。
二、日常生活经验进入诗歌
叙述使得诗歌具有了直接呈现日常小事的能力,使之更直接地和粗糙的生活世界发生关系。它通常是对一个瞬间或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的把握。相对于一丝不苟的诗歌来说,它容纳了废话(废话不等于罗嗦与累赘)、轻松、变得有趣,或许有些偷懒(这种偷懒代表写作姿态上的放松,绝不意味着创作态度上的散漫与轻浮),但却展现了诗人高于生活、时刻保持诗的思维习惯的能力,也许更直接地体现了诗人热爱生活、珍视生活的存在方式。
博尔赫斯用诗歌容纳生活经验表现在他记录梦境与旅行,写刚买回来的圆球蛋糕、看到的手杖、船这些寻常事物。他说,“对于一位真正的诗人来说,生命的每一瞬间、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是富有诗意的,因为其本质就是如此。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那么高的境界。”博氏的说法是种启示,我们日常生活中琐碎的语言与生活都有成为诗的可能性。这是对诗人创造力与感知力的另一角度的激发,也是对诗歌外延的拓展。这样做的最容易或许也是最难的方法便是写作散文诗:容易,因为它有极强的可操作性;难,因为这种写法要写得出色难,太容易浮于生活表面、流于肤浅,如何达至语言的完美也是个难题。不过,既然诗人的生命重心在于文字的存在以及寻找把文字编织成诗歌的可能性,那么对于诗歌语言的探索就是他的义务与责任。
西川在处理日常经验这一点上表现出对于博氏直接的传承性。他在《出行日记》中写“撞死在挡风玻璃上的蝴蝶”、“我顺便看见了日出”、“黑夜里两个吵架的人”……都是以叙述的口吻、散文式的篇章抒写日常的诗意。可能由于生活习惯、所处环境的差异,西川比博氏更多地关注身边的平凡事物与日常生活经验。他们的这些探索为我们开拓了思路,提供了诗的另外的可能性。西川说这种写作使他“觉得在写作能力上获得了一种解放……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写了”。西川的这些诗虽然呈现给我们新奇、个性鲜明的成熟的语言,富有诗意甚至有趣的场景与瞬间,以及诗人独特的尴尬体验,却未能创造出广阔深厚的灵魂空间,缺少更内蕴的情感,机智未能转化为智慧,尽管西川声称这是有意为之。不过,西川一组较新的诗作《三次走在通向卡得波罗海湾的同一条路上》足以使我们对他的忧虑和不满一扫而光:日常的诗意、疏朗的句式、平淡的心境、开阔的诗境、不凡的气度、收放自如的诗艺,堪称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作之一。
“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出于一首独一之诗来作诗。衡量其伟大的标准乃在于:诗人在何种程度上被托付给这种独一性,从而能够把他的诗意道说纯粹地保持于其中。”博尔赫斯已完成他编织梦想的责任。西川或许能达到,他仍在途中。诗人永远是在路上的人,他终其一生都处于成长、发展的状态。即使他已熟练掌握某些技艺,但“吾生也有涯,而学也无涯”以及“诗歌写作是个无底洞”的现实强化了诗人的求知本能,从而促使他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五卷本)[M].王永年,林之木,等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2]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谈诗论艺[M].陈重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3]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八十忆旧[M].西川,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4]西川.深浅[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
[5]西川.个人好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6]西川.游荡与闲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