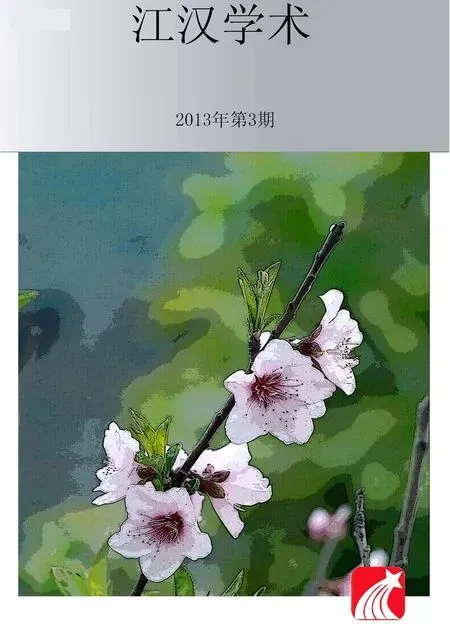个人自由原则与“侵害”概念的界定
——论密尔的自由学说
任付新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济南 250100)
个人自由原则与“侵害”概念的界定
——论密尔的自由学说
任付新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济南 250100)
密尔把他的自由原则概括为一项简单的原则,从而为恰当地保护个体自由提供了充分条件:如果这种行为没有侵害到其他人,个体便有一种自由行动的道德权利。密尔认为他的自由学说是发生在旧主题上的新变异,“自由与权威”这一老问题需要不同的,更加基础性的对待,因为现代文明社会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为了澄清这一观点,他区分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并对这些阶段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关于密尔自由理论最明显的争议是随着竞争性的道德视域变幻的“侵害”的概念,围绕对“侵害”概念的界定,通过对密尔文本的解读以及分析研究者对密尔学说的重新诠释,我们可以发现密尔的原则在根本上是不完善的,自由原则的应用不能够被寄希望去解决相互冲突的道德视域之间的争论。
自由原则;自我认知;侵害;道德权利;密尔
作为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一直是研究的热点①,这些论著主要从自由与个性、平等与民主、人类进步等方面论述了密尔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这些思想认为密尔继承并发展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立足社会现实,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典政治自由主义的现代转型。总体来说,学者们对密尔的自由主义学说赞誉多于批评,本文则试图找出密尔自由原则的缺陷所在。密尔在《论自由》中很清晰地论述了其主要写作目标:提出一项非常简单的原则,以此用一种强制的方式来对个体的社会行为进行绝对的控制,无论此种方式是一种以法律惩戒为表征的身体强制,还是公共舆论所产生的道德强制。笔者认为,关于密尔自由理论最明显的争议是随着竞争性的道德视域变幻的“侵害”概念。围绕对“侵害”概念的界定,通过对密尔文本的解读以及分析研究者对密尔学说的重新诠释,我们可以发现密尔的原则在根本上是不完善的,自由原则的应用不能够被寄希望去解决相互冲突的道德视域之间的争论。
一、密尔的自由原则及其特点
密尔把他的自由原则概括为一项简单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是:
权力能够违背个体的意志并被恰当地适用于文明社会中的每一位个体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防范个体对他们的侵害。个体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身体还是道德,都不足以成为伤害他人的充分理由。[1]223
这样,自由原则就为恰当地对个体的行动自由进行限制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个体的行为侵害到了他人时,个体的自由才应该被法律或公共舆论所限制。换言之,这一原则为恰当地保护个体自由提供了一个充分条件:如果这种行为没有侵害到其他人,个体便有一种自由行动的道德权利。他的全部行动部分地仅仅关注于他自己,他的独立性及其权利都是绝对的。[1]224
密尔告诫读者,他的自由学说仅仅适用于人类自发的演进历程,即在他们自己的判断和偏好的指导下获得自我发展或改善其生活的境遇:“自由,作为一种原则,仅仅适用于人类能够进行平等和自由的协商的时间状态。”[1]224即使一个人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但如果他或她没有最低程度的智识能力,该个体也不能被认为处于自由状态。这样,自由原则就不适用于孩童、处于法定年龄之下的年轻人或者是那种种族被视为野蛮人的社会状态。但是,对所有文明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人而言,强制,无论是以直接的方式还是针对不服从而施加的痛苦和惩戒的方式,作为一种满足自我利益的手段都不再被认为是正当的,此种行为只有为了他人安全的缘故才被视为正当的。
除此之外,密尔指出自由原则还具有四个明显特点:可行性、道德优先性、决定性和新颖性。他认为,自由原则是具有可行性的,因为每一个个体实际上都可以做出不伤害他人的纯粹“自我认知”的选择。密尔论述道,“自我认知领域”包括所有仅仅影响到其自身的个体生活和行动,或者,如果说它也影响到其他人的话,也仅仅是在他们自愿参与下进行的。当我们仅仅提及“个体自身”时,其直接寓意是:任何影响到个体自身的东西通过个体对他人所产生的影响。[1]225
自我认知的行为并不会对其他人造成损害,因为其他人没有直接受影响而违背他们的意志:任何对他人的伤害首先都伴随着对自身的伤害,自我伤害并不会造成对他本人的伤害,除非他的自我伤害是他违反了对其他人或人类的明显而又被确定的责任。[1]281这样,自我认知的领域就成了人类自由的恰当领域,换而言之,在这一领域中,自由被社会正确地保护。
密尔认为,自由具有道德优先性,这意味着自由原则应当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公理被文明社会所接受,无论这个社会具有何种文化和道德环境。自由原则对公民自由而言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无论政府采取何种形式,尊重这些原则的社会在实质上都是自由的,当然,也并不存在绝对的和毫无限制的自由。”[1]226但是,只有自我认知领域被以任何一个可接受的文明社会的文化和道德规范的方式进行界定时,自由原则在文明社会中的普适性才是可能的。更为明确的是,“侵害”的概念(对他人利益的侵害)只是针对有成熟技巧的人们而言的,与它的独特的道德和文化观念无关。
密尔暗示道,自由原则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它能够在文明社会中个体自由的合法性范围方面给我们以明确的答案。值得强调的是,密尔在最佳证据的支撑下获得问题答案的必然性。例如,当“说服性的理由”被平等的提供给冲突着的观念的时候,他并不满足于理性的“信仰的悬置”,密尔论述道:“事实的部分决定一个完全的智识的判断。”[1]245这样一种先在的由以赛亚·柏林提出的假设(我们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不可测度的多元的价值,这些价值之间有着无法解决的冲突)似乎与密尔的思想有着迥异的差别②。事实上,提出自由原则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确保个体拥有在合理证据支撑下作出判断所需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其中包括潜藏于自由原则内部的判断。在密尔看来,思想和言论自由对所有被确证的观点和信仰来说都是必要的。
与我们的观念产生冲突和争执的完全自由是为了行动的目的证实其真实性的条件,没有其他的术语能够为人类的才能提供理性的确证。[1]231除非个体已经平等地介入到与其对手的争论过程,并已凭借流行的理性调查的标准(仅仅作为与公共舆论的对立面)在争论的两端做出判断,那么,他就不会赞同“真理应该被理性所掌控的方式”[1]244。“因此,关键在于对这一原则的真正道德与人类主题意义上的理解,如果不存在所有重要真理的反对者的话,要设想出他们就是无法完成的任务。”[1]245简言之,智慧并不包含关于世界本性的优先性的偏见,这种偏见实际上试图预测未来的思想和协商过程。相反,它由较晚所产生的信条所组成,只要人类在此时能够分辨出合适的证据而不是维持一种变更的状态。
密尔强调自由原则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的新颖性。他强调“这个实践性的问题,对社会所能施加于个体之上的合法性权力进行了划界”[1]220。密尔认为,甚至在现代英国,政治历史的特殊情况已经表现出了对政府直接干预个体行动的嫉妒,事实上,没有被承认的、主张政府正当与不正当干预的原则能够被按照惯例加以检验。[1]223英国人对政府干预的反感不是源于对个体独立性的捍卫,而是源自对政府的一种习惯性的认识,即政府所代表的利益违背了公共利益。[1]223实际上,多数民众都不会为其所不喜欢的、不合习惯的或古怪的自我认知行为被诽谤为不道德而感到疑惑。那些招致司法惩罚风险的人认为,诽谤是有影响力的,正因如此,在社会禁止下的专业见解在英国就不如在其他国家普遍了。
密尔担心的是,当民主取得进展之时,英国的多数民众受制于政府施加于他们的权利之上的权力、施加于他们观点之上的观点,个体自由将很有可能暴露在政府权力的入侵面前,就像在公共舆论领域已经发生的那样。[1]41
二、旧主题的新变异
密尔认为他的自由学说是发生在旧主题上的新变异,“自由与权威”这一老问题需要不同的、更加基础性的对待,因为现代文明社会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为了澄清这一观点,他区分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并在“在自由与权威之间抗争”一章中做出了不同的解释。[1]17
在最早阶段,抗争被一般性地认为发生在被统治的民众(由大多数民众组成)与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精英之间。自由意味着防止统治者的暴政,换言之,自由即是探讨政府合法性权力的限制边界。政治自由通过如下方式被确保:首先,通过获得对特定政治自由或权利的认可,如果这些政治自由或权利被统治者所破坏,个体的抵抗或群体的反抗被视为正当的。其次,通过建立宪法审查机制,分立政府权力,并使一部分统治者可以反对另一部分,使民众避免落入他们的统治者对其施加不正当侵害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有限政府的学说并不涉及任何对个体自发性的见解,它纯粹是为了使多数民众能够免于被少数特权阶层人士施加的政治迫害。
在文明社会的第二个阶段,“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抗争被重新解释为:一个民主政党与其他政党为了控制政治权力而发生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对选举和临时性统治者的新的需要成为了多数政党运作的主要目的,无论这种政党在何时出现;因此这种观点就取代了以往对统治者进行限制的见解。”[1]218自由不再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变成了为了使多数民众感到政治愉悦而能够裁撤临时性代表的自我统治。现在所需要做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身份应当被民众所认同,他们的利益和意志应当成为国家的利益和意志。国家不需要被保护以反对其自身的意志,因为没有必要担心国家施加于其自身的“暴政”[1]218。这种共和国政府的学说不再涉及对任何个体自由的尊重,它也仅仅导向使政府的权力为了多数民众的意志而负责,因为他们设想“民众不需要限制他们自身的权力”[1]219。
第三阶段开始于美国,人们认为即使政府是对多数民众负责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仍是必需的和重要的:
大众的自我统治并不是每一个个体自我的统治,而是每一个人被其他所有的人所统治。而且,民众的意志意味着最大多数人或者民众中最活跃部分的意志、多数人或者那些成功地使他们被作为大多数所接受的人;民众可能渴望镇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因此在掌权者对社群负责的情形下,对政府施加于个体之上的权力进行限制并不会失去权力本身的重要性。[1]219
为自由的抗争变成了限制共和国政府的抗争,换言之,也是为了代议民主体制的抗争,即统治者对大多数人的审慎的意志负责,同时,具备合法性的政府权力被宪法审查机制和一系列基础性的政治权利所限制。现在,自由意味着为了保护少数人免于被多数人和由其选出的代议制机构的不当侵害,而在特定法律限制下的大众的“自我统治”③。但是,这种对大众政府进行限制的学说仍然没有表现出在密尔视域中的那种对个体自由权利的充分尊重。这种学说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强调使政府的权力对民众的审慎的意志负责,这种审慎的感觉将会使政府的合法性权力受到限制成为必需。简言之,这种自由需要大众限制其立法权威,从而不会侵害到所有公民的特定权利。
自由原则在文明社会的第四个阶段的表现是:公众观点在增强其与多数民众观点和习俗的移植性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更具体地说,中等阶层增长的权力为其打上了商业色彩的烙印,其他阶层的人们会认为密尔不恰当地将道德和文化的停滞与衰弱和任何一致性的社会群体联系在了一起:“对人类未来前景最严肃的危险就是商业精神影响的失衡。”[2]198事实上,密尔论述到: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可能宣称文化和道德影响并不会平等地波及到社会各阶层,而是将会对商业阶级发挥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波及到了贵族制时期的英国。[2]196在第四个阶段,自由和权威之间的抗争采取了一种新的维度:个体不仅需要来自于政府权威的保护,也需要保护压制性的中间阶层的观点,从而在根本上不依赖立法或其他政府命令的基础上达成混合性的利益目标。
密尔特别指出,作为商业精神的平衡力量,社会需要一个农业阶级、一个闲暇阶级和一个知识阶级:
为了检测商业精神的唯一发展趋势,在政治领域中需要做的不是公共舆论不应当成为或必须成为统治力量,而是为了建构最好的公共舆论氛围,在社会的某个领域中应当存在支持不同与大多数的观点与情绪的社会力量。这种支持力量的形式可能最好被设想为一个时间、地点和环境的问题。但是(在一个商业国家,和一个军事精神已逝、崇尚人道主义的时代)毫无疑问的是,组成这个支持性力量的元素就是:一个农业阶级、一个闲暇阶级和一个有知识阶级。[2]198
密尔自由原则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关注的是个体的自发性,而不是秩序良好的政治格局。它是个体自由原则,而不是政治自由原则,它划分了在社会权限之外的行动领域,在这一领域中,个体在没有法律、道德法则和社会习俗的干预下恰当地选择他所喜欢的行为方式。相反,早期的政治自由原则至多规定了生活在一个政府权力被限制的社会中的个体的平等权利,它们没有限制公共舆论,本质上是政府权威的合法性界限,而且,它们不保护与普通多数民众的纯粹兴趣相悖的、特异的个体观点与实践。
在密尔看来,个体自由在以前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因为迄今为止,市民社会都是在社会习俗力量的推动下盲目地向前演进。[1]220换言之,在人类行为方面,大多数民众多半纯粹地诉诸于与其他人相似的感觉表征来证实自己的好恶:“引导他们观念的实践性原则便是,在每一个人的思想里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每一个人都应该像他那样行动,那些他所同情的人们也是如此。”[1]220-221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是按照习俗行事,却不对行为后果进行反思和评价,那么,无论多数人所青睐的行为规则是什么,对这种原则本身就不能有任何的限制了。密尔确信在他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事物先在性的条件,宗教信仰除外:
大多数人,满足于他们现在“所是”的生活方式(因为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塑造了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方式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足够好的,而且,自发性塑造的不是在多数民众中的道德和社会改革者的观点,毋宁说是那些心怀妒忌、制造麻烦,或许还阻碍多数民众利益实现的改革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对人类而言都是最优的。[1]261
而且,密尔对其自由原则的未来并不持乐观态度,因为担心“习俗的专制”将最终会被强化:“人类的专制,无论是统治者的还是市民的,都会将他们自己的观念和倾向作为一种统治规则强加给他人,通过对权力进行限制也很难遏制这种趋势,权力不是在缩减,而是在增长。”[1]223实际上,密尔指出,像孔德这样的社会改革者所提出的疯狂建议(社会加之于个体之上的道德专制),超越了包括古典学家在内的、主张最为严酷的法律统治的政治理念。[1]227不幸的是,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体制在20世纪的兴起在最大限度上证明了密尔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这些社会系统大多处于混乱的状态,并因此而出现密尔所预测的由于某种和谐而导致的停滞。
三、“侵害”究竟意味着什么?
密尔在《论自由》中谈到了两个相互关联组成一个统一学说的公理:
这些公理是:首先,个体不必为他的行动对社会负责,只要这种行动只关涉到他自己,没有影响到其他人(自由原则);其次,这种行动对他人的利益存在影响,个体就应当对社会负责,如果其他个体向社会寻求保护时,个体或许要服从于社会或法律的惩戒(权威原则)。[1]292
《论自由》所传递的信息显然是简单的,这个信息就是:每一个个体都有绝对的道德权利去按照他所喜爱的纯粹自我认知行为去行事,因为这种行为不会侵害到他人;而社会则有合法性的权威去规约每一个个体的他人认知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会侵害到他人。简言之,自由原则对“社会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成员的自由权利”陈述了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当且仅当个体的行为纯粹是自我认知时,个体应当享有这样一种权利。
有些评论家认为,自由原则表面的简单性是颇有欺骗性的。密尔并不清楚“侵害”的具体内涵,他模棱两可的观点不能被正确地加以修正,从而挽救其简单原则。[3]针对这种批评,很多学者试图补救密尔的学说,例如,瑞斯(J.C.Rees)将“侵害”的概念修订为“违反正义的规则”[4]168,在此,他将对权利观念的理解作为理解其他规则的关键。伯杰(F.Berger)也采取了类似的界定:一方面,他敞开了“侵害”的概念,另一方面,他将密尔学说的核心观念概括为:“只有当行使这种自由侵犯了他人更高级的权利时,对自由本身的干预才能被证明为正当。”[5]375但是,将“侵害”定义为对权利的侵犯并不能拯救密尔的理论。“侵害”的此种界定暗示着无法对社会权威本身进行划界,因为权力是社会权威的产物。法律权利被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所界定和分配,而不能由法律提供保护的道德权利则被大众舆论所表征的传统和习俗所界定和分配。这些法律和习俗能够被社会正义的规则所表示。但是,如果对“侵害”的界定完全与这些规则相一致,那么,密尔的自由学说就会分崩离析。
首先,在缺乏一种一般性的正义理论的情形下,“侵害”的概念将会随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改变,自由原则也不能解决在理性的个体之间或处于不同道德视域的公民社会之间的争执。其次,尤为重要的是,即使有一种普遍性的正义理论被提出,在我们习得了各种社会所赋予个体的权利的细节之后,人类自由的恰当领域仍然能够被界定出来。对私人行动的界定因此就落入了社会权限的范围内,这就对密尔的见解(社会有合法性的权威去干涉个体的自由)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进一步来看,这种关于密尔学说的阐释允许社会可以合法地移除任何个性的领域,例如,通过赋予每一个个体一种法律权利,从而使每一个其他的个体都应当按照第一个要求他们这样做的个体的意愿来行事。这样的一种社会权利的学说被与密尔同时代的外交大臣波普(Samuel Pope)所辩护。在极端正义理论的影响下,“侵害”概念也包括了纯粹的“不喜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免于痛苦的权利,这种痛苦可能会偶然地由其他人做了他不喜欢的事情所引发。但正如H.L.A哈特所说:
因为造成这种形式的痛苦而施加于人们身上的惩罚,应当等价于因为其他人反对他们的作为而对他们的惩罚,能够与功利原则组成一个融洽概念体系的自由原则是做那些没有人明确反对的事情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无效的。[6]77
密尔对“侵害”概念界定方式的反应和对自由原则的阐释能够从他对波普的极端“社会权利”理论的答复中把握到:
这一原则是极为恐怖的,其危害性远甚于任何一种对自由进行干涉的原则;没有不能被它证明的对自由的侵害行为;它承认没有赋予自由任何一种权利,一旦我认为有害的某种观点从某人口中流出,它就侵犯到了所有的社会权利。这个学说赋予了人类一种既定的利益,它关涉到彼此之间的道德、智力,甚至是身体上的尽善尽美,而且它按照它自己的标准来宣称。[1]288
重要的是认识到波普的学说纯粹是一般性方法的一个变体(一个极端的变体),这种方法将个体自由的恰当领域视为与社会关于个体权利或关键性的利益是什么的判断相适应。这样,除非密尔困惑到一种极端的程度,否则他不能建议我们沿着瑞斯、伯杰的路线来对“侵害”进行界定。
如果密尔的自由原则真如他所说的那么简单,那么他应该如何来定义“侵害”的概念呢?我们知道,密尔必须从逻辑上将“侵害的意义”维系于特定公民社会的法律和习俗,否则,加诸于个体之上的社会权威将无法受到限制,即使关于“侵害的意义”难以处理的争执不会在有着不同道德观点的个体之间出现。更为明显的是,密尔需要能够说出一些不应该被界定为“侵害结果”的“结果类型”。换言之,当一个人没有被侵害时,社会中的大多数成人必须要分享某种信仰。“无伤害”必须被认为是个体的自我改进能力,无论权利被其所处的社会法律或习惯如何界定,也无论它的社会习俗所认可的是何种善行。
密尔明确地认为纯粹自我认知的行为对其他人根本不会有直接的影响,或者,如果有影响的话,仅仅是在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内。[1]225他直接将“侵害”等同于“可以察觉的侵害”或者“可以察觉的损害”,这就暗含着“侵害”从来不能被界定为没有其他侵害证据下的纯粹的厌恶或情感上的痛苦。表达一种宗教观点或者读一本书是纯粹自我认知的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没有对其他人造成明显的伤害(例如身体上的损害或限制、健康的恶化,或者令人失望的契约期望等)。其他人或许不喜欢这些自我认知的行为,他们强烈的厌恶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痛苦,或许可能会造成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的伤害,其中包括原初的代理人。但是他们的痛苦是自我引导的,因为它主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态度和欲求。这并不是纯粹自我认知行动的直接结果,因为其他有着更为宽容态度的人并没有经历过什么痛苦。而且,没有人需要感知这种痛苦或苦难,因此所有人都能够学会容忍这种行为。因此,任何保持不宽容并为自我认知行为感到痛苦的人,而不是行为的代理者,对痛苦以及他持续遭受到的侵害负责。
哈特似乎认为对侵害的恰当界定是次要的,但是他也承认个体自由的辩护者面临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6]89如果“伤害的意义”注定是以此种方式加以界定,那么,任何特殊社会加诸于个体之上的权威就能够被限定在他的“他人认知行为”的界限之内。而且,针对自由原则应用的难以解决的争执也不需要产生,即使不同的个体和社会不赞同在既定的情形下被证明侵害到他人的行动,因为这个原则认为个体自由是具有合法性的,如果除了其他人的厌恶或痛苦,没有别的证据表明对他人已经造成了伤害的话。确证这种“可以察觉的侵害”是否存在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其回答依赖于有矛盾的道德或文化价值。这样,宗教表达自由和读书自由一样,都应当受到市民社会的保护。
综上所述,《论自由》所传递的信息显然是简单的,这个信息就是:每一个个体都有绝对的道德权利去按照他所喜爱的纯粹自我认知行为去行事,因为这种行为不会侵害到他人;而社会则有合法性的权威去规约每一个个体的他人认知行为,如果这种行为会侵害到他人。换言之,这一原则为恰当地保护个体自由提供了一个充分条件:如果这种行为没有侵害到其他人,个体便有一种自由行动的道德权利。但是,密尔的原则在其本性上不完善的,关于密尔理论最明显的异议是随着竞争性的道德视域变幻的“侵害”的概念,因此自由原则的应用不能呈现出伤害概念的判断,这种判断不能够被寄希望去解决相互冲突的道德视域之间的争论。即使我们忽视密尔在此所表现出来的令人奇怪的沉默,提供一个合理化的对“伤害”的界定,然而依然清晰的却是,自由原则不是也不能是密尔所探寻的一项非常简单的原则。
注释:
① 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内学者涉及密尔自由主义的论文有二十多篇,国外学者如麦克罗斯基、柯亨、约翰·瑞斯等都有关于密尔自由主义的重要论文。专著方面,国内比较重要的有:陈鸿瑜:《约翰密尔的政治理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张明贵:《约翰弥尔》,(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周敏凯:《十九世纪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比较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国外方面,(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版;(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其中都有相关章节论述密尔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
② 在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1969)导论部分中,柏林论述道:“密尔自己似乎确信在价值判断领域存在可获得的、可传达的、客观的真理;但是在提供个体自由,并展开调查和商谈的社会领域中却不存在发现真理的条件。我的观点并非以上所述,毋宁说,因为一些价值可能会发生内在的冲突,必须要从原则上发现一种模式,以使冲突的价值观念能够在其中保持和谐一致”(pp.10-11)。
③ 这种自由的观点被《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所强调,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及约翰·杰伊鼓励纽约州民众批准美国宪法。
[1] J.S.Mill.On Liberty[M]//John M.Robson.Collected Works of J.S.Mill(XVIII):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London:Rownled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7.
[2] J.S.Mill.De Tocqueville on Democracy in America[M]//John M.Robson.Collected works of J.S.Mill(XVIII):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London:Rownled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7.
[3] John Gray.John Stuart Mill on Liberty, Utility and Rights[M]//J.Roland Pennock,John W.Chapman.Nomos XXIII: Human Right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1:80-116.
[4] J.C.Rees.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M]//D.D.Raphacl.Problem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Pall Mall Press, 1970.
[5] Fred B.Berger.Mill’s Substantive Principles of Justice:A Comparison of Nozick[J].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84,19(4):373-380.
[6] H.L.A.Hart.Law, Liberty and Morality[M].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2013-02-28
任付新,男,山东聊城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B561.42
A
1006-6152(2013)03-0100-06
责任编辑:郑晓艳
(E-mail:zhengxiaoyan1023@hotmail.com)
——读《论自由》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