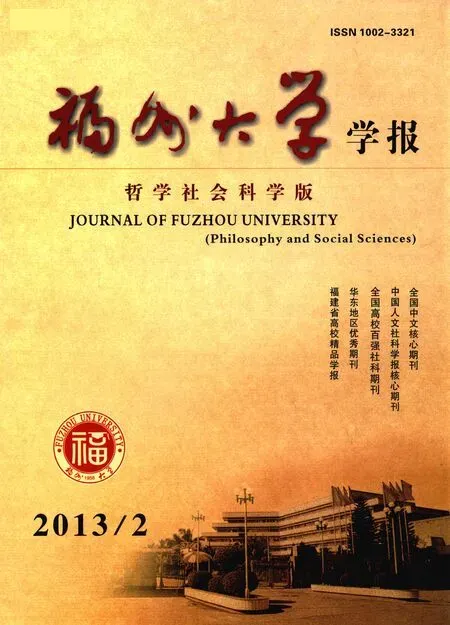本真的生命 诗意的生存:解读劳伦斯自然态的身体理念
李碧芳
(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自然态的身体是奥尼尔提出的身体五态之一的世界态身体概念下的一种表现状态。在描述世界态身体特征时,奥尼尔推出了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即指人类以自己的身体来思考自然与社会的创造性能力。奥尼尔认为,社会最初的身体就是一切人类文化的未驯化的身体(wild body)。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兰克(Otto Rank)也曾经提出,身体的拟人化投射体现出对于整全性和同一性的关注。依照兰克的观点,“肝、脐、头、口、上椎、肠以及子宫,都属于探寻微观世界的过程中的符号源泉”,而“自动物崇拜始,从巴比伦经埃及和希腊而进入基督教,在这条迂回之路上,发生了某种双重转换:从微观宇宙的角度看,是从‘下半身’文化进入‘上半身’文化;而从宏观宇宙的角度而言,则是从尘世文化转向天国文化。根据这一模式,世界的呼吸犹如身体的呼吸,世界和身体仿佛都同时承载着一个物质性的灵魂和一个精神性的灵魂,也就是生命的呼吸。……这样的生命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感触到进出来去,从下半身到上半身,直到理性和智力成为灵魂的居所。依此方式,世界化为肉身,为世界之逻各斯,即为上帝。”[1]基于此,“人类与世界之间,与自然界和野生动物之间,与地球上纷繁多样的家庭文化之间,都存在亲密的关系”[2]。
奥尼尔的自然态身体概念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得到了多层次的文本阐释。作为小说艺术家的劳伦斯,在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中除了他的小说以外,还有他的小说理论。劳伦斯的小说观在其《小说为何重要》一文中得到明确的阐释。他以为,“小说是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3]。劳伦斯所说的“生活”有两层意思。其一,首先要由人的身体去感知生活,而不仅仅是依赖理智或纯粹的精神。其二,生活意味着人的全方位发展。基于以上观点,他的小说创作就十分重视探索和揭示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他善于将人放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之中加以考察,从而真正揭示人与宇宙之间的相关性。劳伦斯的小说观体现在其作品中的多层次的主题之中,它们最终可归于两大类,即自然的主题和性爱主题,而这两大主题在其作品中又具体体现在其倡导的自然态的身体理念之中。归结起来,劳伦斯自然态的身体理念主要表现为他对传统田园式生态农场的眷恋、对人与自然相生相成关系的憧憬和对两性自然的身体对话的追求三个方面。
一
奥尼尔的自然态身体概念突出自然的神性,他提出的“社会最初的身体”即是宇宙原初的存在,是上帝创造的伊甸园,亦是人类灵魂最纯洁的栖息地。古往今来,多少作者在其作品中追寻人类诗意的生存,劳伦斯也不例外,他的作品中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他对故乡传统田园式生态农场的眷恋。劳伦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代。他出生于伊斯特伍德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在劳伦斯的记忆中,他儿时和青年时期的故乡风景秀丽,水库、森林、良田、池塘和农场是这片谷地的主要景观。那里没有汽车,虽发展矿业,但矿井也只占田野的一小角落,无碍大观,而位于它左前方的安德伍德森林是传说中英雄罗宾汉出没的地方,它使那片谷地平添了几分传奇的神秘色彩。在他的笔下,这些乡村和田野都象征了“森林与往昔农业的古老英格兰”的乐土。在其许多作品,诸如《春天的阴影》、《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以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劳伦斯一遍又一遍地回味古朴幸福的田园式诗意生活图景。在《春天的阴影》中,劳伦斯借男主人公赛森重温了故乡的秀丽风光和自然的生态。赛森离别故乡七、八年,再度回乡,心情十分愉悦:
穿过树林的那条小径,有一段路轻松地蜿蜒于一条小山坡的顶上,周围是一片长满细枝条的橡树,它们的叶片刚刚变成金黄色。而在地面上,到处是香车叶草,成片的山靛和一簇簇的风信子,组成了一块块菱形的图案。两棵砍倒的树仍然横躺在小路上。赛森跳跳蹦蹦地奔向一片崎岖不平的陡坡,又来到一片开阔的田野,这片田野朝向北方,仿佛是从树林向外边看的一扇大窗户。他停了下来,越过小山顶上的平坦田野,注视着在那片光秃的高地上零乱地坐落着的小村庄。它好像是从飞驰的工业列车上扔下来,遗弃在那里的。村里有一座僵直的新式灰色小教堂,还有一幢幢一排排零乱坐落着的红砖住宅;村子背后是闪着亮光的矿井井架和隐约可见的矿山。一切都毫无遮盖,暴露在露天里,连一棵树都没有! 这一切全都没有变。[4]
而在其富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中,米丽安生活的威利农场,就是劳伦斯魂牵梦萦的故乡乐土。他热爱威利农场:
他爱那个简陋的小厨房,男人穿着大皮靴在里面踩得咚咚响,那条狗睁着一只眼睡觉,生怕给人踩着;入夜厨房里桌子上挂着盏灯,一切都静悄悄的。他爱米丽安家那间低矮的长客厅,客厅里那种传奇的气氛,又是鲜花,又是书本,还有高高的花梨木钢琴。他爱那些庭院和坐落在光秃秃的田边的红屋顶房子,这些房子向背后的树林伸展,仿佛在寻求庇荫,从山谷这边向下延伸再一直连接到另一边的荒山坡都是一片旷野。只有到了那儿,他才感到精神振奋,其乐融融。他爱莱佛斯太太,她为人古雅脱俗,玩世不恭。他爱莱佛斯先生,他为人热情,充满朝气,煞是可爱。他爱埃德加,每次他去,埃德加都喝得烂醉。他还爱那些小伙子和孩子,还爱看门狗比尔——甚至还爱老母猪赛西和叫替浦的印度斗鸡。[5]
这里劳伦斯所赞美的自然和米丽安家人的生活,其实正是未受工业化污染的古朴醇厚的田园生活,是劳伦斯儿时的故乡美好记忆。正如劳伦斯在《诺丁汉矿乡杂记》所言,在他的眼里,他的故乡“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美丽至极的乡村”,而正由于他对儿时故乡怀有如此深刻的爱,他多次将儿时故乡设置为伊甸园般的故事背景,烘托一对对如亚当夏娃般纯粹的恋情。《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中“笼罩着昔日撒克逊人到来时的那股子原始灵气”的克罗克汉农舍遭遇了艾格伯特和温妮弗莱德新婚两年充满激情的甜蜜,《虹》中“在运河这边安宁的土地上,在阳光灿烂的谷地上”仍然原始、偏僻的玛斯农庄叙述了布朗温一家三代人心灵的浪漫传奇,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麦勒斯和康妮相识相知、唯一一小片不被工业化机器吞噬的童话般的大森林,见证了康妮像花一般神奇地由枯萎而重新灿烂的升华过程。
劳伦斯对儿时田园般原生态故乡的眷恋其实折射出了他的自然观和生态哲学思想。他推崇自然态的生存环境,倡导原始主义,强调自然、本能和简朴归真。如果我们从奥尼尔的自然态身体理念来谈论的话,劳伦斯颂扬的就是“初民的神话”,这些神话“不只是有关真理的寓言或诗性修饰……这些神话是人类秩序和共同福祉不可或缺的源泉”[6]。
二
奥尼尔推出的拟人论强调人类需要遵循的公共准则是“自然重于生命,生命重于社会”[7]。这一公共准则体现了人类与世界态身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与劳伦斯的“人与万物同宗同源”的思想不谋而合。在追溯人类祖先的生存状态时,奥尼尔描述道:“往昔的先辈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体来思考宇宙,并通过宇宙来思考自己的身体,彼此构成一种浑然一体、比例得当的宇宙模型。”[8]奥尼尔所描述的境界近似于劳伦斯作品中阐释的观点:自然景物是人的思想的象征和外在表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内在的精神交流。换句话说,人与自然是相生相成的平衡关系。劳伦斯这一思想体现在其诸多的作品之中。《儿子与情人》中有许多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场景,其中第一章就有一个这样的场景描写:莫雷尔太太怀上保罗的时候,曾与酒醉的丈夫发生口角,被丈夫赶出屋外。当时她十分生气,还抹着眼泪,可是月光下的百合花却安抚了她受伤的心灵,让她平静下来。劳伦斯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月光下的花儿似乎正在伸展开来。她把手指戳进百花蕊里,映着月光手指上简直看不出金黄颜色来。她弯下腰来看看花蕊上的黄色花粉,可是花粉看上去却是黑糊糊的。她深深吸了一口香味,香得脑袋也晕了。
莫雷尔太太靠在花园门上往外眺望,一时出了神。她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除了感到有点恶心,还意识到胎儿的存在,她就象这股香味一样,完全融化在晴朗,苍白的夜空中了。过了一会儿,连胎儿也跟她一起融化在这熔炉里。她和群山、房子、百合花静静栖息在一起,一切仿佛共同浸沉在一场昏睡之中。[9]
这里,人、月光和花形成了十分和谐的相生相成状态:月光照着人和花,花在月光中开放,人触摸花,感受绽放的花蕊和花香,月光之中的花蕊走进了人的身体,胎儿也感受到了花蕊的香气,花蕊的香气融化了人的心,人解脱了烦恼,心归于宁静,与月光、花和周围的群山、房子融为一体,进入宇宙的沉睡之中。此处,宇宙的大爱与宽容,与现实生活中莫雷尔夫妇不和谐的夫妻关系形成强烈的反差,更凸显了人物内心的孤独感。
另一部小说《虹》也有此类经典的场景设置。第十五章“狂欢之苦涩”描绘了厄秀拉和斯克里宾斯基之间纠结的情感,而他们的恋情在冷峻的月光下结束:
在闪烁的亮光中,厄秀拉使劲地抓住他,仿佛突然间有了毁灭之力,两条胳膊环抱着他,箍得紧紧的,同时嘴巴在寻找他的嘴,猛烈地要撕裂嘴似的吻着他,一下又一下不停地吻,甚至他的身体被箍得无力,他的心怕这女妖凶猛地叮啄一般的吻怕得软弱下来。海水又一下冲刷着他们的脚,厄秀拉不理睬,根本没发觉。她好像要把尖尖的鸟嘴紧紧按着直至取出斯克里宾斯基的心脏。……
好像晕过去了,他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他觉察到厄秀拉胸脯异常的起伏,抬起头来看。厄秀拉的脸像月光下的一尊偶像,眼睛呆呆地睁着。从她的眼里慢慢地流出一滴泪水,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斯克里宾斯基觉得好像有一把刀正插入他僵死的身体。……
斯克里宾斯基觉得,要是再看见厄秀拉,骨头都要碎,身体会被压垮,永远就被抹掉了。[10]
厄秀拉和斯克里宾斯基的恋情从一开始就充满变数。他们俩的相互吸引完全出于肉体情欲的需求,这对于正在追寻完美生命的厄秀拉来说,自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她深知自己对精神的更深层次的追求,而斯克里宾斯基在身体上虽接近她,但在精神上却与她远隔千里。他们俩分分合合,互相折磨,拖延着分手的时间,直至这个月光下的夜晚。这里月光有多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月光像一轮明镜,让他们俩看清了各自的真面目,也看清了各自真实的需求。其次,月光代表厄秀拉强大的生命欲求。厄秀拉借助月亮的能量正经历着由凡人向神的蚕变,也正是这个蚕变吓住了斯克里宾斯基,让他不禁冷颤,不禁退缩。再者,月光也代表厄秀拉强大的女性意识。《虹》叙述了布朗温一家三代人的恋情,每一代恋情中男性和女性都形成强大的力的对峙,前两代虽然女性意识也都略占上风,但都以两性之间的某种妥协告终,而到了厄秀拉这一代,女性意识尤为强大,不肯妥协,也因此她们对男性造成的压力也最大。这个片段经典精妙之处在于它将人的情感放置于自然之中接受自然力的考验,它让人进入宇宙磁场,相吸者与之合二为一,而相斥者则与之分道扬镳。这大概就是劳伦斯弘扬的本能与本真吧。
如果说在营造人与自然的相生相成关系时《儿子与情人》选择了相互融合的方式,《虹》选择了相互贯通的方式,那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则选择了相互愉悦的方式。劳伦斯将康妮和麦勒斯的爱巢设置在尘嚣不远处暂时被现代机械遗忘的一小片森林之中。这片森林原本是麦勒斯隐居的地方,康妮散步时偶然撞见了,就被它的宁静和超凡脱俗的境界深深吸引。她深入其间,探到了上帝创造的伊甸园,而自己与麦勒斯也成了上帝创造之子亚当和夏娃。在劳伦斯笔下的伊甸园,人、动物、植物浑为一体,是彼此快乐的源泉。小说第十章描写了母鸡孵小鸡给康妮带来的生命震撼。春天,是生命萌动的季节。作为背景的榛树、报春花和紫罗兰是春天的美丽衣裳,而母鸡孵小鸡和小鸡的调皮好动很好地诠释了春天的内涵和原初生命的神秘与快乐。人置身其中,只能一起勃发生命,一起萌动,一起快乐。这种人与自然互动互乐的情景,恐怕是人间最美的图画了。
人与自然相生相成的理念,人与自然互动互乐的伊甸园般美景的呈现,从自然态的身体理念讲,就是世界与身体共同呼吸,共同承载“一个物质性的灵魂”和“一个精神性的灵魂”,而在劳伦斯看来就是对人类诗意生存状态的最高追求的基础。
三
在奥尼尔设置的世界态身体的宇宙体系中包含了男性与女性在内的二元论符号象征,对于男性与女性这一两极关系,他认为“在男性身体与女性身体之间……并不在于强行让一边高于另一边,无论哪一边,如果失去另一边,都是不可设想的”[11]。很显然,奥尼尔此处称赞的是两性的平等和互补关系,与劳伦斯推崇的两性自然本真的身体对话理念十分吻合。劳伦斯在其作品中描述了许许多多男男女女的情感故事,有满足于肉欲的,有满足于物质欲的,有满足于支配欲的;有纯精神的,还有灵肉合一的。无论他的描述指向何方,他都明白,他是在预言,他是用林林总总的男女情事向世人说明性的真谛。在所有的情感故事中他最推崇的是身体的自然对话。两性自然的身体对话以两性之间的平等、动物性本能、对性爱宗教式的礼拜虔诚和灵肉合一为基础。依照劳伦斯的理解,两性之间需要双方抛开自我,男人不再自以为是世界的征服者,而女人也不能过分地期盼自由和独立,他们实际上共存于一条生命之河里。“一个女人就是一股喷泉,泉水轻柔地喷洒在靠近她的一切;一个女人就是一道震颤的波,她不为人知也不为己知地震动着,寻找着另一道波的共震……男人也一样,他的生活和行动也有着自己的存在价值。他是一道生命的溪水,按照一定的方向向某个人奔流,这个人接受他的生命之水并用自己的相回报,这样相就成了一个完整循环,从而才有了和平。”[12]
劳伦斯作品中两性自然的身体对话表现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类:原始古朴型、智慧顿悟型和相互成就型。《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属于第一类型。作品中的艾格伯特和温妮弗莱德,虽然在其后的生活中两人渐行渐远,作品也以艾格伯特战死沙场,从而结束行尸走肉的生活为结局,但他们有孩子之前的婚姻生活确实美妙绝伦。艾格伯特像“一朵天生的玫瑰”,快乐、自然、健美、高尚,而温妮弗莱德则是“有血性的真正的英国人”。他们一起恩爱劳作于布满沼泽、毒蛇出没的古老的克罗克汉农舍,用他们的快乐和激情叙写一篇“活生生的浪漫小说”。作者用抒情般充满梦幻的语言将古老的天和地,以及褪去铅尘、古朴纯粹的男人和女人编织进一幅本色的水墨画之中,画中天与地相融相汇、天地与人气宇贯通、男人与女人相惜相怜、风景与劳动生活意趣相生,让人不禁联想世外桃园,人间天堂。
智慧顿悟型当属《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伯金和厄秀拉。在彼此相遇之前,伯金和厄秀拉分别都经历过情感的伤痛,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因伤痛而自怜自哀,而是走向更宽广的世界,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作为受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伯金和厄秀拉都苦苦思考人生意义,思索人类的命运,都希望获得个人圆满的结局。他们相同的气质和人生态度使他们终于走到一起。不过,他们的恋情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过了许多痛苦的磨合。伯金需要厄秀拉身上“流溢出的泉水般的金光”而讨厌厄秀拉固执的自我,而厄秀拉呢,她却不肯放弃自我武断的意志,她要求伯金尽爱的义务,因此俩人最初在精神上难以契合,互相折磨,直至他们俩都越过情感与自我的阶段,超越了自身。其结果是,“她发现了上帝始初的儿子,他也发现了人类最初的漂亮女儿”。
至于相互成就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和麦勒斯是最好的例子。康妮的丈夫克里福德在战争中腰部以下伤残而导致性无能,致使他们的夫妻生活维系于纯理性纯精神的状态。在失去性功能的同时,为了维持他们所谓亲密的夫妻关系,克里福德用狂热而空洞的文学兴趣取代夫妻间正常的情感交流,用绝对的压迫性的膨胀自我树立自己与轮椅上半截瘫痪的身体格格不入的大丈夫的形象,使他们生活的拉格比庄园在康妮的眼中成为“毫无灵魂、丑陋无比的中部矿铁世界”,令人窒息。失去话语权和独立个性的康妮因此终日闷闷不乐,生命之花在未曾灿烂开放之时就开始萎缩,不免顾影自怜。而作为拉格比庄园猎场看守的麦勒斯也曾经历非常失败的恋情,致使他对女人长期地失去热情和兴趣,直至遇见康妮。他先是经历了两个讨厌性害怕性的女人,之后与性欲旺盛的芭莎·柯茨结了婚,但婚后的生活却十分不和谐。芭莎·柯茨泼辣尖刻,总试图用性牵制麦勒斯,而且总是自恋,自我放纵,自我宣泄,两人永远都无法和谐相处,最终互相仇视对方,结果芭莎·柯茨搬出去住,跟了一个任她摆布的大男孩斯戴克斯门鬼混去了。这样的两个人,一个渴望自然完美结合的男人,一个期盼肉身复活并以此还原生命本质的女人,在象征着人与自然本真的生命活力的森林中相遇了,他们理所当然地创造了奇迹。作品中多次描述他们和谐的两性关系,作者也不厌其烦地铺张细节,同时还让两人坦诚地探讨两性的关系。当克里福德冷嘲热讽康妮对身体的热爱,称“肉身的生命不过是动物的生命”[13]时,麦勒斯却让她知道“它会在可爱的宇宙中成为再可爱不过的生命,那就是人的肉体”[14]。将虚假的羞耻心烧个干净,同时让她体验阿贝拉德式“激情的微妙之处,肉感的圣筵”[15]。当麦勒斯进入她的体内,“她生命之最生动处受到了触动,她知道她被触动了,她的感觉达到了完美的极点,她飘然而去。她飘然而去,化了,但她出生了,成了一个女人”[16]。而麦勒斯在康妮身上找到了真正的女人味,真正能让他成为本真自己的“人的女儿”,因此,他们相互成就,创造了一个现代版的成人童话世界。
因为世俗和宗教的传统观念,人们往往将性爱等同于“淫秽”和“色情”,因此而生“负罪感”。劳伦斯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我们必须崇拜性。他通过描绘两性自然的身体对话告知人们性爱是人性的一部分,是自然美丽的,是健康温暖的,是真正美感的交流,“如果说直觉是叶,美是花,那么性就是根”[17]。事实上,劳伦斯创造的和谐两性世界已经将性爱从尘世文化转向了天国文化。
奥尼尔的世界态身体概念从理论层面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了劳伦斯作品中所揭示的宇宙与人、自然与人、社会与人等相互依存的亲缘关系。劳伦斯带着乌托邦似的梦想在作品中追忆逝去的田园式生活,通过自然和性爱的主题昭示人类诗意生存的最高境界与和谐共生的两性关系的最高追求,其目的只有一个,即用自然态的身体以及身体的自然对话构建人类理想的社会。在现代文明日益改变人类生存环境的世界里,他的理想对人类始终有警钟的作用。
注释:
[1][2][6][7][8][11]约翰·奥尼尔:《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 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26、28、15、30、13、33页。
[3]D.H.Lawrence,Why the Novels Matters,ed.Anthony Beal,Se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55,p.105.
[4]D·H·劳伦斯:《春天的阴影》,文美惠译,选自《劳伦斯精选集》(上),冯季庆编选,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92页。
[5][9]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陈良廷、刘文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03、32页。
[10]D·H·劳伦斯:《虹》,黑 马、石 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版,第433-434页。
[12][17]D·H·劳伦斯:《爱的行板》,杨 涛译,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4年,第4、96页。
[13][14][15][16]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黑 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45、245、258、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