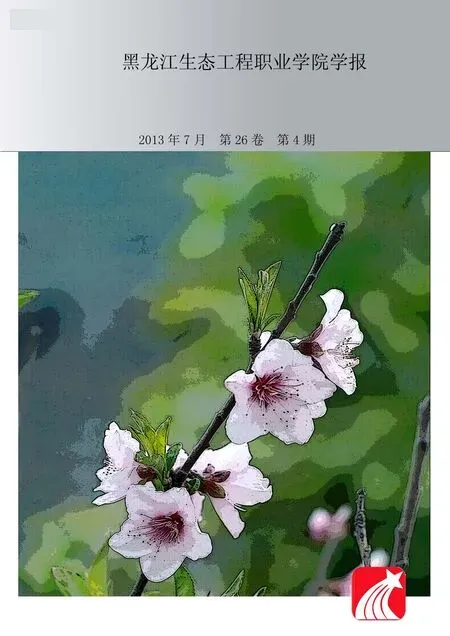论李渔小说的自叙性
陈 一 娜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1 李渔的小说创作
李渔,初名仙侣,字笠翁、谪凡,号天徒。他最受后人推崇的是戏曲理论,其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往往乏人问津。而事实上,李渔的戏曲创作并不突出,但他的白话小说却是可与“三言”“二拍”比肩的清代说部上乘之作。最早为其作传的孙楷第对他的小说颇为推崇:“说到清朝(白话)短篇小说,除笠翁外,真没第二人。”[1]李渔的小说创作主要包括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与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肉蒲团》等四种。这些作品体现出的“作意”的创作理念、“自娱”的文学功能观、“娱人”的审美取向、融通雅俗的文学品味观以及情节结构至上的叙事主张都在前人的白话小说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2]。在李渔小说的种种艺术特征里,“自叙性”是个颇为引人注目、值得玩味的组成部分,也正因此它成为了本文论述的重点。
2 李渔小说的“自叙性”
提到小说的自叙性,人们往往首先联想到五四时期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小说。这些作品已掺杂虚构的因素,但故事集中于一个主人公,并大都与作者自己的身世经历有关,也就是说它们是有“生活原型”的。作品大都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最常用的手法是直抒胸臆,即在表现主人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情景时,对人物心理特征与内心世界的深刻解剖和表现,以情绪作为结构的内核,喷发的是转折时代激奋、狂热、朦胧、感伤、颓废等复杂的主观情绪[3]。相较于此类强烈观照内心世界的“自叙传”小说,李渔小说的自叙性则以出离的姿态指向外部,也就是说李渔小说的自叙性更多地体现于对世情的叙写,而非对人物内心的解剖。在文本中,作者像是一种更高的存在,俯视着人物的悲欢,并饶有兴致地发表评论,进行总结。但李渔的小说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机械拷贝,从他的笔下幻化而出的世界总是与现实似是而非,在这个世界里李渔大张旗鼓地注入了其别出心裁的经验之论与其亲历亲受的自喻自况,表现出了自己鲜明而突出的文化人格和审美取向。这是个虚构出的逼真的世界,在这强烈的文人虚构意识中寄托的是李渔鲜明的自我形象,创造了我国话本小说的“有我之境”[4]。
3 李渔小说的自叙性在文本中的体现
3.1 小说中的乱世印记
李渔生于积弊已久、颓势已成的明代后期。在他的青年时代,病入膏肓的朱明王朝敌不过强大的异族铁骑,终是在战火中灰飞烟灭,留下满目疮痍、遍地饿殍。李渔生活的江南一带受到的冲击虽不及北方,却也是饱受战乱侵扰。发生于1645年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都以战争的残酷而闻名。清顺治三年,也就是1646年,清兵又攻下了浙江兰溪一带,那里是李渔的故乡。受到战火蹂躏的故乡一夜间竟成废墟,我们不难想象这对于青年时期的李渔的震撼。在逃难途中,他不仅亲身体验了那种漂泊无依、惶恐万分的心理状态,而且也亲眼见证了百姓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民不聊生的乱世使李渔对战争既恐惧又厌恶。关涉战争的题材在李渔的各类作品中并不少见,可见易代之际的战乱对李渔的生平经历来说是多么重要的组成部分。
残酷的战争在李渔的生命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战乱的印记同样也留在他颇具自叙性的小说创作中。在《无声戏》第五回《女陈平计生七出》里,李渔就叙写了一个聪慧贞洁的耿二娘在流贼肆虐的环境下与敌人斗智斗勇从而保住身家性命、清白之身的故事;在《十二楼》之《奉先楼》中,李渔又塑造了一个为在流寇猖獗的乱世中保全夫家子息而历尽苦难的舒娘子的形象;而在《十二楼》之《生我楼》中,李渔也以生花妙笔编排了一出由土贼劫掠而引发的阴差阳错。故事里的土贼流寇往往为患极大,恶贯满盈;而故事里的平民百姓,几乎毫无反抗之力,任人鱼肉,承受着战乱带来的一切苦难。结合李渔生存的时代环境,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故事虽然有想象夸张和道听途说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根据李渔的亲身经历、真实情感演绎而来的。可见李渔小说中屡屡涉及的战乱背景是有着作者现实生活的土壤的,也是其小说自叙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3.2 “风流道学”的渗透
李渔妻妾众多,风流好色的“登徒”之名颇为响亮。除正妻外,李渔一生陆续纳妾近十人,人数之众可供李渔组织家庭戏班,进行戏曲表演。这种风流好色的品性也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有所体现。如《无声戏》第七回《人宿妓穷鬼诉嫖冤》写的是小生意人王思迷恋娼妇雪娘,为其耗尽心力钱财,到头来却发现这只是一场骗局,因而死后化为鬼魂,讨回公道的故事。其间详细描写了王四与雪娘的暧昧风流之举,香艳至极。而作为这一回开场的小故事里也多次提及“房中术”,情色意味浓厚。这类带有情色描写的小说不在少数,如《无声戏》之《女陈平计生七出》、《十二楼》之《夏宜楼》《十卺楼》等作品里都有不少这样的描写。可见李渔确是把自己精于男女情事且喜谈闺房之乐的个性融入了小说创作中。
李渔虽妻妾众多,然非但不受“季常之吼”,不遭妻妾争宠之忧,反是饱享妻妾和谐之乐,有诗为证:“自分多应老曲房,山妻挥麈妾焚香。逢人便说闺中趣,拄杖悠然傲季常。”[5]也许是自负其治家疗妒的功力,李渔的小说作品中也多有涉及如何处理妻妾关系的。《连城璧》第七回《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中费隐公妻妾成群,但在他的治理下“正妻不倡酸风,众姬妾莫知醋味”,因而费隐公自诩“妒总管”,向广大为妻妾不合而烦恼的男子传授“弭酸止醋”的良方,还率领其追随者与妒妇进行辩论,终究大获全胜。熟悉李渔的读者不难在这篇小说里看到李渔洋洋得意的影子。除此之外,在《无声戏》第十回《移妻换妾鬼神奇》和第十二回《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等小说里也多次涉及妻妾关系的题材。
李渔肯定男欢女爱的合理性,反对禁欲。但他的男女观念并非毫无底线、一味放纵。相反,李渔非常强调这种关系的道德性。这种“风流、道学合一”的思想当然也体现在了李渔的小说创作中。在给《十二楼》作的序里李渔这么写道:“盖自说部逢世,而侏儒牟利,苟以求售,其言偎亵鄙靡,无所不至,为世道人心之患者无论矣;即或志存扶植,而才不足以达其辞,趣不足以辅其理,块然幽闷,使观者恐卧而听者反走,则天地间又安用此无味之腐谈哉!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痴,殆老泉所谓‘苏张无其心,而龙比无其术’者欤?夫妙解连环,而要之不诡于大道,即施、罗二子,斯秘未睹,况其下者乎!语云‘为善如登’,笠道人将以是编偕一世人结欢喜缘,相与携手徐步而登此十二楼也,使人忽忽忘为善之难而贺登天之易,厥功伟矣!”可见李渔认为小说既应该有趣味、不酸腐,又不能一味风流放纵、“偎亵鄙靡”,也不能满纸道学气,把人憋坏。在小说的创作实践中李渔也是这么做的。
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他的《十二楼》之《合影楼》。小说开篇就说:“所以惩奸遏欲之事,定要行在未发之先。未发之先又没有别样禁法,只是严分内外,重别嫌疑,使男女不相亲近而已。”但是小说讲的却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元朝至正年间,广东曲江县有缙绅管提举、屠观察二人。二人虽是一门之婿,但性情迥然不同,管提举“古板执拗”,屠观察“跌荡豪华”,故二人将一宅分为两院,中筑高墙,甚至在池水之中也立起石柱,铺上石板,砌起一座墙垣。屠家有子名珍生,管家有女名玉娟,二人都常在家中水榭嬉游,各从水面上窥见对方容貌,心生爱慕,因而互赠诗笺,以荷叶为舟载之相互传递,订下终生。半年后,珍生相思成疾,屠观察爱子情切,因使好友路公向管提举求亲,然而为管所拒。恰好路公有女锦云,才貌相佳,屠公因而与路公订下亲事。不料珍生得知此事,病势更重,要求父亲退婚,屠观察只好对路公实言;路公告诉女儿后,锦云亦怨恨而病,路公左右为难,遂心生一计,向管公伪称珍生是自己的儿子,请求玉娟为媳,又言己之女儿已许配于屠公之子,两对新人择日同时完婚。至婚礼之日,管提举方明白新郎实为珍生一人,亦恍然大悟,与屠观察尽释前嫌,和好如初,自此水面上的墙壁被推倒,将两个水阁作为洞房,题曰“合影楼”。显而易见的是,“古板执拗”的管提举代表着李渔心中道学的一面,而“跌荡豪华”的屠观察自然代表着风流的一方。若是李渔是个纯粹的卫道士,那么他不会让管提举受到愚弄,最终将女儿嫁给珍生;若李渔一心成全风流,那么他不会让屠观察屡次求婚被阻,珍生相思成疾。真正让事情得到圆满解决的人既不是“道学”的管提举,也不是“风流”的屠观察,而是那个“既不喜风流,也不讲道学”的路公。可见,与开篇就大书特书的纲常大道不同,在李渔心中,风流而不放荡、道学却不古板的路公才是他在文中的代言人,替他将自己“风流、道学合一”的思想在小说里好好地“自叙”了一番。
3.3 “退一步法”的表现
李渔曾在《闲情偶寄》的“颐养部”中提出过“退一步法”。所谓“退一步法”,其实是李渔从自己的养生理论中提炼出来的。关于“退一步法”李渔自己是这么解释的:“穷人行乐之方,无他秘巧,也只有退一步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以此居心,则苦海成乐地。” 意即当自身处于贫困不得志时,想想比自己更穷更痛苦的人,心理自然容易平衡;若与豪绅富贵人相比,就越比越泄气,越比越不平,这就叫“人比人气死人”。这大概也就是一种苦中作乐的“阿Q精神”吧。
“退一步法”也被李渔融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十二楼》之《鹤归楼》里的段玉初被派往敌方,为免妻子牵挂,有损健康,他故作无情之态,做足了有去无回的样子,让妻子断了念想,安心在家保重自己,最后终得团圆。而不懂得“退一步法”的郁子昌就让在家苦候的妻子相思成疾,抑郁而亡了。在《无声戏》第一回《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李渔的一段话也体现了他的“退一步法”。文中说:“万一姿色七分八分,九分十分,又有些聪明才技,就要晓得是个薄命之坯,只管打点去嫁第一等、第一名的愚丑丈夫,时时刻刻以此为念。”“若还侥幸嫁着第二三等、第四五名的愚丑丈夫,就是出于望外,不但不怨恨,还要欢喜起来了。”其实,在李渔的小说中“退一步法”的运用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3.4 最直接的“自喻之作”
说到“自叙性”,最直接的方法恐怕就是以作者自己的经历为素材来进行创作了,李渔的小说里也有这样的作品。
李渔自称“生平有两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6]他一生先后营建过伊园、芥子园、层园三个园居,个个都是园林设计的经典,结构精巧,花木井然,风光宜人,匠心独运。但园林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囊中羞涩时,李渔也被迫卖过房子。他的小说《十二楼》之《三与楼》就是以自己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里塑造了一个不喜功名、淡泊名利、一生唯好读书和园林的虞素臣,他对园林设计深有造诣,耗费一生积蓄建造园林,终至负债累累,不得不出售自己精心建造的园林。这不就是李渔自己的经历吗?“自叙性”何其明显。
李渔于明清易代之际就自弃仕籍,隐居杭州。他十分享受这种不受科举束缚、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他的隐居生活可以说是充满了艺术气息,在伊山别业隐居时,他终日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养养花种种草,好不快活,留下了《伊园十便》《伊园杂咏》《伊园十二宜》等诗篇,描写了乡村生活的淳朴静美,如:“我爱江村晚,家家酿白云。对门无所见,鸡犬自相闻。我爱江村晚,门无显者车。道傍沽酒伴,什九是樵渔。”[7]在他的小说里也常常涉及隐居生活,比如《十二楼》之《闻过楼》里李渔就塑造了一个为人恬淡、绝意功名、为人耿直真诚的顾呆叟,他为图清静隐居山野,并十分享受这样的生活。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里的顾呆叟是以李渔本人为原型创作的,这也是一种“自叙”。
4 结语
如上所述,李渔小说有着鲜明而独特的“自叙性”,这种“自叙性”虽然也给他的作品带来了过于直接刻露、前后表里相互矛盾等局限,但这种积极将“自我”融入作品,创造“有我之境”,表达个性色彩的尝试仍是意义非凡,值得肯定和研究的。正是李渔这种敢于投入自我、表现自我的鲜明个性让历史记住了这个“小人物”,让我们记住了这个与众不同的李渔。
参考文献:
[1]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J].图书馆学季刊(九卷),1935,(27).
[2]黄果泉.雅俗之间——李渔的文化人格与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97~254.
[3]郁达夫.现代小说所经过的路程(郁达夫文集第6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68.
[4]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60.
[5]李渔.贤内吟其四并序(笠翁诗集卷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27.
[6]李渔.闲情偶寄·居室部·房舍第一(李渔全集卷三)[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156.
[7]李渔.我爱江村晚(李渔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卷二:263.
[8]李渔.李渔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9]李渔.笠翁诗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10]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1]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