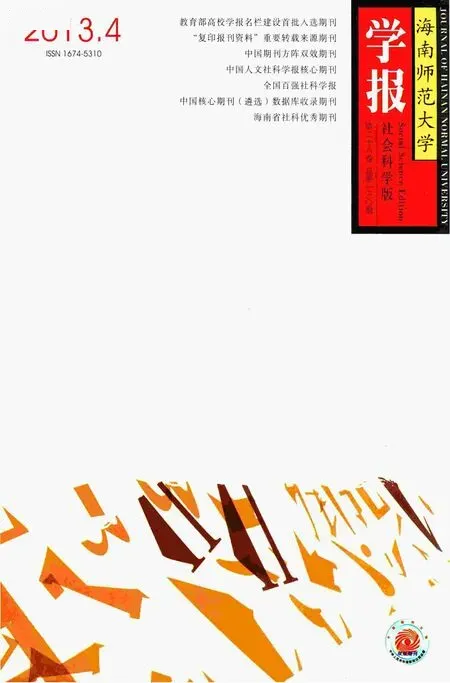无爱的显影:当代散文中的身份歧视
张宗刚
(南京理工大学 诗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4)
所谓身份歧视,是指居于优势地位的人不能平等地对待不如己者,是强势者或自以为强势者对弱势者的轻视,是在权势、财富、文化等方面居于优势的人面对不如自己的人时呈现出的个体优越感。它与平等意识、平权意识是背道而驰的。在现实生活中,由这种身份差异引发的歧视现象比比皆是,诸如城里人歧视乡下人、本地人歧视外地人、富人歧视穷人,以及某些素质不高的外国人歧视中国人;如被指为“名声欠佳”的河南人在京、沪、粤等地受到的种种冷遇,如一些流行的影视剧热衷于拿乡下人作笑料,通过展现农民的愚昧落后,表达某些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居高临下式的观看欲,等等,都是由社会不平等关系导致的身份歧视。身份歧视的根本,仍在于源远流长的封建等级意识。视他人为天生的“贱民”,视自己为命定的贵人,把他人当成泥土,把自己当成珍珠;这就是身份歧视中歧视者一方的主体心理特征。这种无视他人尊严的做法,显示了一个专制传统漫远悠长的古老民族中,那些尚未在文明的链条上真正获得进化和完善的人类的劣根性,更显示了处于世界座标中的第三世界国民特有的不良心态。
身份歧视在当今散文中有着真实的传达。散文中的身份歧视,表现为通过对他人人格的扭曲、贬低和践踏,获取单方面心理的自慰,获得某种虚假的精神凯旋。不愿真实地面对别人,也不愿真实地面对自己,是身份歧视现象中某些强势者或貌似强势者的真实心理特征。这种歧视,不仅仅呈现为五十步笑一百步的状态,甚至也呈现为一百步笑五十步的状态。身份歧视是明显缺乏爱心和同情心、缺乏人道情怀和人文素质的体现。身份歧视所表现出的,恰恰是歧视者一方的丑陋、卑下和不健康,正如某类意在炫耀自身美丽的大鸟,试图亮出华羽,却不慎暴露了不雅的屁眼。这往往是为歧视者所始料未及的。
《借我一生》中,余秋雨以“衣着潦草的古先生”指称与他打官司的古远清教授,口吻里含有明显的身份歧视意味,其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你古远清哪有我余秋雨这般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形象得体,气质出众?你又哪里配与我打官司?!彰显以貌取人的市侩气息和轻薄的势利眼作派。周涛的《雪却输梅一段香》是一篇逞才使气的应景文章。文中说有一回和朋友在高档酒店吃饭,服务小姐要求作者在白方巾上为她题写“梅须让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的诗句,于是周涛认为这位服务小姐“不简单”,因为她“能劳动、有品位”,然后大发感慨:“此句出于女博士,不足奇。出之女教授,不足怪。惟出自这位自始至终端菜斟酒的年轻服务员,令人始觉一惊诧继而一敬重再而一深思。正是‘骨格清奇非俗流’,不似黛玉似晴雯。”轻佻的话语,显示出作者那种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的日常姿态。难道仅仅因为对方的身份是酒店服务员,就不应该知道“梅须让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这样流传颇广的诗句吗?作者竟为此大惊小怪,实在是一种由身份歧视引发的无聊之思。《训话》写及自己的当年的连队指导员时说:“看得出他是那类精明强干、头脑灵活的乡下佬”,周涛在此坦然使用“乡下佬”这一侮辱性字眼。该类早已被禁用的词语在作家笔下的复活,正是潜伏于主体意识深处的身份歧视的自然流露。《包包趣闻录》谈及自己养狗的体会时说:“想我半生,咄咄逼人,恃才傲物,招恨同群,口出狂言,目空一切,视庸夫为草芥,以丑类如贱民,岂料竟能对狗如此关爱仁慈,呵护备至?人之为人,实是非常奇怪的。”此处悍然使用了“庸夫”、“贱民”等专制时代的词汇,于一派颟顸无礼、粗鲁霸道中,流露出对平民大众的轻蔑与歧视。
池莉一向以“平民”和“平民作家”自居。但在她身上,等级意识是根深蒂固的。长达10 万言的散文《怎么爱你也不够》就充满露骨的身份歧视。作者写自己生下女儿后,家中请了一位保姆:“在六月份的一天,我家来了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小保姆叫秋。”池莉当仁不让地写道:“中国农民对城市居民有着深刻的仇恨,这是我早在十七岁下放农村当知识青年的时候就发现了的。从理论上,我们的国家管这种现象叫‘城乡矛盾’。自我回城上学之后,关于城乡矛盾的种种问题自然离我远去,渐至消失。小保姆秋却把这个巨大的矛盾带到了我们家。”接下来,池莉开始发泄对小保姆的不满:“虽说秋只有十六岁,但她非常有个性。她对社会上时髦的一切十分敏感并渴望拥有,对于自己在城市只能当个小保姆深感无奈和不服气。她聪明地利用她的年幼无知来表示出她的反抗。”这话未免有些以偏概全,不排除有个别保姆素质确有欠缺,但生活中的保姆多数都是朴实的,自重的,自爱的。何况按中国社会通行的惯例,年龄未满18 岁者尚属未成年人,雇用未成年人做保姆,本已是不妥的做法,却又在感情上对保姆如此排斥如此挑剔,显出了作家的小鸡肚肠。接下来作者对小保姆进行了一系列丑化乃至妖魔化的表述:“来到我家的第一天,我就看见了她头发上爬动的虱子。……秋轻蔑地说城市真见鬼,连农药都没有。……秋洗衣服只用清水漂一次,说她在乡下在河里就清一次。秋冲奶粉总忘记试试水温。秋用煤气老记不住关好总开关。我给秋买了水果让她吃她装作不屑一顾,晚上到她睡觉的地方却偷吃人家的水果。秋一开口就我们乡下什么我们乡里人什么。”作者刻意放大小保姆的无知,语调里充满城里人对乡下人的优越感。“她装作不屑一顾”,“偷吃人家的水果”等语,因意气用事而带有了明显的贬斥色彩。对于一个没有见过多大世面的16 岁的乡村少女,何必这样苛求呢?从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的不厚道,不宽容,看到了作者的斤斤计较。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就这样,小保姆秋从此不再对我使她乡下姑娘的乡下脾气了。”作者在此特意点明“乡下”,发散出既不得体更不健康的身份歧视味道。在与小保姆相处的日子里,作者的抱怨越来越严重:“秋进入了我们的家庭,日渐随便起来,有了一种自家人的平等感觉。甚至还经常自作主张地摆弄家里的物件。”池莉抱怨的理由,竟是这位小保姆在她家“有了一种自家人的平等感觉”。这不禁让人困惑:“平等”又有什么不好和不对呢?当今中国,雇主和保姆之间原本就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职业合作关系,不存在谁高一等谁低一等的问题。然而池莉似乎不懂得这一基本常识,这显得她既缺乏民主观念、现代意识,也缺乏古道热肠、善良心地。
小保姆秋让池莉抱怨不已的理由是:秋“喜欢用我的润肤霜,随意拿我的手绢、发卡之类的女性爱物。说心里话,我是多么讨厌秋的这种行为啊!无论秋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哪怕是王室成员,我都讨厌。”接下来又不无伪善地说:“许多次,我话到嘴边,又强咽回去。我知道十六岁的乡下少女秋她不懂这些。我如果说了她,她只会认为我是瞧不起她这个乡下人。她会闹着要走……要学会容忍一个毫未受过帮佣职业训练的乡下姑娘简直太难了!”最后干脆直截了当地说:“秋哪里知道,她才是万恶之源。人过日子是需要环境和气氛的,正是她,破坏了我们原有的环境和气氛。”将小保姆斥为“万恶之源”,真是不宽容得可以。16 岁,这是一个混沌未开懵懵懂懂的年纪,这个年纪的城市少女尚还可以围着自己的父母撒娇,乡村小姑娘秋却为了生计,离开父母来到城里做保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有时可能会真的“没大没小”,在雇主家里随便了些,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乡下人一贯淳朴的民风民俗决定的。比起某些以邻为壑的城里人,在传统的中国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亲密而简单的: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也不介意成为你的东西。来到城里后,小保姆秋还是不免于像在乡下与人相处时那样,“随意拿我的手绢、发卡之类的女性爱物”,这种做法本身确实有些不甚妥当,但作者竟然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相信读者看到这里,对这位不十分“懂事”的小保姆秋,未必真的会生出多少恶感;倒是对这位有“文化”的家庭主妇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文中还显示出,作者的丈夫更是一个“狂暴粗野”的人,喜欢无缘无故地发火。比如有一次,仅仅因为他自己的皮夹克从衣架掉到了地上,妻子和保姆没有及时拣起来,他便大耍老爷威风,气呼呼地把热水瓶、电冰箱都砸了个遍,“接二连三地大举扫荡这个家庭”,最后竟“抓起一只椅子扔过来,那椅子越过双人床准确地砸在我的腿上。”同时霸道地把“我”也即他的妻子赶出家门:“你给我从这个房子里滚出去!”令作者的自尊心遭受重创。饶是如此,作者竟还有心思把丈夫的发脾气归因于不懂事的小保姆招惹所致,对丈夫的行为则未予谴责:“我明白他的心。我也敢说他还是爱我的。”依然单向度地发泄着对小保姆的不满与牢骚。最后,当作者决然将小保姆辞掉时,文中写道:“秋蹲在地上,抱住了桌子的腿,说我不走,你知道我不愿意回乡下,我讨厌我那个家,我和你们过得不是很好吗?”漫画式的小说化笔法,将作者对乡下人的歧视推向极致。之后作者又写她到居委会开办的保姆站去找保姆,一个劲地抱怨“保姆站许多姑娘连身份证都没有,来历不清,底细不明,谁也不能保证她们安全可靠。”由此可见,作家潜意识里的这种身份歧视和地域歧视何等地顽固。
池莉家里来了第二个小保姆冬梅。作者写她带冬梅坐公交车时:“冬梅被上车的人挤得东倒西歪。人们厌恶地议论:如今乡下人都跑到城里来了,傻头傻脑的,连车都不会坐。……我不无忧虑地想,像从前的秋那么伶俐聪明都难以进入我们的家庭,冬梅这憨乎乎的劲能行吗?”这段话透出,池莉是完全认同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和轻慢的。幸而冬梅很“懂事”:“冬梅是一个外表憨拙但内心灵秀的姑娘,她深知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农民对城市的仇恨她也同样地有,但她决不流露在表面。……尽管冬梅也有许多缺点,比如拿家中有急事立即要回家为借口要挟我们给她涨工资,比如有时候偷点小懒撒点小谎之类的。但从大体上来说,冬梅堪称一流的小保姆。”作者好歹给了保姆一个不错的评价,前提却仍然是要列举她一些诸如偷懒、撒谎、要挟涨工资之类的缺点。究其实,出于某种防范心理,池莉对保姆是不能够也不愿意坦诚相见的,根本没有一种让对方尽快融入自己家庭的正常愿望。另外,由保姆的话题,作者所动辄断言的“农民对城市的仇恨”、“中国农民对城市居民有着深刻的仇恨”,究竟有多大的学理和道理可言呢?事实上,这种所谓的“仇恨”,根本不可能是农民的普遍心理,它不过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普遍怀有的一种对城里人的敬畏和羡慕罢了,把这种敬畏和羡慕说成“仇恨”,是离谱而离奇的,是蓄意夸大城乡对立和城乡矛盾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农民的侮辱。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作出的与事实不符的价值判断,显系一种由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所导致的过敏性心理症候。池莉对冬梅产生好感的重要理由是:“冬梅还有一种优良的品质,即忠实,更是一般人少有的。”用“忠实”作为评价一个人品质的标准,明显带有封建时期主奴关系的阴影,发散着某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气息。写到冬梅要走时,作者说:“实际上冬梅是舍不得离开的,与当初我从同事家领她出来相比,冬梅已判若两人。她不仅服饰全换,而且讲究卫生,爱好整洁,温文尔雅。她已经习惯了我们家的生活。”言下之意,是我们这个“讲究卫生,爱好整洁,温文尔雅”的家改造了小保姆,使她得以脱胎换骨。接下来,怵目惊心的话语出现了:“我也是舍不得让她走的。我们虽为主仆,但关系十分融洽。我的举止态度她都能心领神会。”保姆和雇主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竟被作家当仁不让地理解成了真正的“主仆”关系!由是,池莉对冬梅的客气,也便成了“主子”对“仆人”的恩赐。作者还认定冬梅只会料理家务,对她寻求个人发展的想法不以为然,一厢情愿地宣布:“冬梅是个料理家务的好手,做别的还不一定行。她如若能够安心呆在我们家里,兴许于她于我们都是一种福气。年轻的姑娘就是在这一点上明白不过来,个个心比天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她身在乡下,家境贫苦,自己文化不高,又不爱书本,也无其他技艺……但她被社会上商业热潮扇动得五心不定。她想赚大钱,想开店,想发财,终于她还是走了。”其实,焉知冬梅就不擅长去开店和赚钱呢?既然作者承认她是个“外表憨拙但内心灵秀的姑娘”。从文章中看得出,池莉对小保姆是不乏真情的,她本人也有着善良热诚的一面。可惜,作者的“刀子嘴”害了作者的“豆腐心”,比比皆是的歧视性话语,破坏了池莉文本的整体境界。从这篇献给女儿的长篇散文中,我们还看到,作者一方面对自己的女儿吕亦池百般呵护钟爱,另一方面又毫不掩饰对那些“马路边乱跑的拾垃圾的孩子”的蔑视。这种只爱自己的孩子,不爱别人的孩子的想法和做法,表现出人之为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的同情心和爱心的缺失。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中国为什么难以产生伟大的作家,哪怕是出色的作家——正是过于狭小的精神器局和过于低下的人文境界限制了他们。
近年大规模转向散文创作的老作家李国文,文本中也存在着颇为严重的身份歧视问题。比如,作家对于草根阶层颇为不屑,动辄斥为“小农”、“农民”,流露出名士的清高和市侩的刻薄。《美人计》嘲笑历史上那些农民政权的统治者是“昨天的庄稼汉”、“腿上泥巴还未洗净的农民”、“只求一种动物本能的宣泄”;《假如阿Q 当作家》说:“我们从历代农民革命起义首领的身上,也可以证实草根阶层的性事,更多缘起于动物本能。刘宗敏进了北京,第一件就是找陈圆圆,恨不能当场按住,宣泄他的性饥渴。那个洪秀全还未打到南京,弄了许多美人共眠宿,其性行为与踩蛋的公鸡无异。”对草根阶层的“动物本能”极尽嘲讽之能事。《唐朝的声音》为了衬托唐玄宗的风流高雅,写道:“一般来说,出身于农民阶层的统治者,天一黑,通常就使出全部精力于室内的床上作业。”这是一种“唯出身论”,一种想当然。《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说:“和珅,作为小农,鼠目寸光,作为穷人,惜财如命”,作者在此把出身世袭贵族的八旗子弟、将门之后和珅的身份故意改写为农民,仅仅是为了表达身份歧视的需要,显示出某些市民阶层人物对农民群体的莫名排斥。《李后主之死》则说:“中国皇帝平均文化水平较低,而且大部分出身农民,这也是中国文化人屡遭皇帝蹂躏的原因。”在《关于交椅之类》中,李国文还想当然地评说情同手足的水浒英雄:“卢俊义,林冲,柴进,与这些落草为寇的土豹子,打家劫舍的流氓无产者(指李逵等——引者注)不同。他们曾做过大官,曾当过贵族,曾带过兵马,见识过帝王排场,皇家气象,觉得这种小儿过家家式的排座次,争交椅,不过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大老粗们的自得其乐罢了,肯定背过脸去,会捂着嘴偷着笑。”字里行间散发着某种粗鄙刻薄的不健康心态。《李卓吾之死》尤其彰显市侩式的等级偏见:“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强,存活率特高的一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投机,敢于冒险,敢于钻营,敢于巴结,甚至敢于无耻的精神,比之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强上百倍。由于出身清苦,处于底层的原因,这些人对于财富的冀求,权力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这段话里流露出的身份歧视是空前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来英雄不问出处,古人尚能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发出“将相本无种,白屋出公卿”的人生宣言,正在步入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的今天的现代人,更应懂得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个体都有公平竞争的权利,都可以循着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各逞才俊。而这却让我们的一些作家很感不安,竟至于认为寒门子弟的“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能干的乡下人抢走了城里人的饭碗,压倒了城里人的风头,于是便愤愤不平,念兹在兹,简直成了去不掉的心病。这与其说是一种身份歧视,无如说是一种因为看到乡下人的出色表现而激发的“既生瑜、何生亮”式的偏狭之思。古往今来,多少风云人物、时代精英,均来自李国文所说的“穷乡僻壤”;这些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优秀农家子弟,不屈不挠地抗争命运,发展自我,在各个领域立大功业,成大气候。不排除其中确有不择手段者,但个别不能代替全部,李国文这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更何况由于种种现实原因,身受生存环境制约的中国农民的每一点进步和成功,往往都要付出数倍于城里人的努力,缘此又引发了多少出师未捷身先死、未曾飞翔已折翅的乡村子弟的奋斗悲剧。总之,通过个人奋斗,既能够促进个体的完善,也能够更好地为群体服务,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正当权利。李国文散文所流露的,却是一种意欲强行剥夺他人正当权利的霸道心态。如是,一个作家倘连人类基本的健康心态都不能保持,更遑论人文关怀了。
韩小蕙《欲问年龄的优势劣势》中提到:“在防范非典最严峻的日子里,有一天在北京的闹市中心,一个进城农民随地吐痰,在我的批评之下,他立即态度谦卑地擦掉了。这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日子里,都简直是一则瑰丽的神话。”这段话不免给人以“柿子专拣软的捏”的感觉,进城农民在“我”这个城里人面前,“态度谦卑”地擦掉了自己吐的痰,怎么竟至于就成了一则“瑰丽的神话”?作者显然是在以信口开河的笔调向读者暗示:“随地吐痰”式的不文明行为,总是与“进城农民”联系在一起的,农民,他们正是不文明现象的制造者。如此居心不良而又煞有介事的身份歧视,恰恰暴露出创作主体的浅薄可笑。张梅《没有花伞的赛马会》欣欣然写道:“那天我和石娃去看赛马……赛马会在我们的期望中应该是一个社交场所,是绅士淑女消遣的地方。干干净净的男人,打着花伞的女人。想起安娜在赛马会上为渥伦斯基跌倒而失态,一段私情由此触发;想起那些花伞下的窃窃私语,眼波传送;男男女女在看台上的飞短流长,种种景象,是我们这些在贫穷的社会中长大的人所向往的。”然而真实的赛马会现场打破了她们的期望与幻觉:“我们美丽的鞋子走在灰尘里,身边满是那些汗流浃背的人,看上去就是广大的劳苦大众,而且一看就是梦想用十块钱赢一百块钱的人。”显然,作者对那些“汗流浃背”的“劳苦大众”充满了遏止不住的厌恶排斥。通过身份歧视来建构自己的有闲认同,正是以张梅为代表的“小女人散文”惯用的手法。《绿薄荷酒》中,张梅写道:“绿薄荷酒似乎特别能喝出女人的优雅和风度……但这么多优雅的女士争着要在酒吧喝它,总给人以媚俗的感觉。就像许多人千方百计要讲自己出身高贵一样。媚俗是不会消亡的,因此绿薄荷酒永远好卖。”这段话不无批判的锋芒和清醒的反思,在以张扬享乐为主旨的“小女人散文”里堪称难得。但很快地,作者的思维定势又迅速滑向小资、白领和中产者的清高自矜,文章结尾赫然说:“总不能想像一双因劳作而变形的劳动女人的手拿着高脚杯喝绿薄荷酒。劳动女人是劳动女人,绿薄荷酒是绿薄荷酒,二者永远存在着界限。”以“因劳作而变形的劳动女人的手”所不敢染指的绿薄荷酒,来衬出上流女人的高雅,把自己的休闲,自己的享乐,自己的快感,建立在对为生活而奔波劳碌的下层民众的恶意嘲讽之上,彰显强者对弱者的轻慢,生活舒适的“上等人”对生活艰难的“下等人”的不屑,体现出某类堪称无耻的心理。其语调之刻薄,口吻之冷漠,心地之窄仄,勾勒出的正是一种似清高实下作的伪贵族情态。这种身份歧视背离了基本的社会公德,也显示了“小女人散文”的精神病象,暴露了她们灵魂深处的垃圾。
散文中的身份歧视现象,是一种创作主体滥用话语霸权的典型表现。对他人的歧视,也往往印证了歧视者自身的无能——歧视的另一面,又焉知不是一种嫉妒?!自傲者往往自卑,无畏者往往无知;矮化他人的人,到头来所矮化的可能恰恰是他自己。背负数千年封建传统的现代中国文人,当务之急仍是普遍性的“补课”:在思想深处补上“现代意识”和“公民意识”之课,以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理念不断荡涤自己,提升自己。大象不可能在茶杯里洗澡,大树不可能在花盆里成长。伟大的文学,须有伟大的爱心作支撑。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有什么样的精神格局,就有什么样的文本气象。“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1]苏东坡爱宇宙山川,爱花鸟树木,爱兄弟朋友,甚至也爱他的敌人;这位命运艰蹇的北宋文豪,因为心中有爱,所以一生快乐,并把这种快乐带给他人,点染出千古风流。一个拥有良好人文素质的创作主体,不论置身象牙之塔,还是驻足骚扰之巷,都应永葆光风霁月般的澄澈心地和坦荡情怀。谢冰莹曾这样评价徐志摩:“志摩是一位最热情,最得人缘的人,梁实秋先生说,他在数十年中,见过的人不少;但从来没有一个像徐志摩那么讨人喜欢的,他赞美志摩有:‘丰富的情感,活泼的头脑,敏锐的机智,广泛的兴趣,洋溢的生气。’胡适之先生也说:‘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因为他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爱与同情,构成了志摩的人生观,他没有嫉妒,更没有仇恨,所以陈西滢先生说他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一个人,得到少数人的喜爱、崇拜,是不足为奇的;假如人见人爱,就不简单了。志摩好比中药里面的甘草,什么场合都少不了他。无疑义地,他是个天才诗人,天才作家,他写过小品文、小说、戏剧、从事过翻译,每一种都有优良的成绩表现,林语堂先生特别赞美他的诗和散文,他说:‘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以西洋语句,了无痕迹。’”[2]与苏东坡一样,徐志摩的赤子情怀,也是堪为文人样板的。人性的真善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仿佛草木萌动,禽鸟嘤鸣,仿佛天心朗月,普照一切。作者之心,惟有与天地接通,与众生共鸣,才可完美地演奏出仁爱、博大、真诚、壮丽的人性交响。文学因何而伟大?艺术因何而永恒?这是一个值得永远探讨的文化课题。凡文学巨人,无不首先是精神的伟人。想一想“五四”巨子鲁迅,对于无告而蒙昧的弱者,对于饱受欺凌而麻木不仁的大众,鲁迅始终怀有巨大的悲悯和爱意,为此不惜以个人之力独战众数,搏击黑暗,在孤军远征中完成了灵魂的自塑和人格的构筑,留给后人永世的震撼,永远的景仰。再想一想湘西之子沈从文,他对旧时代受尽欺凌和损害的妓女、水手、伙夫等下层百姓始终怀有的那种深深的同情,无言的悲悯,又是怎样一种令人感动的广大爱意!“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3]鲁迅、沈从文、徐志摩,这些在精神上可以巍然自立、淡然自持的生命个体,揭示出了“五四”一代及“五四”稍后一代作家的文本何以成为不朽的奥秘所在。面对他们,某些患有身份歧视症的当代作者在愧怍之余,是很可以深长思之的。
[1]林语堂.苏东坡传·序[M]//苏东坡传 武则天正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8.
[2]谢冰莹.徐志摩[M]//谢冰莹文集(中).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186.
[3]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M]//湘行散记.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54.
——旧诗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