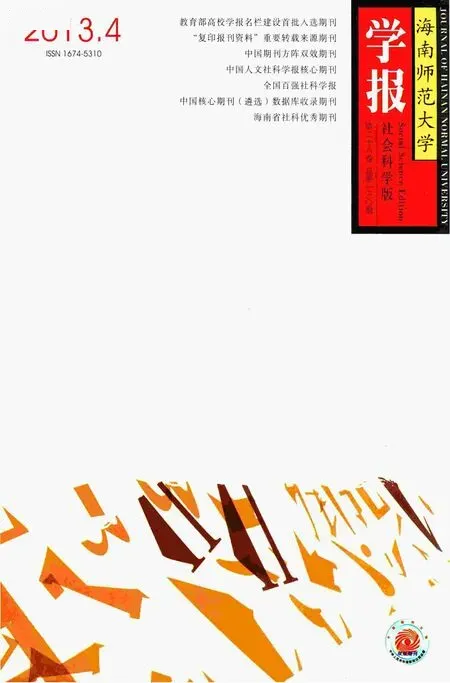80年代民俗风情小说的类型
毛 峰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如何界定民俗风情小说,学术界说法不一,大体上“是指以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时期的习俗风尚、礼节人情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这里的习俗风尚、礼节人情不再仅仅作为一种背景存在,而是与小说人物形成整体,形成一个有意味的存在;并作为一种文化,成为小说的描写主体”。[1]可以说民俗风情小说扎根于民俗文化这一向度,或虚拟想象、或描摹参仿以构筑一个诗意的文学世界,并于中寄托遥思,以唤起主体对于世界魅力的感知,因而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与价值。
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开始,民俗风情小说的书写面还是比较狭窄的。最早以鲁迅为首的启蒙知识分子以及后来的乡土小说派的创作母题往往以文学来完成对民族国家的寓言想象,鲁迅的《祝福》、《孔乙己》、《药》、《风波》、《阿Q 正传》等小说通过对民俗事象的描写,揭示长久以来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中的各种封建伦理道德。以后的乡土民俗小说无疑是承继鲁迅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作家们大量描写各类原始的、野蛮的、未开化的民俗事象,并在作品中蕴蓄着深沉冷峻的社会批判意识。在20年代,稍微能保持点距离观照的便是废名,他在对故乡民俗风情的梦幻般的抒情中,用饱含着禅趣的笔法来表现农村淳朴而又美好的性情。直到3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成熟以后,民俗风情叙事的表现手法也开始多样起来,大体以三种方式进行:出于文化批判的老舍、李劼人和艾芜、40年代的沙汀、赵树理等人;采用浪漫笔法的沈从文、萧乾以及早期的艾芜等;采用诗化写实方法的萧红以及40年代的孙犁等,这些具有不同人文情怀的作家,从不同的视角、维度对民俗风情进行了描写,绘就了一幅幅锦绣的民俗风情画。
遗憾的是,建国以后由于战争文化心理的蔓延,这些具有传统民俗情调的话语书写便被扣上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个人主义”等帽子,大部分作家停止了创作,但是抒情性、民俗性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被意识形态内化或者改造了,成为革命浪漫性的组成部分,如在《智取威虎山》中,东北独有的雪林风情被内化到杨子荣身上,杨子荣在东北深山老林中一个人深入虎穴,并且唱着带有东北民俗的京剧,在环境映衬和民俗积淀下的他洋溢着一种革命乐观性。
而新时期以来的民俗风情小说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它逐渐走向生活化、写实化,情调化,并没有带上非常强烈的启蒙色彩。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要对其进行一个详细梳理恐怕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因为80年代以来随着价值的多元化,文学回归边缘状态,对于民俗风情的界定不同作家是相异的,而且各种地域文化不断地凸显出来,即使同一个地域作家群他们对于民俗风情的展示也是不同的,是无法全部归拢起来的。与此同时,当代文学还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各种新变也是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所以限于本人视野比较狭隘,在此仅以80年代的民俗风情小说为研究对象,以类型作为划分标准,并结合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加以分析。
一 80年代民俗风情小说的三种类型
80年代的民俗风情小说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以古韵感见长并携带市井风情的小说,陆文夫是其代表;以厚重感见长并蕴涵民俗思考的小说,邓友梅、冯骥才是其代表;以清新感见长并具有乡土气息的小说,汪曾祺是其代表。
(一)以古韵感见长并携带市井风情的小说
江南水乡,市井繁华,这些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人文风情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的小说家们,因而表现江南市井风情便成了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开掘的主题。这些小说大都充满柔情画意,有一种温软的地方风情韵味,各个地区之间又有不同差异,其中尤以陆文夫特有的苏味类型为最盛。
陆文夫的小说充满了丰富的地域色调,特别是他笔下以江南小巷风情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不仅描绘了江南秀丽的自然风光、古老的民俗风情,而且在对江南市民生活的细致描绘中,透露出丝丝缕缕的古文化气息,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幽远的文化意味。而且他还特别善于捕捉一种更加内在、深层次的东西——他已经深入到南方小城镇所积淀下来的特殊的地域文化心理中进行探视。作为现代苏州人,他深感这种地域熏陶的意义,他深深感受到了地域文化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苏州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
更具体地讲,陆文夫对苏州小巷和人物特别钟情。他的两本作品集就是以“小巷人物志”命名的,里面大多数是他平生所得意的中短篇小说。他热爱苏州,眷恋那细长幽深的苏州小巷。在陆文夫的眼里,小巷是他“梦中的天地”,他决心在小巷中“寻找艺术的世界,去挖掘生活的独特的宝藏”。他的创作是要为苏州各行各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作志。就这一点来说,陆文夫更像一个民俗学家,他是把小说当作风俗来描写的,展开的是一个时代文化的长廊,正如郁乃尧所评价:“陆文夫对小巷人物心态的贴切描摹,与他对苏州普通人的熟悉分不开的,是在苏州普通人生活领域中拓展文学创作天地的。著名中篇小说《美食家》是作者长期生活在以美食著称的苏州城的结晶,仿佛信手拈来,妙手偶得。即使他为少年儿童所写《牌坊的故事》,也是从姑苏城内常见的牌坊入手的。陆文夫把苏州文化、民俗有机地组织在作品的故事情节里,无疑地增添了‘苏州味’的特色。包括苏州的乡镇习俗、大桥小桥、城河城墙、幽深曲折的石块小巷、黑白分明的围墙、幽深无比的宅院、优美绝伦的园林、千年遗存的吴越古迹、美味佳食风味小吃等。作家方之曾作过这样评价:陆文夫的‘现实主义是糖醋的现实主义,有点甜,还有点酸溜溜的’,而这糖醋味来自他所描绘的既甘甜又辛酸的苏州,普通人的生活。”[2]
陆文夫的代表作《美食家》讲述了朱自冶——一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吃的经历,其中特别是对吃文化的描写,可谓精炼独到,如小说中所描写的:“你们的店里过去有一只名菜,名叫西瓜盅,又名西瓜鸡。那是选用四斤左右的西瓜一只,切盖,雕去内瓤,留肉约半寸许,皮外饰以花纹,备用。再以嫩鸡一只,在气锅中蒸透,放进西瓜中,合盖,再入蒸笼回蒸片刻,即可取食。食时以鲜荷叶一张衬于瓜底,碧绿清凉,增加兴味。”朱自冶背完了食谱,又摇摇头:“其实那西瓜盅也是假的,鸡里并没有多少瓜味。瓜甜鸡咸,二者不配,取其清凉之色而已。我们可以创造出一只南瓜盅,把上等的八宝饭放在南瓜里回蒸,那南瓜清香糯甜,和八宝饭浑然一体,何况那南瓜比西瓜更有田园风味!……”[3]还有在《梦中的园林》中所描写的:“巷子里一片灯光,黄包车辚辚而过,卖馄饨的敲着竹梆子,卖五香茶叶蛋的提着小炉子和大篮子。茶馆店夜间成了书场,琵琶丁冬,吴语软侬,苏州评弹尖脆悠扬,卖茶叶蛋的叫喊怆然悲凉”,[4]陆文夫把一幅幅苏州市井民俗画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仿佛亲眼看到了这一幅幅的景象,令人赞叹。同时,美食家还将民俗风情与历史政治变迁结合起来,朱自冶的“吃经”、“吃史”折射的是半个世纪来以的社会政治变迁,作者以饮食文化来透视人在不同政治境遇下的心态与心理,现实化的生活中透出历史的倒影。
由此可见,陆文夫是一个本土意识很强的作家,他在接受2500年的苏州文明哺育的同时,也在积极构筑、雕刻着那种生活化、原生态的苏州文化。特别是他对苏州的市井民俗和地域风貌细致的描绘,不仅仅是描写着静态的苏州样貌,还善于从历史深处表现了近代中国复杂频繁的社会历史变迁,发掘人物在历史环境下的生命形态,这种表现既是生动的又是充满沧桑感的,这样的描写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审美特性。
(二)以厚重感见长并蕴涵民俗思考的小说
80年代随着文学书写主题的多元化,一些擅长文化思考的小说家活跃于文坛,在其写作中呈现出一种厚重感。冯骥才、邓友梅的小说是其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看到长久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北方,天子脚下的殊荣和朝代更迭的演绎不断地累积成特殊的汉民族文化形态。邓友梅、冯骥才以一种“清明上河图”式长卷方式展开对京津地区的描写,往往站到历史的高度去俯视社会、观察人生,以知识分子特有的人道主义情怀来表现北方文化的沉郁,发掘民族风俗文化背后的深意,塑造了一批诸如傻二、那五、聂小轩、乌世保等带着北京历史烟尘和世俗色彩的民俗人物形象,使得小说既具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又带有浓厚的民俗学风味。
邓友梅自觉追求“京味风情小说”的书写,他宣称:“他的这类作品都是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5]他以民间生活和民间风俗作为视角,以此来表现历史的变迁,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史诗性的特点。他的小说在民俗人物的基础上浸透着老北京特有的民俗风情,作者以揭秘般的手法绘出一副浸润着浓郁“民俗学风味”的“清明上河图”,所以他的小说往往带有一种独特的北京历史文化情致和美学意蕴,而这种独特的北京历史文化情致表现之一是对民俗风情和文物工艺的描写。
如《寻访“画儿韩”》中画儿韩对假画一段精彩的鉴定就是对音韵学、历史学、气象学知识的揭秘:“这画看来惟妙惟肖,其实只要细心审视,破绽还是挺明显的。比如说,画名《寒食图》,画的自然是清明时节。张择端久住汴梁,中州的清明该是穿夹祆的气候了,可你看这个小孩,居然还戴捂耳风帽!张择端能出这个笑话吗!你再细看,这个小孩像是在哪儿见过。在哪儿?《瑞雪图》上!《瑞雪图》画的年关景象,自然要戴风帽。所以单看小孩,是张择端画的。单看背景,也是张择端画的。这两放在一块,可就不是张择端画的了!再看这个女人:清明上坟,年轻寡妇自然是哭丈夫!夫字在中州韵里是闭口音,这女人却张着嘴!这个口形只能发出啊音来!宋朝女人能像三国的张飞似的哇呀哇的叫吗?大家都知道《审头刺汤》吧!连汤勤都知道张择端不会犯这种失过,可见这不是张择端所画……”[6]比如《烟壶》中说书人一开始就用单口相声的讲述技巧介绍了烟壶的繁复的种类,并对其制造技术极为推崇:“一句话,烟壶虽小,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审美习尚、技术水平与时代风貌。”[7]邓友梅的小说凭借独有的人物、浓郁的京味儿民俗、浓厚的北京历史底蕴形成了自己的类型。虽然他设计了一个爱国的主题,但是他所关注的中心却是晚清北京城的社会生活与风俗世界,他以封建社会末期文化培育出的人物为表现对象,生动地展示了底层市民的众生相和北方地区的民俗相。再比如《铁龙山一曲谢知音》中对戏曲艺术的介绍,使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民俗和文物工艺方面的知识。
邓友梅小说的民俗味还来源于他对边缘人物特别是底层那些三教九流的、玩世不恭的人物的刻画,他们多半是八旗子弟、没落贵族、市井俗侩等,他们身上都带有浓郁的旧文化习俗,吃喝玩乐、不思进取,在他们身上邓友梅寄予着一种浅层次的国民性弱点的批判。
与邓友梅的风俗画相比,冯骥才的描写明显要深刻得多。在“怪世奇谈”系列中,他以丰厚的笔墨勾勒出一幅幅“津味”十足的画卷,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冯骥才在对民俗文化的描写上不仅仅是留于表面,而是深入其中,探究其文化意蕴,探究汉民族文化中某种恶的成分,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了挣脱恶性文化习俗束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令我们不能不佩服作家的笔力和思想的深刻。
比如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这三部小说其实是对传统文化中代表性的辫子、小脚和八卦完成的一个绝妙隐喻。以《三寸金莲》为例,作者所要表现的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缠小脚”这种民俗对人物心态、行为的影响及带给我们的启示。“小脚”只是一种象征物,“三寸金莲”被推崇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人性被压抑、被扭曲、被扼杀的历史。仅仅通过这个简单的“缠小脚”,小说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物的心态行为,写了在“缠小脚”这一恶性民俗氛围中生存的可怜又可悲的人物。作家对民俗事象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中糟粕的大曝光,让人们了解恶性民俗的全部内幕,人们透过眼花缭乱的小脚、绣鞋,了解了人物命运变迁背后的文化根源,看到那些表面上合情合理的民俗下所掩盖着的肮脏、龌龊和文化自身的糟粕。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作者是用貌似赞美的口气写“三寸金莲”,表面看是对这种文化的欣赏,其实是想让人们充分意识到并去思考这种病态的美为何在那个时代具有这样的魅力。作品是从对历史的观照中,让人们感受到历史在现实中的无形存在,言在此而意在彼,借历史之形物写现实的某种需要刨除的畸形意识。同时冯骥才也似乎在沟通“雅”“俗”文学之间做过一些努力,他的这些小说往往是取材于世俗生活或者是带有民俗文化积淀的历史遗迹,呈现出一种通俗化的倾向,但是与此同时他又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这些事物“俗”的描写中,而是贯穿着严肃文学的思考,对个体、对于生存价值关注是比较到位的。
综上所述,邓友梅、冯骥才通过对小说中民俗风情的的描写表达了他们对于汉民族文化的体认。如果说邓友梅是从历史文化领域中去展现北京的历史文化情致,那么冯骥才更多的是从传统文化入手去挖掘封建社会中的畸形文化从而达到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批判,使人们对清末的社会历史有个更全面的认识,从而使人们更好地去把握历史的本质。并且,他们不仅仅善于从细微处进行捕捉透视,也善于从大处进行全面描述,以充分发掘文化中的心理积淀,对文化中善的因子予以赞美,对于不好的积淀也给予了警醒鞭挞。
(三)以清新感见长并具有乡土气息的小说
这类小说的类型与以陆文夫为代表的小说有某种近似性,不同之处在于以陆文夫为代表的小说具有一种悠远的古韵,描写的是世俗人生,日常生活中的小人小事;而以清新感见长并具有乡土气息的小说多半是一种乡土气息浓厚、人性古朴美好的散文化小说。如果说前者是民间健康的良知和市民群体意识在当下社会的文化呈现,那么后者更多的则是传统文人精神气质、性格修养在当下社会的一种自我确认。在此以汪曾祺小说为例加以阐明。80年代初,大家还是处在伤痕文学的控诉中的时候,汪曾祺就以清新、隽秀的文字给文坛带来一股淡雅之风,从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文人情怀对他创作的影响。我们知道,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此处自古便是一个情韵之乡,他师承沈从文,自然十分注重小说的审美情趣。汪曾祺的视点都是放在自己的故乡高邮,那个未经渲染的乡土之地。在创作中他将民俗、风情、风物都提到与人物同等的地位,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从而取得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汪曾祺的乡土民情、“异秉”人物系列小说往往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相联系,而且在这种联系中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氛围,这或许与他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汪曾祺在其短篇小说选自序里就说过:“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我的小说里有些风俗画成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能为写风俗而写风俗。作为小说,写风俗是为了写人。”[8]他的小说常常以风俗作为环境背景,如《大淖记事》;或使风俗成为人的心理和活动的契机,如《受戒》;或写风俗本身就是在写人,如《岁寒三友》。特别是他的《大淖记事》,里面涉及到大段大段的风俗民情描写:“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从淖里坐船沿沙洲西面北行,可以看到高阜上的几家炕房。”[9]
在他细致的描写中,我们体会到的是顺乎人的自然本性,也体会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追求。读汪曾祺的作品,虽然有很多枝节,但是却让人有种曲径自然的感觉,仿佛似水般在流动,很安静,动静相宜。又如《受戒》中塑造的人物是世俗的,但是却让人感到率性自然,虽然他们是俗世的一员,但是本身却完成了一种超越,让人看到的并不是俗世中人的纠缠,而是一种超功利的潇洒与美丽。在他小说中,没有特定的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有的只是自然,纯美的人性。和尚可以娶妻,可以赌钱,也可以有七情六欲。汪曾祺讴歌的是民间的道德立场,虽然也写到了很多穷苦人们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但是侧重的是他们反抗的坚强和不屈。虽然从总体上看,他的叙述比较节制,感情色彩不浓,呈现一种和谐、中和的美学倾向,但是在乐感文化的背后仍是有某种隐隐之痛,如《陈小手》这样的作品也是暗含着作者的悲悯情怀的。
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是洗练的现代汉语,正如作者所言:“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10]他的小说语言叙事简洁,舒缓有致,文白相间,雅俗互化,很多都是近于口语化的描写,鲜活明快。故事性不强,叙事者的插入成分较多,富于生活气息,对话往往精练传神,体现出小说文体的典范性。
总体来看,汪曾祺在对于民间文化的无间的认同上,与邓友梅、冯骥才等人的叙事立场不同,他用民间的真善美来净化乡土生活,描摹乡土生活,通过语言、意象塑造等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清新的、淡雅的类型,屹立于文坛。
二 80年代以来民俗风情小说的意义
民俗不仅是数千年来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而且也是具有现实形态的存在;而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也总是不断地渗入到主体的创作之中,从陆文夫、汪曾祺等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首先,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环境来看,随着文艺政策的变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意识形态的不断松动,这就为文学的抒情性的回归提供了土壤,这个过程中乡土风俗文学以鲜明、活泼、明净并且充满知趣的形态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乡土风情小说缓慢的、写实式的叙述笔调引动着伤痕、控诉的文学风气的转变,并自觉地与意识形态形成了隔绝,划清了界限,回归了文学自身应有的审美属性,可以说民俗风情小说为文学真正回归本源贡献了一分力量。
其次,民俗风情小说有的描摹民间本源的生存状态,关注文化场景的审美意义,如邓友梅、汪曾祺;有的深入传统文化的深处进行探究,开启了人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视野,如冯骥才。他们都为寻根小说派的触发提供了契机,在文化启蒙意义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当下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民俗风情小说,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扮演着一个“扶弱抑强”的角色,既是对弱势的传统文化的支撑,也是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纠偏。
最后,民俗小说与审美现代性是暗通的,它所带来的审美意义是不可估量的。自从经历过“文革”这个扭曲的现代性阶段以后,社会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为现代性正常伸展带来了可能。80年代先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时代,体制改革之后,文化消费日趋繁盛,资本与罪恶一同来到人间,不断发展的社会带来的是整个时代的变迁,人已经将传统、将诗意丢失了,物欲横流、精神荒芜、暴力野蛮,各种被打入底层的诱惑浮出历史地表,谁来填充人的灵魂的空白?谁来拯救人的苍白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作为与传统文化续接,蕴含着传统文学的抒情性、古典性的民俗风情小说或者散文,它们关注着美、宁静、纯洁,关注着心灵,这些都构成了一种审美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现代性是要求关注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发展,它促使人们反思对环境和社会所造成的危害。
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讲,20世纪以来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在西方世界面临着普遍的异化和焦虑感,人们寻找失落已久的精神世界,寻找可供填补的精神家园的努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所以海德格尔才发出“诗意的栖居”的感慨。从当下背景看,9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乃至当下的新生代小说,诗意便一直在流浪,太多的生存压迫和形而上虚无思考使得人们灵魂从未放松过,也着实反映了当下精神生活资源的贫乏,在民俗小说家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静谧的世界,一个能令人们的心灵久久震撼的图景,如何安居,怎样生存,或许在陆文夫、邓友梅、汪曾祺那里获得答案;民俗风情小说不断地召唤人们进入一个诗意的生活场景,哪怕是一个精神乌托邦,都足以寄托疲惫的心灵。
总之,80年代的民俗风情小说不仅塑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艺术形象,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人物画廊,其对于文坛、对于当下生活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结 论
以上简单勾勒了80年代的民俗风情小说的类型,但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作品类型,如韩少功等一批作家表现怪诞的原始民俗风情,多是从想象的角度完成对民族文化的寓言,其民俗风情价值则是很难界定。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小说,柔情的、厚重的还是淡雅的,立足点都是文化背后的“人”,因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人学。民俗风情小说与其他类型小说观照个体的不同方式在于其“民”与“俗”的交叠——文化上的“俗”与作为个体的“民”的交叉,作家们在对文化的叙写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对个体的深情审视,这个“民”并不是一种集体的指称,而是表现为具体的、感性的个体生命以及过程。因而现代民俗风情小说往往是以个体的‘民’为出发点来解释人生,并在世态风情的包裹中表达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因而更具有形象化和具体性的特性和优点。可以说,在这类小说的研究中,民俗风情与人物塑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作品通过民俗文化来透视个体生命过程中的现实生存困境、心灵困境和人性困境等等,而这些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意义。如何在这一层面乃至更深层的意义进行发掘,则有待于现代民俗学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
[1]王万森,吴义勤.中国当代文学50年[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157.
[2]郁乃尧.陆文夫的人生追求[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07-21(7).
[3]陆文夫.美食家[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94.
[4]张学军.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102.
[5]邓友梅.邓友梅小说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1.
[6]邓友梅.中国小说五十强(1978~2000)[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290.
[7]邓友梅.京城内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8.
[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3)[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19.
[9]张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上)[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4.
[10]汪曾祺.自报家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92.
——由《苏州杂志》解读陆文夫的三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