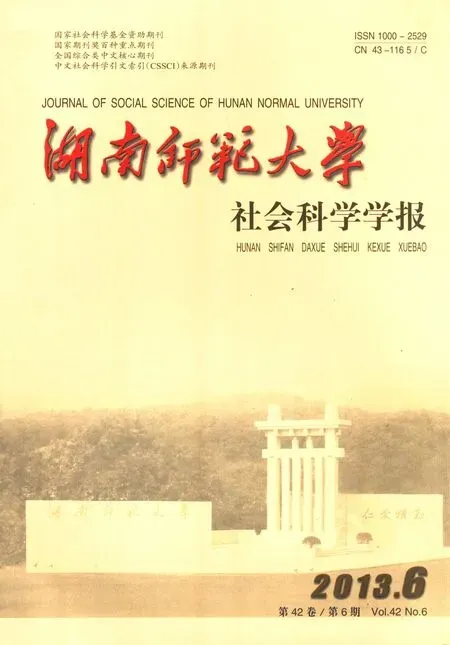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李清良,夏亚平
比较文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已有一百余年,但对究竟“何为比较文学”,即究竟如何对其进行学科定位,迄今仍无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使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学科该向哪里走也还不明朗”;所以来自学科内外的“危机”之声一直不绝于耳,确实可如美国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所说,比较文学依然还是一门“将成”而未定型的学科。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其实已有不少突破,真正做出了具有国际意义的大贡献,也越来越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突破是,为比较文学学科提供了一个更适应其发展趋势的定义,即明确主张比较文学应以跨文明研究为基本任务,并以此为核心建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体系。①近年来又有学者明确提出,应将“新人文精神”作为比较文学的精神和灵魂。②这实际上是试图超越方法论层面,从学科精神与境界来界定比较文学并推动其发展。这方面的工作虽然还只是刚刚起步,但其意义相当重大,必将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和理论建设的新方向和新任务。本文想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在开展这一重要工作时,颇有必要认真回顾和清理各国比较文学已有的人文主义传统,它们不仅丰富而深厚,而且在新时代并未过时。
一、克罗齐的质疑与法国学派的人文主义传统
比较文学诞生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张力之中,也一直处在这种张力之中。如所周知,比较文学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人文学科的自我定位已经深受自然科学模式影响,“比较”一词就有浓厚的科学色彩,“比较文学”之名意味着它是一项恰如“比较解剖学”、“比较语言学”般的科学研究。所以法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③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相当明显。
但这种科学主义倾向遭到了克罗齐的尖锐攻击和强烈反对。其反对理由不仅在于“比较的方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朴素的研究手段,它没有权利要求限定一个专业的全部领域”,更在于科学主义取向将从根本上抹杀文学的个性,从而也抹杀作为艺术直觉的人的个性,而这种个性正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应当泯灭,不应当消逝在历史的其它部分中,而应当保持其固有的独特的意义和特征”④。克罗齐的反对当然不能阻止比较文学的继续发展,但其影响持续而深远,成为了比较文学必须不断与之“较劲”的“他者”,迫使比较文学学科一再基于人文主义立场反思自身的正当性。后来韦勒克在批评法国学派时就颇受克罗齐思想的影响。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学者苏珊·巴斯奈特于2006年的《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中仍然说:“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这使我回想起伟大的意大利批评家克罗齐对比较文学的高度怀疑”⑤。可见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克罗齐的声音依然在不断回响。
韦勒克等学者指出,西方比较文学的兴起是对19世纪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对法、德、意、英等国很多文学史家的孤立主义的异议;换言之,正当国别文学研究日益紧缩,与西方世界的重大思潮与表达形式人为隔绝之际,“比较文学观点曾把一种世界主义态度带给国境内外的文学研究”⑥。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的理念紧紧相连(尽管所谓“总体”与“世界”曾被不恰当地理解为没有差异的统一体),并开展出这样一种人文主义面向:努力突破民族界限,在“国际视野”中审视文学与人性,充当相互对话与沟通的中介。所以毫不奇怪,最早促成比较文学成为一门学科的那批人,多是“站在国家之间的十字路口,或者至少是一国的边界上”,有着“充当两国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者的真诚愿望”⑦。
也许正因如此,比较文学法国学派虽然认同科学实证主义,但也有其人文主义追求一面。早在1921年,法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巴登斯贝格(F.Baldensperge),就在《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这篇纲领性导言中明确宣称,比较文学乃是为“新人文主义”作准备,“将为新的、人道的、有生命的、文明的信念开辟道路”,“比较文学的广泛实践尤其可以促成这种新人文主义”,因为具有国际视野的比较文学可使文学研究具有更高的精确性与客观性,可为我们这个脱了节的时代建立某些“共同准则”提供“比较可靠的核心”。⑧梵·第根在《作为国际理解工具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也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将导致一种“新人文主义”:“大家知道15世纪和16世纪的人文主义是什么,比较文学的研究导致的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这是比前者更广泛更丰富的人道主义,更能使国家之间相互靠拢。……比较文学……迫使实践它的人们对于我们的天下的兄弟们采取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采取一种文化的自由主义,没有这些,任何一部共同的作品在人民之间不能被尝试。”⑨此处所谓“人道主义”当译为“人文主义”。韦勒克曾批评说,早期法国学派的这种人文主义追求,事实上常“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不过应该承认,他们对于人文主义的愿望是真诚的,虽在实践上还远不够,却为后来者提供了基本理念。
勒内·艾田伯(RenéEtiemble,或译为艾金伯勒、艾琼伯)的主张尤能体现法国学派的人文主义倾向。陈思和教授对此已有专文介绍与研究。⑩1963年艾田伯在《比较不是理由》中,开篇就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试图以此“定义我们这门学科的精神”,即在比研究方法和学科定义更高的层面上,指明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及其精神境界。正是基于这种人文主义关怀,他接受了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的批评,但反对将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主张比较文学应是“将历史方法与批评精神结合起来,将案卷意见与‘文本阐释’结合起来,将社会学家的审慎与美学家的大胆结合起来,从而最终一举赋予我们的学科以一种有价值的课题和一些恰当的方法。”[11]1974年他在《总体文学论文集》中,又谴责西方学者定义和介绍比较文学时仅以欧美为中心,“所有的书目都局限于印欧语系的几大语种,这在今天已经落后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而且缺少地球上四分之三的地区”。[12]为此,他在1985年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大会上,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1980—1985年中国的比较文学》为题做了大会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就并展望其无限潜力与前景。[13]
法国学派的这种传统,在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等人于1983年修订出版的《什么是比较文学》这本权威性教材中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该书“引论”说:“作为一种普通的文化工具被接受的比较文学,在法国还在寻找它的高级科研的纲领。机构和它很不适应。它本身似乎还在两种基本的使命之间摇摆,一方面,是在各种形式下对人道主义进行广泛的创新;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科学”,“照我们的看法,在方法的概念下,可以把这两种使命结合起来”;就前一种使命而言,“可以把比较文学称做萨特谈存在主义时所说:它是一种‘新人道主义’。艾琼伯在一个开一代风气的格言式的标题中证明了这一点”[14]。此处所谓“艾琼伯的格言式标题”,就是指艾田伯《比较不是理由》第一章导言中“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这个小标题。
二、美国学派的人文主义传统及与法国学派之关系
美国学派崛起的标志,是韦勒克于1958年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教堂山会议”)上以《比较文学的危机》为题对法国学派予以尖锐批评。他认为法国学派存在三大毛病:一是使比较文学背上了“十九世纪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重荷”,成为了忽视文学作品和“文学性”本身的“外部研究”,从而“把文学研究非人化”;二是“在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构筑一道人造的藩篱”;三是“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使比较文学研究变成了“为自己国家摆功”、“计算文化财富”、书写“文化功劳簿”的“文化扩张主义”。[15]1965年他在《今日之比较文学》中坦承,他对法国学派的这种批评源于20世纪20年代,从那时起他就接受了克罗齐、狄尔泰等人文主义者对于科学主义的不满;1927年他到美国后,又在以白璧德(Irving Babbitt)、穆尔(Paul Elmer More,也译作莫尔)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运动”中发现了同样的不满。因此,他在1958年对法国学派的批评实可视为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的反抗——“‘人文主义’的确切含义正是教堂山大会的议论中心,也仍然是今天比较文学中的问题”[16]。
韦勒克这篇《今日之比较文学》表明,以白璧德和穆尔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于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有着重要影响。其中说到:“白璧德的《文学与美国大学》写于1908年,至今仍是一颗投向十九世纪博识的重磅炸弹。他认为这种博识与德国有害的学究气是一路货。他预言,‘比较文学如不严格置于人道的标准下来研究,将成为最微不足道的学科之一’。莱文(Harry Levin)之被授予白璧德比较文学教授,不仅是表示人们对欧文·白璧德的敬重,而且也是人道标准在哈佛得以延续的保证,尽管莱文对‘人道’一字的理解与白壁德所赋予该字的特殊意义有所不同。”此处所谓“人道”皆应译为“人文”,白璧德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严格区分人文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nitarianism),其《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的头两章对此有详细分疏。该书第五章又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如不严格置于人文标准下来研究,将成为最微不足道的学科之一。”或译为:“若非严格遵循人文标准而加以研究的话,比较文学将会变成最为琐屑无聊的课程”[17]。
尽管对“人文标准”或“人文主义”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但白璧德的上述主张,显然为韦勒克以及白璧德的学生们深深认同,因此对整个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18]上文提到的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莱文就是白氏的学生(1980年代初他曾来华访问讲学并与钱钟书等人有过深入交谈),与韦勒克合写那本著名的《文学理论》的沃伦(Austin Warren)也是白氏的学生。对于白璧德的这种影响和贡献,韦勒克非常恰当地评价道:“他的研究的一大功绩在于认真看待思想问题,而当时美国学术界则几乎一味沉潜于求实考证的古籍研究。白璧德的视角包罗古代,英国、法国和德国文学,还浮光掠影涉及远东文学,所以促进了比较文学的事业,他历来强调地推荐这门学科,对于它的隐患有着恰当的意识。……人们也不可低估他对一群学生所产生的作用……。”[19]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派的人文主义倾向又突出表现为强烈反对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的一股新风气,即热衷于空谈新理论(如接受美学、叙事学、符号学、解构主义等)而不作价值判断、不重实际批评。在1985年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大会上,以韦勒克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对此风气大加挞伐,认为这是“否认生活的感知一面”,“否认美感经验”,“瓦解作品”,因此是“反美学的象牙之塔”,是“新虚无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欧文·艾德里奇(Owen Aldridge,伊利诺大学教授,曾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还专以《美国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美学》为题,重申比较文学必须是“人文的”(humane),不仅应有人的感情在内,还应重视道德标准,应以文学中的精华为评价标准,而不应是形式主义的分析和抽象推论。亲临大会的杨周翰教授对此一言以断之曰:“他们维护的是人文主义原则。”[20]
美国学派的人文主义倾向也受到法国学派的影响。有两个例子可以表明此点。一是陈思和教授已指出,艾田伯的《比较不是理由》于1963年出版后,最热忱的响应者就是美国的两位比较文学教授。他们不仅很快翻译了这本小册子,还对艾田伯“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这一观点加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并说:“总体而言,创造是一个深刻的社会现象:呼唤人与人跨越分离彼此、使其孤立的鸿沟,比较文学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的耳朵对这种呼唤变得更加敏锐。”[21]另一个例子是勃洛克(Haskell M.Block)。他于1969年发表了《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赞同韦勒克的基本观点,也客观评价了法国学派的贡献与功绩,最后说:“巴登斯贝格曾设想通过比较文学的发展来‘为新的人文主义做准备’。二十世纪的混乱历史为他这个设想作了辛辣的评注,但这种想法本身仍旧延续了下来。由于比较文学要求研究者具备聪明、机智的态度,它将把我们引向人类的相互同情和团结。我们彼此需要。我们正投入一项集体合作的事业,很可能,通过发现、解释和妙悟,我们将对这个人文主义有新的体察,而我们的文明的存亡正有赖于这个人文主义。”[22]高度评价了巴登斯贝格的“新人文主义”主张,并主张所有的比较文学研究者都应遵循人文主义精神,跨越国别和派别的鸿沟,“相互同情和团结”,“投入一项集体合作的事业”。
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以及同一学派内部之间,对于“人文主义”或“新人文主义”的理解,当然有着各种或显著或细微的歧异。不过,“人文主义”的确切含义本就随人而异、随时不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指出,“人文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派别或哲学学说,而是一个包含着各种不同甚至相反观点的传统,“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念的维度,以及一场持续性的辩论”。当然,人文主义作为传统也有如下“最为重要和稳定的特点”。其一,人文主义是与神学思想和科学思想不同的一种思维模式,不仅强调以人本身为关注焦点,更强调以人的实际经验为思考基点,“包括价值观与全部知识在内的任何概念,都是人的心灵从经验当中汲取的”;其二,强调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尊严,都有拓展、提升、改善自己并具备自由意志的潜力,因此极为重视素质教育和个人自由,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唤醒人性意识从而充分发展个性与潜能;其三,重视思想,但不信任仅凭理性和逻辑建立起来的抽象体系,也不认为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更不主张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总是综合考虑普遍与特殊、古与今、我与他等各个方面和层面的经验;与此相应,既高度重视传统、经典与文学艺术,也多倾向于对现实生活的积极参与。[23]对于比较文学来说,其中第三点最为密切相关,它在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具体表现,就是由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所开展出来的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主张跨越民族界限,以“国际视野”与胸怀更为客观而全面地审视文学与人性,努力“充当两国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者”;二是强调文学传统和经典作品不仅是抽象理论的注脚,更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创造和保护了某些最高的、普遍的价值,对人性培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三是重视审美经验与文学批评,反对将文学研究变成“中性的科学主义”、“冷漠的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
由此看来,西方比较文学从来就有其人文主义传统,其基本精神可概括为:以探求共识、完善自我为宗旨,以亲身参与、共同经验为依据,以广采博稽、综观异同为方法和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基于文学对于人性拓展、提升、改善和实现的重要作用,充分重视由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经验的各个层面与方面(如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国、理性与情感、逻辑与现实等),既不任凭它们成为相互孤立或对立的“多”(the Many,diversity),也不强迫它们成为简单混同和化约的“一”(the One,unity),而是既彰显其中的区别与差异,又力图加以综合和平衡,使之相互映发和交融。西方人文传统的这种方法与原则,若用中国传统术语表示,实可谓为“融会贯通”,简言之即是“会通”。
总之,人文主义实是西方比较文学向来就有的传统并已开展出多个面向。正是这个传统,使得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样截然对立,而是逐渐从对立走向和解,走向相互尊重和理解,也相互影响和吸纳。也正是这个传统,内在地促使比较文学不断对其学科定义和学科方法进行反思和否定,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学科“危机”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正是其内在的人文主义精神所遭遇到和感受到的“危机”;每一次“危机”的解除,则是其人文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开拓和实现。假如没有这种人文主义追求,比较文学既不会感到“危机”,也不能克服“危机”。可以说,人文主义正是西方比较文学的内在精神、灵魂和动力。因此,从西方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来看,我们也可得出与艾田伯相同的结论——比较文学的“精神”就是人文主义。比较文学归根到底是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文学研究,是“科学”永不可能完全同化的“他者”。
三、中国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早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传入之前,中国学者就已有了比较文学,它实际上是中外文明相互冲突、交融的表现与结果。所以正如学者们指出的,与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局限于文明内部不同,中国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从一开始就“跨越了东西方文学,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24]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开阔的世界视野,以及在中-西(文明)和古-今(传统)相互竞争和冲突中力图实现综合、交融和平衡的追求,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天然地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现象,因此也对凡具人文主义色彩的中外思想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与亲和。中国比较文学无疑受到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按照上述布洛克的观点,将中国传统思想尤其儒家思想视为一种“人文主义”应不为过。就连对“人文主义”涵义辨析甚严的白璧德都认为,中西两种文化“均主人文,不谋而合”,尤其儒学传统中更有“优于吾西方之人文主义者”,包含了“极其美妙的人文主义因素”,因此他又有“儒学人文主义”的提法。[25]更何况,自伏尔泰、狄德罗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本就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白璧德的思想也是如此。[26]不过此处将着重分析中国比较文学对于中西人文思想进行会通的一贯传统。
吴宓也许是最早正式向国内学界介绍西方“比较文学”的中国学者。他于1918~1921年间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师从“新人文主义”创始人白璧德和穆尔并成为其忠实信徒。其《论新文化运动》一文首次向国内简要介绍了西方比较文学:“近者比较文学兴,取各国之文章,而究其每篇每章每字之来源,今古及并世作者互受之影响,考据日以精详。”[27]这显然主要是针对法国学派所极力标举的影响研究而言。但此文主旨是反思并批评“新文化运动”的片面化与激进化,认为“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文化与文学皆不当简单以新旧论高下,因此“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必当“博采东西”、“并览今古”、“比较异同”、“互相发明”、“融汇贯通”。这种主张,与他在美国接受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一脉相承。这就决定了他心目中的比较文学,并不局限于单纯的影响研究,而是如白璧德所教导的“严格遵循人文标准而加以研究”。在“中西古今”空前冲突之际,吴宓实是以中西人文精神的互相比较和会通为其基本取向和宗旨,这非常鲜明地体现于他归国后所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文学与人生》等比较文学课程上。如所周知,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与压力下,本来就有不少中国学者依据中国传统学术的“会通”观念明确提出了“会通中西”的主张(尽管在“会通”的层面和基点上有着不同意见),吴宓本人在出国前也是如此。因此,当吴宓归国后重提“会通中西”时,对于国人来说,几乎不觉其根据已是来自西方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正如吴宓本人所说:“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28]
重要的是,不止吴宓一人如此。同样颇受白璧德影响的陈寅恪,也像吴宓一样,谈到“比较文学”时谨守西方的学科定义,但其实际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却远远超越了这种定义,而将其与中国传统的“综贯会通”观念相融合,由此倡导一种更为宏阔精深、立体多维的“通识”之学(包括中外打通、古今打通、地上与地下打通、官书私著打通、学科界限打通、真伪打通、“同情”与“批评”打通、探求真实与提供鉴诫打通,等等),并强调其最终理想就是要造就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通人”理想。[29]这种“通人”、“通识”之学,其实正是“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既吸收了包括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内的西方人文传统,又将其与中国固有的人文传统尤其是“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相融通。
这就表明,从一开始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就连同其内在的人文主义精神被一齐传入中国,也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本有的人文传统尤其是“会通”观念交融一体而难解难分。这就使得中国比较文学从来就不局限于西方的定义与方法,尤其是不局限于由早期法国学派所特别标举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还有另外一种情形:有意回避或很少提及“比较文学”,却以其实际贡献推动着中国比较文学突破西方定义的局限而自觉走向中西人文传统的会通。在这方面,朱光潜可算是典型代表。他对中西文学和美学的比较研究深广而系统,一向被视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大家。但他却从未提倡过比较文学,也从未认为自己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甚至连“比较文学”一词都很少提到。晚年时,他在一次比较文学座谈会上说:“做一切科学工作,都免不了比较,或者相关的问题比较,或者发现了问题来比较。……真正的研究一定要看这纵的传统和横的影响。这样,比较文学的范围就应当非常宽,不能狭窄”。[30]这实际上是从方法论角度否定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独立性,只将其纳入运用比较方法的文学研究;也就是说,尽管他在法国学派的中心——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过,但他并不认可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定义。他其实是有意“对比较文学始终保持着高度缄默的态度”。[31]朱光潜对比较文学的这种看法,源于他曾深入研究过的克罗齐,克罗齐当年正是从人文主义立场出发,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科学主义”倾向深致不满和质疑。朱光潜通过克罗齐、尼采、黑格尔、莱辛尤其是维柯等人,深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不过,朱光潜的上述看法,也源于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比较流行的“会通”观念的影响。这就导致他的中西比较研究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会通”特色:会通古今,会通中外,会通各家。朱自清非常准确地指出,朱光潜是在“比较各家学说的同异短长”的基础之上“加以折衷或引申”,“公公道道地指出一些比较平坦的大路”,所以,他既重视西方,也“未忘记中国”,甚至连“相反的理论”也“有同样的地位”,如此一来也就“有他自己在里面”。[32]由此可见,朱光潜有意对源自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保持高度缄默,正是为了突破其局限,而以其实际成就引导中国比较文学走向会通中西人文传统一途。这与吴宓、陈寅恪等人实是殊途同归。
吴宓、陈寅恪、朱光潜等人主要以学术典范和榜样的方式引导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同时,他们的上述取向也较早渗入了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甚至教育体制中。在这方面,吴宓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他在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和代掌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改为外国语文学系)期间,明确主张应以培养“会通中西”的“博雅之士”为目标:侧重研究国学的当“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又能“具有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侧重西学的则当“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又能“汇通中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33]所谓“博雅”或“博通渊雅”,是“会通”态度也是“会通”结果。“博”而能“雅”表明,“会通”的结果既是广度的拓展(“通知全体”而“明辨异同”)又是高度的提升(判断精当而“融会贯通”),而“会通”的目的则不仅在于求知,更在于明德成人,成为一个真正具有人文素养和精神的文明人。吴宓的这种思想及其实际举措,“不仅为清华,而且为全国开拓了中西贯通、融西入中的教育传统”。
正是在上述学术榜样和教育思想的影响之下,出现了一批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杨周翰、李赋宁等。他们继承并拓展了前辈们的会通精神,积极倡导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科学与人文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实现沟通和理解;其中钱钟书的探索更是空前深广,并集中体现于其“打通”说(对此笔者将于另文中详加分析)。他们又以会通中西的精神指导了一批又一批弟子,并以其实际成就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国学界。可以说,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中国学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包括力主比较文学应扩展为跨文明研究,都是在他们的影响甚至是支持下才得实现的。正是在他们的教导、影响和支持之下,新一代学者遂得更进一步,自觉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身份,向国际学界明确而全面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与倡议。
由此可见,会通中西人文思想而自觉超越西方局限,实是中国比较文学自始至终从未间断的传统。正因如此,中国比较文学才得不断开花结果,最终形成了不断开拓创新的“中国学派”。艾田伯所谓人文主义是比较文学的“精神”,这对中国比较文学传统而言也同样适用。
四、结 论
如今随着全球在生态环境、科学发展、身心认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危机日益加深,学者们再次强调比较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意大利著名比较文学家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 Gnisci)就提倡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比较文学,认为由此“也许会导致一种全球的多层次的‘新人文主义’公式”。[35]我国学者乐黛云教授更是大力倡导以一种“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作为“未来比较文学的灵魂”。她认为,此种新人文精神以实现人与人之间、学科与学科之间尤其是科学与人文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为途径、“以人的幸福和文化的和平多元共处为根本目的”;之所以说“新”,“不仅是指所面对的问题新,而且是指人类当前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和过去很不相同了”。[36]
本文的分析可以表明,这种人文主义追求不仅有感于现实需求,也深合于比较文学的一贯传统;同时也试图表明,历史上已经有过各种明言或未明言的“新人文主义”,它们的提出都是因为“面对的问题新”,不过其基本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却未必和整个过去“很不相同”,而可能只与某些历史阶段甚至只是某些群体或流派的主导倾向(如片面追求理性和普遍性)很不相同。事实上,经由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群体和派别,比较文学学科的人文主义传统已经突破了某些一度流行的主导倾向,而开展出多个面向、多种“新人文主义”,并完全可以在基本精神上包含或通向当今的各种“新人文主义”主张。因此,为使比较文学更好地体现人文主义精神,认真总结其已有传统和不同面向,与认真面对时代新问题实是同等重要。如上所析,对于传统不是采取笼统和割裂的态度,而是加以“融会贯通”即充分检视、辨析、融贯与拓展,正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
注 释:
①曹顺庆:《中国学派:比较文学第三阶段学科理论的建构》,《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②[36]乐黛云:《比较文学与21世纪人文精神》,《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1期;《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1期;陈戎女:《上天责我开面目,创辟用启铸华章——乐黛云先生访谈录》,《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夏之卷,等等。
③⑥⑦⑧[11][12][15][16][22]干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第 56-57 页,第 127 页、第191页,第 127页,第 47-48页、第 126页,第 102-103页,第 77页,第122-135页,第 160-161页,第 206页。
第四,共享经济的运作离不开信息技术平台这一关键媒介和载体,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是保障共享经济顺利运行的重要保障,能够为其带来很多支持与便利。
④张敏:《比较文学的学科依据——试论克罗齐世纪初对比较文学的诘难》,《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
⑤(英)苏珊·巴斯奈特:《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黄德先译,《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
⑨[14](法)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张连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3页,第11页。
⑩[21]陈思和:《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之精神基础——论勒内·艾田伯的“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3][20]杨周翰:《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动向——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1届大会述评》,《国外文学》1986年第3期。
[17](美)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张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18][26]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考察》,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7期(2002年6月)。
[19](美)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6卷),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62-63页。
[23](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年,第2页、第163-169页。
[24]杨周翰:《镜子和七巧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页、第17页;乐黛云、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整体观》,《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25](美)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说》,胡先骕译,《学衡》第3期(1922年3月);吴学昭译:《欧文·白璧德与吴宓的六封通信》,《跨文化对话》第10期(2002年)第150页、第152页。
[27]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 4期(1922年 4月);
[28]吴宓:《吴宓诗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214-215 页。
[29]李清良:《熊十力陈寅恪钱钟书阐释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2-96页。
[30]朱光潜等:《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座谈纪录》,《读书》1982年第9期。
[31]钱念孙:《比较文学消亡论——从朱光潜对比较文学的看法谈起》,《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32]朱自清:《〈文艺心理学〉序》,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28页。
[33][34]徐葆耕编:《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3-174页、第204页,前言第19页;陈建中、蔡恒:《吴宓的“博雅之士”:清华外文系的教育范式》,《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35](意)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罗湉译,《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