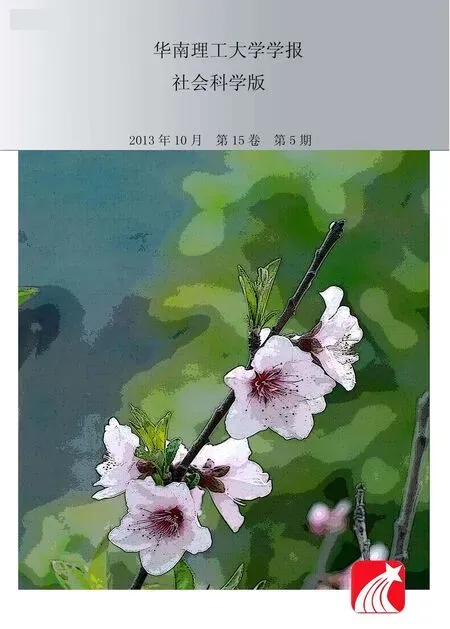幸福工程的短板与幸福教育的意义*
王 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一、幸福工程的短板
“幸福”可谓近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大热词。“幸福”作为日常话语的高频词汇,随着政府对民生的日益重视,上升政治核心话语成为施政导向,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表明,各级政府正在试图摆正社会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诠释。如何打造幸福工程?目前的基本思路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民生福祉、法制建设、政府改革等几个方面进行。这样的思路凸显了以民生为导向的社会发展理念,我们从中看到了可贵的人文情怀,然而,这样的思路更多的是着眼于社会建设,着眼于通过改善外部的客观环境以提高幸福指数,却忽略了有关幸福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幸福是一种内在心理感受,具有主观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个理论上的迂回,对幸福的内涵进行剖析。
幸福可以被理解为对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需求得以满足时的愉悦心理体验。愉悦的心理体验是幸福的主观形式,而需求得以实现是幸福的客观内容。换言之,幸福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是主体对客观生活的主观感受,是主观性与客观性双重维度的统一。幸福虽然有赖于人的主观判断,但有待于客观内容来填充;幸福虽有客观的内容,但终究表现为一种主观感受。故而对于幸福而言,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皆不可或缺。
从以下哲人对幸福的定义中,都可以看到幸福所具有的主客观双重维度。梭伦将人的幸福概括为中等财富、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好的儿孙、善终五个方面[1]31-37;伊壁鸠鲁指出,幸福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不受干扰”[2]94-95;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善的实现,善的事物有三类,一是外在诸善,如财富、尊荣等;二是灵魂诸善,即德性;三是身体诸善,如健康等,这其中,德性最为根本。不难发现,财富、身体、尊荣属于外在的客观内容,而愉悦宁静的心灵、完善的人格属于内在的主观形式。先哲们对幸福内涵的揭示深刻地说明: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幸福,必须客观维度与主观维度同时满足,缺少前者,幸福如薄冰行走般艰难,镜花水月般虚幻,比如阿Q;而缺少后者,再优良的条件与资源亦不能被贪婪、扭曲、阴暗、颓废的心灵转换为幸福的体验,比如那些“身在福中而不知福”的人。这意味着,一个人要获得幸福,除了“外求于物”,还必须“反求诸己”。
幸福所具有的主客观双重维度表明,要打造幸福工程,离不开良好的外在客观条件,如富裕的经济,可靠的保障,安全的治安,公平的制度,高效的政府,同时也离不开每个个体用积极、健康的心态去对幸福进行体认。然而遗憾的是,主流话语对幸福的客观维度强调得很充分,而主观维度并没有在政府幸福工程的蓝图中给予应有的重视。当然,就目前的社会状况而言,幸福客观维度的建设可能更为迫切,但这并不意味着幸福主观维度的塑造可以搁置起来,因为幸福的主观维度同样会对幸福感的形成产生根底性的影响。
心理学家对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SWB)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与俗常的幸福观形成了较大的反差。通常我们认为,更多的经济收入会导致更高的幸福水平,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会更加强调金钱对幸福感的决定意义,然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一定范围之内,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金钱对幸福感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3]。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统计结果显示,当人均收人达到3000~5000美元后,经济发展与幸福水平的关系越来越脱节[4]。Diener等曾对1985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100位最富裕的美国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与一般的美国人相比,他们只是稍微幸福一点点[5]。这就是Brickman等提出的著名的“幸福水车”(hedonic treadmill)现象,即经济收入像水车轮子一样滚滚向前,但幸福水平却在原地打转,并不随经济发展而显著提高。
我们可以依据幸福所具有的主客观双重维度,将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如人格、预期、动机、社会比较、应对方式等,外部因素如经济水平、社会支持、生活事件、身体状况等。外部因素是直观的、显性的,而内部因素是潜在的、隐性的,因此外部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往往被过分放大,内部因素的效应则被漠视。当我们感到幸福缺失时,通常会把原因归结于外部因素的缺失。尤其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我们会把原因归结于经济收入的匮乏。这让我们产生一种心理幻想:只要经济收入水平提高之后,幸福的问题就会自行解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所谓“美国困惑”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Myers对二战以来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到20世纪末,整个社会的财富几乎比1957年时翻了一番,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都有了明显增加,但“非常幸福”的人数却从1957年的35%下降到1998年的33%。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离婚率翻了一倍,青少年自杀增长了3倍,暴力犯罪增长了4倍,抑郁症患者尤其是青少年患者的人数急剧上升。他把这种物质繁荣而社会衰退的现象称为 “美国困惑”[6]。
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指出:“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7]Heady和 Wearing的研究也表明,外部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短暂的,内在的人格特质或认知因素对幸福感的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收入的增加或减少,会在短期内提高或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但是由于受到人格因素的调节作用,人们最终会回复到之前的幸福感的水平[8]。Diener的研究显示,幸福感的关键,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和目标如何在外部事件与生活质量之间进行协调[9]。Lanchman和Weaver的研究也发现,那些收入低但能够维持高度控制感的被试组报告的幸福感的水平几乎与高收入的被试组一样高[10]。这都表明,外部因素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必须通过人格等内部因素作为中介。换言之,决定幸福感的并非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件本身,而是人们对事件的解释。
笔者用如此之多的篇幅,引介当代心理学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无非是想说明,经济收入等外部因素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对幸福具有主宰性的作用,而内部因素尤其是人格却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但遗憾的是,这一至关重要的内部因素所产生的效应,长期以来被官方主流话语低估。虽然,早在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曾提出,要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011年更是首次将“社会心态”写入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辅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这表明政府开始逐渐重视幸福主观维度的建设,但目前我们似乎尚未看到政府在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方面有进一步的重大举措。
二、幸福教育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说,培育心态是个人的事,政府参与的是外部的公共事务,对幸福的内部因素无力进行干预。诚然,幸福的主观性决定了政府无法替代个体成为判断幸福的最后因,“被幸福”的幸福不是幸福,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对于幸福的主观维度,政府束手无策。相反,我们急切地需要政府在改善个体幸福的内部因素方面有所作为。
内部因素当中的人格因素,被认为是主观幸福感最有力、最稳定的预测源之一[11]。乐观、自制力、外向、智慧、勇气、爱、毅力、宽容、创造性、责任感、利他等积极的人格,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而这些积极人格的形成,与后天教育密不可分。在2010年的“积极心理学与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达成一致共识:积极人格对身心发展十分重要,这种品质有些是与生俱来的,但更多的是通过后天努力和学习获得的,而且越早学习越好[12]。比如,如果父母悲观,孩子通常也具有悲观人格,但乐观可以通过教育而形成,一个悲观的人可以通过心理教育转化成为乐观的人,从而感受到更多的幸福。这意味着,人们感受幸福的能力是可以习得、塑造的,幸福感可以通过教育得以提升。当然,这种教育非同于目前普遍存在的异化教育,而是一种“幸福教育”。
让每一个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本是教育所应追求的永恒的、终级的价值,我们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与技能,追根溯源无非是让自己更加幸福,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校几乎无一例外地把那些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而遗忘了目的本身,背离了教育的初衷。现如今,我们的学校惟智主义倾向严重,片面强调智育,注重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训练,淡漠道德教育与情感教育,忽视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塑造,人文教育被当作可有可无的装饰。现行的教育模式,虽然能够让学生改善幸福的外在客观条件,比如工作和收入,但却无力改善幸福的内部因素,无力成就完善积极的人格。
而幸福教育则能够弥补现行教育模式的缺陷。幸福教育即关于幸福观、幸福品质以及幸福能力的教育,旨在让人们获得判断幸福、感知幸福与创造幸福的能力。幸福观、幸福品质、幸福能力是构成幸福的重要要素。幸福观是对什么是幸福、幸福的标准等方面的根本看法,幸福品质是感受幸福的一种人格力量,而幸福能力则是指创造幸福、实现幸福的资本。
幸福教育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现实作用:其一,幸福教育有助于人们树立健康的幸福观,比如将幸福与享乐主义、及时行乐区别开来,对君临天下的消费主义与庸俗成功学具有反思的能力。其二,幸福教育有益于人们形成乐观、自制、智慧、宽容、利他、坚毅等良好的幸福品质,懂得为生活赋予意义,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增强心理免疫力,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能在热爱自己、热爱他人、热爱世界的过程当中拥有幸福。其三,幸福教育有助于人们提升改善幸福客观维度的现实生活技能,从而创造出更多有利的外部资源。Seligman的研究发现,幸福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生产力和收入。该研究测量了272名职员的情绪,追踪他们在之后18个月内的工作表现,结果发现上司给有幸福感的人的评价比较高,薪水也比较多[13]47。总之,幸福教育能够同时对幸福感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产生积极作用,尤其对主观维度这一长期被忽略的领域产生显著的正效应。
通常,只有当我们的心理产生重大疾病,感到精神上的损伤与缺陷时,才会重视主观维度对于幸福的意义,从而求助于心理咨询与辅导机构进行医治。而如果我们能够早期对主观维度给予更多的关注,有意识地为心灵补给仁爱、希望、责任、勇气、达观等精神营养,致力于塑造积极完善的人格与优良的心理素质,就能有效预防很多重大心理疾病的发生,并让幸福成为一种习惯,成为自身性格中稳定的一部分;对于社会而言,诸如自杀、毒品依赖、暴力犯罪、性犯罪等社会问题也能因此而大幅减少,而文明、互助、和谐等景象,则会成为最常见的社会表情。幸福教育的意义亦正在于此。幸福教育不仅要帮助那些处于某种逆境条件下的人们,学会如何修复心灵的损伤与缺陷,更要帮助那些处于正常境况下的人们,学会如何通过挖掘自身的潜能与力量,建立起高质量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
幸福教育是对教育终极目标的回归,对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大有助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幸福课”之所以会成为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也正缘于此。由泰勒博士主讲的幸福课,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选修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甚至连学生的家长以及媒体人士,也出现在课堂上。有学生这样评价:“我认识的每个上过这门课的人都说,这是他们在哈佛上过的最好的课。一位和我要好的女生说,它改变了她的一生。”甚至连助教们也这样评价:自打跟泰勒博士教授幸福课以来,心情、饮食、睡眠、人际关系、人生的方向感都得到了改善,“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当学生们离开教室的时候,都迈着春天一样的步子。”[14]
幸福教育已被实践证明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幸福教育还显得非常陌生,她的意义与价值远未被充分揭示,更未进入主流话语的平台得以彰显。她被当今盛行的教育模式挤压到边缘化的位置,成为零星点缀,难敌功利主义与惟智主义的双面夹击。幸福教育作为一个弱小的新生事物,尚处草创阶段,需要政府大力的提倡、培植与推行,在制度上为幸福教育的开展与实施保驾护航。
如何让人们过得更加幸福,这是一个关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构筑幸福之塔,固然需要许许多多不同的基石,但笔者相信,幸福教育一定是其中举足轻重的一块,这块基石的质量,将深远地影响到幸福之塔的高度与稳固。
[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3]李静、郭永玉.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J].心理科学进展,2007,(2):974-980.
[4]姜奇平.互联网导向的价值分析[J].中国计算机用户,2007(32):65-66.
[5]Diener E,Horwitz J,Emmons R A.“Happiness of the very wealthy”[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85,16:263 -274.
[6]Myers D G,“The funds,friends,and faith of happy people”[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1):56 -67.
[7]戴廉.幸福指数量化和谐社会[J].瞭望,2006(11):24-26.
[8]Headey B,“Wearing A.Personality,life events,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Toward 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9,57(4):731-739.
[9]Diener E,“Subjective well- being: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J].American Psychologist,2000,55:34 -43.
[10]Lachman M E,Weaver S L,“The sense of control as a moderator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well- be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74(3):763-773.
[11]Diener E,“Subjective Well- Being”[J].Psychology Bulletin,1984,95(3):34-43.
[12]朱凌云、郭喜青.积极心理学与教育国际研讨会综述[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0(19):40-41.
[13]马丁·塞利格曼.真实的幸福[M].洪兰译,北京:万卷出版公司,2010.
[14]董月玲、张开平.哈佛的幸福课[N].中国青年报,2007-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