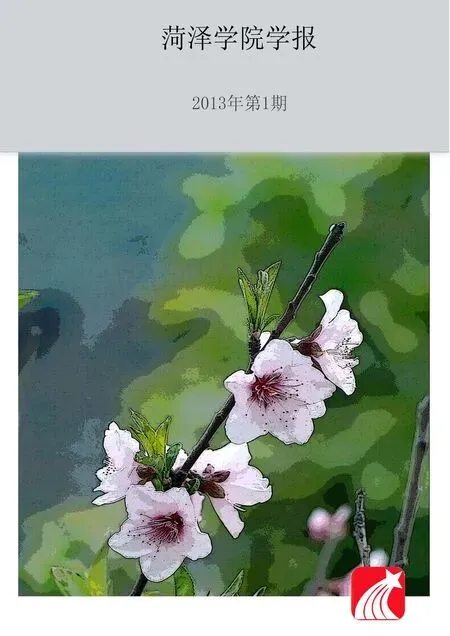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与深化教学改革
——以电影史教学为例*
李玥阳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10)
英国左派特里·伊格尔顿曾经对于现状表示深深的忧虑。在他看来,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曾经令人心动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大师们一一逝去,理论资源正面临枯竭。与此同时,学术界发生了至关重要的转型,消费和快感代替了批判性思考,人们迷醉于身体、性与暴力。学术开始回归日常生活,但在回归的同时产生了巨大的危机,即人们正在丧失批评生活的能力。伊格尔顿认为,此时对于批判理论及其历史进行反思将是十分必要的,虽然文化批判理论作为喷涌而出的理论潮流已经成为过去,但它所留下的丰富遗产仍然可以作为思考的武器。[1]毋宁说,伊格尔顿对于文化批判理论的反思和未来的预见是富于洞察力的,并且给今天的中国主体的借鉴与反思提供了空间。反思的必要不仅在于文化理论所蕴含的批判性思维正是唤醒创造力的方法,更在于中国正面临着与文化理论日益相似的语境。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互为表里,正在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建构资本合法化的种种表述。由此而生的景观与物化正在阻断人们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从中国学术界不断援引的法兰克福学派、“景观社会”、“符号 -物”[2]的批判来看,文化理论在中国不仅尚未过时,甚至愈发适用于中国当下语境。而批判性思维则无疑构成文化理论赖以支撑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将批判性思维贯穿在教学过程中,将是更大限度培养学生对历史现实反思能力,以及建立历史感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在任何文化体中,批判性思维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批判性思维的形成是充分历史化的,也就是说,这一思维必须基于对于自身历史/现实(包括历史/现实中的异质性元素)的整体性把握,并从整体性把握中托生而出。法国激情燃烧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是例证之一。法国知识界正是基于对彼时欧洲现实的整体把握,创造了崭新的横穿近一个世纪的知识王国。但整体性的缺席正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所共同面临的困境。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对于自身历史/现实的失忆与分离是当下尤为突出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青年一代(及青年一代的文化)在文化领域中的登场而更加凸显。青年一代所能触及的历史地平线仅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所能提供的童年、青春甚至中年叙事都与网络及大众文化密切地裹挟在一起。而网络文化自其诞生便携带着去历史化的致命成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异质性历史和隐秘记忆早在青年导演执镜之前便已经被顺利编码在“有中国特色”的日渐强大之中。作为既成的成功者,记忆中繁复的置换和无名丧生的幽灵只需修个坟墓给个名字,或被指认为成功的阵痛就可以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既往历史的“失忆”更像是结构性的事实。在此,不妨以中国正在青年中盛行的恐怖片作为例子。如果说,对于历史/现实的失忆并非只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它事实上构成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的共同焦虑,那么这种“失忆”的焦虑正构成了东南亚恐怖片兴起的内在动力之一。在伴随泰国电影新浪潮而兴起的泰国恐怖片中,一个不断复制的意象便是朱拉隆功大帝的回返。在殖民主义时期,在朱拉隆功大帝的带领下,泰国成为周边唯一一个没有被殖民的国家,成为殖民主义裂隙中的“缓冲国”。这种独立的身份构成泰国人引以为傲的资本。但当殖民主义已然成为过去,当泰国正在发展的理念中前进,人们却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独立”的身份,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了。正如女导演Surapong Pinijkhar在其《暹罗复兴》中描述的景观,女主人公面对祖先(朱拉隆功大帝)诉说:“我们穿得很像西方人。……我们喜爱西方喜爱的任何东西。我们想成为他们,却拒绝接受自己。……我们接受一切,唯独不接受我们自己。”[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泰国恐怖片不断唤回朱拉隆功大帝的幽灵才具有耐人寻味的意义。它至少表明,当后殖民主义已然改变并阻断泰国人的历史记忆,青年导演们正在自觉地回到历史记忆深处,在整体性把握历史的基础上重构自身的身份认同。与泰国恐怖片相比,中国恐怖片显得默默无闻。这种默默无闻并非只是偶然的艺术质量,而是携带着对于“失忆”本身的漠然与无视。或者说,中国的青年导演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历史/现实正在被掏空,而是十分悠然地享受着主体中空化的过程。从近期中小成本恐怖片的盛行来看,这种对于“失忆”的无视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大多数中小成本恐怖片似乎失去了表述中国主体恐怖感的能力。影片中的恐怖感大都是通过过度调度的视听能指来完成的,杀戮者总是穿着《惊声尖叫》的黑袍,防御者时不时拿着高尔夫球棒,女鬼都要坐在镜子前梳头。当青年导演移植这些能指之时,似乎并不介意这些超验原型与中国现实语境之间的距离,或者说,青年导演失去了将恐怖原型语境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丧失正是由于历史/现实的缺席。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泰国与中国共同处在全球化浪潮与危机之中,但泰国青年导演对于历史的钩沉无疑应为中国青年主体学习。毋宁说,泰国恐怖片之兴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自觉的反思,或者说,来源于全球化过程中的批判性思考。这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恰恰是尚未进入中国青年意识层面的。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将是至关重要的。[4]如上所说,这包括恢复被抹杀和遗忘的历史/现实,在恢复记忆的基础上尝试整体性地把握历史,从而建立自我反思的能力。应当说,这种唤回历史的意识应该贯穿于课堂的方方面面。首先,一个老生常谈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事实上,问题意识与批判性思维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者都试图对于一个看似平滑的叙事进行祛魅,发现其中的短缺和断裂点。换言之,二者都试图还原自然化表象之下的陌生化效果。对此,营造一个随时准备接受质询,时刻需要提出问题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学生在必须提出问题的压力之下会不得已提出问题,但由于学生对于学科脉络和历史的不了解,初始阶段的问题可能完全不能进入论题,但尽管如此,必要的提问也对学生树立问题意识有不可否认的益处。其次,在教学中突显“建构”的意义。让学生了解,一切看似自然的东西都可能并非那么自然,历史和现实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叙事性。重要之处并非做对错的价值判断,而是了解这一叙事是谁建构的,叙述者的位置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叙述。例如,第三世界的历史叙述常常是破碎而断裂的,中国电影史的叙述也是如此。在通常的表述中,中国电影史是以1905年的《定军山》作为开端的。但仔细琢磨便会发现,将丰泰照相馆这一带有试验性质的摄制作为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可能携带着诸多偶然性。毕竟早在丰泰照相馆的拍摄之前,外国电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成为影院中的主打。那么,此处的问题便不是中国电影史的开端究竟是哪一年,1905年是不是对的,而是为什么在电影史的叙述中,要将1905年(而不是好莱坞进入的年份)作为中国电影的开端,这样做的内在诉求究竟是什么。当学生进入这种思路之中,也就能够在话语,换言之,在超越本质主义的意义上进入电影研究。
在另一个层面上,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建立学生的整体性视野。这种整体性的重建将与当下日常生活中“景观”对于整体性的拒绝形成对抗。如果说,消费主义和景观社会正在通过提供精选的比现实更逼真的影像序列将人物化,或将人与现实分离,那么在课堂教学中,整体性的回返将是必要的目标。这包括重新以辩证唯物主义建立事物之间的联系。就电影史而言,将电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建构的“纯艺术”中拉回现实,重新恢复电影与政治经济学、资本涌流之间的关联,是亟待完成的任务。诸如,当下电影界的全面亏损绝非中国电影的“纯艺术”范畴所能解释,中国电影在海外电影节获奖也并非“纯艺术”所能囊括,以上种种是由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重关系共同决定的,必须放置在更为广阔的语境中才能进行讨论。只有在培养学生整体性把握,或者对于整体性的意识基础上,批判性思考才是可能的。
[1]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9.
[2]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泰国电影.暹逻复兴[M].Surapong Pinijkhar导演,2004.
[4][美]诺丁斯.批判性课程:学校应该教授哪些知识[M].李树培,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20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