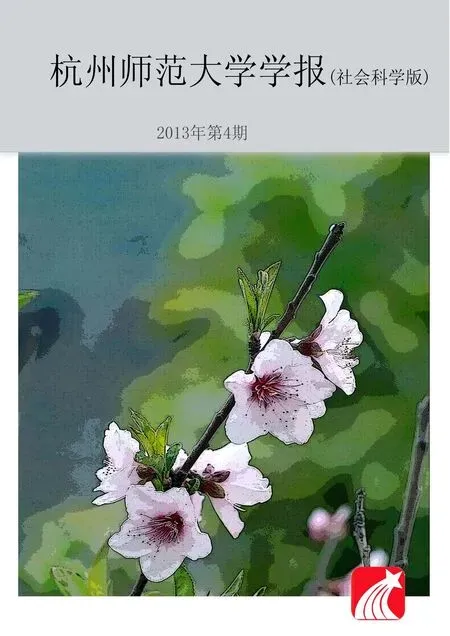“文学者的态度”
——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陕 庆
(清华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84)
文学研究
“文学者的态度”
——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陕 庆
(清华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84)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遭遇创作危机,同时不断重申以胡适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传统,这种文学主张和态度与他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沈从文关于作家主体、创作的重要性、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回乡之行”的写作与五四新文学的理想遥相呼应,从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沈从文;创作危机;五四新文学
一
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针对新文学发表了很多引人注目、确有所指的议论,这让他在40年代回想起来,俨然已是文苑旧战场。本文正是首先通过重返这个旧战场,试图找到一些40年代作家的抽象议论的历史对应物。40年代的沈从文寓居昆明,创作不顺,却极力思考很多或近或远的人事哲理,留下了一些晦涩、抽象的文字,他自己后来将这段时期的创作危机带有几分自嘲地称之为“抽象的抒情”。拙文《从“抒情”到“抽象的抒情”》[1]主要分析了《边城》和《长河》文本内部包含的文学的政治诉求和形式探寻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理解沈从文的创作危机提供了一个角度。实际上沈从文的创作危机联系着整个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逻辑,或者说是这个整体性的文化实践在特定个人身上的反映,正如在新文学的重要作家鲁迅、周作人、茅盾那里的反映。为了论述的方便,姑且用作家在1933年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2]的题目之意来提挈线索。《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本身并不复杂,主要针对游戏态度的文学,但如果对照沈从文这个时期诸多的讨论,这个“文学者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两个层次:一是五四新文学理想和沈从文对五四理解产生的对写作主体的要求和期许;二是由于对文学功能的认识而引发的对于中国现代主体的思考,以及与此相关的启蒙的难题。这两个层次构成本文第二部分的写作,在这一节,我将试图描述作家的基本写作态度。本文第三部分试图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重读《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将1934年沈从文“回乡之行”作为个人生涯中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将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母题充分细读和语境化,进而将之与1937年沈从文抗战爆发后迁徙过程中对现实的思考和创作的雄心相呼应,勾勒出实际上从1934年就已经初现端倪、持续整个40年代令作家十分痛苦的创作危机中所包含的整体性政治、文化困境的维度。
二
1934年,沈从文写完《边城》之后就再也没有自己满意的作品。1936年,他说:
我这枝笔一搁下就是两年。我并不枯窘。泉水潜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我不过不曾继续用它到那个固有工作上罢了。一个人想证明他的存在,有两个方法:其一从事功上由另一人承认而证明;其一从内省上由自己感觉而证明。我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我走了一条近于一般中年人生活内敛以后所走的僻路。寂寞一点,冷落一点,然而同别人一样是“生存”。[3]
这种心境落寞却并不自觉内在枯窘的状态隐约是鲁迅“待死堂”、周作人“知堂”的旧影重现,虽然情调或阴郁、或自负、或无奈,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是对自身内部与外界关系的一种反省和自知,而表现为唯一的也是终极意义上的行动就是写作。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从源头上具有的整体性文化实践的特性。40年代的沈从文多次在五四纪念日发表以“五四”为题的文章:1940年,《五四二十一年》,发表于5月4日香港《大公报·文艺》第830期,同篇文章又以《“五四”二十一年》为题,发表于5月5日昆明《中央日报·五四青年节特刊》,署名沈从文;1947年,《五四》发表于5月4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 》第39期,署名编者;1948年,《纪念五四》发表于5月4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 》第90期,署名沈从文;同年同日又有《五四与五四人》发表于北平《平明日报·五四史料展览特刊》,署名“窄而霉斋主”,这篇文章时隔多年于1989年5月25日重新发表于《民国春秋》第3期,同时发表了当年《五四史料展览特刊》编辑宋伯胤的文章:《为重刊沈从文〈五四和五四人〉说几句话》。
在这些文章、以及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提到“五四”的文章中,沈从文的五四观几乎是当时新文化立场知识分子的共识: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而在描述“文学革命”时,他使用了胡适当年赋予的词:“工具”。此时谈“五四”既是“借古讽今”,也难抑自己创作受阻的失落,他将五四的新文化实践与后来展开的历史之间作了清晰而简略的联系:“把明白易懂的语体文来代替旧有的文体,广泛应用到各方面去,二十年来的发展,不特影响了年青人的生活观念,且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4]并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面上描述这个“工具”产生的成果:“民十六的北伐成功,民二十以后的统一建设,民二十六的对日抗战。”而这些政治上的成果是由于文学这个工具对于这个民族精神上产生的作用:“使这个民族从散漫萎靡情形中,产生自力更生的幻想和信心”,“粘合了这个民族各方面向上的力量,成为一个观念,‘不怕如何牺牲,还是要向建国目标前进!’”,“这种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分析说来,就无不得力于工具的能得其用。”[4]而与此相应,他认为政治的混乱也是由于“工具”的滥用和误用。
在这样的描述中,文学革命与历史不仅是简单直接的联系,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因果联系。而支撑这个因果联系的则是“民族精神”的决定性作用。这里不是为了重新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延伸到鲁迅的“弃医从文”脉络清晰的一条线索;而是由于顺着沈从文对五四的回望,提醒了我们去注意这个回望所包含的内容与其写作的内在逻辑之间有怎样深层的联系。
有必要回顾一下胡适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所强调的一点:“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5]胡适在这篇关于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文章中,从首先强调白话文是一切的基础和首要条件,到最后提出只有先创作出“国语的文学”才会真正创造出“文学的国语”的主张,这看上去是一个互相缠绕,淆乱因果的表述。胡适用学习语言表达的经验来证明他的观点,我们在学习阅读、书写的过程中,一定是先读伟大的作品。似乎这个论述也并没有留下严重的理论漏洞或哲学困境让人质疑、困扰,多数五四作家都从实践的层面上接受了这一表述。因此,写作者这一身份才会变得如此重要,它足以让一个长久消沉的人有足以振奋起来的理由,如鲁迅的“听将令”,也足以让一个颇有成就的人如临崩溃,如沈从文。与此相应,有没有好的作品自然事关整个事业的成败。并且在这个论述中,从好的作品到好的民族精神,从好的民族精神再到好的政治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因果联系。
五四之后的三年,茅盾认为没有出现足以反映这个时代的伟大的作品,这也几乎是当时一些人的共识。30年代沈从文批评“差不多”也是基于对作品的不满意。对沈从文来说,优秀的作品超越于立场、派系之争,“不管那左翼文学或民族主义文学,你得有‘作品’,你的作品至少得比同时别的作品高明些,精美些,深刻些,才有人愿意看”。[6](P.150)这并不奇怪,五四的“新文学”或“新文化”的提法或胡适的“国语的文学”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如何建立新的国家的文学和文化,而对于具体的道路却没有特定的描述,所有的分歧都是在后来实践展开的过程中发生的。虽然,对通往“新”的道路理解不同,萦绕在五四文学家心头的焦虑却都跟这个“新”字相关。他们一方面希望用新的文学塑造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又感叹因为时代没有更新,所以也不会产生真正的新的文学。正如张旭东在《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7]一文中所注意到的,在鲁迅看来,1927年的“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对旧制度挽歌,对新制度讴歌;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正是青黄不接,忙于革命的时候。不过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8]而周作人40年代用“汉文学”这个词来谈中国文学,似乎也表征了20年代他站在新文学立场向旧文学营垒发出凌厉攻势的时期彻底成为过去。
在张旭东的论述中,从1925年开始,鲁迅就告别了用新的文学塑造新的时代的启蒙理想,而是决然地对这个意义上的文学作了一次否定,将自我投身于时代之中,用“执滞于小事情”的方式,产生出与时代融合一体的书写形式——杂文。可见,新文学真正的焦虑是书写与时代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家认为传统的体制内的文学从来就不具有独立于时代,更不必说超越时代的意义。而是不断在书写与时代的互动中探索书写的有效性和可能性。鲁迅这种对书写自身保持警醒的心迹尤其在历史的某些关键时刻表露得显著。“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结尾处的因为极度的痛苦和愤怒而“无话可说”,“哪里还有什么言语”透露出了书写自身的无力。在同一事件中,周作人也遭遇到难以书写但又必须要写的情境,“我是极缺少热狂的人,但同时也颇缺少冷静,这大约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一遇见什么刺激,便心思纷乱,不能思索更不必说要写东西了”。[9](P.340)他力图条分缕析地写出对这件事的感受和看法,结尾却对自己拟挽联悼念的举动表示惭愧:“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9](P.343)而后文将要提到的沈从文在抗战爆发后对于写作本身的期待和焦虑正是这一情境的再现。
怎样才能保证写作的有效性?写作者是关键。对鲁迅来说,是“摇身一变,化为泼皮”;在茅盾看来,新文学家“非研究过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不办”[10]。沈从文则认为写作者必须首先具有严肃的态度,他在批评文章中将矛头直指受人追捧却名不副实的新文学家:新文学是让老古董一见就摇头的文学,直到如今新文学还没有什么让那些老古董点头的了不起的成绩,但是另一面,却诞生了十年中出够风头的新文学家,尤其在青年中具有号召力,间或还起着毒害青年的作用。他将这样的新文学家称为“新文人”。[11]毫无疑问,新文学是对旧式的文人文学的克服,但不想实际上又产生了自身的蜕变形式。所以,这个严肃性和诚挚性是需要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保持的。正如茅盾不赞成青年以成为文艺家为目标,*茅盾在《致文艺青年》(1931)中说:“如果现代大多数青年当真打算做文学家,那就不折不扣是混乱的现中国的严重的病态!如果我们只认为是青年本身之过失,那就和浅薄的小说家一样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罢了。”沈从文则说,经常有青年写信说立志于“文学”,大多数或者还只是有志于作“新文人”。[11]所谓“文人”所指的无非是不关心社会、自娱自乐、自我标榜的一种文化态度。在他看来,鸳鸯蝴蝶派即属于这种——抱着白相态度把文学当作玩具,而不是把文学当作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工具;而对由这些文人组成的所谓“文坛”自然极为鄙视,奉劝那些杂志不要整天刊登文坛消息,而要提供一点真实的生活。[12]
沈从文敏锐地发觉新文学自身在发生蜕变,“新”时刻面临不断退回到“旧”的危机,但就写作自身而言沈从文无论如何是站在外部批评的,不构成自己写作时遭遇的难题。而另一个问题就复杂得多了,那就是一个诚挚、严肃的写作者如何才能有效地写出时代?30年代沈从文对于新文学的一个核心的担忧是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谈论新诗时,他说:
中国诗歌趣味是带着一个类乎宗教的倾心可以用海舶运输而流行的,故十九年时代,中国虽一切还是古旧的中国,中国的新诗,便有了机械动力的声音。这声音,遥遥来自远处,如一袭新衣样子,因其崭新,而装饰于诗人想象中,极其流行,因此唯美的诗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连云高楼,写着进步的都市的赞美诗,普罗诗人,也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到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写着锻铁厂,船坞,以及其他事物倾心的诗。[13](P.37)
这段话形象而刻毒,包含着沈从文对于时代和写作的明确判断——民国十九年的时代,中国还是古旧的中国,而中国的“新诗”之“新”都来自对他者经验的盲目仿效。这里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一如既往地执着于作品,而非政治立场。批评“差不多”,仍是出于对作品的不满,认为造成作品都差不多的原因是大家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一个流俗的、往往是外来的理念、判断。在沈从文看来,不管是整个文学写作脱离实际地接受外来理论,还是写作者个体对现实判断的从众心理,都是一个症状:“对人事拙于体会,对文字缺少理解。”[14]而这个魔障是不容易逃脱的,他说:“作家要救社会还得先设法自救。自救之道第一别学人空口喊叫,作应声虫,第二别把强权当作真理,作磕头虫。”[15](P.150)沈从文将这个原因归于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奴性,换种说法也就是真正的“新文学家”没有诞生。那么作家怎样才能挣脱这重重束缚获得主体性以及写作的有效性?沈从文的回答是:“思索”。
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所谓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
不拘左或右,习惯已使人把“思索”看成 “罪恶”。[15](P.148)
“思索”,这个暂时悬置了宾语的动词,在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中是文学者最终的态度。“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两句《抽象的抒情》一文的题记后来被刻在墓碑上,也确实恰切。“思索”一词不仅是沈从文作为文学者最终的态度,而且是文学者有所作为的关键。在“思索”上获得对文学不断被体制化、商业化的敏感,也获得对意识形态的规避,对理想的追求,并由此获得他所说的自由与独立。其实“思索”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的能动性,归根到底还是来源于其主语——文学者在文化实践中的作用。
由于文化实践的具体性,文学者不仅为作品负责,还须为读者负责。沈从文不仅提出了“思索”来强调文学者的主动性和着力点,而且期待了一种理想的、应然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上文提到,新文学如何在建立之后走向旧文学相同情境的堕落,沈从文认为是由于新文学这个“工具”被滥用。“文学被一些读书人看得俨然异常重大,实有理由可说。”[16](P.63)因为他们两手空空,无力无势,生活窘迫,却富有理想和热情,有严肃的社会责任感。也正因为“近十年来本国人把文学对于社会的用处,以及文学本身的能力,似乎皆看得过于重大了些。在野达士通人,认为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作为治国平天下工具的很多,在朝官吏委员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工具的也很多:因此自然而然发生了如下现象,就是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16](P.62)这种制度对写作者造成挤压,而另一面则造成了一种“因袭的文学观”:
文学与政治不可分,且属于政治的附产品或点缀物。[17](P.167)
从民十五六起始,作家就和这种事实对面,无可逃避。……现代政治的特点是用商业方式花钱,在新闻政策下得到“群”,得到“多数”。这个多数尽管近于抽象,也无妨害。文学也就如此发展下去,重在一时间得到读者的多数,或尊重多数的愿望,因此在朝则利用政治实力,在野则利用社会心理,只要作者在作品外有个政治立场,便特别容易成功。[17](P.168)
这里面的意思发生了好几次转折:一方面官和商都在滥用这个工具,另一方面,正是现代商业的方式决定了现代政治的特点,表现在写作上就是不择手段地获取作为大多数的读者,这无疑是出发点极具合理性的启蒙主义的陷阱。因此,沈从文跳出来说:“一个有艺术良心的作家,对于读者终有个选择,并不一例重看”,[17](PP.169-170)因为:
从作品了解作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一个诚实的作者若需要读者,需要的或许倒是那种少数解味的读者。作者感情观念的永生,便靠的是那在各个时代中少数读者的存在,实证那个永生的可能的梦。[18]
由于对新文化起源的认识,沈从文一直坚持关于“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辩证法。他这样描述五四:当多数人信奉一种旧式的文学观念,“少数人却以为那不成,青年人想自救必先自觉,因此有‘新学’,也就有‘革命’伴着种种改革与一切牺牲,产生了一个民国。”[19]但这个“少数”与“多数”的关系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条件的,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真正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沈从文看似轻描淡写地说到的“少数”自觉的作用在胡适的论述中则扮演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胡适认为新文化必须“为民族造不亡的远因”。因此,文学者的任务就不仅是姑且去尝试写作这么轻松,而必须为大多数人提供理性的指导,对这一宏阔的理想的坚持或许是沈从文至终不放弃少数人与多数人的辩证法的原因。沈从文一方面坚信少数人的先知先觉,另一方面又将先知先觉的可能放到实践中去,来否定表面的文化身份的高下。正如他对作者与读者关系的一种理想化的寻求,他对于写作者的希望也十分理想化:希望经历了生活现实的人写作。这种精神和态度,正如他对五四精神的概括:天真和勇敢。[20]如果单独来看,尤其是在今天的知识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很容易被当作一种人文主义的症状轻易打发掉。其实,回顾沈从文的文学道路,细读他关键时期的重要文本,就会发现这一精神性的词汇,具有怎样的历史对应物。
通观30年代至40年代沈从文对创作实践、理念的言说,从中可见作家在每一时期与新文学的源头所作的呼应,新文学的任务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明晰;另一方面,沈从文也在他所遭遇的具体问题中,不断对新文学理想内部的具体环节进行修正、补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大略了解新文学的逻辑及其展开道路中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包含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逻辑:写作者的主体性是写作者自身无法规避的问题,他必须为作品和读者全权负责;而正是因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开创与文学写作在源头上的共生与紧张关系,使得文学史中写作者对主体性自觉与文学对国家、国民的主体的探寻具有天然的诚挚性和历史感,而另一方面,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文学写作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
由于整体性文化实践的历史决定性,文学者是个举足轻重的主语,“思索”是沈从文作为写作者的实践,虽然宾语没有得到落实,但在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中,文学者和“思索”还是得到了较为具体、清晰的呈现。
1933年沈从文写作《文学者的态度》时已是见解刚健的成熟的写作者,回顾沈从文的文学道路,正如晚年自己坦言,写作首先是为稻粱谋。他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集取名为“习作集”,绝非出于谦虚,他确实像一个学徒,需要经过勤学苦练才能进入一个行业。30年代,沈从文终于获得了一个作为文学生产者的市场,期间,他最为自得的是富有作品,牢骚最多的是被商人盘剥稿费。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不断通过批评文坛现实弊病来实践新文学理想。作为写作的主体,他经历了一个走向自觉的过程。正是这样的渐渐自觉的主体,在抗战爆发之后,对历史产生了崇高的体验,以及强烈的写作的责任感。
1938年,在给滞留在北平的妻子的信中,他描绘了在一个雷雨之夜坐在灯下书写的情景。他感到“历史在重造”:
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21]
这番书写极具现场感,作为人类社会总体的历史的重造过程如自然界的电闪雷鸣让人心生惊惧,但“我”不仅能体验到个人的感受,而且能体会人类经历这个历史过程所产生的情绪。因此,“我”的内心是充盈的,在不沉静中保持沉静,在沉静中体会不沉静。这一切都因为“我”拥有与历史相关联的行动:写作。在重大的历史变迁之前,“我”是一个写作者。也正因此,他赋予了正在写作的《长河》以重要的意义。
他说《长河》是继续《边城》的思路,最后要写翠翠离开了家,到未知的异地去。关于《边城》与《长河》之间的内在联系,拙文《从“抒情”到“抽象的抒情”》[1]认为作者借《长河》这部小说来探寻翠翠(在《长河》中对应的主人公是夭夭)这样的自在的生命形式在面临外来危机时怎样才能找到出路,由于作者不忍心看到淳朴的人性受到玷污和损害,所以无法真正与恶势力展开斗争,最终表现为无力挽歌。而小说中所描写的乡村世界面对外来侵袭的情形与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化之初的情形极为相似,因此在历史的流程中反而显出小说的“滞后性”,这与作者试图通过小说探寻乡村社会未来的初衷不甚相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来自作家理解社会斗争时对政治经济学视野的不满和拒绝,《长河》中对受无妄之灾的地主王四癞子的同情和对夭夭一家勤劳致富的描写,表明作家心目中的美好人性,也就是《边城》中的那个“人性的小庙”,有了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由勤劳带来的财富积累,并进而以此来否定左翼的阶级论,批判右翼统治对乡村社会的破坏。然而,沈从文怎样在这两重的不满中“思索”出自己的道路?回溯到1934年初,此时《边城》处于创作的中途,沈从文因母病独自从北京回湘西。这一次返乡,他目睹了当时中国农村经历的经济萧条,期间留下了两个心迹历历的文本,一个是回城之后发表的《湘行散记》,另一个是80年代才公开发表的《湘行书简》。今天读来,《湘行书简》中的一些内容是《湘行散记》一些篇章的原始文本,由于是实时、私人的写作,作家的心理历程也更为真实、清晰。这两个文本各有侧重地呈现了沈从文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的反应,以及作为写作主体的自觉过程和对中国现代主体的思考。
如同他写作之初的不自觉,他对这次行程的最初打算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其时作家正和新婚的妻子离别,一路上写信作画,表达浓情蜜意。
信从桃源开始写起,已经到了湘西地界,风景也优美起来。他有意要描摹好的风景,向新婚的妻子表达爱意,也向一个没有来过此地的城里人传达审美的感受。阔别了多年,故乡的风景照样会引起惊喜。刚开始他的笔下充满诗意,感官贪婪地摄入一切可爱的事物:桃源的吊脚楼,摇橹,唱歌声……他感到“这些人都可爱得很”,[22]“在这条河上最多的是歌声,麻阳人好像完全是吃歌声长大的。”[23]但随着船渐渐上行,随着我对这些水上人的现实生活的贴近认识,感受到他们经济上的贫困,看见他们行船过程中会有生命危险,原先的诗意顿时打消不少,笔端渐渐沉重起来。
经济很萧条,船多货少,那些划船的麻阳人的生意随时都可能赔本,近来连做鸦片烟生意的也无利可图,因此多数水上人的生活都很悲惨。这河里的情形已经不如十年前热闹了,如果照这样下去,这些人的生活还将更悲惨。[24]他又暗地估算了一下为自己撑船的水手的收入:“掌舵的八分钱一天,拦头的一角三分一天,小伙计一分二厘一天。”然而就这个收入,不管天气怎样,他们都要从早到晚地操劳。该下水时下水,应当到滩上爬行时爬行,毫不吝惜自己的力气。最后,“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了,一生也就算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想起了这件事情,我轻轻的吁了一口气。” [25]
但沈从文仍然没有顺着这个思路去在社会经济上追究原因,“想起这些人的哀乐,我有点忧郁”[26],“这分生活真使我感动得很。听到他们的说话,我便觉得我已经写出的太简单了。”[27]如果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思考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他的文学写作将是另一番景象,而他首先反思的是自己以前的写作是不足的:“写得太简单。”然而,怎样才算写得不简单、深刻有效呢?他想到的是生存的意义,而要考虑这个问题,又必须首先考虑“少数人”、“多数人”的区别和关系。这种多数人的生存是为了什么?他们有没有想过?是为了生而生吗?
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放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放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得把自己凝聚起来![28]
因此,此刻作为少数人的“我”重新置身于原先出于想象、回忆之中的现实,不免反躬自省,产生愧疚之情。
因为这个愧疚之情让一路上“我”的所见所闻,很难印证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所说的“风景”的发现。柄谷在书中举国木田独步《武藏野》中的人物大津讲述的“难忘的人们”的例子,大津说到自己从大阪坐小火轮渡过濑户内海时看到岛屿,岛屿上田地里劳作的人,岸边捕鱼的人。这在旅途中擦肩而过的情景,却是“那以后至今的十年间,我多次回忆起岛上那不曾相识的人。这就是我‘难忘的人们’中的一位。”柄谷说:“作品中的人物大津所看到的,那岛上的男人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一个‘风景’。”[29]国木田独步笔下的大津是一个孤独的现代人的形象。在一个分裂的现代主体面前,“风景”被发现了。在柄谷行人的这本书中,风景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等一起被视为日本文学现代性的标志。这本广为阅读的书也成了我们理解何谓现代性的一个窗口,然而,这种对于日本文学现代性的描述是否适用于中国呢?这里无法做一种概括式的判断,仅从沈从文而言,这个问题有其特定的语境。沈从文的现代主体正是对这种分裂的反思、警惕甚至愧疚之中生成的。正是最容易被风景化的回乡途中的见闻克服了风景化,形势没有向着柄谷行人所分析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风景的发现”方向发展,相反“风景”这一现代装置在经验呈现和主体回忆的裂隙中发生了摇晃,并迅速发生了清晰可辨的逆转。因此,与其说是“风景的发现”,不如说是“我”的重新发现,“我”的自觉。
刚开始“我”被所见所闻打动,“我”的身份是不自知的。渐渐地,“我”在这些人的眼中看见了今天的自己。水手们称呼“我”为“先生”;“我”的“一张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脸,同一件称身软料细毛衣服,在一个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是一种如何幻想……”[30]因此,“我有点担心,地方一切虽没有什么变动,我或者变得太多了一点。”[31](P.253)在《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中,“我”是在多面镜子中照见自己的。除了当地的水手,还有一个是“三三”*《湘行书简》中对收信人妻子的称呼。,或者说是读者,在他们看来,“我”既是旅行者也是回归者,与当地既是一体,又有疏隔。另外还有一个,是过去的自己。“把鞋脱了还不即睡,便镶到水手身旁去看牌,一直到半夜,——十五年前自己的事,在这样地方温习起来,使人对于命运感到十分惊异。”[32]破折号之前的生动细节在瞬间失去了时间性,无意间重复的动作和情景,使得过去的经验忽然绽现,像“玛德莱娜”小甜饼那样带来神奇的体验*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情节。;不仅如此,过去与现在豁然畅通,记忆从凝固中融化开来,帮助“此刻”克服了干巴巴的主观立场。因为“我”曾经是那些水手、士兵,现在是离开之后又回来的“二佬”*《边城》中的主人公。。“我”显然已经从他们当中分离出去,可是“我”怎么与他们建立一种新的联系呢?“我”又看见了翠翠、夭夭、柏子和虎雏,*《边城》中的主人公翠翠,《柏子》中的主人公柏子,《虎雏》中的主人公虎雏。而这些人只是引起“我”的忧虑和感伤,“我”无法拯救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就像“我”不能爱夭夭,*《湘行散记·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的主人公。也正像我靠现代教育对虎雏的改造也归于失败。但“我”应该为他们整体找一个出路,现有的启蒙话语所预设的理想是否适合他们,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明确“我”对自身的理解以及对他们的理解。
在《湘行散记》中,过去与当前的经验以及小说文本(《从文自传》《边城》《柏子》等等)交融在一起,虚实难辨。下午四点钟的阳光下,沈从文坐在舱口,汤汤流水引发他彻悟人生。过去俨然迎面向他走来,那充满了牛粪桐油气味的小小河街,还是原来的模样,好像看到过去的自己,那些记忆中的,写到作品中的人事,他们重又从文字中解放出来,兀自按照自己的时间序列生活到此刻。也许出于作家预料的是,有意的类型化写作留下了这样自我反省的空间;而对沈从文来说,故地重游,此刻仿佛就是过去,而过去仿佛换了一个模样,过去写下的文字仿佛换了一个版本。
沈从文到了湘西才发现自己变得太多,发现了湘西的没有变,这一组“常”与“变”的对立与其说是哲学的辩证,不如说是对应为都市与乡村、知识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断裂,而作为一个写作者,最触动他的仍然是写作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具体而言是文字所书写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断裂: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鹭鸶,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31](P.253)
这时候,历史已经从现代延伸出来,也包括时下的书写,因为今天的书写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在对“相争相斫”的历史书写拒绝之后,沈从文试图展现恒常不变的现实:“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鹭鸶,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是一种努力让事物自身说话的描写,呈现的是事物自身的颜色、形状、方位、速度。这种情境,以及人的情感,对待生存的态度,表面上是去历史化的,实际上是对既定历史的反抗,并试图重新历史化。这段文字的雏形出现在《湘行书简》中篇名叫做《历史是一条河》,而在整理发表后的《湘行散记》中则题为《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篇名的变化,也许可以印证作家从将历史还原为恒常状态,到勇敢地接受线性历史的前提下重新让这种无名的恒常状态获得历史意义的反思和努力。
而这个历史化的根据和基础就是生存的庄严。何谓“生存的庄严”?或许可以分析为两层含义:一是生存(命运)自身的严肃性,甚至严酷性;二是人对这种命运勇于承担的诚挚性。这是暂且将社会历史抽离之后的“天生烝民”的原初意义上的庄严性,也正是首先回到这个意义上,写作才得以将人与人、文明与文明恢复到不容玷污的平等和尊严上来。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也为由于政治经济的弱势和挫败造成的奴役状态开辟了重新发掘主体性的空间。由于无法想象现代世界必须在斗争中获取正义,对主体投入社会斗争心存疑虑和恐惧,沈从文“建造人性的小庙”,在头脑中构筑的意义世界,仍然是天—地—人结构而成的古典境域。回顾以平等、尊严为新的着力点的现代主体的建构,不管是五四时期平民文学主张还是30年代大众语的讨论,抑或沈从文曾经想象过的诚挚、火热的被战火阻隔的另一世界延安正在进行的文艺实践,这一以退为进的意义重建未尝不为这一整体性文化实践在诸多面向的努力提供了一种对原初意义诉求的表达。
然而,就作家个人而言,他的实践是失败的。昆明八年,《长河》的写作是一次明知逾矩的情况下失败的突围。此后的写作大致有两个类型,一是抽象的内心絮语,二是努力为抗战写下的“有用”的文字。“思索”确实是落空了,它没有走上茅盾式的主观可以不断认识客观的有迹可循的道路。他写的抗战文字中的人物无论是仆人王嫂,还是前线下来的年轻人,都是出于写出人物美好的品性,是为了给读者以信心。他自己并没有成为那个在现实中战斗的写作者,却每天过着跑警报、看死人尸首的日子,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历史的崇高性面前,那种曾被王德威拿来与鲁迅作比较的对待砍头的态度已经全然失效。遍读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字,无不充满焦灼,那是一种对思绪混乱、写作破碎的焦灼,但有一段文字却极为清晰、流畅地表达了他的这种焦灼。这段话描述的是自己有一天到郊外散步沉思,眼前满目是春城葱茏的绿野,而心中想到的却是世事的纷扰和杂乱,自然与人世的两相对照尤其令他感到人性、民族的堕落。他思索如何改变这一切,却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悲观,陷入到一个想象当中:他发现自己好像沉陷在无边无际的海洋里,迷失了方向,这艘几千年来装载着理想的大船已经被一种卑鄙自私的力量摧毁,船上的人想要抓住一些碎片,却发现已经完全朽烂,但竟然还有人收拾着这些碎片,扎成一个简陋的筏子。他在无助之中抬头看到天空的星光,他想,那些星光代表着人类永恒的、崇高的价值,但它毕竟离现实太远。正当他陷入绝境之时,又被眼前的景象唤回到现实之中:
微风掠过面前的绿原,似乎有一阵新的波浪从我身边推过。我攀住了一样东西,于是浮起来了。我攀住的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一切活人素朴的心;年青男女入社会以前对于人生的坦白与热诚,未恋爱以前对于爱情的腼腆与纯粹,还有那个在城市,在乡村,在一切边陬僻壤,埋没无闻卑贱简单工作中,低下头来的正直公民,小学教师或农民,从习惯中受侮辱,受挫折,受牺牲的广泛沉默。沉默中所保有的民族善良品性,如何适宜培养爱和恨的种子!
强烈照眼阳光下,蚕豆小麦作成的新绿,已掩盖远近赭色田亩。面对这个广大的绿原,一端衔接于泛银光的滇池,一端却逐渐消失于蓝与灰融合而成的珠色天际,我仿佛看到一些种子,从我手中撒去,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时同样一片蓝天下形成的繁荣。[33]
这是一段流畅抒情的文字,包含着绝处逢生的百感交集,而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仍是思索的结果,在思索中现实向他敞开了另一个视野,他看到了别人忽视的东西。此时,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他意识到真正未来生长的土壤是什么,而对于“种子”,也可以呼应那个五四的“为民族不亡造远因”的符咒一样深植在新文学之中的理想,在想象之中仍然是从自己的手中撒出去的,但它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另外一时同样一片蓝天下形成的繁荣”。但是,“我” 不管是困惑还是顿悟都是孤独的个体,“思索”的宾语呼之欲出,但仍是一种想象性的存在,与“我”之间是一种想象性的关系。在历史的变迁面前,写作者个人的伦理选择成为古典的“有所待”:一方面,个人的写作已经从时代中退场,另一方面也预示了这个新文学的理想仍然会对未来起作用。
历史永远大于个人,永远会对书写提出要求,文学者面临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在或崇高、或悠久、或未知的历史面前因为有所寄托而心情回复平静。整个40年代,沈从文极为寂寞、辛苦,但从未真正绝望。汪曾祺曾说:“多数现代作家对这个问题是绝望的。他们的调子是低沉的,哀悼的,尖刻的,愤世嫉俗的,冷嘲的,沈从文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沈从文的小说的调子自然不是昂扬的,但是是明朗的,引人向上的。”[34]50年代,他给年轻作者的信中,一再表示,自己已经过时了,现实和未来应该是这些年轻人来写。正是因为这个新文学理想,文学者可以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共同体,让文学书写有可能与历史相抗、相配。
(编者按:本文所引沈从文原文,皆据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的《沈从文全集》,引文皆经核对无误,一些表述及用语与现在的用法略有不同,为保存原文风貌,一律不作修改,特此说明。)
[1]陕庆.从“抒情”到“抽象的抒情”——对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的再研究[J].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1).
[2]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M]//沈从文全集:1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46-53.
[3]沈从文.沉默[M]//沈从文全集:1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04.
[4]沈从文.五四二十一年[M]//沈从文全集:1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33.
[5]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M]//胡适全集: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56.
[6]沈从文.再谈差不多[M]//沈从文全集:1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张旭东.杂文的“自觉”——鲁迅“过渡期”写作的现代性与语言政治[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1-2).
[8]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M]//鲁迅全集: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0.
[9]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M]//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钟叔河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0]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M]//茅盾全集:1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9.
[11]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M]//沈从文全集:1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83.
[12]沈从文.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M]//沈从文全集:1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
[13]沈从文.窄而霉斋闲话[M]//沈从文全集:1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7.
[14]沈从文.作家间需要一种新的运动[M]//沈从文全集:1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03.
[15]沈从文.再谈差不多[M]//沈从文全集:1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6]沈从文.禁书问题[M]//沈从文全集:1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7]沈从文.一种新的文学观[M]//沈从文全集:17.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8]沈从文.小说作者与读者[M]//沈从文全集: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73.
[19]沈从文.青年运动[M]//沈从文全集:1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03.
[20]沈从文.纪念五四[M]//沈从文全集:14.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98.
[21]沈从文.致张兆和——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M]//沈从文全集:18.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16.
[22]沈从文.水手们[M]//沈从文全集: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9.
[23]沈从文.河街想象[M]//沈从文全集: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33.
[24]沈从文.过哨子铺长潭[M]//沈从文全集: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50.
[25]沈从文.辰河小船上的水手[M]//沈从文全集: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71-272.
[26]沈从文.夜泊鸭窠围[M]//沈从文全集: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53.
[27]沈从文.鸭窠围清晨[M]//沈从文全集: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61.
[28]沈从文.横石和九溪[M]//沈从文全集: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84-185.
[29]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M].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4.
[30]沈从文.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M]//沈从文全集: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65.
[31]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M]//沈从文全集: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2]沈从文.鸭窠围的夜[M]//沈从文全集:11.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47.
[33]沈从文.黑魇[M]//沈从文全集:12.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73.
[34]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67.
“TheLitterateur’sAttitude”:ShenCongwen’sWritingCrisisandtheIdealofChineseModernLiterature
SHAN 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In the 1940s, when Shen Congwen was experiencing writing crisis, he reiterated the ideal and tradition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led by Hu Shi), and his opinion and attitude about literature at that time ca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from the 1930s, when he made some assertions about “Chabuduo” (many literary works are similar) . His statements on the writer’s subjectivity, fundamentality of literary work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together with his own writing practice during his back home journey in 1934, corresponded to the ideal of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from which the specificity and complexit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s modernity can be interpreted.
Shen Congwen; writing crisis;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2011-11-16
陕庆(1980-),女,安徽南陵人,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近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
I207.4
A
1674-2338(2013)04-0063-10
(责任编辑吴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