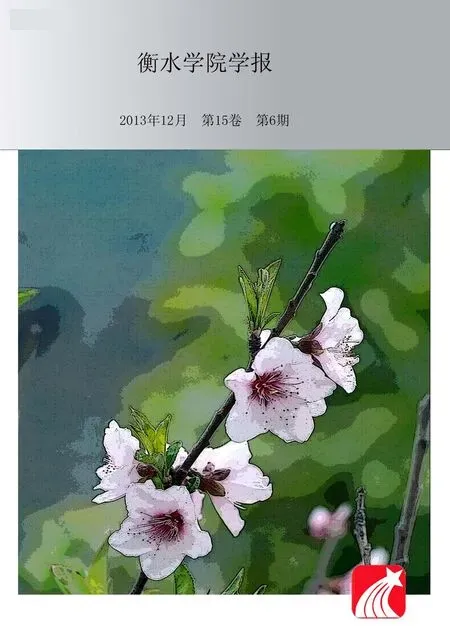董仲舒神学化自然观的逻辑进程
路高学
董仲舒神学化自然观的逻辑进程
路高学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儒学到了西汉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其显著的标志就是董仲舒把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自然主义”思想与儒家“人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化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性,也有某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它根源于人们对自然界“同类相动”的普遍认识,经董仲舒“天人同类”的证明,必然形成“天人感应”的认识。
董仲舒;自然观;同类相动;天人同类;天人感应
自然观是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看法,是人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诸子百家不同,先秦儒家重人伦而轻自然,阴阳五行之说并不是儒家的理论。但是到了汉代,阴阳五行与灾异图谶之说在社会上已广为流行,成为各家学说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汉儒思想受阴阳五行支配,实为一普遍趋势”。“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受时代的影响,董仲舒把阴阳四时五行等关于自然界认识的学说纳入到他的理论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构成了汉代思想的主要特征。其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说就是“天人感应”论。这种关于人与自然的认识“不是董仲舒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是董仲舒通过详尽的论证,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后重新提出来的。
一、同类相动
“同类相动”源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对自然界的观察。在古代社会的文献资料中,有大量关于“同类相动”的自然知识记载。最早的农书《夏小正》记载:
正月:启蛰。言始发蛰也。雁北乡……雉震呴。震也者,鸣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呴,相识以雷。鱼陟负冰……冻涂也者,冻下而泽上多也。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记时也。农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农夫急除田也。
这是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发展来的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代,“同类相动”思想发展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很多方面。《易传》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周易·乾》)这是有关圣人和万物“同类相动”的记录。各事各物都能“从其类”而动,而“本乎于天者”的圣人降生,万物都能感觉得到。根据物物“同类相动”,人们由此而逐渐地认识到天与人、人与人之间也能相应相动。荀子曰:“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湿。夫类之相从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观人,焉所疑?”(《荀子·大略》)
战国末期,为了适应国家统一的需要,吕不韦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把古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与当时已经取得的自然知识结合起来,把“神人交通说成是某种必然联系,并建立了固定的周而复始程式”。《吕氏春秋·十二纪》是专门为君王进行政治活动所安排的月程表,它把实际观察到的自然知识和某些神秘观念附会起来,提出“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吕氏春秋·序意》),以实现“法天”之治。如:“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吕氏春秋·孟夏纪》)。这种天神崇拜可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天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但是还没有涉及到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
汉朝初年,陆贾提出“事以类相从,声以音相应”(《新语·术事》),“治道失于下,则天示变于上”(《新语·明诫》)。后来的贾谊更进一步,他认为“天之处高,其听卑,其牧芒,其视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谨慎也”(《新书·耳痹》)。这说明两人的思想中已经有了某种天神的观念,物物“同类相动”的观念已经发展到“天人同类相应”的认识。后来的淮南王刘安编写的《淮南子》收集了大量关于同类相应的材料,如:“鹊巢知风之起,獭穴知水之高下,晖目知晏,阴谐知雨”“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蜺见,万物有以相连,精禄有以相荡也”,得出“天之与人,有以相通”的结论。
然而,以上这些关于“同类相动”的观念仍然“只是由感情、传统而来的‘虚说’,点到为止,没有人在这种地方认真地求验证”,还没把这个原则普遍化,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完成这个工作的是董仲舒。因为从他开始才“在天的地方,追求实证的意义”。董仲舒充分发挥“同类相动”的思想,他在阐释的过程中,自觉地反对各种神异化的学说,认为“同类相动”根源于“类”的相同。也就是说,由于事物在“数”上是“相副”的,从而导致了它们在结构上是相似的,因而在功能上是相通的。
董仲舒以“气”为“同类相动”的“类”,同时他也认为气有阴阳,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万事万物皆有阴阳。因此,阴阳二气是“同类相动”的真正根源。董仲舒曰:
金木水火土,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这说明董仲舒十分突出阴阳的作用,《史记·儒林列传》谓董仲舒“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
董仲舒找到“同类相动”的根源,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此。而是用“同类相动”的推论方法,“以类相推”“由人而推之于天,认为人是如此,天也是如此”。
二、天人同类
“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一切是非的最高裁决者。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不天生。”(《春秋繁露·顺命》)也就是说,“天”是世间万物的根源,万物都由“天”而生,“人”亦由天而生。然而,由“天”而生的“人”,如何与“天”“同类”呢?董仲舒是如何由“人”而推及“天”呢?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之前,先来讨论董仲舒的“天”。
1. “天”的结构
董仲舒认为:“天有十端”(《春秋繁露·官制天象》),即天、地、阴、阳、火、金、木、水、土、人;“天有五行”(《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即木、火、土、金、水。它们都因“气”而“同类相动”。“气”是物物“同类相动”的中介和构成万物的质料,也是“天的构造的基本因素”——“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由此可知,“一”即“气”也。而根据“一元者,大始也”(《春秋繁露·玉英》)和“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可知,“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即“元气”。“元气”分而有“阴阳”,“阴阳”分而有“四时”“五行”。
2. “天”的属性
董仲舒的“天”有多重属性:
第一,自然属性。董仲舒把天看成是“万物之祖,万物非不天生”。“天”创造万物不是有意而为的,而是通过物质性的“元气”分为“阴阳”“四时”“五行”而产生万物的一种自然而然、不待作为的过程。如:
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此种意义的“天”,相近于老子的“道”。
第二,神性。儒家本不讲鬼神观念,《春秋》一书中虽然记载了大量的自然灾异,但是却“纪异而说不书”(《史记·天官书》)。董仲舒受“墨家‘天志’、鬼神之说和阴阳家迷信说法的影响”,认为“天”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是最高的神。他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不天备,虽百神犹无益也。”(《春秋繁露·郊语》)而这样的“天”能“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是“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汉书·董仲传》)。自然界万事万物及其变化,都是这个“天”的意志的体现。
董仲舒不但把“天”当成是最高的神,而且大谈灾异迷信,把自然灾异说成是“天”对人间社会的谴责和警告。他认为: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春秋繁露·阴阳义》)
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这说明,董仲舒的“天”实际上是一种有意志、有目的的神秘力量。
第三,道德属性。董仲舒把“天”当成是一有意志、有目的的神秘力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突出“天”的道德属性。他说:
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亦权之类也。虽曰权,皆在权成。是故阳行于顺,阴行于逆;逆行而顺,顺行而逆者,阴也。是故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阳出而南,阴出而北。经用于盛,权用于末。以此见天之显经隐权,前德而后刑也……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经而后权,贵阳而贱阴也……是故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董仲舒赋予“阴阳”“德”“刑”的性格,恶“阴”而好“阳”,贬“刑”而尚“德”。这实际上是基于其政治上“尚德”而不“尚刑”的主张,“想为此要求在天道上得一根据”,才如此划分,表现“天”重“德”而不重“刑”的道德属性。但是,“德”“刑”兼备的“天”为什么会重“德”而不重“刑”呢?董仲舒认为“天”有仁德之心,他说:“仁,天心,故次以天心。”(《春秋繁露·俞序》)“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而有“仁心”的“天”以“阴阳”“刑德”创造万物、管理万物时,当然会“以阴为权,以阳为经”,表现出重“德”而不重“刑”的道德属性。
从以上“天”的3种属性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董仲舒的“天”具有“自然之天”“神灵之天”“道德之天”3种意义。“天”的自然属性是宇宙万物产生和存在的基础;“天”的神性表现了它对宇宙万物的主宰性;“天”的道德性是其神性的表达方式。董仲舒的“天”不仅有“仁心”,而且还有人才有的“喜怒之气,哀乐之心”,这实际上是一种“天”性的人格化。然而,董仲舒为什么要这样理解“天”呢?对于这个问题,董仲舒是这样理解的,即:人如何有了“天”的属性?
3. 人副天数
人如何有了“天”的属性?董仲舒认为这是由于“为生者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由此才“上类天”(《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从根本上讲,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乃是模仿于“天”的,即“人副天数”。对于“数”是指数字、数量,“副”是相符合的意思。“人副天数”就是说在人和“天”之间存在着相互一致的数量关系。对此,董仲舒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第一,在形体结构方面,董仲舒认为人身体的各个部分的数字和“天”的各个部分的数字相符的,也就是说人是“天”的副本。董仲舒在这一方面论证比较详尽。他说:
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求天数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数终矣……以此见天之数,人之形,官之制,相参相得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
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第二,在来源方面,董仲舒认为人“生”也合于“天数”。董仲舒曰:
天之大数,毕于十旬。旬天地之间,十而毕举;旬生长之功,十而毕成。十者,天数之所止也……是故阳气以正月始出地,生育长养于上,至其功必成也,而积十月。人亦十月而生,合于天数也。是故天道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合于天道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第三,在情感意志方面,董仲舒也认为“天”“与人相副”。董仲舒曰:
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
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这表明,不仅人的一般道德情感怒哀乐与“天”“相副”,而且儒家最高的道德“仁”也是来源于“天”,与“天”“相副”的。
从以上董仲舒关于“人副天数”的论证中,可以明白他为什么讲“为人者,天也”,也就明白了人如何有了“天”的“属性”,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讲“天……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董仲舒讲“人副天数”是为了说明“天人同类”“天人一也”,而其最终目的在于证明“天人”同类“相感”。
三、天人感应
秦汉之际“天人感应”是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观念,董仲舒通过“人副天数”证明了人不仅“生”合于“天数”,而且外在的形体结体和内在的道德情感都是模仿于“天数”的。因此,人是“天”的副本,“天人同类”,而根据“同类相动”的道理,必然得出“天人感应”的神学自然观。
1. “天”人如何“同类相动”
董仲舒认为天地之间充满着阴阳之气,常常影响到人类,就像水对鱼的影响一样。董仲舒曰:
然则人之居天地之间,其犹鱼之离水,一也。其无间若气而淖于水。水之比于气也,若泥之比于水也。是天地之间,若虚而实,人常渐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乱之气,与之流通相殽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这说明“天”和人是通过气来进行感应的。就个体的人来讲,由于“天”和人都有“阴阳”“五行”,那么如果在“天”的阴气占上风的时候,人体内的阴气因与“天”的阴气同类,就会出现相互感应的现象。例如,董仲舒认为人体的腰部和膝部阴气比较集中,所以一遇到阴雨天气阴气流行的时候,这些部位就会出现相应的感应现象,表现出腰酸腿痛的现象。而就人类社会来讲,董仲舒认为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状况都会通过气来影响到“天道”的运行,而反过来,“天”也会通过气表达它对人类社会状况的意见。他讲:“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说,社会如果治理得不好产生混乱就会产生邪气,邪气会通过阴阳二气传感于“天”,“天”就会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产生出灾异。同样,如果人间社会治理得非常好,福瑞之气就会产生,“天”就会降下祥瑞之兆。这正如董仲舒所讲的“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2. “天人感应”的主要内容
通过气来实现的“天人感应”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灾异谴告。董仲舒认为天命灾异和政治人事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必须加以重视。其言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书·董仲舒传》)这种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他的“谴告”说中。董仲舒认为自然现象中除了正常的现象外,还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他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一般情况下,在发生大的灾异之前会出现一些小的灾异对人间社会进行“谴告”,如虫灾、水灾和旱灾等;如果统治者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应对这种现象,“天”就会降下更大的灾异来“惊骇之”;如果统治者仍然没有认识到此种现象的严重性就会重新更改“天命”,受于有德之人。
第二,符瑞吉兆。董仲舒认为,“天”不仅会降下灾异来“谴告”统治者的过失,而且还会降下符瑞来表达对人间德政的赞誉。他说:
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风凰麒麟游于郊。(《春秋繁露·王道》)
君王是国家之首,王者正,行德政,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麒麟出现等美好的现象和事物就会纷至沓来。这表明,祥瑞也是“天人感应”的表现,它也是基于人的行为。
第三,受命之符。受命之符,即符应,是指有德之人承受“天命”的征兆。“天”降下灾异警示失德之君,如果君王不及时采取措施以修正自己的不正之处,“天”将拿走赋于他的“命”,通过符应给予有德之人。董仲舒曰:“周将兴之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者……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见此以劝之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这表示如果帝王将兴,“天”会降下相应的符应,而得符应之人将会受“天命”而为王。“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就是暗示周将受符应而得天下。
3. “天人感应”的影响及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天人感应”论不仅只是一个“天”作用于人的理论系统,而且是一个人也可以作用于“天”的循环系统。这种“天人感应”的神学认识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把这个循环系统全面地贯彻到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里,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理论。董仲舒学说中的核心命题,如“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亲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都深受其“天人感应”观念的深刻影响。如:“《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天人三策》)即是董仲舒认为天下大一统是天地间最长久的普遍原则,是“天”意的体现,任何人都不能违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董仲舒之所以言“天人感应”实际上是为其政治主张提供一个合理性的根据,为大一统的社会提供一个合法性的证明。同时,他把这种合理性的根据和合法性的证明看成是非人力所能及的,而是“天命”所为。董仲舒曰:“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春秋繁露·符瑞》)这实际上说明了“天”通过一定的现象来表示它的目的,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干预,展示了“天”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董仲舒认为,一个新王朝之所以能建立,根本原因在于统治者上承“天命”,为“天子”,而新受命的“天子”就应该通过改制而上应“天命”。由此,也就有了“张三世,通三统,亲周、故宋、以《春秋》作新王”。董仲舒曰:“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春秋繁露·符瑞》)这是董仲舒想通过说明孔子因在狩猎中得到麟的符应,承受了“天命”而为“素王”,借以给孔子的理论主张提供合法性证明而为自己的改制思想寻找合法性根源。董仲舒曰:“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春秋繁露·楚庄王》)此表示董仲舒认为新王应该通过改制表明其政权的合法性是上承于“天”的。
综上所述,“天人感应”是董仲舒在总结前人关于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神学化自然观。他把人和“天”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念。此种观念与孔孟开创和发展的儒学旨意已大有转变,“其申天之人格性,如言天为百神之大君,人之曾祖父,亦实近墨者;而与孔孟之重天道,而不重天之人格性者不同”。但是通过对“天人感应”这种神学化自然观的逻辑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必然性。孔子讲“仁”;孟子讲“仁政”,并把人“仁”归于人心;而董仲舒也主张实行“王道”“仁政”,但他把“仁”的根源归于“天”,认为“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他们各自都从自己的时代情况出发来思考问题,不可能超越于时代之上。董仲舒正是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为实现一个儒士的人生理想,以当时普遍存在的自然知识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人感应”的自然观。
[1]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2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5.
[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
[4] 周桂钿.董学探微[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2.
[5]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91.
[6]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 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8]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54.
(责任编校:卫立冬 英文校对:吴秀兰)
Logical Process of Dong Zhongshu’s Theological Views of Nature
LU Gao-xue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Confucianism had its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obvious sign is that Dong Zhongshu combined the socially prevalent "naturalism" with the Confucian "humanism" and formed the unique theological views of nature, namely “unity of heaven and man” and “heaven-man telepathy”. The formation of the views of nature not only has its profound feature of times, but also has some kind of logical inevitability. It was rooted in the general knowledge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ame kind” in nature and the views of “heaven-man telepathy” was inevitably formed with the proof of Dong Zhongshu’s “man and heaven being the same kind”.
Dong Zhongshu; views of nature; interaction of the same kind; man and heaven being the same kind; heaven-man telepathy
10.3969/j.issn.1673-2065.2013.06.005
B234.5
A
1673-2065(2013)06-0020-05
2013-05-29
路高学(1986-),男,河南新郑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