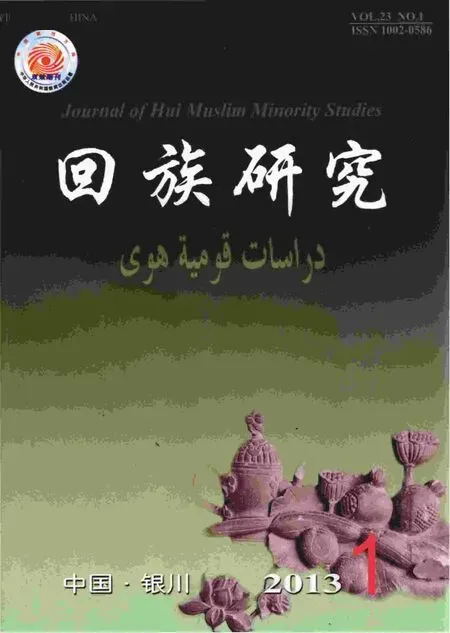“骑手”已过花甲年
雷 雨
(江苏省南京市评论家协会,江苏 南京210009)
在中国文坛,作家形形色色,但每个人似乎都以其言行书写着自己的历史,而大浪淘沙,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无情,许多炙手可热、心胸万丈甚至张牙舞爪几近疯狂者最终却湮灭无闻甚或被人反复诟病与羞辱。但有一个作家,尽管争议颇多、毁誉难一,却自20世纪70年代末跃上文坛至今,始终特立独行、风骨凛凛,以其决绝的文字、孤傲的精神、坚定的拒斥,以笔为旗,独树一帜。他,就是张承志。
阅读《骑手为什么歌唱》《黑骏马》,尤其是《北方的河》时,正值青春年少,精力旺盛,只是粗略地知道,他是回族,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其导师是著名的葆有自我人格的翁独健教授。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在“文革”十年,尤其是“文革”前期,在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的号召推动之下,在中国大地掀起狂飚巨澜的所谓“红卫兵”运动也有张承志活跃的身影,而“红卫兵”这三个字的命名者居然就是当时在清华附中读书的张承志,我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的。在闭塞的乡野之中,向往外面的世界,痴迷地理的宏阔,往往会站在家乡的河流边,注目流水汤汤而遐想无限,这个时候捧读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会被小说中的激扬文字昂奋热情点燃得热血涌动神思飞越,因反复阅读,简直到了能够背诵的程度,在当代中国作家中,能够让我如此着迷的,除了贾平凹的《商州三录》《浮躁》,也就唯有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了。
再后来,便看到了张承志的《西省暗杀考》《心灵史》,我所看到的《心灵史》,大概是四川一家出版社的版本,字号很小,纸张很差,很是粗疏不堪,但文字却如电光石火般敲击着我脆弱的神经,而抚书怅想,却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和莫名的兴奋。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有西北五省区的漫长行走,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遍布着中国的穆斯林,在宁夏泾源县的流连中,在塔尔寺的游客中,每每在与当地人的攀谈中,我都会问他们对张承志的看法:他是怎样的人?读过他的什么书?即使在2012年,又到银川,在六盘山顶大风狂啸令人难以站立的短暂时间,我还与一位朴实得令人心碎的隆德县吴家堡的回族汉子聊起了张承志。说到张承志,这样的似乎很不文化的小伙子流露出难以抑止的崇敬,还有亲切。张承志一再申明,这些真诚的好意有诸多误读甚至夸大的成分,但相互传抄必然带来歧义与错讹,张承志为此而发下宏愿,倾注大量精力与心血修改增删《心灵史》。只要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有体会,不要说修改自己的旧作,即使耐下心来,重新翻阅自己数年前写过的东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承志如此严苛地对待自己书写的文字,他甚至不无激愤近乎自虐地公开宣称自己对《金牧场》的厌恶之情,据说是什么知名歌手出演依据他的《黑骏马》拍摄的电影,对这部影视作品,张承志更是奋加痛斥,未曾假以辞色。我们知道,张承志对日本歌手冈林信康可算是挚爱有加,追踪二十年热情不减,一篇《绝望的前卫》,令冈林信康这个日本歌手潸然泪下认做异乡知音。
在当今这样的时代,谈论文学与正义的关系,光明磊落地呼喊信仰,爱憎分明地表明立场,壁垒分明地抑制招安,可能会被某些人认为是神经不太正常。依张承志这样的起点和资格,他哪怕是有稍许的随和与苟且,也会得到多少下流文人奢望得近乎疯狂的冷炙残羹,但他没有,他选择了远行与拒绝,他坚定地走向最为浑厚而苍凉的底层,几十年来都是努力地保持这一姿态,殊非易事。他笔下流泻出来的文字因这样的行走与思悟,而具有了别样的意义。从《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牧人笔记》《鞍与笔》《以笔为旗》《一册山河》《谁是胜者》《鲜花的废墟》到《敬重与惜别》,拿张承志的话讲,这些文字所散发出来的气韵、思想,可以说与别的中国本土作家无一丝一毫的雷同与重复。
《谁是胜者》是2003年秋冬时节,我在黑龙江萝北县城的一家小书店里买到的,夜宿黑龙江边上的狭小旅馆,长夜漫漫,听着江水奔流,还有对岸就是俄罗斯远东旷野的阵阵犬吠声,默念着张承志如此锥心泣血痛彻心肺的文字,身在旅途的寂寞与孤单一扫而空,不时萌发与朋友彻夜长谈分享感受的冲动,那真是神清气爽豁然开朗的美妙时光。而《绿风土》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用菜票在六朝松附近成贤街上的一家小书店购来,看着如此别致的书名,读着别具一格的文字,第一次领略了小说文本之外的张承志,自此心仪神往其随笔文字,屈指算来,似水流年,已有近三十年春来暑往了。张承志大致说过这样的话:我已经失去了虚构的热情,随笔这样的文字更能表达我的思考。也许缘于这样的认知,在浩如烟海的关乎鲁迅的文字中,张承志的《读先生》《鲁迅路口》因其别具只眼的高度令人叹服,张承志甚至认为,鲁迅一定是胡人的后代。
众所周知,中日关系表面上看是因为钓鱼岛而陷入最低谷,实际上是自甲午以来恩怨纠结迨至1945年草草了局大陆内争迫在眉睫而日本朝野上下都不认为自己是败于中国,石原慎太郎年过八旬还能呼风唤雨不甘寂寞在中日间挑起如此波澜,岂是一人之力?能够用日语写作且有多年旅居日本经验的张承志以其《敬重与惜别》向我们展示了他多年来体察与思悟的日本。张承志以极其庄重的历史责任感与道德勇气,通过自己的严肃观察与深刻思考,给自己的国家与民族提出切实中肯的忠告与警示。他笔下复杂难说的服部幸雄、令人肃然起敬的本多胜一、他眼中的横须贺,他对广岛长崎因被原子弹轰炸后的种种作为的观察,他作为曾经的海军一员登上日本宙斯盾驱逐舰的感慨,他对日本左翼中的一支“赤军”的耐心钩沉,更有对日本家喻户晓的赤穗泉岳寺“四十七士”的细致解读,尤为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张承志毫不避讳地对所谓“亚细亚主义”的梳理,令人触目惊心哑口无言。
辛卯年九月初五的南大夜晚,所有的媒体上都在集中言说中日因钓鱼岛的纷争,浮浅地表态虚张的声势空言误国的文职军人所谓“大兵压境”要展开海上“游击战”的荒唐,更有央视主持人面对如此重大问题的漫不经心吊儿郎当语无伦次,张承志却以激昂沉郁的声音,深入解说着始作俑者已经80 岁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处心积虑长久盘算。石原慎太郎这位当年的文学青年因《太阳的季节》获得芥川文学奖而引人瞩目,他能四次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足见其拥有的超高人气,而当年能够揭穿其画皮者,则是名叫佐藤春夫者。张承志在演讲现场复述了佐藤春夫对石原慎太郎的颇具先见之明的宣言:
我并非一味排斥反伦理的《太阳的季节》。只因如此风俗小说即使作为文艺,也是最低级的东西。作者佯装敏锐的时代感觉,其实未出媒体人及演出商的框子,而绝非文学者之作。又从作品可见作者对美欠缺节度,尤不知害羞喋喋强词之态度更属卑劣。如此无端可取的《太阳的季节》被多数表决选中,于我而言心感可耻,因而我作为评选者,对其当选不负连带责任。
张承志在书中还提到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李香兰,提到了被处以极刑的川岛芳子,提到了英年自杀的太宰治关于鲁迅的小说《惜别》,他甚至还提到了当年的毛泽东与萧三一同求见日本著名的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这一不大为人所知的史实,毛泽东的求见信全文是这样的: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睹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丰采,聆听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
据张承志考证,这封信写于1917年,宫崎滔天到长沙参加黄兴的安葬仪式,毛泽东闻讯,前去求见,邀请宫崎滔天到自己学校去演讲,故有这样情词恳切的学子投书。
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有消息传来,石原慎太郎还有弃两年半的任期于不顾,宣布辞职,成立新党,目标就是要搅动日本政局,修改和平宪法,而10月26日正是1909年的此日,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志士安重根所刺杀的日子。在《敬重与惜别》即将末尾的时候,言犹未尽的张承志甚至有这样的预感:
真没准,在我的小书出版之前,应该成为一切国家和民族理念的、永远弃绝战争手段的和平宪法,就会在日本被人修改。
也没准,就在我们还在讨论两国之间的民族心理,还在探寻用追求民族的存在之美来谋求共存,穷酸的议论尚未开始,枪炮已换过几遍的舰队便会从“一衣带水”的对岸启航,为同文同种的兄弟再上演一场黄海大战。
历史在循回,时代也在催促。鸦片殖民以来的屈辱羞耻、汉唐元明承续的大国传统加上专制——这三座大山使顶戴着它们的中国人,难作追问,时而失语。言论的缝隙是狭窄的。但他们还是向日本追究,从道、德、仁,到信、义、耻。百年的失败,沉重的遗产,恐怖的体制,使他们的声音,痛苦而喑哑。
背负着两颗原子弹灭绝轰炸的苦难,以及自己对于苦难结局的负罪感,日本人深藏着对中国的满腹心事,缄口不言。他们对中国的终极情结是:对日本的判决,并不能使中国逃避——对大国主义的反省。但他们大多不喜发言,如同享受沉默。
张承志毫不掩饰他对一些人的厌恶。对张爱玲,他这样说,“与《忠臣藏》女性对应的反面例子,莫过于‘笔写色与戒,人做汉奸妇’的张爱玲,虽然作为百年反共工程的女神像,被刻意美化由裙及脚,但她在家国破碎的血泊中,被她所顺从的日本的女性光彩,映衬得丑陋不堪。为她的辩护,还会聒噪不止甚至统治主流,但她已经败了。在一种女性美感的对比中,她败得如风卷纸灰,渐渐无迹无痕。虽然她不会承认,打败她的,正是中国的古典精神”。讲到一部关于“七十四士”的作品,张承志说“它是一种熊熊燃烧的民族精神,灼烤照射,使诸如张爱玲、李安的《色戒》那样在中国层出不穷的下流制作:反衬形秽,崩溃融销,荡然无踪”。如此不留情面直截了当地表达对张爱玲的憎恶,也许显得偏激,但这样的拒绝委婉暧昧直言无碍,也是一种风格吧。读着佐藤春夫关于鲁迅“真挚优雅的文字,我唯有震惊和享受。除了用政客腔编造小说史的夏志清那种‘教授’,凡正直的人,都会对鲁迅赢得的尊重,感到高兴”,夏志清的小说史是政客腔调吗?对在大陆上风行的《菊花与刀》,张承志认为,“著者从来没有去过日本,只靠对全体被美国拘禁的美籍日本人进行调查获得资料”,再高大的权威也无须仰视。对于毛泽东身边的李志绥,张承志居然也愤慨不已,在评说“七十四士”的义烈千秋时,张承志这样沉吟:“咀嚼着七十四士事迹”,“它所依仗和宣扬的,不过一种愚忠。但它在实践时的异端和美感,却使愚忠变做了人性。人的尊严、信诺、情义夺门而出,压倒一切。在凛冽的精神面前,对旧道德的讨伐踌躇了。何谓忠的愚贤?况且今日,破除东方的愚忠,往往是无行的右翼精英宣誓效忠西方帝国主义时的见面礼。若李志绥对毛泽东知遇的背叛,以赤穗义士的道理来看,不过是无耻小人的‘卖主求荣’”,而对于被多少人奉若神明的周作人,这位苦雨庵里的知堂,张承志这样笔扫千军:我们见到,诸多的大人物,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并没有一本关于日本的经典。仿佛跻身低檐之下,难写大气文章。浏览着甲午之后的日本谭,虽然新书总在推动旧版,绵绵的游记评论,各有妙处长所,但毕竟大同小异:不仅戴望舒周作人抠抠琐琐,即使鲁迅更语出暧昧欲言又止。时而我们能从鲁迅涉及日本的文字中,读出一种掩饰混杂的微妙”。对于日本,张承志引用了一位日本人的话,令人震撼:我们互相握手,手掌之间渗出了血!
张承志的影响,自不待言,朱苏进、刘醒龙等写作者同行都公开撰文表达对张承志的钦佩之意,此前,通过凤凰壹力贺鹏飞先生,曾多次表达拜访张承志的愿望。前一段时间,张承志因要到巴勒斯坦向当地难民捐助10 万美元而行旅匆匆,如今在他演讲现场看一幅幅图片,看到巴勒斯坦人中居然有这么多的黑人,看着张承志戴着头巾面对异域的信仰同路人的尊重与慈祥,对他人命运的殷殷关切与感同身受,一个有别于他人的作家形象似乎更加明晰起来。
在论述文学与正义的滔滔演讲中,张承志提到了他当年在内蒙古大草原的经历,说到如今教育的问题已经严峻到了关乎人道的坚守问题,他到了他眼中的作家的“暮年”,提到了他对文字的敬畏与节制。他表示,一旦自己感觉写不动了,绝不多写一个字,遗羞于世人。但看上去,张承志并不像步入花甲之年的老者,而是依旧目光炯炯,浓眉倒竖,黑色风衣,斜跨背包,一副行者打扮。虽然言辞激烈,但是周详温和,回答大家的提问乃至应约与听众合影在书上签名,都是耐心有加,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青面獠牙”。
演讲结束,与几位来自宁夏、甘肃、云南的正在南京读大学的几位穆斯林小伙子和女孩子交谈,他们年轻而富有青春朝气的脸庞上写满了满足和欢快。宁夏的小伙子说,多年仰慕,终于见上了一面!
需要提到的,依旧挺拔伟岸的董健先生的主持言简意赅,但字字千钧,令人感叹老先生依旧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恍然间,“骑手”已经64 岁了。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看张承志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