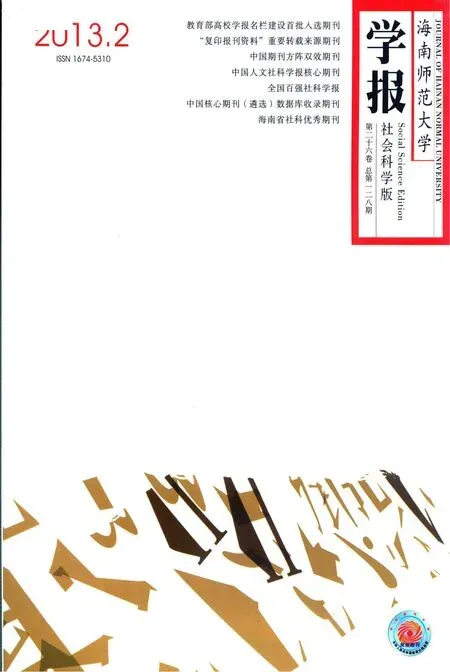作家的自我认同与读者接受——解读“路遥现象”
张立群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为了能够全面、深入地解读近年来的“路遥热”及其相关问题,本文所言的“路遥现象”除了包括学界普遍注意到的文学史书写以及先锋批评家对路遥小说的漠视与大众对路遥小说持久阅读之间形成的“两极对比”,还将其作为一个融合作家创作心理、读者接受以及随时代发展而呈现某种变化的问题加以审视。结合近年来为数众多的研究者大有通过文章为路遥“正名”的态势,笔者以为,只有从更为广阔的文学史视野来看待“路遥现象”,并具体涉及当代文学创作方法、文学批评标准的变迁以及近年来文学的创作现状等问题,才能在还原路遥及其创作的同时,得出合理的解释。
一 现实主义的“资源构成”与“历史书写”
关于路遥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历史定位,自路遥创作被关注之日起,就成为一个共识性的话题。结合路遥的创作、言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实主义对于路遥创作的深刻影响。然而,就研究的角度而言,路遥创作中现实主义的资源构成及其合理展开至今似乎还并未得到全面地梳理,这一点,显然会影响到对路遥创作的准确定位。如果对路遥的现实主义资源进行一次“历史的描述”,那么,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巨著和19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可以首先成为其资源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路遥多次介绍自己喜爱的中外名著以及熟练引用其代表作家的言论,我们不难感受到《红楼梦》和以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大师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①关于路遥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喜爱以及言论引用,可参见路遥《答〈延河〉编辑部问》,《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3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86、94 页。而作为一种“延伸”,路遥自觉继承我国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特别是以柳青《创业史》为代表的创作,又可以作为其现实主义资源的“当代构成”的重要方面。这一点,可以从路遥强调严肃继承《讲话》的“宝贵遗产”,②路遥:《严肃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7—29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高度赞扬前辈作家柳青、将其作为文学“教父”以及痴迷于《创业史》的行为等就可得到证明。①这些言论可见路遥的《病危中的柳青》、《柳青的遗产》两篇文章以及《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等文章。其中,在《病危中的柳青》、《柳青的遗产》中,路遥高度赞扬柳青及《创业史》,称柳青为“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路遥将柳青称之为文学的“教父”,具体见《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5、24、26、119页。此外,他还在《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漫谈小说创作》中多次涉及对柳青的崇拜。而其痴迷于《创业史》,除上述文章外,还可以从后来的回忆文章,如闻频的《雨雪纷飞话路遥》等加以佐证,具体见申晓主编:《守望路遥》,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当然,作为一个有着丰富阅读经验的作家,路遥自然懂得现实主义在不同时代会因生活的变化而丰富、发展的道理。正如他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中指出:“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从这样的高度纵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就不难看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几十年的作品我们不必一一指出,仅就‘大跃进’前后乃至‘文革’十年中的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做了根本性的歪曲。……‘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了一些,但根本谈不到总体意义上的成熟,更没有多少容量巨大的作品。尤其是初期一些轰动社会的作品,虽然力图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可是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和真正现实主义要求对人和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相去甚远。”[1]89显然,在路遥看来,现实主义不仅是一个创作方法的问题,还是一种深刻表现时代生活的写作精神;这种精神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生活中呈现“新的内容”。由此结合路遥在80年代创作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所谓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路遥以高加林、孙少平的形象为代表,写出了这一时期青年一代的成长主题以及潜藏于主人公身上的个人主义的东西。不但如此,与以往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相比,路遥还敏锐地注意到了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丰富内涵。《人生》之所以在发表之后产生全国性的“轰动”、高加林的形象之所以在当时评论界被反复追问“是什么样的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路遥“改写”了五六十年代文学中青年一代简单的“返乡模式”,塑造出一个既真实可信又性格复杂的典型形象。除此之外,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改写”的过程中,路遥还发现小说形式的某种更新同样可以改变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比如,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路遥就注意到了“从我国当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结构看,大都采用封闭式的结构,因此作品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描述都受到相当大的约束。某些点不敢连接为线,而一些线又不敢作广大的延伸,其实,现实主义作品的结构,尤其是大规模的作品,完全可能作开放式结构而未必就‘散架’。问题在于结构的中心点或主线应具有强大的‘磁场’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就是结构的艺术,它要求作家的魄力、想象力和洞察力;要求作家既敢恣肆汪洋又能细针密线,以使作品最终借助一砖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势。”[1]98-99应当说,路遥对于现实主义的深刻认识已成为影响其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事实上,结合其创作也不难发现这也正是其最终敢于选择以“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部作品”[1]86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历史地看,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倚重,客观上仅取决于自身的成长道路和阅读经验的汲取与转化等因素,但这种在80年代已遭遇严峻“挑战”的方法依然使路遥的创作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相对于《人生》、《平凡的世界》在发表后,相继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成广播剧全国热播,后又分别被改编成电影(《人生》1984)、电视剧(《平凡的世界》1989)的局面,路遥笔下的“现实主义”除了可以全景式、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场景之外,切中特定时代的生活主题、深度把握当时人们的心灵世界、揭示传统与当下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也成为其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以路遥在随笔、创作谈中反复提到的“城乡交叉地带”为例,路遥本人的生活经历无疑使其最熟悉和最适合展现这块连接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叉地带”,进而揭示其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②关于“城乡交叉地带”,可参见路遥的《致〈中篇小说选刊〉》、《〈路遥小说选〉自序》、《路遥自传》、《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等文章,后均收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由于其文字大同小异,这里就不一一具体注明。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在80年代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城乡交叉地带”中的生活现象与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它不但可以生动再现新旧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还可以以空间隐喻的方式揭示年青一代的成长焦虑乃至人格的分裂,而建国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迁史就这样在路遥笔下得到了全新而集中的表达。
如果将路遥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与“改写”作为其创作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坚持文学现实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则俨然成为路遥上述创作观念的一个显著特征。然而,在这一观念呈现的过程中,如何达到热播、热读甚至大有经久不衰的态势,却不能不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按照有些论者在阐释路遥小说时所持有的“通俗性”的观点,[2]我们确实可以从路遥小说的阅读难度以及《人生》、《姐姐》、《平凡的世界》中的主人公恋爱模式(“城/乡”、“失败”式的)中看到蛛丝马迹,但这个就路遥本人来说恐怕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评价“字眼儿”,却更多应当归结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及其潜移默化的“规训效果”。既然路遥已然将“整合”后的现实主义带进一个全新的空间地带,那么,或许只有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作家的创作心理和读者接受的角度加以全面的考察,才能得出潜藏于“路遥现象”背后的复杂内容。
按照路遥“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种流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精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说法,人们似乎不难明白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过程中,路遥为什么要强调“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1]86-87任何一种新文学流派和样式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所以,在路遥看来,当时所谓的“现实主义过时论”自然更值得商榷。怀着对于当时中国文坛现状和现实主义生命力的认识,路遥自然会采用一种对比后的“选择”以及针对读者的“考量”:
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当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这就更有必要以多种文学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何况大多数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这种文学样式。“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庸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
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1]89-90
显然,路遥对于现实主义同时也包括现代派创作的客观认识,构成了他最终使用此手法进行《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前提。当然,与此同时,路遥也坦然承认对于这样一部耗时数年的作品,在创作时绝不能“盲目而任性”,它需要自己熟悉的和可以把握的方式进行。这样,路遥所持有的“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也就在成为其创作基本心理动机的同时,具有了某种“挑战”意识。[1]91
二 作家的责任及其心理探析
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贯性认同,自然也影响到了路遥小说的艺术特征与接受层面。正如所有阅读过路遥作品的人,都注意到了路遥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圣徒般的品格、高度的责任感、严肃的现实精神以及强烈的读者意识。这一特点,事实上也成为路遥作品颇受大众读者喜爱的重要原因。当然,若将本文所言的“路遥现象”作为一个阅读接受的问题,那么,其具体展开及有效分析的途径无疑是“反方向的”。
早在写于80年代初期的一些随笔中,路遥就强调面对现实生活的变化,作家应当有义务用“一种折光来投射”现实生活,进而使读者在欣赏的过程中,“获得认识方面的价值”。[3]出于对自己农民身份的无意识认同和对土地、人民的挚爱,路遥深知“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不幸,成功与失败,矛盾和冲突,前途和命运,永远应该是作家全神贯注所关注的。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地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4]为此,对于自己的创作,路遥首先强调艺术的真诚,“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作家用生活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的心。”[5]其次,则是作家进行创作活动时,必须对社会抱有的高度的责任感,“归根结蒂,我们劳动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人类生活更加美好”;“一个热爱人民的艺术家,有责任提高公众的审美水平。”[6]由于对于作品接受与鉴赏层次的关注,路遥十分尊重读者的接受,“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7]“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1]86而这种追求的最终结果,是使路遥的创作上升为某种伦理意识,“我以为,在写作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最纯洁、最健康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为一个明确的目的而付出,哪怕是燃烧自己。这样,可能会使身体累垮,有可能让你丧失许多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但作家必须这样做。”[8]直至成为“心灵的需要”。
追本溯源,路遥在其创作中呈现的上述特点,与其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出生于陕北山区的一个贫苦家庭,7岁时因为家里困难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文革”时期,出于对政治的热情,路遥当上了延川中学红卫兵组织的首领,不久,年仅18岁的路遥又以群众代表的身份成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就在路遥逐步走向政治巅峰的时候,由于某种原因突然被宣布免职,遣回乡下重新成为农民,他的知青恋人也在此时提出分手。仕途失意,爱情受挫,使年轻的路遥非常痛苦,他曾当着后来成为其文学启蒙老师的曹谷溪的面,失声痛哭。尽管,路遥在回乡之后不久被转为民办教师,但从政之路显然离他已经相当遥远了。后来,路遥幸得诗人曹谷溪的提携,开始一步步走上文学之路,并凭借自己在文学上的才能脱颖而出。至1973年,路遥经推荐幸运地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开始转向小说创作。①关于路遥早年的经历,本文主要参考了曹谷溪的《关于路遥的谈话》,高歌的《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后均收入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从路遥这一时期的创作情况来看,《基石》(1973)、《优胜红旗》(1973)、《父子俩》(1976)在主题上依然显示了作家本身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具有鲜明的政治焦虑倾向;而作为一种潜在的主体意识,上述作品与年轻一代渴望继承革命传统、渴慕英雄的思维同样密不可分。路遥在1975年大学还未毕业时,就被借调到《延河》(原名为《陕西文艺》)编辑部,后成为小说编辑,完全走上文学之路。从路遥70年代的生活经历可知:文学之路对于当时尚处青年阶段的路遥来说,既有无奈之后的选择,也有不幸中的幸运。文学创作改变了路遥的人生之路,抚平了由于政治挫折留下的心灵创伤,从这样的独特经历分析路遥早年的创作心理,“弃政从文”很容易隐含着一种焦虑的转移,②关于这些论断,本文主要参考了张红秋的文章《路遥:文学战场的“红卫兵”》,《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李遇春的文章《焦虑的踪迹——论路遥小说创作心理的嬗变》,《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而作为一种结果,这种心理一方面使路遥的创作能够敏锐地触及时代的主题,另一方面,则使路遥通过创作缓解内心的焦虑,直至在不断获得成功的过程中将创作化为一种精神的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关于这一潜在的心理轨迹及其外在呈现,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那种渴望超越自己、近乎圣徒殉道而又不失自虐倾向的文字记录,如“应该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等,加以感受。
从路遥的成长经历看待其创作,苦难、青春励志、积极向上、正义感、道德、悲剧英雄以及平民关怀、大众意识直至生活、生命哲理的探寻,很容易会成为路遥钟爱的主题及其创作的特点。而这些在充满理想、渴望成功、惧怕失败的80年代,又恰恰可以作为引起广大读者关心的创作题材。正如有的研究者在比较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创作之后指出的:“在三位作家中,路遥作品对现实的参与性最强。路遥作品因其苦难意识、底层立场、青春气息、温暖人情和进取精神而具有持久打动人心的魅力和‘励志’效果。对道德的不倦关怀和对完美的道德伦理的呼唤,使路遥作品洋溢着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光辉和令人服膺的崇高感以及对生命意义不懈追问的价值关怀,这是它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葆有永恒魅力的最重要力量源泉。”[9]这种可以被称为“人民性”的内容,基本概括出了路遥创作的生命力和多年后依然受到读者“热读”的奥秘,至于那种源于读者阅读需求的“考量”以及地域性(方言、文化、民俗等)的呈现,更会使路遥的作品带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三 传播、接受与批评标准的嬗变
在先后探究与“路遥现象”有关的创作方法、作家责任等方面的问题后,“路遥现象”的解析最终回到了传播、接受与批评标准的层面上来,然而,这一方面显然比前者更为复杂,不仅如此,就实际展开来看,它还因文学史的今昔对比等而涉及更多方面的内容。
首先,就路遥作品传播的角度来说,至少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其一,是路遥作品在80年代因获得荣誉而产生的影响: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当代》1980年3期),获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1981年《文艺报》中篇小说奖、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当代》1982年5期),获1982年《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人生》(《收获》1982年3期),获1983年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80年代初期,新时期文学起步的年代,路遥3年3篇作品发表于文学大刊并获奖,这在文学可以产生轰动的年份,自然为路遥的声名及其作品传播产生了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后来的《平凡的世界》在1991年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更为路遥作品的传播增加了“砝码”。其二,是路遥作品在80年代获得了传播媒介的良性资助。《人生》、《平凡的世界》相继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成广播剧全国热播,后又分别被改编成电影,显然为路遥的作品特别是这两部作品的传播拓展了渠道、增加了受众面。“广播剧是一种留有巨大空间的艺术,很能激发人的想象力”;“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直强心剂”;来到北京后,路遥在中央台演播室发现了已堆积在这里“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而“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因为它使自己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中”以及由衷地发出“文学借用这两双翅膀(笔者注:广播和电视),能作更广阔的飞翔。我将以更亲近的感情走向它们”[10]的感慨,已从路遥本人的角度,证明了意义和价值。上述两方面如果再以当时文学的地位、传播媒介匮乏作为侧证,那么,路遥作品在80年代的影响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其三,是路遥的作品在当下仍然具有大量的读者及其问题探源,这一点因当下已脱离了路遥作品的“生成语境”,其实已切近“路遥现象”的实质部分。关于路遥作品在9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的热读现象,以往许多文章已经提及,至于像邵燕君在《〈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一文中更是列出了“几份令人震动的调查报告”及其包括的十分详细的数据。[11]对此,笔者以为,“调查报告”由于种种原因,虽有某些误差,不过,它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路遥作品的接受情况,何况还有许多文章持有这样的看法。在路遥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形成文本之后的20年间,时间的流逝、语境的转换、文学主潮的变迁并没有“遮蔽”这些因时间短暂等因素、尚不能称其为“经典作品”的“形象”,其生命力、穿透力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从读者接受的方面看,同样应当坚持历史和当下结合的作法。由80年代路遥作品产生的“热读”,看待当下的“路遥热”,所谓代际构成、怀旧意识以及阅读旨趣、阅读水平等,不乏隐藏着内在的传承性和某种阅读期待的问题。当然,这种可以感知但却不能精确的“客观事实”,同样应当从更为全面的视野加以审视:如果只是偏重于路遥作品的读者数量,那么,姚斯所言的“文学史的更新要求建立一种接受和影响美学,摈弃历史客观主义的偏见和传统的生产美学与再现美学的基础。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在于一种事后建立的‘文学事实’的编组,而在于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先在经验”,[12]自然可以作为路遥作品被写入文学史和以消费为标准持续产生影响的重要依据。然而,在阅读大量有关路遥创作的评价性文章之余,我们会发现指责90年代以来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学史没有记录路遥俨然已是一个“普遍性的论调”,而像某位论者在其文章中以不点名的方式记录的“一个‘新’字号的‘小说家’在文章里攻击完托尔斯泰‘矫情’之后,气宇轩昂地宣布:路遥的小说,读一页给五十元钱,他也不干!”以及“我经常听到一些‘纯文学’批评家贬低路遥的作品,说路遥缺乏‘才华’,说他的作品‘文学价值’不高,不是‘真正的文学’”,①可分别见李建军:《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南方文坛》,2002年6期;李建军:《真正的文学与优秀的作家——论几种文学偏见以及路遥的经验》,收入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似乎更容易使研究立场在鲜明化的同时流露出“矫枉过正”的倾向。上述援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再次证明“路遥现象”从不是一个简单、孤立的问题。
第三,是“路遥现象”与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诸问题的历史再思。对于90年代之后出版的较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关于路遥的写作情况,比如: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2007年2版修订);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都没有提到路遥的创作。由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设有“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思考:《人生》”一节,但没有提及《平凡的世界》。世纪初10年由孟繁华、程光炜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第十五章1985年后的小说(一)”的“第一节小说界的变化”,谈及路遥;由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第十七章第五节“找寻深入写‘人’的新路子”中提及路遥;由陈晓明著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第十二章 历史选择中的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的“二现实的期望:改革攻坚战”中谈到路遥的《人生》,等等。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对路遥研究的重视,2005年之后的“路遥现象”研究已有所好转。当然,文学史家不在自己的著作中评价某位作家从不是评价文学史版本成就的惟一原因,正如以上提到的没有或未充分书写路遥的文学史同样成绩斐然、好评如云,文学史的永恒流动与具体文学史家的评价标准其实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不过,从路遥作品在80年代的影响、上述许多在90年代之后颇具影响的文学史没有记录直至新世纪初几本文学史的“路遥再现”,我们倒可以察觉其中潜在的变化过程。从路遥在着手《平凡的世界》时进行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比,和其感受到的“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1]130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在80年代中期之后渐成声势,确实构成了当时文学创作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而其影响至今、成为20余年来中国文坛的热门话题在今天看来也是可以成立的。按照文学创作的超越机制和对文学批评会产生重要影响的逻辑,路遥的创作不被先锋或曰前卫、新潮批评家认可,其实在于一种审美的“错位”。靠“吃生活”、与时代共振而非天才和技艺进行创作、且个性化的意识严重匮乏的路遥,当然不在现代派、后现代以及先锋的视野之内,而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强调成长、个性的主题,又很难被简单归类(如“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的范畴)并与“重写文学史”的审美指向相去甚远。因此,阅读路遥就与评价路遥之间呈现出了所谓“大众/精英”之间的“接受断层”。此外,对于2005年之后路遥受到文学史的关注,还应从追崇路遥的批评家不断努力、争夺文学史权力,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精神普遍匮乏,“底层文学”、书写苦难在新世纪之初的文学中成为主潮的角度加以思考,而作为某种启示,“从今天的匮乏来对应性地寻找路遥或以路遥为代表的当年有的东西。一方面我觉得这可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我觉得这可能是无效的”[2]所包含的“警惕”与“提防”,更成为“路遥现象”研究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向。
至此,在“路遥现象”的溯源与述析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察觉到:所谓呈现于文学史、批评与读者之间的“两极对比”,自确立之日起便成为另一重意义上的“传播”与“接受”的问题。关于“路遥现象”可以引申的问题,如路遥创作与近30年代意识形态的关系、现实主义创作的当代认识及评估等等,当然还有很多。但就其“现象”的本质来看,正是由于路遥以严肃的文学实践,获得了读者参与同时也是自身作品持久传播的权利,证明了文学创作方法从无高低之分、只有时代之辨,因而,继续以历史、发展的视野审视这一现象,必将为深入认识路遥的作品以及当代文学史的发展与转型提供生动的个案,而这也正是本文最终将其视为一个动态过程的前提与结论。
[1]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M]//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2] 张书群.“80年代”文学:历史对话的可能性——“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J].文艺争鸣,2011(10).
[3] 路遥.这束淡弱的折光——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M]//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5-16.
[4] 路遥.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M]//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8.
[5] 路遥.答《延河》编辑部问[M]//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33.
[6] 路遥.关注建筑中的新生活大厦[M]//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177.
[7] 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M]//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57-58.
[8] 路遥.写作是心灵的需要[M]//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59-60.
[9] 梁颖.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4.
[10] 路遥.我与广播电视[M]//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69-70.
[11] 邵燕君.《平凡的世界》不平凡——“现实主义常销书”的生产模式分析[J].小说评论,2003(1).
[12] H·R·姚斯,等.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