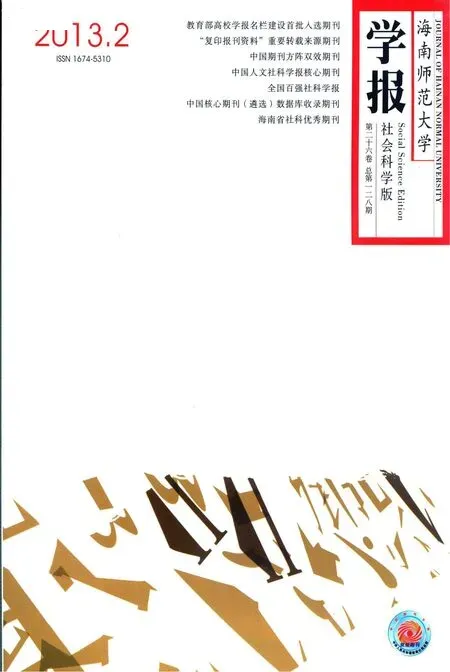《边城》:自由的限度——兼与凌宇等先生商榷
魏 巍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重庆400715)
对于《边城》中的婚姻爱情关系,似乎早有定论。凌宇先生在其《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中谈到,“在翠翠和傩送之间,站起了那座碾坊,一种在它上面,凝聚了[1]243在这里,凌宇先生首次提出了他的“封建买卖婚姻”说。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他再次撰文重申了这一思想,认为“车路—马路、碾坊—渡船两组意象的对立与冲突,在本质上便是苗汉文化的对立与冲突”,因为“走车路”的媒人提亲被认为是汉族地区的“封建婚姻形态”,而“走马路”以歌传情则被认为是“苗族社会中一直保存并延续至今的原始婚恋形态”。而碾房,是“买卖婚姻的象征——团总女儿以一座崭新碾坊作陪嫁,其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而渡船,则是‘一个光人 ’,即除了人之外,一无所有。——《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2]这种对碾坊的象征性解读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响应,严家炎先生在其《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中几乎全盘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边城》“透过种种误会和偶然机缘,在原始淳朴的民情这一背景上,深切揭示了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于另一种与此不调和而又难以抗拒的力量——封建买卖婚姻的力量:团总女儿作为陪嫁的那座碾坊,毕竟胜过破旧的渡船,因而成为翠翠与傩送幸福结合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这一出湘西小儿女不能自主地掌握命运的人生悲剧,作者寄托了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3]黄修己在他主编的文学史中,对凌宇的观点有所发展。他认为“原始的民族性与封建宗法关系交织在一起,而金钱关系也必定冲击着原来相对封闭的民族生存环境和人们的心灵”,“翠翠和傩送爱情悲剧的根源正在于原始的、纯真的民族道德观念,包括爱情婚姻传统观念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这里边不仅存在封建宗法关系,而且资本主义关系正渐渐侵入”,因而“民族古老传统受冲击正急剧销蚀、崩溃”。[4]刘洪涛先生在其《〈边城〉与牧歌情调》一文中也认为:“现实因素对田园景观的渗透,在《边城》中表现为碾坊所代表的金钱交换关系对纯洁爱情的破坏。”“在第十九节,碾房和渡船再次交锋。沈从文在此处将中寨团总女儿与二老婚事还原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5]①其原文是沈从文把这种关系还原的。但是,从我后面的论述里,我们就会看到,与其说这是沈从文还原了这种金钱关系,倒不如说是我们后来的评论者追加上去的。基于此,本文试图从碾坊意象入手,通过辩难梳理碾坊在《边城》中的作用,进而考察“边城”的自由形态。
一 碾房:象征还是诱惑
不能否认,沈从文的某些作品确实反映了凌宇先生所说的“苗汉文化冲突”,如创作于1929年前后的《月下小景》、《神巫之爱》和1932年的《凤子》,但是,具体到1934年的《边城》,说其“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似乎就有了问题,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碾坊不能作为这一冲突的象征来解读。笔者认为,在《边城》中,碾坊不是索取物,而是赠予物。首先,碾坊不是作为婚姻成立与否的前提条件介入的,而是伴随着(在二老与团总女儿婚姻成立的条件下)婚姻的陪嫁妆奁,并非以提亲用的聘礼出现在文本中。且文本里熟人和老船夫的对话也明显认可碾房是陪嫁物。②参见沈从文:《边城》,收入《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其次,傩送是男人而非女人,就算我们不用考虑性别问题,团总也没有要求先把二老“娶”过去,再把碾坊给船总顺顺。由是观之,确认“碾坊,是买卖婚姻的象征”似乎言过其实。
在文本中,碾坊与渡船并无“买卖婚姻”的象征意义,而只是诱惑的大小。要渡船与要碾坊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而只有财富的多寡之别:都是作为结婚时与女方一起的陪嫁物出现的。傩送对爱情的选择,无涉陪嫁物。③此语有文本为证。在《边城》中,中寨来顺顺家要回信,顺顺问及二老意见时,二老说道:“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它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参见沈从文:《边城》,收入《沈从文全集》(第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一下:把翠翠和团总女儿的身份互换,如果翠翠是团总女儿,而团总女儿换成老船夫的孙女,在同样以一座新碾坊作为嫁妆的情况下,傩送会想着要碾坊还是渡船?按照《边城》里傩送对翠翠以及翠翠对傩送的感情逻辑来看,傩送要的只是翠翠这个人,而附带着人的陪嫁品并不重要。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把碾坊看作是“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似乎就有待商榷了。走“车路”还是走“马路”固然突出了两种民俗在面对爱情时的冲突,但是,如果在两情相悦,双方家长也不是极端“专制”的情况下,④在《边城》中,双方的家长也并不能让我们看出“专制”的端倪来。从文本中,我们也多少能够看出双方家长的“民主”性。这一点凌宇先生自己也是很清楚的,在《从边城走向世界》里,他就认为:“在翠翠与傩送的主观精神方面,没有虚假、动摇与情感更移,也不存在双方家长的强行干涉。”(第241页)因此,就小说文本逻辑来看,就算走了“车路”,双方家长也应该考虑到自己孩子的“利益”,况且,大老二老最终选择的是走“马路”。最多也就只剩下路数的不同而已。更进一步说,如果说“车路”靠媒人提亲是汉族的婚姻模式,碾坊是买卖婚姻的象征性证据,那么,在《龙朱》里面,作为具有正宗苗族血统背景的龙朱在经过唱歌互通情意之后,同样以“三十只牛三十坛酒下聘,作了黄牛寨寨主的女婿”,又是不是买卖婚姻呢?“三十只牛三十坛酒”的数量和一座碾坊的价值究竟相差多少?再有,在小说第十节里,作者就借人之口反复强调娶王乡绅家女儿与娶老船夫的孙女在物质上的所得并不会有什么区别,“别说一个光人;一个有用的人,两只手敌得过五座碾坊。”[6]104“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6]108或者,五十步的渡船与一百步的碾坊,我们究竟应该对谁作出批判?我们完全可以不用考虑团总或者船总是否具有汉族血统,因为《龙朱》中黄牛寨寨主的女儿就是花帕苗,两个苗族的年青人尚需以下聘的方式结合,以此反观《边城》,把碾坊说成是“买卖婚姻的象征”,并以此推出这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就显得有些拔高问题意识的嫌疑。或许,我们还可以找另外一座碾坊来作为参照物,在小说《三三》中,“一个堡子里的人,都愿意得到这糠灰里长大的女孩子作媳妇,因为人人都知道这媳妇的妆奁是一座石头作成的碾坊。”在这里,碾坊照样是作为“妆奁”出现的,三三家的碾坊与团总家的碾坊并没有任何质的区别。妆奁之物只是作为一种风俗习惯而存在,这在《三三》中写得很明白:“按照一乡的风气,在女人未出阁以前,有展览妆奁的习惯,一寨子的女人都可来看”,可见,团总家的碾坊也只是一种妆奁,是一种婚娶中的风俗使然,而并非就是一场婚姻买卖。这个连翠翠自己也清楚:“碾坊陪嫁,稀奇事情咧。”碾坊在文本中固然重要,但绝对不至于重要到成为买卖婚姻的本质的地步。但是,我们要如何去认识它的重要性呢?
碾坊的出现,对傩送跟翠翠的爱情来说,也就仅仅充当了情与利取舍的试金石而已,它的出现,不是对婚姻自由构成了挑战,而恰恰是对婚姻自由的考验。同时,碾坊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自由的本身:它的介入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自由。它的介入,不仅证明了以渡船为代表的船夫孙女有恋爱的自由,也证明了以碾坊为代表的乡绅女儿同样有恋爱的自由——不管其陪嫁的是一座碾坊抑或一座金山,都应该有她追求自己婚恋的自由。在小说第十节里,王乡绅的女儿是“自己来看船”的,她不是遵照某种父母之命,也不是遵照某种媒妁之言,也就是说,她是自主的而非封建包办的,她本身既不是权力的牺牲品,也不是金钱的附加物,而是作为一个人“来看人”的。那种以“碾坊所代表的金钱交换关系对纯洁爱情的破坏”的言论实际上是谋杀了代表着更多财富的家庭子女在婚恋上的自由,以碾坊代表着婚姻买卖的本质的言论,实际上是剥夺了拥有更多财富的家庭子女们在自由上的权利。就是帝王家的子女,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有自己爱的权利,这不是财富的多寡所能够剥夺的。
当我们关注碾坊,认为它代表了物质力量,是苗汉文化冲突的象征的时候,恰恰忽略了二老的选择自始至终都是自由的;同时,我们也忽略了老船夫与顺顺在这场恋爱过程中,都是充当了自由人的角色。如果说船总顺顺有不满于二老与翠翠结合的时候,他也只是站在一个与二老平等的立场来给予建议的,而非强制性的,就是王乡绅,在文本中也没有以钱或者以势压人,去逼迫二老娶他家女儿,这三个家庭的家长,都给子女的婚恋关系留下了他们自由选择的空间。
碾坊只是一种诱惑,一种以物质财富的堆积来达成对情感精神上的诱惑,它或许可以使原本在两者间存在的爱情发生偏移甚至位移,但是,爱情本身作为一种情感自由意志,它是不能买卖的。没有别人不自由而自己自由的自由,那种自由只是一种霸权的自由。因此,对碾坊的意象,似不应夸大。在《边城》里,自由不仅是老船夫家翠翠的自由,同时也是二老,是王乡绅家女儿的自由。自由,或者更确切一点,爱情自由,不是我们人为划定的一个范围,它不仅应该存在于穷人间,也应该存在于代表了所谓财富的碾坊中间。它不是穷苦人的专利,任何人都不能垄断它。
二 婚姻:自由的选择
暂且不管评论家是否存在着对文本的“误读”,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稍加一点注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对“封建买卖婚姻”产生厌弃,认为金钱关系破坏了纯洁爱情的言论,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先在的标准之上的: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捍卫着某种作为人的自由。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是一个自由的王国。这从沈从文小说中所表达出来的湘西儿女的情爱描写中见出一斑,例如其情欲自由支配的野合(《夫妇》等),法律制度尚不及于湘西而自然流露的,于当今社会看来是与世俗道德律令背道而驰的情爱自由(《柏子》、《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边城》尤其如此。在这个地方,“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极其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6]73“边城”是一块自由的飞地,他们那里的纠纷不是靠以官方面目出现的权力来解决的,而是靠“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顺顺出面来调解,完全是一种民治自为的环境。
这种自由也表现在学界对沈从文笔下“人性”论述中,“在沈从文心目中,人性的发展,应该顺其自然之道,包括灵与肉的个性,应该能够自由地张扬。”[7]“沈从文所要恢复的人性自由是”“立足于这个民族的现代与未来,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美好素质输入于现代文化的重建中,弥补和缝合现代文化的裂痕”。[8]尽管后来有人做翻案文章,认为“看重人的自然属性而轻视乃至排斥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做法导致了学界盲目的沈从文“人性”健全说,这样就“赤裸裸地表现了对社会性精神性的排斥而将人的自然属性等同于健全人性”。正是以此来反观,“沈从文的作品不是表现了人性的优美健全,恰恰相反,他的作品表现的是人性的贫困和简陋!”[9]如果我们不是站在非此即彼的立场来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论的话,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对沈从文笔下的人性持赞赏还是反驳的观点,其核心之处都在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主人公的人身自由之上。赞赏的人说,他们是自由的,所以人性也就很美;反对的人说,那太自由了,自由到没有节制,自由到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律令所允许的,所以人性就简陋和贫困了。其实,在这个争论上,两者间或许都过于把“自由”作为武器来看待了,事实上,自由应该是一种存在,它不是手段。自由是一种状态。在沈从文的很多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中,自由是一种天然存在,它不是通过法令来维持的,而是一种民间自为的状态。这也就是刘洪涛先生所说的“排斥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认为在一个人身上,重要的不是他所从属的那个阶级、民族、时代,而是与生俱来的性、本能”的“非理性”,[10]28具体到《边城》,就正如文本所说,“若照当地风气,这些事认为只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着;二老当真喜欢翠翠,翠翠又爱二老,他(船总顺顺)也并不反对这种爱怨纠缠的婚姻。”在这里,“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具有较充分的自由。”[1]213当然,这种自由只有在“边城”里才能看到,在沈从文关于都市的作品里,就只能看见“阉寺性”人物了——这种自由是沈从文赋予“湘西世界”的特产。
在那些对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的人性赞赏有加的文章里,甚至在那些认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是贫困和简陋的文章里,自由都不是一种先验的存在,也就是说,自由是为了突出其“人性”而人为附加上去的,而不是文本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这就使得我们在关注湘西的人性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自由在文本中的地位,也忽略了自由在现实中的地位。在“边城”这样一种自由环境的前提下,我们得以去审察沈从文笔下人物的人性,那么,其表现出来的人性状况所体现出来的意蕴,贫困也好,丰富也罢,就不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而应该把以人性来通达自由之路的小说内涵作为我们讨论的重点。那些被认为体现了“人性美”的事物,只是这种自由状态的一种显现方式而已。既然沈从文的“人性”体现的是自由,那么对人性的其他限定性用语,都仅仅只是为了突出其自由之下的人性。自由摆在那里,不管你以什么样的人性来限制修饰它,它都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沈从文的小说里。因此,自由,也只有自由,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主题。
在整个婚姻抉择中,二老是自由的,不管他选择了碾坊还是渡船,他都有选择与不选择的自由,同时,文本的描写也给予了他这样的自由。他不是一个役于物的人,也不是一个役于人的觉新式的物,他是一个完全具有主体性的人。他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去选择碾坊,也没有因为面对兄弟相争的女人而遵从长幼之序退出竞争,而是主动地以唱歌的方式来解决爱情的归属权问题,没有受到人与物的强制。大老死后,二老面临着自我设置的兄弟与爱人间的二元决断,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留下并与翠翠结合,无疑会掉入自我设置的兄弟之义的感情陷阱,事实上,二老也正是掉入了这样的陷阱里,加上“得不到翠翠理会”,才赌气出走的,但是,不管他是出走还是留下来与爱人长相厮守,都是二老的自由选择,离家出走也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对二老来说,在这个二项选择中,他有选择任何一项的自由,或者,也有都不选择的自由。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说,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他可以有其他的任何选择。
但是,“自由作为一个人的定义来理解,并不依靠别的人,但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我的自由追求不可。我不能把自由当作我的目的,除非我把别人的自由同样当作自己的目的。”[11]从这一方面来说,二老的选择就是不自由的,他的选择必须在考虑到他人的时候,才是自由的。面对翠翠的爱情,二老是心知肚明的,惟一不能理解的是翠翠对他的逃离,他不会明白一个少女的心思,也就由此而加深了他对老船夫的隔膜。事实上,二老的最终出走也同时意味着:在对翠翠的爱情与对哥哥大老的感情纠葛中,面对死去的哥哥,二老从心里有种负疚感,这种负疚感使得他不能再继续选择翠翠,他以出走来赎罪。我想说的是:是二老的最终行动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两个人间感情的深浅。至少,在这个文本中,在哥哥已经死去的情况下,他的出走对于哥哥来说是无关的,并不会产生任何善的或者恶的影响。惟一产生了影响的,只是那个与风烛残年的祖父相依为命的翠翠。一旦二老离家出走成为必然,也就意味着他作出了选择,最终的出走则意味着他行动的落实,这时,翠翠所守望的爱情也就只能变成悲剧。照萨特的理论,①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要以存在主义理论来解读《边城》,而只是想以他理论中的某些普世性的东西来看待我们这个世界。“只有我的自由能够限制我的自由。”“我们在使他人的实存回到我们的考虑之中时看到,在这个新的水平上,我的自由也在他人的实存中发现了它的限制”,[12]也就是说,自由是有限度的,它存在相对性,甚至充满悖论,他人的自由是我的自由的基础。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翠翠的爱情就只能停留在她自己的幻想里,尽管她在面对大老与二老的爱情选择中是自由的,然而,这种自由因为二老的出走而成为了二老的自由选择所套在她身上的枷锁。
二老的出走与否,也正如他可以选择渡船或者碾坊一样,是自由的。或许,正是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会把这个充满悲剧的结局认为是由“一连串误会”[10]132引起的,而没有去责备男女任何一方。故事的结局在充满等待的氛围中落幕,也正是对二老自由选择的某种期待。然而,撇开这种作者主观上的期待来看,恰恰是二老在他的自由抉择时没有考虑到翠翠而漠视了她的自由,因此,二老的自由也就成为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自由。不能认为二老的自由是一种承担责任的自由,恰恰相反,它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自由。
三 阻隔:爱情的流产
如果我们非得要在《边城》中找点封建买卖婚姻本质的话,或许,适当关注一下大老的言行就更有意思。在小说第十节里,为大老做媒的人反复提醒老船夫说,只要“人家以为这事情你老人家肯了,翠翠便无有不肯呢。”“人家也仍然以为在日头月光里唱三年六个月的歌,还不如伯伯一句话好。”这里的“人家”毫无疑问是指向大老的,媒人在这里借“人家”之口转述了大老的话。而老船夫则反复更正说“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虽然我们不能剑走偏锋就此断定大老能够替代之前碾坊在评论界的位置,但是,翠翠和二老的爱情结局却确实跟他有关:是他的介入使得老船夫不断地去猜测翠翠究竟喜欢大老还是二老,也由此引发了二老一家的误会;是他的死最终决定了二老的出走,才留下了这曲挽歌。与此同时,如果把“走车路”认为是汉族的婚姻形态,并以此作为“苗汉文化冲突”的依据,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老船夫会主动对来替大老打探口风的人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各的走法”这样的事实,也不能解释与二老一奶同胞的大老一开始要“走马路”找媒人向老船夫提亲这样的事实。这样一来,对二老与翠翠婚姻关系造成破坏的,就不仅仅是碾坊,还应该加上作为汉族身份的大老。按照凌宇先生等人的观点,我们是否可以推出二老与团总一家均具有汉族血统?只是如此一来,二老与翠翠的婚姻就无所谓遭到了外来力量的破坏:它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破坏,他们间的爱情一开始就体现了“苗汉文化冲突”。可是,按照同样的逻辑,这样的爱情我们还能称为爱情吗?
在“走车路”受阻之后,大老和二老以“走马路”来解决这场爱情“撞车事故”,这本来就隐含着某种悲剧性的结局:如果翠翠不小心把代表了大老的情歌当作了二老自己的歌声而选择了大老作为回应的对象呢?按照二老与大老的约定,二老就得退出,二老这样的决定很难说考虑到了翠翠的自由,他把爱情当作可以让渡的权利来看了,两个人的决定是私下的,并没有征得翠翠的同意,他们替翠翠作了决定,假定翠翠也同意他们这样的决定,换言之,在这个时候,翠翠是作为不在场者被搁置一边的,她只与婚姻结果有关,而与爱情过程无缘。她缺席了这场属于自己爱情的谈判。这也是对翠翠自由意志的隐性剥夺。他们间的兄弟之义是以牺牲翠翠的爱情来作为前提的。以此来观之,翠翠和二老的爱情悲剧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与碾坊的介入并无必然联系。
当两个人对爱情的争夺都以二老的歌声来决定的时候,这种公平的竞争也就带上了随机性。我不敢妄加揣测沈从文在这时是否想到了一种公平的自由,所以让二老的歌声以梦的形式出现在翠翠那里而不为其所知,但是,就结果来看的话,效果确实达到了:翠翠没有听到二老的歌声——同时也是大老的歌声,她没有做出任何选择,因为,如果这时候她做出选择,她的自由就会严重受损,同时,大老的自由也会在这种“勇气与义气”的掩盖下受损。不管翠翠选择的是代表大老的歌声,还是选择代表了二老自己的歌声,她在本质上选择的都只是二老一个人的歌声。正因为只是一个人的歌声,所以才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沈从文是对的,他让翠翠处于梦中,而自己则偷梁换柱地代替了翠翠悄无声息地做出了选择:一种没有选择的自由选择。
事实上,抛开大老与碾坊不论,二老和翠翠的爱情悲剧在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从翠翠与二老见面的那一刻起,两人就在相互的不理解中消耗着自己的感情。当二老邀请翠翠到楼上去等她爷爷的时候,翠翠却认为二老是不怀好意。并且,当翠翠在朦胧中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二老以后,连最开始能够产生误解的对话也中断了,她和二老之间的爱情隔着了一层幕布,不管是二老夜晚唱给她的情歌,还是过渡时想要的见面,都被翠翠有意或者无意之间错过。在湘西,至少,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歌是两者间沟通的手段之一,然而,二老在夜里的山歌成了翠翠的催眠曲,由于翠翠并不知道这回事,他唱给翠翠的情歌就成了单相思的独语自白。理解是在对话中形成的。二老对翠翠的爱情表达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在对话这样的沟通行动受阻的情况下,理解就变得不可能。“没有对别人的理解就不会有爱,没有相互承认就不会有自由。”[13]二老的离去,也事实上证明了两者间没有达成相互承认的爱,于是,两个人间的爱就成了封闭的而非对话交流式的。刘西渭认为“《边城》是一首诗,是二老唱给翠翠的情歌。”[14]确实,二老是给翠翠唱了情歌,但是也就仅仅只是唱给了翠翠的情歌而已。正如巴赫金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问题时说的:“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15]在感情的沟通与理解上,二老所唱的情歌做了无用功。而翠翠,则成了那些用蜡塞住耳朵以躲避塞壬歌声诱惑的古希腊水手——虽然她也知道那样的歌声很诱人,也是她想听的,可是她什么也没有听到。“梦”在这里成为了类似于德里达在《二部讨论》里所讨论的“处女膜”一样的东西:既成为一种保护性屏障,也成为双方可能达成沟通理解的障碍。原本可能相互沟通达成的理解在翠翠的梦里中断。我在这里用了“可能”,而不是“可以”,原因就在小说的第十节里。当爷爷问翠翠如果有人在对溪高崖对她唱歌她该怎么办时,翠翠的回答也明显不能让祖父满意:她只愿意听对方唱下去,却还没有想到懂歌里意思的程度。究竟是心智不成熟还是羞涩所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二老与翠翠间的相互沟通只是停留在一种可能性上,他们的爱情其实先天就存在着缺陷。
二人的最后结局,也跟翠翠自身有很大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翠翠对二老夜里的情歌毫无所知,也表现在她的行动中。翠翠每从二老的眼皮下逃离一次,她所面对的爱情也就后退一步。由于羞于表达,翠翠的爱情受到了自我的限制,成为有所局限的自由。这种爱情天然是有缺陷的。对于自己的爱情,不仅面对自己的爱人羞于启齿,就是面对自己祖父谈及自己的爱情的时候,也是要么“不作声”,“有意装听不到”,要么走掉。而与她竞争的团总家女儿则明显主动得多,虽然小说中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她的心理活动,仅仅把她当做一个配角来写的,但是,我们至少知道,在赛龙舟的时候,她是自己去“看人”的,仅仅就这一个细节,也足以说明她对自己的爱情是积极的,以此反观翠翠和二老的爱情结局,我们就会感到,如果没有奇迹出现,他们的爱情悲剧几乎就是必然的。她和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的祖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交流,翠翠与祖父的对话是一场没有说清楚的对话,“没说清楚的对话依然是一种虚假的对话,是一种次要的交流,与失声同义。”[16]这使得祖父最开始在猜测孙女的爱情时,竟错把大老当作了自己未来的孙婿。翠翠的自由爱情只有通过老船夫之口才能得到表达,可是,一个只凭想象的老年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明白、理解年青人的想法呢?翠翠从来就没有清楚地告诉她的祖父她究竟喜欢谁,这也就使得祖父只能靠猜测在大老和二老之间为她挑选合适的夫婿。对于祖父来说,重要的或许不是大老和二老之间的区别,比如说像有人归结的大老的世俗或者二老的诗性,而是在翠翠自己喜欢的前提下,能够有一个可以在自己死后照顾好翠翠的男人。
当他明白翠翠的爱情对象时,老船夫对孙女爱情自由的表达在二老那里却变成了误解。误解产生于不理解,产生于交流的不畅。惟一能够消除误解的就是自由的对话交流,可是由于老船夫的含蓄,一切的补救又总是弄巧成拙,不管是与二老的对话,还是与顺顺的对话,都显得扭扭捏捏,无用而多余,以致得不到二老一家的理解。“老船夫对于这件事情的关心处,使二老父子对于老船夫反而有了点误会。”也正是这种双重误解,这种对话交流的不畅推动了悲剧的最终形成。
等到老船夫死后,翠翠自由表达爱情的传话筒也就随之消失。老马兵接替了翠翠保护人的位置,就连翠翠是否应该住到二老家去,也是老马兵“为翠翠出主张”。翠翠在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始终表现出一种受限的自由。可是,如果翠翠始终对自己的爱情保持缄默,这个老马兵又能充当她多少年的传话筒呢?况且,他是否也会如自己的祖父一样,继续在双重误解中期待她的爱情呢?这样的爱情结局是否会循环下去呢?
四 余论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顺便追问:这样的自由交流不畅原因何在?事实上,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甚至可能并不是翠翠和二老,或者碾坊与渡船之间的问题,而是沈从文自己在写作中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去考虑沈从文在文本之外对湘西文化、风俗以及个人品性的近乎天然自由的论述与描写,比如那种以情歌对唱互诉衷情,彼此相爱后随时随地都可以作点“呆事”的民风民俗并没有体现在这对湘西小儿女身上,单单就在《边城》中,小说第二节里所提供给我们的“边城”背景在后面的行文中就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那种连妓女都能够敢爱敢恨的个人品性在随后的行文中消失殆尽。换句话说,人物是生活在环境之外的。完全可以说是沈从文人为地把他们的自由给抹杀了。翠翠和二老的爱情结局,是生活环境与人事错位的必然结果。不过在这里这都不是主要的,因为我们不能用实证的态度去思考文学的问题。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这样的结局与其说是针对二老的回来与否,倒不如说是针对翠翠那有所缺陷的自由而论的,针对那因自我限制的自由表达所造成的无助爱情而言的。因此,与其说是碾坊的介入谋杀了翠翠与二老的爱情,倒不如说是二老的大男子主义式的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对自由的限度把握不准而造成的人间悲剧。
[1]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1985.
[2]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J].文学评论,2002(6).
[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20.
[4]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卷)[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342-343.
[5] 刘洪涛.《边城》与牧歌情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1).
[6] 沈从文.边城[M]//沈从文全集:第8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 吴立昌.“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自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3.
[8] 赵学勇.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修订版)[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188、192.
[9] 刘永泰.人性的贫困和简陋——重读沈从文[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2).
[10]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8.
[12]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书店,2007:636.
[13]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信仰和知识——“德国和平书业奖”致辞[C]//李惠斌.全球化与现代性批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99.
[14] 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C]//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01.
[15]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40.
[16]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