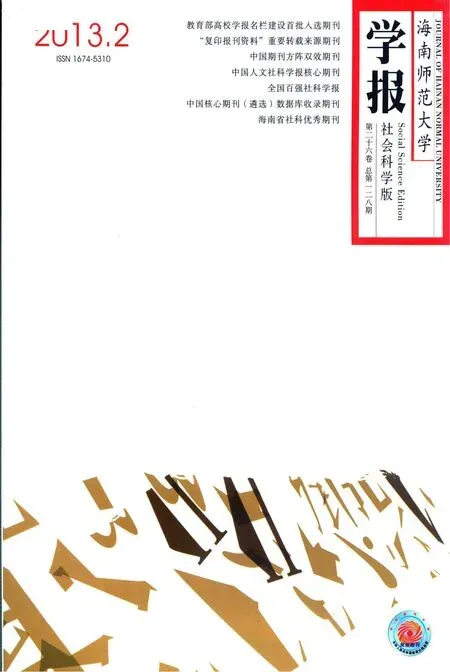二十世纪初中国“科幻小说”中的西方形象——以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为中心
邹小娟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20世纪初,中国创作小说数量达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高峰,小说门类繁多,出现了描写未来世界,充满“乌托邦”式美好想象的小说,此类小说在报刊中被称之为“科幻小说”或“理想小说”。著名汉学家王德威用了“科幻奇谭”替代“科幻小说”,因为此类小说“叙事动力来自演义稀奇怪异的物象与亦幻亦真的事件,其叙事效果则在想象与认识论的层面,挑动着读者的非非之想”。[1]292王德威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上理解晚清小说中新出现的门类。实际上“科幻小说”是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发展基本完善之后出现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以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创作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富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为标志,后来有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艾洛斯和查米恩的对话》(The Conversation of Eiros and Charmion),法国科幻小说之父的儒勒·凡尔纳的标志性作品《海底两万里》。这些科幻小说以科学知识来刺激读者的想象,所虚构的情节使读者充分领略科学所带来的奇妙世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和美国尤为流行,四五十年代科幻小说发展到巅峰阶段,题材无非也是利用“科学”的方式来言说或想象未来的社会。因此,20世纪第一个10年新出现的“科幻小说”的命名充分证明其特殊性:糅杂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与域外小说特征。这个特殊文类在当时中国作家所创作的篇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严格来说,“科幻小说”受到当时翻译小说的影响。19世纪西方人颇为看重的科幻小说在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译介,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和认同。翻译小说从数目上超过创作小说,估计占有全数量的2/3。[2]184其中,以科学为主题的科幻小说占有很大一部分。从最早付梓翻译的《百年一觉》到林译小说的盛行,各类报刊、文学杂志争先刊登翻译小说,而翻译科幻小说占很大的比例。阿英粗略统计了科幻小说大致有:《电术奇谈》(吴趼人,新小说社,1905年)、《千年后之世界》(包天笑)、《梦游二十一世纪》(杨德森,商务,1903年)、《空中飞艇》(海天独啸子,明权社,1903年)、《新舞台》(东海觉我,日本押川春浪,1905 年)[2]190等。翻译作品毫无疑问成为晚清作家学习的蓝本,加之在中国风气开化的地方,“西学东渐”之风盛行,西方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所以,作家们会有意识地选择这一题材表达他们心中的未来世界。作者通过想象,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梦幻的、自由的、平等的、祥和的未来社会。诚如王德威所言,科幻小说的背后是作家和读者结合政治理念,对于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思索,或者说仅仅是小说的一种修辞策略。[1]294但科幻小说家基于对新知识的崇尚心理和对美好未来的想象,采用熟知的话语模式书写科幻小说,[1]295这一事实却无法否定。
本文以署名荒江钓叟撰写的“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中有关西方书写的文字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梳理该小说中的西方形象,讨论作者言说的文化身份、文化心理和社会原因。
《月球殖民地》原载《绣像小说》第21—24、26—40、42和59—62号上,1904年出版,全书共35回,未完。这是一部科幻小说,全书以日本义士玉太郎驾驶热气球为中国人龙孟华寻找妻子凤氏和儿子龙必大为主线展开的故事,他们在寻找妻子和儿子的过程中亲身经历诸多劫难,亲眼目睹很多荒蛮小岛的恶风陋俗,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使得龙孟华全家团圆。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幻想小说,书中主要人物的名称别具意义:龙孟华指代龙的传人,华夏子孙,也就是中国人,凤氏也是中国人的别称,中国文化中素有“龙凤呈祥”的指代,“龙必大”隐喻中国必然强大的意思。小说中所出现的西方形象主要呈现出友好、亲善等神性特点。主要包括玉太郎与气球、圣女玛苏亚、西方外科手术以及所历经岛屿的所见所闻。从艺术方面评价,该小说的艺术成就不能算高,但所塑造的西方器物形象和西方人物形象各具特色。
一 西方人:东方的拯救者
荒江钓叟笔下的西方人物有日本义士玉太郎和美国圣母玛苏亚,虽然身份不同,但都散发着神性的光芒。在他们的帮助下,具有象征意义的主人公之一的龙孟华终于和失散已久的妻子凤氏和儿子龙必大团圆。两位救助者无疑承载了作者对弱小中华民族的救助者的美好想象。
(一)日本义士玉太郎
小说的主人公日本义士玉太郎,是作者笔下完美外国人形象的化身。他不光熟练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而且具有志士的智慧和侠士的义气。通俗来讲,玉太郎是位文武双全、智勇结合的“英雄”式人物。英雄救国当然是中华文化中的不老神话。作者以此为小说的叙事方式,其目的还是围绕“救亡”的时代责任。作者以不同的叙述方式,对玉太郎进行了深度刻画。
玉太郎,就名字而言,本身具有中西文化结合的特点。君子如玉,太郎是日本文化中武士的常用称谓。他的独特身份与中国人有不解之渊源。其父是日本东京志士藤田犹太郎,因为按照《万国公法》,保护了被中国朝廷追拿的罪臣李安武,并把他带回日本,学习普通格致化学。其妻濮玉环也是位杰出的中国女性,不但贤惠,而且异常聪颖,所以玉太郎虽以日本人的民族身份出现,但他的身上融合着日本与中国两个民族的亲缘特征,具有跨文化的特性。
玉太郎的出场颇有中国文化的神话色彩,在花好月圆之际,他驾驶着气球缓缓而下,降落在梅花香气四溢的月夜:
酒到半酣,抬头一望,只见天空里一个气球,飘飘摇摇,却好在亭子前面一块三五亩大的草地落下,两人大为惊诧,看那气球的外面,晶光烁烁,仿佛像天空的月轮一样,那下面并不用兜笼,与寻常的作法迥然不同。忽然叮当一声,开了一扇窗棂,一个人从窗棂里走下。那人生得仪容不俗,举止堂堂,看见这里梅花盛开,便从容赏玩。[3]244
这就是玉太郎的梦幻式的出场,他仪容举止不俗,宛若月宫仙子,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以神仙的形象出现在龙孟华等中国人面前。神仙必定具有救苦救难之社会功能。
玉太郎非凡俗之辈,与其父犹太郎一样,具有侠义心肠,对中国人尤为友好。在华人在西方国家遭受歧视和虐待的历史背景下,他不顾个人的得失,带华人龙孟华踏遍全球寻找其妻。在纽约,遇到长相异常凶恶,脑袋像炮弹一般,待中国人最是无礼的美国捕头,软弱无为、无视民族荣辱又剥削中国百姓的中国领事官,具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日本领事,作者以这些异域人物与玉太郎作比较,旨在讽刺中国官员的昏庸和无能,赞颂玉太郎与日本官员救赎积贫积弱的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
再次,玉太郎的侠义精神还体现在寻找孟妻的旅途中。他驾驶气球自由行驶,从亚洲转向欧美,又到达非洲、大洋洲等地,旅途中经历和目睹了世间万象。这一漫长的旅行过程,实际隐喻了中华民族所存在的恶瘤。作者以玉太郎的视角来再现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残酷现状。
6个岛屿,风俗险恶,分别再现了中国社会不同方面存在的巨大问题。第一个岛屿名叫蝙蝠岛,一群毛人,朝着玉太郎和鱼拉先生坐的气球乱扔石子,此岛屿的毛人对于气球所代表的外来文明持抵制和拒绝态度。第二个岛屿是柏儿来斯华勒岛,岛屿上的土番隐喻中国的社会现状,野蛮、落后、凶残、迷信等特点。第三个岛屿,鱼鳞国是典型的畸形发展的国家,男女都身残志不坚,国家没有任何生机和前途。第四个岛屿叫做尚仁岛,岛内风景秀丽,土壤肥沃,人口众多,却有坏的风俗,一班读死书的人和一班假斯文的人,害得岛内人口只剩下几十人,城里成为毒蛇猛兽、猪狗狐狸的窝巢。第五个岛屿叫做司常煞儿岛,是吃人饮血,杀人如麻的专制社会,酋长吃人饮血,穿人皮革,遇着祭天神大典,必然宰杀人做牺牲,奖赏品也是烧烤全人或人皮革衣服,岛内人只好把房屋砌在地底下。第六个岛屿叫做石帆岛,也是荒芜却恶相丛生。
以上这些野蛮岛屿是作者对于中国社会的描摹。王德威认为每一处岛国都是中国的缩影,作者旨在批判。[1]334的确如此,各岛国都以自己特有的野蛮风气而著称,作者以隐喻的修辞方式揭示了中国政治的腐败、黑暗,习俗的丑恶、文化的腐朽,老百姓生活的艰难等等社会现状,对于本民族存在的危机有着很深的焦虑感。小说在这一点上与谴责小说家以诙谐的方式表达的讽刺意义相同。
玉太郎一行人亲眼目睹了野蛮岛屿的险恶情况,并且利用先进的科技设备,与恶势力积极搏斗,所以说他是作者理想化的日本人形象,集中了人性的优点,身上带有浓厚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烙印,忠厚、仁慈、儒雅、义气,但又超越传统的儒士,具有英雄气度。作者对于玉太郎的描写可谓是浓墨重泼,极力刻画他的性格特点。作者在塑造玉太郎的同时,也对本国人进行了认真审视。龙孟华虽有满腔爱国热血,但面对险恶的外部世界,他软弱的性格使得作者大有“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情结。龙孟华与玉太郎形成鲜明对比,并构成“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作者言下之意是中国缺少像玉太郎一样具有优秀品质的义士。在小说里,玉太郎被作者塑造为一个“拯救者”的完美的形象。他带着知书达理的中国妻子、中国朋友、英国医生一起驾驶气球寻找龙之妻和子,在天空中自由行走,在气球上俯视隐喻中国社会的岛屿,最后抵达月球,见到月球童子投胎的儿子“龙必大”。龙必大后又与月球世家女子结亲,乘坐更先进的气球接父母去月球居住,圆了龙孟华旅居月球的美梦。玉太郎的完美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的民族主义话语。针对千疮百孔的中国,若要实现强国美梦,不但应该有民族英雄,还不能缺少具有普世精神的外来力量的帮助。后崛起的强国日本,与中国同种,又是邻国,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巨大转变与日本的民族英雄有关。作者站在富国强民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书写玉太郎,玉太郎身上寄托了作者的强国梦想。
(二)美国圣母玛苏亚
由于文化差异,西方宗教在20世纪初并没有像一个世纪之前来华传教士所预期那样深入中国人的生活,而是仅仅存在于局部,大部分晚清作家对西方宗教的了解也只停留在表面,“传教士”形象出现在他们对西方宗教的理解基础之上,但“圣母”形象却很少涉及。在西方基督教中圣母玛利亚以其圣洁、完美无瑕、博爱、伟大等品质成为西方宗教完美人物形象的典范。《月球殖民地》小说中,作者以想象的方式虚构出一个中国式的西方“圣母”形象,她既具备西方圣母玛利亚的博爱仁慈特点,又兼有中国刚烈女子的性情。
如果说日本义士玉太郎被作者塑造成“东方拯救者”的形象,那么玛苏亚女士则是另外一位与玉太郎一样舍己救人的“圣母”形象。她无私帮助小说的主人公龙孟华之妻龙凤氏,不光搭救其性命,而且收留她,竭力帮助龙凤氏寻找丈夫。在寻找途中,不幸为海盗所迫,为保全贞洁而自杀。
玛苏亚的故事并非作者亲自讲述,而是通过女教士和龙凤氏的叙述告诉读者的,这样增强了故事的可靠性。女教士从宗教的角度讲述了玛苏亚的生平事迹:出身富豪家庭,但不惜钱财,捐巨资给慈善机构。她出于人道主义拯救了落水妇女龙凤氏,并且和她情似母女。龙凤氏在教堂里请玉太郎之妻濮玉环代她叙述有关玛苏亚的故事:玛苏亚帮助义女凤氏寻找丈夫和儿子,母女两人因坐邮船在海上遇险,搭了一只小渔船,不巧遇到海盗夺财,并打算将两人贩卖到其他地方,两人无奈,只好选择跳海逃生。玛苏亚跳海时,不凑巧头发被船上的锚挂住,只好开枪将自己打死,凤氏抱着一支折断的船桅在海上飘荡。玛苏亚不惧艰险,英勇对抗邪恶,生死关头,凛然选择死亡,死亡将她的伟大人格升华为永恒的神性,所以说她是女中豪杰,不但是妇女学习的榜样,而且是人类效仿的典范。作者对玛苏亚极其崇拜,视她为圣母式的西方女性,寄托了作者美好的想象,也是他对于中国妇女的一种期望。
作者同样采取神话故事的叙事方式来塑造玛苏亚。玛苏亚在家做了一个梦,因为行善,感动了女仙,女仙下凡赐予她女儿和孙子,所以她受神的指示,拥有了干女儿凤氏和孙子龙必大。这是“善恶有报”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体现。女仙的出场颇有神话色彩:
仿佛半空像有作乐的声音,渐渐的落下。……见那音乐部的歌童舞女都和这世上两样。当中有位女仙,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那容貌的庄严,比着我们的圣母娘娘还庄严得许多。……女仙也起身去,走到门外,只见一个团团圆圆的大月球,那女仙便和一班儿歌舞队冉冉的上去了。[3]309
神话叙事首先会有感官上的审美愉悦。色彩和音画的变化,构筑了似梦似幻的艺术效果,是中国传统小说常用的叙事策略,作者通常借助神话故事来表达神话背后更深刻的意义。在此,女仙和众歌童和舞女都是超越于凡尘的人物,他们降临于玛苏亚身旁,增加了神性色彩,暗示了玛苏亚已经介于人与神之间的特殊身份。玛苏亚所做的善事得到仙子的认可和赞同,音乐、歌舞、大月球、女仙、婴儿等意象展示的是一个圣洁的世界。这些艺术描写手法共同表现了玛苏亚的特殊身份,她是圣母的化身,贯穿宗教意识的宇宙精神。她具有“永恒女性”的大爱之美,她追寻上帝的真理,具有热烈的宗教情感,显示出光辉、快乐,满怀期待,并能保持内心的平静,积极参与神的事业,是理想基督徒的代表。对身边的人给予同情和强烈的爱心。
作者塑造玉太郎与玛苏亚这类具有“神性”特点的西方人物形象,虽然叙述技巧各异,但他们实际上都承担了“东方拯救者”的社会功能。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作者借助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企图改造落后软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心理。
二 西方器物:神奇的气球
“气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仍然是美好的想象,是先进的西方器物的典型形象,在科幻小说中成为国富民强的重要标志。在19世纪中期,走出国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气球就有详细的记载。志刚在1868年随同出任中国政府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a)等人作为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员,他的《初使泰西记》记述了使团1868年至1870年在欧美国家的所见所闻,其中就有对西方“气球”的记载,他称之为“天船”:
西人有天船,可升空际,以资瞭望,泄不通之信,非止作奇器、炫奇观也。其法,缝皮为大球亩许,鼓空气于众,而掣出炭养之气,止留淡气。则中气轻于外气,如沈木于水而自浮。球底系皮兜,恰受两三人。俟气球浮空,连兜带起,谓之船者,借称也。[4]
志刚第一次见到这个神奇的升空之物,疑是天上飞来,所以称为“天船”,说明了气球的新奇特点,是他从未见过的神秘之物。清朝同治年间,年轻的翻译张德彝在同治十二年记下了他1871年随崇厚前往法国解决教案,在他旅法日记《燹后巴黎记》中记载:
当德兵围困巴里时,法于城内思安江两岸,各设气球公司,以便乘之出入,窥探军情、往乞救援等用。盖气球可以腾空俯视。今制则高必六十丈,用照相镜下映敌营,则其兵阵地形一一映入。并可携带电线,以千里镜俯视一切,随看随报,极其迅速。小说所云腾云驾雾,其神奇殆不过是云。[5]
法国人以气球作为军队装备,用来侦察敌情,非常方便。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中就有对气球历史的详细总结,记载如下:
气球创于百年之前,法国战事初用其器。后阅七十年之久,视为废物;三十年前,始复兴用。……近十年前,始更精求其理法,以便多用于战事。惟今所放气球,仍用绳牵而鬆放之,气球尚未多进益。近来法国于其电气机器考求益精,将来或能够造船形气球,迎风逆气,或借旁风而速前行,则或借以清兵解围,或通信营垒,其益最大。[6]
以上文字说明气球不断被改进,不但被用在军事上,而且用于通信。不仅如此,同时期的各大报刊登载大量有关这个奇异之物的文章。《时务报》刊登《伦敦东方报》(西五月初八日)的一篇有关气球的文章《天气雷》这样写道:
电学新报,近论气雷甚详,雷系一小球,加满天气,能在离地五尺至一千尺高处,气球底挂一篮,篮内盛最烈炸药,遇物炸裂,其力甚猛,交战备用,颇称简便。据创造气雷者云,凡围困城池,或解重围,寻常非大队不能奏功。用气雷年一卒,足以济事,其简便如此,讵非行军之利器乎?①见《时务报》,1896年第1期。
气球无非还是用在军事上,可以解围,便捷有效。1896年8月14日译《伦敦东方报》登载的另一篇文章《英重气球》:
其由气球掷放炸药亦须细行试验云,各种炸药由气球从上掷下,试验之处,定在阿尔豆晓地方,不久即可举行。其试验之时,高处如何,低处如何,并与天气性情有何相关之处均须细察,军中新式气球,现在阿尔豆晓地方制造,以备试验之用,其造法该厂颇讲究云。①见《时务报》,1896年第6期。
《清议报》光绪二十五年岁四月十一号域多利泰晤士报刊登《新式气球》,报道德国军队气球营使用新式气球情况:
其起落行驶之捷速而耐久。为从前所无。十点十二分初离德营,时值顺风,至午时一点钟时,即过霸利士城,三点钟即抵德奥交界地,气球离地面约有五千尺。四点钟时,球落于奥国,计球行六点钟之久,共行四百二里。该地人见气球落地,莫不惊慌,疑为空中鬼物……又疑为是奸细……。②见《清议报》,1899年第14期。
这段话详细介绍了气球的捷速耐久的特点,其他地方人见到前所未见之物的反应。到了1900年代气球不仅仅应用于战争中,而且普通人还可以观赏。康有为在光绪三十年旅行至欧美,在法国公园看到游人乘坐的气球是这样的:
球大五六丈,内实空气;系绳无数,以悬藤筐。筐以架轧成,中空而周阑广六七尺,可座数人。……是日登球至二千尺,飘然御风而行。天朗气清,可以四望。俯瞰巴黎,红楼绿野如画,山岭如陵,车马如蚁。……此事非小,他日制作日精,日往来天空,必用此物。今飞船已盛行于美,又觉汽船为钝物矣。至于天空交战,益为神物。[7]
从以上史料的详细记载来看,气球原是战争中使用的一种新式武器,在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都有制造。后来气球演变成为方便、快捷、新奇的空中交通工具并非是纯粹的美好想象,而是建立在对西方各国先进科技发达的事实基本认知之上。在1902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前,气球是惟一可以在天空中飞行的器械,是作者借“它山之石”来言说自我心中的理想 。气球帮助玉太郎完成寻找和救赎的人道主义使命,也是民族强盛的标志,作者预见到未来国家之间的争夺在于高科技的掌握,所以说气球寄托着作者的强国梦想。
气球在《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有象征意义。首先作为能离开地面飞行的先进交通工具,是人工智慧集成的成果,为主人公日本义士玉太郎自由出入提供了可能,扩大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其次,气球作为重要道具,推动了小说叙事。[1]331小说的主人公随着气球的移动和上升,视角也发生了改变。他离开是非之地,进入广阔的视野,见到不同的景象。小说以新奇、刺激的感官重新审视国家民族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扩大了想象和叙事空间。
气球是日本义士玉太郎花费了五六年的心力制造成的,气球的外观和性能独特神奇:
那机器的玲珑,真正是从前所没有见过的。除气舱之外,那会客的有客厅,练身体的有体操场,其余卧室及大餐间,没有一件不齐备,铺设没有一件不精致。……忽听得气轮鼓动,那球早腾空而起。[3]245
气球不仅是行动自如的现代化交通工具,而且还具有便捷的生活功能,它如同长了翅膀的房屋,超越于实现,具有魔幻色彩,更能衬托出玉太郎的神性。正因为驾驶气球,义士玉太郎才能够发挥救赎者的作用,随心所欲带着中国人龙孟华越过千山万水寻找亲人。坐在气球上,他们感受非常独特,瞬间掠过山峰和海洋,从高处看到繁华的纽约都市,纽约犹如掌中之图画。
纽约的都市好比是画图一幅,中间四五十处楼房,红红绿绿的,好比那地上的蚁穴、树上的蜂巢,那纵横的铁路,好比那手掌上的螺纹。[3]256
明显看出作者以新奇的眼光俯瞰纽约,纽约的繁华景象让他感到兴奋。作者在看纽约,而在小说的第九回,玉太郎驾驶气球到了伦敦后,英国人聚集起来观看这个新式气球。
那满都市的博物学士、天文学士、地理学士以及各种的科学生徒,没有一个不摩拳擦掌,想看这新式气球的样子,以便仿效制造。[3]265-266
同样是在“看”,但作者是看纽约,伦敦人是在看气球。同为欧美强国,但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不一,相比之下,对于英国人更为关注。玉太郎的气球在此代表着黄种人的东方现代化文明器物,超过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作者想象出英国人看到黄种人更先进的科技文明,专门派专家去日本查访,学习或购买,生怕这权利落在了日本人手里。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对抗直接反映在现代化文明的竞争层面上,所以,作者虚构气球的技高一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者强国梦的具体呈现。
结 论
作者荒江钓叟的具体身份无从考证,其小说总体上属于科幻小说门类。虽然作者以光怪陆离的叙述方式讲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奇特故事,塑造的西方形象呈现被“美化”的总趋势,西方人物带有极强的“神性”色彩,西方器物具有超强的神奇功能,但实际上,作者想象中的西方形象并非真实,与现实中真实的“西方”存在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正是作者独特情感体验的综合外在表现。
由于作家处在中国社会从旧到新的转型期,中华民族受到西方势力的挤压,加之西学东渐的时代大潮,作家的思想意识也随着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传统的时代责任感使得他们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不再一味沉湎于传统的文化观念之中,而是主动接受西方文化,向科学技术先进的西方学习。西方是他们寻求救国的良方,因此,作家视野中的“西方”不仅是东方的拯救者,而且还是科技水平相当发达的地方,作者以美好的想象,勾画出了心中强国梦的渴望。
作者对西方的亲善态度与作家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和接受建立在一定的实用功能上,19世纪的西方呈现出民主、和谐、自由、发达等新风貌,而同期的中国社会仍然处在闭关锁国的落后状态,西方国家和中国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参照。在动荡时期,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保种之路,西方的社会模式和现状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一种理想范式,在这一点上,科幻小说家比其它门类小说家更容易选择先进的西方形象作为书写对象,直观展示心中的理想,比其它门类小说家更为敏感于西方形象之于构筑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重要意义。
西方形象不仅是社会内容镜像的反映,而且还是作者对“自我”与“他者”内在关系的深入思考。虽然文本中的西方形象以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呈现出灿烂多姿的形态,但其精神内核与当时中国社会两大时代主题之一的“救亡”紧密相关。作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出对强大的“他者”的想往,所以他们以大胆的笔触尽力表现一个进步的、审美的西方。运用“他者”视角揭露“自我”存在的问题。为了批判病态的中国社会,作者自觉地对“西方形象”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与改造,使其符合中国文化自身需要,以“为我所用”的文化心理模式来塑造其视野中的西方。
[1] 〔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阿英.晚清小说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3] 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M]//章培恒,王继权,等.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4] 志刚.初使泰西记(走向世界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324.
[5] 张德彝.燹后巴黎记(走向世界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449.
[6] 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走向世界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605.
[7] 康有为.法兰西游记[M]//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走向世界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