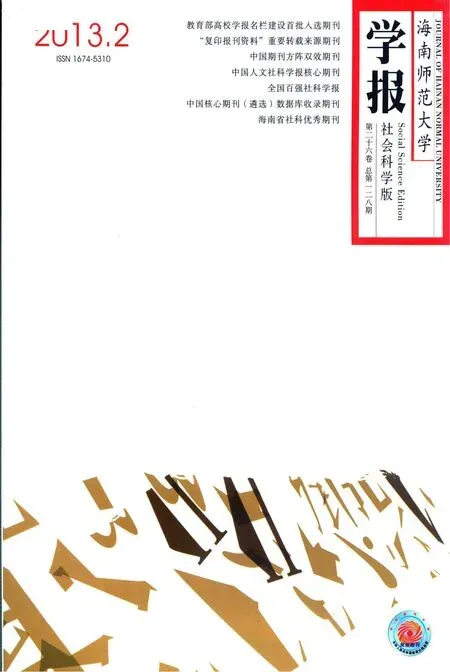批判意识与悲剧精神——重读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
李海音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成书于1991年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是洪子诚从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给北大学生讲授“当代文学”课程的讲稿中整理而来。该书从文学内部来对80年代纷杂的文学现象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进行了清理,在肯定80年代个别文学思潮的社会和政治批判意义的同时,着重从文学史的角度揭示了其在艺术上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洪子诚认为,真正构成我们有可能创造出富于生命力的文学作品的基础的,主要与创造者的心灵、精神境界、艺术才能有关。这就意味着他对文学创作主体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有着高度重视,对其生存方式和精神结构有着浓厚的兴趣,对其创作姿态和自我意识有着严格的要求。
《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建构在“精神结构”和“文学传统”的问题框架上,分别对“感伤姿态”、“寻根趋向”、“忏悔意识”、“超越渴望”这四种创作心态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这涉及到对80年代文学中“感伤”倾向的批判,对“寻根文学”的反思,对“巴金式的忏悔”和“杨绛式的反思”的阐释,对试图脱离文学传统而渴望超越的心态和作家批判意识与悲剧精神的失望和希望等方面,指出“一个民族的健全的丰厚的文学传统,是建立在作家独立精神的持续性和艺术形式的积累的基础上的”。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洪子诚,对于重塑作家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的殷切期望,对于重建独立的文学传统的学科意识。
一
洪子诚对80年代文学中的“感伤”倾向的批判,是建立在他对恩斯特·卡西尔和苏珊·朗格的符号美学理论的继承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是基于他近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立场的,甚至可以说整本书都是基于这样的知识背景。他认为感伤主义,一方面因感情的泛滥和放纵而导致了思想的浅薄,另一方面忽视了艺术的“构型”而导致了艺术形式上的欠缺。他反对“文学是情感的表现和自然流露”的观点,反对把文学艺术看作是对人的感情的“复写”,认为艺术“既不是对物理事物的摹仿也不只是强烈感情的流溢。它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1]在他看来,对感情的体察、探索的程度越深入,他对感情的分析,控制的能力就越强;而放纵自己的情感,沉迷于其中,就难以对感情进行“反省”,因而也不可能有自我意识的真正醒觉。对由卢梭过分推崇情感而导致西方浪漫主义过分夸大感情在文学中作用的不满,对梁实秋等人极力反对创作的感伤、滥情倾向的回顾,主张文学中情感的理性与节制等,无不体现了洪子诚对白璧德文艺理论的倾心。
然而,洪子诚也意识到了“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80年代的作家们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和坎坷的遭际,若是要他们一开始就保持艺术创作所必需的平静心境,恐怕很难做到,也过于苛刻。所以,在舒婷、顾城、梁小斌等人充满“感伤”和“自怜”的诗歌中,他说他不仅不感到反感,有时会觉得可爱,表达了同情和理解。但他又说,理解并不就意味着必须和合理。一个批评家始终是铁面无私的,对于批评的对象始终不能放低要求。因为作家在坎坷的个人生活和错乱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完全具有自主性,他可以选择陷入弱者自怜的浸淫之中,但也可以达到对社会、对世界认知的深化,生命体验取得进展,意识到生命的悲剧性质,使精神境界有所超越。这就取决于作家是否具有那种“自我意识”。洪子诚所要求的作家的“自我意识”在这里已经初见端倪,即对人生的悲剧意识,并化悲痛为创作的全部力量。这就需要一个艺术家应当具有一种超越的精神气质。
二
跟“感伤姿态”相比,洪子诚对于80年代文学中的“寻根趋向”的批判态度显得不那么鲜明。虽然他观察到:寻根运动不过是80年代沸沸扬扬的“文化热”的一个组成部分;“寻根”只是在东西方文化、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的比较、碰撞所产生的惶惑、痛苦中做出的反应与采取的对策的一种;作家们不是在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经验的层面上来考虑精神归宿的问题,他们最有力的动机主要还不是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他们感受最深的仍然只是发生在当代的现实问题;甚至某些“寻根”作家对传统文化所持的不过是一种“新鲜感”和一时激情;但是,在面对“寻根”思潮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时他却表现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也对他们的艺术成就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或许是因为,这种精神探索和精神重建的努力本身就足以让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意识的洪子诚感到些许宽慰,况且“寻根”的提出是中国当代作家有关“文学重建”的努力所采取的一个有意识的步骤,而80年代文学寻根的潮流在相当程度上重复了“五四”时期的启蒙者的思维和感知方式。洪子诚在回应李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没有彻底贯彻知识学立场时,回答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于启蒙主义的‘信仰’和对它在现实中的意义,我并不愿轻易放弃;即使在启蒙理性从为问题提供解答,到转化为问题本身的90年代,也是如此。”[2]由此可见洪子诚所秉持的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寻根文学所表现出的暧昧态度。
洪子诚对寻根文学的同情和理解还在于,在80年代,“精神失落”不仅来自于对“现代化”将要造成的“文化后果”的忧虑,而且来自于“文革”等现实的社会政治因素。这两方面的压力,加重了作家的精神探索的负担。因此,寻根作家们寻找精神归宿的努力便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更确切地说是悲壮色彩。从“超越渴望”一章可以看出,这正是洪子诚期望的一个现代作家所要达到的一种精神状态——由现实与理想、理性与感情、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与矛盾带来的内心痛苦和忧伤,因为只有精神上的受难者才能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而他们的确也是在关心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关怀人们遇到的心灵冲突,探索摆脱矛盾的出路,虽然这不过是给面对重重矛盾、陷于精神困境中的现代人以心理的、情感的补偿,但也值得暗自庆幸了。洪子诚对批评对象的这种显得多少有点苛刻的要求和期望,如前所指出的,是对作家“自我意识”(悲剧精神)的再次重申,也体现了他自己的人生观和文艺立场:人生始终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命运就是一出悲剧,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应该也能够看到生命的这一真实面目。
三
80年代文学有一个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十年“文革”之后的知识分子的“反思”,或者如洪子诚所说的“忏悔”与“自审”,围绕着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来展开。透过历史的纵深来展开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分析,发现当代文学的思想、艺术、问题等与传统的连续性,从而更深刻地进行认识和反思,这是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特色,这也是一个文学史家进行文学批评时的优势。洪子诚并不认为一个时期的文学跟上一时期有什么必然的断裂,即使是80年代这样的看似全然不同面貌的“新时期文学”也是脱离不了文学的过去的。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的历史形态进行回顾和阐释,洪子诚指出,这种自审的意识是历史的延续,是“五四”以来思想界和文学界连绵不断的主题。在对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诗人们的“忏悔”形态的分析中,洪子诚发现了“忏悔”的两个主题:一是由作家的艺术生产来表达的“启蒙”或“救亡”,一是作家直接对自己灵魂“阴暗面”的抉剔解剖,由作家对自己的思想和人生道路作直接讲述。“启蒙”的意识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从30年代开始,“救亡”便压抑了“启蒙”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迫切性,到了五六十年代则彻底转向了后一种。对洪子诚来说,“忏悔”的意义和价值并非始终是好的崇高的,其实,他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独立性的丧失正是从30年代开始的。而他对于“启蒙主义”的信仰的坚定态度,正是由于他对于知识分子精神独立性的高度重视。
而80年代文学中的“忏悔”主题和作家们的“忏悔”意识,并非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反思文学”的主题,也并非我们惯常以为的有多么地深刻,或者似乎都拧着一股劲儿在一根绳子上出力。洪子诚告诉我们,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甚至是更糟糕。洪子诚清理出了三种“忏悔”的姿态:一、虚构英雄以回避自剖;二、说出“我不是堂吉诃德”式的从“英雄”幻觉中走出的清醒者;三、以英雄姿态进行自审。
第一种实际上算不上真正的反思,也达不到反思所需要的深度,它“不过是为了给形象曾受糟蹋的知识分子恢复‘本来’的面目,也是为了博取人们的同情,在自怜自爱中陷入感伤主义”。第二种以杨绛为代表,是知识分子面对人生的痛苦遭遇后走向淡然、宁静的姿态,认为“如果真要救人、救国的话,最好是先考虑救出自己,挽救在各种压力下已经失去的本性”。对后一种,洪子诚姑且不论,其批评的姿态依赖于对“巴金式的忏悔”的分析和理解。
洪子诚重点剖析了以巴金为代表的第三种。他指出,与四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经过反省明确自己的根本性弱点,而走向模糊自己的个性特征和“自我”的精神独立性不同,80年代的自省通过“我是谁”的角色辨认,表达了对消失的个性、自由意志、独立思维精神的信仰和召唤。其实“我是谁”在巴金他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就是“文人英雄”。巴金的《随想录》展示了一个“战士”的姿态,表现了作家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学所意识到的责任。洪子诚对巴金显然是充满着感动和敬畏的,重要的一点在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责任问题,“像巴金这样的严格自省的写作者,确实还不很多见”,[3]虽然他活得过分沉重,但却活得庄严。
然而,批评家并非止于同情和理解,他对于《随想录》艺术上的缺陷同样给予了否定,因为对于一个艺术家和作家来说,艺术创造本身就是目的。而在他看来,《随想录》最大的不足,则是关于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本身的问题。一方面,巴金把自己在“文革”中的“罪行”看作是对自己良知的违背,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忏悔意识,正如邓晓芒在《灵之舞》中指出的:“不是把自己的罪过视为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看作与自己的意志和‘本心’相违背的结果。”[4]洪子诚显然对此也有不满,虽然他的批判姿态比较含糊,也没有进行深入分析,但他指出“他们并非游离、自外于这部社会机器的转动运作,而是参与推动它的运动”,这种认识其实相当具有意义,也击中了要害。巴金并非是迫于生存等压力而违心地犯下了不可谅解的罪行,实际上他是清醒的是有意识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知识分子)早已丧失了精神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由于巴金仍坚持一种人的理性力量能控制一切、实现一切的神话,并在这“神话”受到一定摧毁时感到难以置信而惊愕和痛苦,这阻挡了他的体验、探究的向前延伸。联系到洪子诚对感伤主义的批判,而这里又对理性产生质疑,我们不禁感叹:这种徘徊游移于同情、纪律和选择之间,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调和,而不是简单地择取一端而守之的姿态,不正是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立场的坚定吗?①关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参见段怀清:《梁实秋与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
但洪子诚对巴金这个人的批评显然有失公正了。如果始终把巴金看作是艺术家,并认为他的反思必须承担文学的使命,这本身就是批评的误区。《随想录》是巴金作为一个人而不是艺术家对过去的反思,既然巴金主观上并没有文学创作的意识,并不在乎其在艺术上存在的缺陷,那就无所谓人生与艺术的冲突问题,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对理性力量的坚定信仰并不妨碍他的艺术创作。要知道,并非所有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思想和情感都是文学(艺术)作品。洪子诚否定了“文学是情感的自然流露”,难道没意识到文学也并非历史事实的载体吗?把《忏悔录》作为80年代“反思”的文学现象的代表来进行剖析并不一定正确,更不见得是研究视角的独特。其实,洪子诚对作家(艺术家)姿态进行的反思与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往往混淆不清,这也就能解释为何他在巴金与杨绛之间态度并不鲜明的问题。
实际上,对三种“忏悔”姿态的分析,是批评家本人对自己的一次深刻的反省和内心探索,因此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他在努力要以旁观者的清醒角色来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的同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犹疑、苦涩和同情。但无论如何,他必须从中选择一种姿态,这恐怕也是所有知识分子接受良心拷问时不能逃避的抉择。他不禁问道:是否所有的作家都应承担这样的责任(巴金式的)?作为作家,又是否能承担这样的责任?是否只有在充当作家的同时又投身现实行动,并以文学作为行动的“武器”,才是一个“完全”的,值得充分肯定的作家?显然,洪子诚对于维护知识分子“美好”形象的自怜自爱式的“忏悔”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以英雄姿态进行自审的巴金式的“忏悔”是持怀疑态度的,或许走出英雄幻觉的杨绛式的“忏悔”才是一种较好的选择,虽然有点无奈。如果时代环境不允许,他想做的是朱自清等作家一样的知识分子: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更清醒认识到自己的特点(包括弱点),在这样的基础上,寻找与社会、与时代可能建立的联系的新方式;潜心于写作,潜心于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并不完全是对学术研究等特别沉迷,其动机也有着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执着。洪子诚颇有点以此自况的意味,既然做不了“英雄”、“战士”,便做一个身在江湖心在庙堂的学者。这不依然是传统文人知识分子的心态吗?他们对社会的责任不是把身体投入现实的洪流,而是用心灵去观察,用艺术去反思,摆脱不掉的依然是那种“文人英雄”的意识,这跟洪子诚的“启蒙主义”的信仰立场是分不开的。
四
“超越渴望”是80年代文学界的一个共同的心态,他们有着这样一种普遍性的意识:不满足现状的进取精神,与害怕落伍、惧怕被人讥为浅薄、担心只是拾人余唾的惶恐,对文学作品的生命力的短暂充满忧虑。洪子诚认为,80年代作家们的突破与超越并非只是“走向世界”的现实因素,其基点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学。这再次印证了洪子诚强烈的历史意识: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审视不能脱离我们曾有的文学传统。80年代作家的起步正是建立在对六七十年代文学中的“写真实”与“干预生活”两个口号的反思和清理的基础上,“在人生道路上体验了许多的悲剧之后,当代作家终于达到了这样的对‘悲剧’肯定的审美,并在美学风格的层面上肯定了作家坚持其批判意识的合理性。”但这种超越的渴望过于急躁的一点,就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并不够,导致了人们在“跨越”这一曾长期横阻在中国作家面前的障碍时,只愿意用自己的作品,或用一种情绪化的粗浅语言来加以解决。这种剖析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80年代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洪子诚指出,80年代的作家们要改变在创作模式上的雷同化趋势,要达到艺术的深度和特殊价值,需要拓展思想的视镜。许多作家所坚持的依然是已经日益狭窄和困窘的政治视角,这导致了他们无法扩大视镜,增加体验的深度。不要以为过去所发生的失误、曲折、坎坷,只是社会历史和人生过程的链条中一个偶然、短暂的段落,也不要以为“它终将会成为过去”。在这里,批评家并非只是对历史道路做出的反思,更多的还是对作家的内心世界提出的一种要求。他最怕的是:当作家们的这种遭遇结束、命运得到改善,获得声誉上、地位上、物质上的各种补偿之后,很快就使原先空虚、惶惶无着的心灵获得满足,原来所有的批判意识与悲剧精神便会消解而过渡到圆满心态。洪子诚虽然并不认为过去的苦难就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精神财富,但的确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把它变成一笔精神财富,要求作家始终要有批判意识和悲剧精神,抗拒对历史的遗忘,这种心态又颇有点巴金式的悲壮。经历了各种社会政治动荡,尤其是“文革”的灾难,为何中国始终没有出现“新的《神曲》”,就是因为作家们没有“永恒痛苦”的意识,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悲剧精神。
洪子诚引用余光中的话:“敢在时间里自焚,必在永恒里结晶”,指出一个作家只有拥有对现实人生的“苦难”的体验,并有所孕育和升华,才会有“不朽”的永恒。因此,他要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经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既然“他对精神,对人的心灵,对世界前途的思考和探索是永不停歇的”,而现实生活的一切与生活理想之间始终存在着距离和冲突,那么他就要接受这样的命运,勇敢地在时间里自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定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灵魂的骚动和精神探求的不安构成了他的精神结构。这种对艺术家的苛刻要求,何尝又不是批评家本人内心世界的反映呢?其实,洪子诚本人才是真正的苦行僧,是他自己眼中的“真正的艺术家”。然而,他似乎是无怨无悔的。虽然“精神的人的道路伸向远方,但并非伸向幸福”。[5]但在艺术里,他可以寻找到灵魂归属的位置,他的灵性可以在这里得到发挥,心灵自由在这里得到确立,生存个体可以在这里从暂时性的生存体制中得到解脱。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洪子诚虽然给中国作家的内疾开出了药方,也给中国文学传统的重建指明了路向,但具有历史意识的他也无不透露出一种不太乐观的情绪。他看到,20世纪以来,中国很大一部分作家在人格上是分裂的: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努力摆脱精神上的依附地位,他们富于使命感,代表着社会良心,企图以自己的思想和人格给社会以影响和启示;但作为艺术家,他们又实际上走在朝着建立精神独立地位相逆的道路上。[6]这种自我矛盾固然与中国20世纪强大的社会现实压力有关,但更多源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性格,正如洪子诚在《作家意识与自我姿态》中分析的他们具有强烈的“文人英雄意识”,而这种传统心态并没有那么容易就能转变。但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重建,失望归失望,没有道理不抱着一种殷切希望。
[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86-187.
[2] 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M]//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8.
[3] 洪子诚.我的“巴金阅读史”[N].中华读书报:2005-11-18.
[4] 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46.
[5] 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16.
[6] 洪子诚.文学传统与作家的精神地位[J].文学自由谈,19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