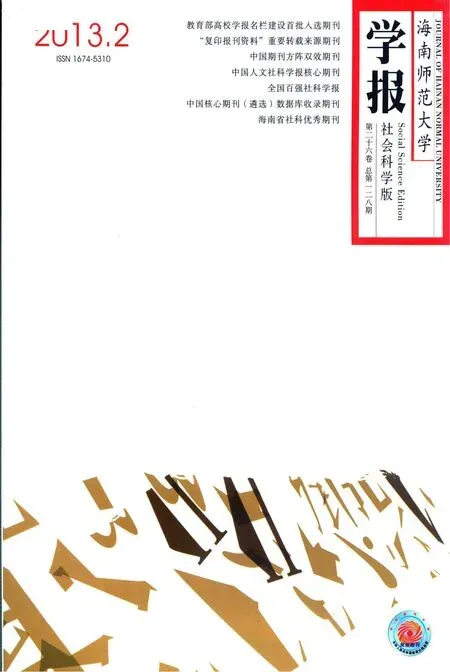对“革命”与“叙述”的重新定位——评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
刘卫东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1949-1966年的文学因为与政治关系密切而曾经饱受诟病,晚近的研究者大都避开这一话题,切入“政治话语/日常生活”之间的裂隙,寻找“日常生活”中的颠覆因素,论证“政治话语”的空洞乏力,从而给予1949-1966年文学新的“正当性”。“再解读”就是这一思路。我赞同“再解读”的工作,因为“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被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和暴力”[1]。结果是,1949-1966年文学中其他的质素被挖掘放大,此前政治话语控制下的叙述模式因此破产。就此而言,“再解读”功不可没,但是,我认为这对1949-1966年文学来说只是一种“搭救”,充其量只能证明“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并未使之获得自身独特的历史地位。蔡翔先生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以下简称《革命/叙述》)中的研究,恰是对1949-1966年文学的重新“定位”。我以为,蔡翔的工作不仅丰富、推进了1949-1966年文学研究的发展,还带来了方法论上具有启发意义的探索。蔡翔的研究涉及到“文学”和“文化”及其“想象”,为了表述方便,下文只用“文学”指代蔡翔的研究范畴。
一
蔡翔的研究是从为1949-1966年文学“正名”开始的,或者说,这是他的立场。我们学界现在的问题是有学问,没立场;即便有,也并不清晰。汪晖曾经注意到中国学界对60年代的“沉默”:“这个沉默不仅是对60年代的激进思想、政治实践的拒绝,即不仅是对作为中国之‘60年代’的标志的‘文化大革命’的拒绝,而且在不同语境中也隐含了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的怀疑以至否定。”[2]虽然汪晖并非专指1949-1966,但是他描述的学界“拒绝”的立场大致不错。相对于汪晖所谓的“沉默”,研究1949-1966年文学的有的学者采取了“犹豫不决”①洪子诚巧妙地搁置了意识形态争议,以“考古学”的方式“还原”了当代文学发生的某些现场。参见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的立场。与以往1949-1966年文学研究者将态度定位为“暧昧”(这一视角已经有悖于“否定”),换取“零度”和“客观”视角不同,蔡翔的研究建立在对中国革命“正当性”的“重新”论述上,当然,他不是回到既定的阶级斗争框架下,而是基于“弱者的反抗”的“正当性”(这个问题下文讨论)。蔡翔持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如此高调,无疑也因此成为标榜“客观”的学院派中的另类。蔡翔对此有清醒认识,他认为“当代文学六十年,实际已经成为一个战场”,“在自欺欺人的‘去政治化’的喧嚣声中,却是更为强劲的政治性诉求,只是,有的人愿意承认,有的人不愿意承认罢了。”[3]1我不太同意“更为强劲”的说法,因为我认为其实政治意识只是在某个时候或显或隐的问题,但是对“去政治化”实则是个幌子的判断表示认同。其实任何学者都有自己的立场,而且不尽相同,刻意“去政治化”,回避或遮蔽立场,往往会模糊讨论的问题的理路,反而会损害问题提出和展开的“正当性”。我以为,学者和思想家的区别就在于:学者不愿或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思想家相反。萨义德就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4],他的要求确实很高。
蔡翔站在“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立场论述1949-1966年文学,不仅意味在当前语境下“逆向思维”,而且还要清理复杂的理论历史与现场。蔡翔或许明白,自己的研究是否有价值,就在于对此问题的新的诠释。对于“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毛泽东有过耳熟能详的论述:“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5]48毛泽东的经典论述是从历史宏观发展的视角建立中国革命正当性的。蔡翔避开了这一视角,在书的导论中开宗明义,强调秉持一种“历史的态度”:“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这样一种‘历史态度’,即对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强调——这一正当性正是建立在对‘弱者的反抗’的基础之上,它要求把劳动,也把劳动者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我想,我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一现代的‘造反行为’解释成一种非正当的政治诉求。”[3]2在这里,蔡翔试图建立一个“弱者”的视角,而这是此前研究者鲜有提及的。蔡翔应该知道,他或许无力建立一个“新的”叙述框架,说明“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并且把文学、文化想象纳入其中,成为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我没有看到蔡翔对体系的热衷,但是,却能够感受到他对“弱者”命运的关怀。回溯蔡翔的研究经历不难发现,他对“弱者”的关怀不是兴之所至,而是带有历史关联性。蔡翔是较早关注现实底层命运的学者。1996年,他就发表了带有强烈理想主义气质的《底层》一文,认为“底层仍然在贫穷中挣扎,平等和公平仍然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6]。相对于此后更多关注底层的作家和理论家,我确信蔡翔不是投机。由“底层”问题到“弱者的反抗”,蔡翔的论述重心显然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蔡翔《革命/叙述》的工作是他对现实关注的理论延续。
“弱者的反抗”,似乎天生具有“正当性”。其实关于“弱者的反抗”,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有提及:“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5]16当然,毛泽东是在申明农民运动的必要性的语境中论述这个问题的,他认为农民的反抗“完全是对的”。毛泽东并未给出理由。蔡翔谈论“正当性”的时候并未做出解释,但是可以看到他是在施特劳斯“自然正当”即“什么东西本然地(by nature)就是对的”[7]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蔡翔未在此多做纠缠显然出自一种学术策略,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陷入概念的泥淖,但是,也留下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我想,我们有必要就此问题再分析一下。我以为,蔡翔把“弱者的反抗”指认为“正当”,且没有预设前提条件,无疑忽视了对“弱者”的分析。在蔡翔的论述中,“弱者”是指劳动异化状态中的劳动者,这个指认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与国际歌中“饥寒交迫的奴隶”形成互文,他们被迫劳动却失去基本权利,因此他们的反抗就获得了正当性。而就此而言,在道德伦理的范畴内,“弱者的反抗”(或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具有无可争议的“正当性”。我同意蔡翔的这个分析,也认同此时的“弱者的反抗”的正当性,但是,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如何获得?蔡翔并未回答,或者在他看来这并非是一个问题,因为,革命叙事讲的就是用暴力获得正当性的故事,不过,这里的暴力被赋予了正当性。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了这样一幕: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中,地主李如珍被农民活活打死,死相惨不忍睹。县长委婉地批评农民们说:“现在的法律,再大的罪也只是个枪决;那样活活打死,就太,太不文明了。”农民的逻辑是:“县长!他们当日在庙里杀人的时候,比这残忍得多。”[8]类似“弱者复仇”(在“复仇”时弱者明显转变为关系中“强者”)的场景在现代文学中屡屡出现。在复杂的情境中,可以看到,“弱者”在理直气壮的背后,暴露出了令人质疑的一面。问题出在哪里?我的看法是,“弱者的反抗”在理念上具有“正当性”,但是在实践中,“正当性”并非“弱者”的尚方宝剑,而是应该被限定在一定范畴内。一旦作为“弱者反抗”的理念转变为“弱者复仇”的革命,就会发生“弱者”和“强者”间的逆转,“正当性”也就无从谈起了。我以为,在这里,“弱者的反抗”转变为无序和盲目的冤冤相报,失去了正当性。我之所以这样判断,基于抛开“弱者的反抗”在伦理学上容易获得的大众情绪的支持,引入罗尔斯对正义的分析。在罗尔斯建立的正义论的体系中,没有使用“弱者”这一概念,而是使用了“最少受惠者”这一概念,并且强调“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样,他就始终站在“无知之幕”的立场上,不受具体历史语境的干扰。在罗尔斯看来,正是这种抽象的“正当性”,才是我们社会的“道德基础”。[9]我以为在此可以这样阐释罗尔斯的观点:“正当性”应当是建立在“无知之幕”上的抽象正义,是假定性的。相比而言,此前讨论的“弱者的反抗”的正当性恰是具体和形象的,带有即时性,因此,不能成为论述革命正当性的“基础”。因此,蔡翔所说的“历史的态度”,即对“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讨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不应将其绑定在“弱者的反抗”之上。
二
蔡翔并非站定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立场,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而是对革命的“正当性”也有所反思:“我们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对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强调上,相反,我可能更在意的,除了这一正当性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经验形态,还在于这一正当性又如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3]3蔡翔的这个说法多少让人联想到“左倾错误”这样对中国当代思想问题的反思。虽然我认为“正当性”相对的概念并非“无理性”,但是也想看到蔡翔是怎样在自己的范畴内论述“无理性”的,因为这已经是关于1949-1966年历史话语中的老生常谈。可以说,如何处理这个棘手问题是蔡翔重新解读1949-1966文学的关键所在。在这里,蔡翔进行了一个技术上的转换:他不是阐述“无理性”是什么,而是落脚到如何解释这个“无理性”。比如,关于国家现代化语境中的“合作化运动”,蔡翔说:“当‘集体劳动’被置放这样的语境之中,所谓的‘合作化运动’就获得了极其重要的现代性意义,这一意义事关未来,或者说,是在‘激进的、未来主义的目标下’所展开的一种想象,因此,‘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在这里被更多地赋予乌托邦的意义。也许,这一想象在其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并未获得预期的成果,但是,今天,我们却没有丝毫的权力嘲笑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一曾经蕴藏着巨大热情的乌托邦想象。”[3]49蔡翔的这段论述要从两方面分析。一、不可否认,1949-1966年文学是建立在一种乌托邦想象的基础上的。正如当年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所说:“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①《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见《人民日报》1958年12月19日。关于中国语境乌托邦的意义,一位西方学者说得非常到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一个前工业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各种冲动和人们的心理现象”,这是一种“被浪漫化了的,但却又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殇逝乡愁,并刺激出了平等主义乌托邦的未来梦幻。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被知识精英所独占,并被发展成为一种形式上的意识形态”[10]。我赞同这位学者的说法。因此,我以为,蔡翔强调“乌托邦意义”有很大意义,“乌托邦”作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争辩的正当性;二、蔡翔没有进一步分析的是,乌托邦一旦成为中国语境中的代表“现代性”的正当性,必然会暴露出它逻辑中暴力一面。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所提到的,绝大多数社会建构是“生长”出来的而非“设计”出来的,[11]而蔡翔所说的“集体运动”恰巧带有设计和强制因素,并成为《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艳阳天》等作品的主要冲突。问题的关键是,此时“弱者的反抗”失去了革命语境的支持,完全被宏大的乌托邦过程遮蔽,以至产生了这个过程中的“无理性”。我以为蔡翔对第二方面的“无理性”强调得不够。我们现在可以清晰认识到:1949-1966年文学的“创新”之处在于站在新的“现代性”的角度用新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现实和未来。这种“现代性”试图建立一种“正当性”,用乌托邦目标的实现来反对和削除人性中的问题,但是在此过程中采取了不适当的手段,因此损害了追求的“正当性”。因此,我们反对乌托邦,不应该反对它的理想,而是反对实现的方式,即采用集权和运动的方式。我以为,我们讨论乌托邦,应该把目的、手段和结果分开。我不以为“好心办坏事”能够博得同情,但是分析乌托邦必须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我感兴趣的恰是蔡翔打抱不平一样不断呼吁回到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而这种语境被“结果”所累,早已经无人问津了。
蔡翔在另一个表态性质的谈论“当下性”的场合中曾经说,要“寻找、召唤”“某个历史的亡灵”来“创造当下”。[12]他发表这个态度的时候,大概正是本书杀青的时间。如果说到“某个历史的亡灵”,我想至少蔡翔语境中的“劳动”应该算一个。“劳动”在当代思想中的地位不可谓不显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形成就是基于对“劳动”过程的分析和研究,他正是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13]。“劳动”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但是在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并不能看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举例子来说,有的文学史在论及闻捷的时候说,闻捷的诗歌是“爱情和劳动的赞歌”,但是“陷入了‘劳动至上主义’的泥坑”。[14]就算闻捷的诗歌表现了“劳动至上主义”,但是将其作为“泥坑”,显然出自对劳动本质的贬低。还有的文学史在论及闻捷的时候说:“在闻捷那里,受到赞美的爱情只有一种:那就是与劳动、社会主义建设、高尚的政治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情”,接着说,“这样的爱情观无疑是过于简单,甚至有功利之嫌了”。[15]浅尝辄止。这也是与劳动擦肩而过的例子。就我对目前通行的文学史的翻检,没有哪一个将1949-1966年的文学与“劳动”联系起来,更没有从劳动的本质解读文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代思想中,可以看到,“劳动”的“正当性”(!)经历了一个从神圣到消解的过程。蔡翔在自己的语境中赋予了劳动新的意义。在蔡翔看来,“劳动”问题非常重要:(劳动)“直接指向尊严,这一尊严不仅是个人的,更是阶级的,离开个人从属的阶级(或族群),空谈个人尊严,实际并无太大的意义。而在某一方面,中国革命同时也是这一尊严政治的实践过程,或者说,离开这一尊严政治的支持,中国革命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3]271蔡翔的这一表述不仅是对“劳动”这一概念的重新擦亮,更是基于对中国当代历史实践的“亲历”性把握。我以为,蔡翔本书的最大亮点就在于他对劳动与个人尊严问题的反思。作为1949-1966的现代性实践的主要遗产,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也越来越明显。大而言之,蔡翔关注到历史变迁中的个人,并站在他们的立场考量历史,无疑是新历史主义背景下的对当代历史重新叙述的实践;小而言之,蔡翔一以贯之同情、关注“底层”的命运,并试图寻找经济途径之外的解决之道,显示了学者的使命感与人间怀抱。我略感遗憾的地方在于,因为蔡翔只把“劳动”作为了他考察的一个方面,没有将其作为宏观把握1949-1966意识形态的关键词。我想,这与蔡翔关注的问题过于庞杂有关。
三
我们看到,蔡翔对这个被历史废弃的“未完成”的乌托邦大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前来做一次感喟世事的凭吊,而是在“坍塌”处反复考量,试图找到弥补的方式。在《革命/叙述》中,显而易见的一个特点是,蔡翔建立了文学文本和社会历史分析的互证关系,并且重点考察“想象”。我以为,蔡翔把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做了一个位置前移,相对于1949-1966年文学“是怎样”的尴尬,他着重考察的是1949-1966年文学“想怎样”,而这一点经常被“只看结果不看动机”的研究者忽略。蔡翔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宏观的构架,用当代社会学成果来对照1949-1966的文学描写,在相互参照中,厘清中国现代化追求中的诉求与冲突。甚至可以极端地说,这是一部蔡翔谈论当代政治的著作,文学成为了政治的“文化想象”,处于对照的地位。我觉得,在课题越小越好的现代学术制度氛围中,蔡翔能够拿出如此大的气魄,实在是一种抵押了自己辛苦积累起来的学术信誉的冒险。事实上,此前,还从未有人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做过这一工作。蔡翔当然意识到了某种危险,他在本书的后记中说:“我在写作中,尽量地在文学史和社会政治史之间建立某种互文的关系,这可能不是一种最好的研究模式,但对我来说,却是一种有用的研究方式。”[3]394其实,这样略带辩解的声明没有什么意义。一种模式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是否新颖或自己是否满意,要看它解决问题的能力。
改变研究1949-1966年文学的既定格局,必须要有原创的思想。我以为,蔡翔是一个对自己的问题有着“自觉”的学者。从他的表述能够看到问题如何被发现、剖析和解决到何种程度。有如此清晰学术方位感的学者,并不多见。蔡翔说:“我的写作略显庞杂,这是我有意为之。我想,我不可能始终在这个领域工作,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想法包括问题的提问方式,尽量地呈现出来。如果,这些想法和问题的提出,将来对一些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学者有所启发,并继续向前,甚至对我现在的工作形成挑战甚至颠覆,那么,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3]395我们讨论的问题不一定被解决,但至少应该是真问题。蔡翔做到了用自己的方式讨论自己的问题。
[1] 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代导言)[M]//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
[2]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M]//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5:1.
[3]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4]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17.
[5]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6] 蔡翔.底层[J].钟山,1996(5).
[7]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8.
[8]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M]//赵树理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72.
[9]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
[10] 〔美〕莫里斯·迈纳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张宁,陈铭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
[11] 〔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2.
[12] 蔡翔.如何面对文学史的解读[N].中华读书报,2009-09-16.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8.
[14] 金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19.
[15] 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