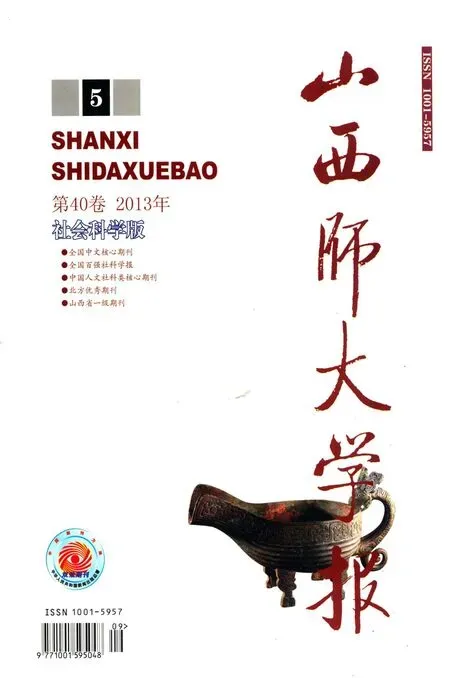茅盾与《文心雕龙》
——兼论中国现代文论与批评的“民族性”问题
权 绘 锦
(兰州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20)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论与批评的建构实质是以西方话语为范本的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此,必然导致对传统文论价值的颠覆与否定。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现代文论与批评又自有其“民族性”品质。无论哪一个流派或个人,也无论其秉承何种外来理论范式,又都程度不同地经过了中国化的过滤,因而保证了其并非“全盘西化”的产物,自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探讨现代文论与批评的“民族性”是个颇具挑战的课题。这不仅由于“民族性”本身是一个伴随文学实践而不断建构着的历史过程,还由于现代文论与批评固有的复杂性。现代批评家所受外来影响并非单一,同时,他们个性精神的张扬和自由开放的文化心态也决定了在文学观念、理论体系及批评话语上的千姿百态。正是这种影响源头的多元化和批评个性的丰富多样,再加上“民族性”本身的理论瓶颈,造成了探讨这一论题的难度。但并不意味着有理由绕开这一必须正视的问题,可以尝试的有效办法之一是对现代批评家与传统文论进行古今比较,通过对二者在理论话语、批评方法、审美理想诸方面的比较,寻绎其中的契合、一致与相通,使现代文论与批评的“民族性”品质得以凸显,并获得有说服力的论证。
茅盾是现代居主流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奠基者和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坚,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文心雕龙》是中古时代集大成的文论巨典,六朝之前的文学思想都在这里汇聚,后世诸多文学观念大都以此为源头。选取这二者为标本,对其中某些核心观念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或可为阐明现代文论与批评的“民族性”提供一条途径。
一、 过激批评与历史还原
与诸多现代文学大师一样,茅盾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他却对传统文论批评过激,多次否定《文心雕龙》。早在1922年他就说:“中国自来只有文学作品而没有文学评论;文学的定义,文学的技术,在中国都不曾有过系统的说明。”“《文心雕龙》之类,其实不是论文学,或文学技术的东西。”[1]156在《“文学批评”管见》中,他认为,《文心雕龙》只是“文体的主观定义罢了”[1]254。茅盾对《文心雕龙》的否定之偏颇显而易见。作为一部集大成的文论巨典,正如鲁迅所论,堪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相提并论[2]332。
首先,它是鲁迅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3]504的产物。至六朝,“文”的体式已极为丰富,“这就提出了一些需要在理论上加以探讨的问题:每一种文体,要不要有一种明确的目的,一种规范的写法,一种标准的体式?每一种新的技巧、新的表现形式的是非得失如何?等等”。[4]183文学体式的发展给文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素材,也提出了重大课题,需要概括与总结。《文心雕龙》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所论文体达三十三种,涉及名称、性质、渊源、发展、代表作家作品、体制特色及规格要求等。刘勰对这类问题的探讨深入而又自觉,可为后世楷模。
其次,《文心雕龙》中的文学观念趋于独立。刘勰时代,文学处在走向独立的过程,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引人关注。包括刘勰在内,时人尽管观念上还比较模糊,但已开始从各个方面探讨文学独有之特质。从《情采》对“情文”的强调,《丽辞》对骈偶的注重及“文笔之辨”,《声律》对声韵的研究,《夸饰》对艺术夸张的探讨,《比兴》对两种艺术手法的区别,《神思》对文艺心理的细绎,无不表明,在刘勰那里,纯文学观念正在滋生,正在从与学术著作和实用文章混同一体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实用功利观念正在淡化。刘勰对这些涉及文学根本的问题在理论上的探讨,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再次,《文心雕龙》是从理论内容到理论形态都最为完备的传统文论专著。全书五十篇,以“为文之用心”为核心,将文学本体论、文学本质论、文学形态论、文学功能论、文学心理论、创作过程论、文学分类论、文学批评论、文学风格论、作家修养论、文学技巧论、文学发展论等诸多范畴,熔铸为一系统整体,将此前文论中的基本概念网罗罄尽;同时,还将理论阐释与具体批评融为一体,以海纳百川式的气魄,全面总结了历代文学之经验教训,系统考察了此前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公允评价了历代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和现象,具有宏观审视和微观考察相结合的学术品格。
最后,《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影响不可忽视。它既是对齐梁之前文学思想的全面总结,也以其独立完整、博大精深的体系和为数众多、阐释精妙的范畴为后世发端。虽然在刘勰生前仅为沈约等少数名流所重,但随着唐代文化的繁荣,影响逐渐扩大。完全有理由说,《文心雕龙》是自隋唐至清末中国文论主要概念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来源,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贡献应充分肯定。
通过历史还原不难看出,《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必须肯定,茅盾的贬低与否定不外乎三重原因:一是传统文论与西方现代文论在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及话语形态上的差异。从现代眼光看,一千多年前的《文心雕龙》当然缺陷颇多,但这并不能成为苛责古人的理由。二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特有时代思维。因为传统文化过于强固,只有对之表现出过于激切的态度,才能达到对民族文化彻底改造之目的。这是“五四”以来激进知识分子共有的思维方式。三是为输入西方近现代文论张本。只有彻底颠覆传统,才能在废墟上重建现代民族文化体系,这是“五四”以来激进知识分子的共识。同理,只有贬低与否定传统文论,才能使西方现代文论为国人信服。因此,茅盾的批评并非个人见解,究其根源,实为“五四”以来激进主义思潮之反映。
二、 “作家论”美学与“知人论世”
《文心雕龙》论及作家近二百位,贯穿着刘勰“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历史意识、整体观念及“知人论世”的批评精神。“作家论”是茅盾文学批评的主要体式,是他对现代文学批评的重大贡献,也是现代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础。茅盾的“作家论”同样具有鲜明的历史纵深感与宏观性。同时,他还努力将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将作品评价和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作家思想倾向及其成因的分析融为一体,呈现出整体性特征。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继承,也是传统批评方法的延续,因而具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特质。
历史意识和整体观念是刘勰作家论最突出的美学特征,《辩骚》对屈原的评论堪称典范。两汉以来,对屈原众说纷纭。在刘勰看来,不论是刘安、王逸、汉宣帝及扬雄的赞誉,还是班固的贬责,都没能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入手,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刘勰正是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宏观角度展开的:“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这一评价高屋建瓴,大气包举,屈原既接续了《诗经》传统,又因对楚国政治黑暗之怨怼和改良政事之“壮志”,发言为诗,为情造文,再加上流放沅湘,仰观俯察,得“江山之助”,用惊人的天才,创作出了《离骚》。正如其“赞”所言:“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离骚》成为中国文学自《诗经》之后的另一个起点。据此,刘勰对屈原做了准确的历史定位:“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
刘勰还指出了屈原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汉赋实为《楚辞》之流变:“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赋家皆受惠于屈原:“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汉之后,其影响并未消失,延续至六朝。刘勰还指出,屈原对后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后人对其影响的接受因人而异:“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如此各取一端,显然不可能得屈原之精髓。为此,刘勰又提出了学习屈原的正确方法:“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劾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
与刘勰一样,茅盾的作家论也从文学发展入手,既溯其源流,又寻绎其影响,既阐明作家个人的创造性贡献,又在民族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中准确定位,具有历史纵深感和整体宏观性。在《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一文中,茅盾首先从19世纪后半期整个世界文学发展趋势立论,认为从托尔斯泰开始,俄国文学勃兴,其势“竟直逼欧洲向来文艺思想而变之,且浸浸欲逼全世界之思想而变之”。此后五十余年,“实托尔斯泰与其同时文豪之时代也”。[5]14接着又指出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渊源。在他看来,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俄国文学与古希腊相似,而托尔斯泰及《战争与和平》主要受荷马影响,在近代文人中独得荷马之“真趣”[5] 16。最后,茅盾也论述了托尔斯泰对后世的影响,尤在思想与社会革命方面,必将风靡全球。[5] 35茅盾不仅厘清了托尔斯泰思想艺术之渊源,也从19世纪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整体层面肯定了其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显示了茅盾作家论的宏阔视野和高远史识。此后,不论评价肖伯纳等外国作家,还是评价鲁迅等中国作家,历史意识和整体观念都贯穿其中,成为现代社会历史批评之楷模。
从另一方面看,刘勰与茅盾的作家论都延续了传统“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知人论世”强调作品与作家及社会的有机联系,要求读者在这种有机联系中理解作品。所谓“知人”,即要了解作家的家世、经历、个性、才情与品德;作家不可能脱离时代,外在的社会生活、时代背景及创作环境又会影响作家,所以,还须“论世”。只有将这相辅相成的二者紧密联系,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
“知人论世”作为一种具有民族特征和源远流长历史传统的批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心雕龙5时序》对“建安文学”之评论极为精当:“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首先指出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和文人的经历及遭遇。由于曹氏父子爱好文学,善于创作,且尊重文士,诸多文士前来投奔,集结为邺下文人集团,出现了文学之繁盛。其次,建安文人在经过这一番社会历史与个人生活的巨大动荡后,虽整日过着饮宴、咏诗、谈艺的悠闲生活,但其创作却透露着慷慨悲凉之底色,使整个建安文学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最后,刘勰还指出,建安文学之所以有如此风格,一方面在于因社会长期动乱而来的时代风气衰败和人民怨恨,建安文人不能不受此影响;另一方面,建安文人情志深远,因而笔力充沛,所以写得慷慨激昂,富有气势。刘勰不仅将建安文人及其创作与东汉末年特殊的社会背景及其变迁联系起来,也将建安文人的个人经历及由此形成的思想情感特征作为评价建安文学的有效视角,既“论世”,又“知人”,从二者的有机联系中揭示了建安文学的总体面貌和特征,为“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作家论中的成功运用树立了典范。
茅盾的作家论一方面受丹纳等西方理论家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对“知人论世”传统的继承。茅盾认为,评论作家首先要“知人”:“我相信文学批评的对象至少也要是一个作家的全体,……在一篇作品里决不能捉摸着整个作家。”[1]275其次,还要能“论世”:“文学批评者不但对于文学有彻底的研究,广博的知识,还需了解时代思潮。如果没有这样的素养便批评,结果反引人进了迷途了。”[1]125此外,“做一个文学理论家、文艺批评家的话,书本的知识当然是很必要的”,但“还是不够的。他还要研究社会经济的情况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文学就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6]1159。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论后,茅盾将“知人论世”与阶级分析相结合,形成了其作家论的基本模式。其中,《冰心论》可谓代表。茅盾指出,冰心最初的“问题小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她所关注的是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问题。但冰心的个性又使她不可能正视现实的丑恶或走向极端。因而,她笔下的人物都是“软脊骨的好人”。冰心还试图给那令她痛苦的丑恶现实搽上所谓“爱的哲学”,结果是“诗化”了现实。冰心的“问题小说”之所以从关注现实,提出问题,企图给出答案,转向逃避现实,“诗化”现实,关键在于其“中庸思想”:“她那不偏不激的中庸思想使她的解答等于不解答,末了,她只好从‘问题’面前逃走了。”[1]154而这一过程是“五四”时期众多具有正义感而又孱弱的青年人共有的经验,冰心只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茅盾认为,将冰心的“中庸思想”和“爱的哲学”仅归结于基督教和泰戈尔的影响并不完全,还应包括其家庭背景、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冰心出身于生活优裕的仕宦之家,父亲温和风雅,母亲知书宽厚。从幼儿起,冰心即随父母孤处海边。正是这半新不旧的家庭,培养了冰心的中庸思想;正是这温和风雅的父母与和平时期的海边生活,形成了冰心以歌颂母爱和大自然为主题的“爱的哲学”;而孤寂的成长经历和喜欢沉思的个性又使她的“爱的哲学”偏向神秘主义;生活经验的贫乏及视野的狭窄又使冰心将社会看得极单纯,无非是“爱”与“憎”的交织。最终,是“爱”说服了“憎”[1]157。
可见,茅盾作家论体现出的美学思想和批评方法与刘勰相当一致。由此虽然并不能得出茅盾受《文心雕龙》直接影响的结论,但至少可以证明,在中国文论和批评的古今演变中,传统美学精神仍发挥着潜在影响,因而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三、“真实”的独特内涵及其功能
因受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理想等制约,中国文学中“真实”的内涵与西方有着本质区别。先秦以降,中国文论关于“真实”的论述大多琐碎而模糊。至《文心雕龙》,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始系统而清晰,有所发展,并影响后世。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真实”观被纳入了西方及俄苏文论轨道,形成了与本民族传统并不完全相同的新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真实”观就没有了借鉴的必要和继承的价值,也不意味着现代文论在建构自己的“真实”观时,对传统完全弃之不顾。相反,在包括鲁迅、茅盾、李健吾、胡风等诸多现实主义文论和批评家那里,仍然可以看到对传统观念有条件的吸收和择取。正是这有限的吸收和择取,使其与西方和俄苏理论有别。
“真实”是茅盾孜孜不倦的美学追求,也是其文艺思想之核心。以往的研究大多强调西方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其与传统文艺美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与他“要使东西洋文学行个结婚礼,产出一种东洋的新文艺”[1] 1的新文学建设理想相一致,茅盾也是在广泛吸收西方和俄苏理论的基础上,继承本民族文艺美学传统,自觉融合二者长处,建构其现实主义文论体系的。这使其既具有崭新的时代意义和个人特色,也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首先,以“真诚”为本,认为文学的“真实”在于主客体统一是传统文论一大核心。抒情言志是中国文学之主流,强调情感的真实和态度的真诚乃其固有传统。在《情采》中,刘勰明确提出“为情造文”,并以此为标准,纵论古今文学:《诗经》伟大,在于其为“情文”,在于其真实,在于其能真诚地抒情言志;而后世作者“为文而造情”,只图文采华艳,了无真情实感,态度也不真诚,当然每况愈下。在《物色》中,刘勰还提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学的真实既在于主体的真情实感,也在于对客体的逼真描绘。只有主客体二者统一,才能达到“情貌无遗”之真实境界。刘勰这一观点,后世文论既有所继承,也有发展,成为传统文论极具民族特征的遗产。
受自然主义影响,茅盾早期“真实”观的核心是“实地观察”和“客观描写”[1] 271。不久,他就认识到过分推崇客观之弊,转而强调主客统一:“一切‘人为的艺术品’之创造,都经过一定的过程:社会人生种种色相通过了作家的主观作用(爱憎,取舍,解释,褒贬),而后再现出来,依靠形象化的手法,成为某一文艺的式样。”[7]552茅盾同样认为,“真诚”是“真实”的前提,作家应当“心里怎样想,口里就怎样说。老老实实,不可欺人”[1]271。他还呼吁,作家应从真诚出发,以自己的“血”和“泪”,创作出反映现实人生的“血”和“泪”的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真实感人的“真文学”,才能进而指导人生。[1]11
其次,将“真”与“美”统一起来,视“真”为“美”之基础,乃传统文艺美学之一大关键。刘勰在继承前人基础上,多次论述之。如《征圣》中有所谓“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即内容的真实与丰富是形式完美的前提。《宗经》中所谓“六义”,也是对“美”与“真”的辩证理解。
茅盾对“真”与“美”之关系的概括极其精确:“‘美’‘好’是真实。”[1]13茅盾对文学的评价是以“真”为主,以“真”为“美”的基础,强调二者的统一。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新旧文学中割裂“真”与“美”联系的倾向进行批评:旧文学有两种恶劣倾向,皆因缺乏“真”而不“美”:一是甘为帝王弄臣者歌功颂德的东西,因脱离时代,与现实隔绝,毫无真实性可言,自然与美无关;一是以游戏态度将文学视为消遣者,更是毫无价值。而新文学中“为艺术而艺术”者,因割裂了文学与生活真实之关系,将会对新文学发展造成危害。[1]278不论是对旧文学的批评,还是对新文学的警告,都体现了他以真为主,强调真与美统一的基本观点。
最后,把文学之“真”视为发挥“善”之功用的源泉,是传统文艺美学一大特色。孔子曾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情欲信,辞欲巧”。即言论须有真实内容和真挚情感,加之优美的形式,才能说服别人或传之久远。刘勰将这一基本原则贯穿《文心雕龙》始终,如《明诗》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说,诗要抒发真情实感,此为感动读者的先决条件。
茅盾主张文学“为人生”。“为人生”的文学就是启蒙的文学,之所以能唤醒民众,关键在于“真”,是“真”赋予了其力量。他抨击旧文学的“大团圆”只能造成瞒和骗的文学,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1]272因此,茅盾强调新文学要表现人生“真的普遍性”和“真的特殊性”,使人们“去接触现代的罪恶”[1] 324。只有如此,才会激发人们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唤醒人们改良人生、变革社会的热情和信心。茅盾这一观点对新文学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其实,不仅茅盾及其“真实”观,众多现代批评家都是努力糅合东西方美学之优长,遵循既符合民族传统,又能体现时代意义的美学原则来构建各自理论和批评体系的。由此,现代文论与批评呈现出“现代性”与“民族性”交辉的奇异光彩。
[1] 茅盾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 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 茅盾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 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7] 茅盾.茅盾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