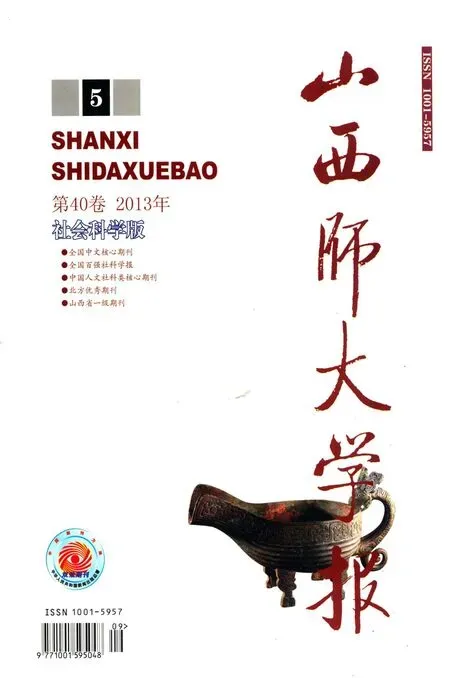从“天命”到“道法”
——黄老道家和先秦政治话语的转变
王 海 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 陕西 杨凌 712100)
在政治哲学视域中,先秦儒、道之争实为两家“治道”之争。道家中的黄老一派继承老子的政治哲学并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他们认为“无为而治”的实质即“道治”,“道治”的具体化即“法治”,据此他们构建了一个以“道法”为标志的“治道”模式,推动了先秦政治话语从“天命”到“道法”的转移。
一、从“天命”到“天道”:“道”的话语的滋长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言说方式的转变往往是思维方式发生变化的外在征兆。从西周末年开始,作为传统政治之支撑的天命论逐渐崩溃,这一过程反映到政治话语上就是天的神性的隐退和“道”的话语的滋长。从“天命”到“天道”,虽只一字之异,却蕴含着思想史上的重大转进。在天命论传统中,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既是自然界秩序的来源,也是人间政治秩序的决定者,这是一种典型的宗教神学政治论的思维方式。天作为至上的所在,是人崇祀、敬畏的对象。与天相比,人至为渺小,试图去认识、把握天那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僭越。这就是所谓的“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语在先秦早期文献中多见,《列子·仲尼篇》载小儿所歌《康衢歌》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大雅·皇矣》亦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可见此语由来甚早,正是早期宗教神学笼罩下,人对于天的敬畏的写照。。识与知是人类理性能力的运用,但在崇高的上帝面前,人类的理性微不足道,只能被动地“顺帝之则”。
“道”的本意为道路,引申为有规律之意。规律是人可以运用理性能力去认识和掌握的。“天道”概念的出现表明人对于天已不仅是敬畏,而是试图去认识天、掌握其运行规律。尽管在中国思想中,天的多重含义从来就没有完全剥离,但在“天道”话语系统中“天”的意义和天命论话语系统中的“天”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陈来认为,春秋时代的“天道”观念,略有三义:第一种是宗教的命运式的理解;第二种是继承周书中的道德之天的用法;第三种就是对“天道”的自然主义的理解。[1]64而这三种意义又“来自于两条线索,一是人文主义,一是自然主义”。[1]61这两条线索都与传统的天命论相去甚远。郑开认为:“‘天德’双关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Laws of nature)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然法(Natural laws)。”*参见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代思想史》,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34页。郑开认为:“殷周以来常说的‘天理’、‘天性’、‘天志’、‘天行’、‘天运’、‘天则’、‘天工’、‘天常’、‘天命’、‘天德’等等,都是天命和天道的同义语,这些词所折射的观念是:自然过程中的秩序和人类社会中的秩序都出自天命的赋予。”(同上书,280页)此处的论述和他关于“‘天德’双关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Laws of nature)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然法(Natural laws)”的论述之间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本文认为天理、天性、天则、天常、天德等概念与天道几乎是同义语,天志则和天命的意义更为接近。如果我们把这里的“天德”换成“天道”,那么这一论述所揭示的正是“天道”的两重含义。“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泛指一切自然事物的运行规律,在旧天命传统下,某些不正常的自然现象往往被看作上帝意志的表达,或者预示着吉祥,或者预示着凶灾。在“天道”观念所指向的思维模式下,人们不再将其归诸上帝的指示而试图用自然事物的运行规律去解释它们。“法律意义上的自然法”这一意义上的“天道”指向人类社会的政治事务,既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指价值评价的终极体系。
先秦及秦汉文献所载的有关“天命”和“天道”论说的消长充分反映了在先秦政治哲学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转折。在上古文献《尚书》和《诗经》中,“天命”一词反复出现,而且几乎都与政治有关,当时的统治者声称,一切政治活动无不是秉承天命之为。《尚书》中虽亦有“天道”一词,但并不可靠。*今本《尚书》(包括《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中,“天道”分别于《大禹谟》、《仲虺之诰》、《汤诰》、《说命中》、《毕命》中出现。《今文尚书》本不一定是先代之旧典而出于后人的编订,《古文尚书》出于孔壁,汉末已经失传,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之伪已成定案,以上出现“天道”的几篇恰好都是《古文尚书》中的,因此并不可靠。《诗经》所收诗歌上自周初,下迄春秋中叶,但其中并无“天道”一词。“道”在《诗经》中只有“道路”和“言说”两意,还没有作“规律”的用法,因此,“天道”一词的出现不得早于春秋中叶。春秋时期,“天道”的意义也经过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天道”于《左传》中始见于襄公九年,即公元前564年,其意义近于陈来所言“宗教的命运式的理解”*《左传·襄公九年》:“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但到了春秋后期,“天道”就已经明显具有了科学意义上的自然法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然法的双重意义。比孔子稍早的郑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裨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所言“天道”的具体意义虽不十分清楚,但其区分天道与人道用意正在于使“人道”从“天道”中独立出来,其对“天道”的理解显然不是“宗教的命运式的理解”。而在春秋末年范蠡的言论中,“天道”的意义更为抽象: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下》)
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国语·越语下》)
凡陈之道,设右以为牝,益左以为牡,蚤晏无失,必顺天道,周旋无究。(《国语·越语下》)
范蠡所言的“天道”既非上天的命令亦非不可改变的运命,甚至不是直观可见的天体的运行终而复始的过程,而是抽象的具有普遍意味的规律。春秋时的某些思想家还表现出对“天道”的疏离,上引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言论就是极好的例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天命论的崩溃使得人们经历了一个对天“祛魅”的过程,《管子·枢言》已经喊出了“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的响亮口号。另一方面当时的“天道”主要与天象有关,天象与人间祸福吉凶的关联是通过占星术等一系列巫术式的解释过程而建立起来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滋长使得人们不再满足于这些近似巫术的解释方式。
“天道”立论的高潮出现于战国至汉初这一段时间内。在战国至汉初,特别是受黄老思想影响的著作中,“天道”的出现频率远高于“天命”。《老子》一书中,“天道”或“天之道”共出现七次,《庄子》中,“天道”在三篇中共出现七次;两书中均无“天命”一词。《黄老帛书》中天行、天之道、天地之道、天运、天德、天常、天理等概念反复出现,其频率不下于“天命”在《尚书》中的出现频率。时代更晚的《鹖冠子》和《文子》中,“天命”只在后者中出现一次,“天道”或“天之道”则出现二十余次。《吕氏春秋》中并无“天命”一词,“天道”或“天之道”出现七次;《淮南子》中,“天命”出现三次,“天道”或“天之道”出现二十余次。这种情况并非偶然现象,它表明,当时学者们据以立说言政的最高根据已经从天命转移到了天道或与之相近的概念。“天道”也多次出现于荀子和韩非的著作中,但荀韩的思想与黄老之学有深厚的渊源。可见,在先秦政治话语从“天命”到“天道”的转进过程中,道家包括黄老学派是主要的促成者。
二、从“道法自然”到“道生法”
从“天道”到“道”是一个更为抽象的过程,它意味着“道”成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概念。据郑开考证:“《左》《国》政治语境里‘德衰’较‘道衰’为常见,战国秦汉时期著作里则‘德衰’、‘道衰’杂而用之,似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国祚,以及政治行为的合理性。……政治语境中的‘道’、‘德’语词往往没有区别,却反映了思想史上的‘德’、‘道’主题和特征话语之间的转变,即道的崛起和德的没落。”因此,“由于春秋末年诸子学蜂起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道论’,其核心仍在于政治理念。”[3]424在儒家那里,无论是“德”还是“道”都与天命相联系,所以孔子既言“天生德于予”,又言“天之将丧斯文”,这里的“斯文”即孔子所承担的道统,其能否实现取决于天命。而在道家那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德”脱离了与“天”的关联而与“道”联系起来,成为“道”的“分存在”。在道家的话语中,“德”即是“得道”,相应地,“德衰”也就是“道衰”、“失道”。
就目前所能依据的文献来看,第一个把“道”提升为哲学概念的正是道家宗师的老子。李泽厚曰:“有关天道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但在《老子》这里终于得到一种哲学性质的净化或纯粹化。而这正是《老子》之所以为《老子》。”[3]92所谓“哲学性质的净化或纯粹化”即是指在《老子》中,“道”不再以附属于天人,即以“天道”或“人道”的形式出现,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仁、义、礼所代表的正是儒家所崇拜的周代礼乐制度与精神,在老子看来,它们的产生不是在天命的秩序里而是在道缺失的状况下不得已的手段而已,根本不具有目的意义。道与政治哲学发生实质性关联从老子那里开始,老子通过对道和万物关系的论述,建立了一个包括道与物、道与人的全方位体系,这个体系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在老子看来,人与万物同出于道,道不仅是万物的生成者,还赋予万物以运动、发展的规律。老子道论对政治哲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维路向中。老子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对理想政治模式的建构无不遵循这一思维路向,黄老道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政治思维方式亦可从中发现端倪。
“道法自然”并不意味着道于自然有所取法,而是指认万物之自然。就道、物关系言,即道无为而万物自然。万物虽出于道,但一旦生成就具有了独立性,有其产生、发展的规律。正因为道的无为,即不对这些规律进行干涉,万物方成其为万物。人对“道法自然”的取法意味着统治者无为而人民自然。“有为”与“无为”相对,古代社会,统治者的“有为”往往指发动战争、兴建大型工程、制定烦苛的刑法等违背人之本性的行为。这些行为违背了百姓顺其自然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的愿望,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为老子所批判。在《老子》一书中,我们随处可见“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等对战争的破坏作用的描述,以及“却走马以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之类的反对战争的主张。其对苛法的反对和对无事、无为的提倡更是俯拾皆是。对于无为而治,老子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小鲜”即小鱼,鱼肉较嫩,若反复搅动则鱼烂而无全鱼。老子无为而治的要旨即在于此。
尽管老子反对现实社会的各种礼法制度,在其小国寡民的理想国中也不见得有法存在的必要,但以法治作为治国的有效手段的思想并不同《老子》的思想要旨扦格不通,也不妨碍黄老道家的学者们将道作为法产生、制定、运行的终极根据。正如龙大轩所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当我们将这段话倒过来释读、理解时,便知道老子是为人定法的进步完善设定了可资追求的理想目标:礼法制度要尽量合符人的情理、进而合符人的良知、进而合符德,最终才能逐渐接近道的要求,成为良法。这就是老子设计的‘道法’的原形。”[4]55
换言之,老子虽然没有从正面指出现实社会应该有什么样的“法”,但却从反面给我们以启发。黄老道家正是将老子的这段话倒过来释读和发扬,从而提出“道生法”的命题。这一命题既是黄老道家处理道法关系时最有代表性且一贯坚持的观点,也是其政治哲学的总纲,标志着“道法体系”的形成。由于“道生法”命题明确指出了道、法之间的关系,当代的许多研究者都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如余明光先生认为:“(道生法)强调法是从‘道’中产生的,这就使法具有神圣的意义。”[5]35丁原明先生亦认为:“(道生法)是从‘道’之本体论的高度对‘法’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予以充分的肯定的接纳。”[6]97把道作为人类社会之法的形上依据的思维理路在《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里就已经得到充分的表现,“道生法”命题的提出只不过是这一思想更清晰、更集中的表达而已。
三、黄老道家“道法体系”的具体内容
首先,黄老道家的“道法体系”以“道生法”为首要原则,以法治为“治道”之手段。“道生法”之“法”并非泛指“社会的各项法度”[7]2,它不包括统治机构内的各种具体制度的建构和道德规范,而是专指法律、法治意义上的“法”。在黄老道家的政治话语中,人类社会的各项法度、规范诚然都可说“生于道”,但道德、仁义、礼、法等规范,前三者一向是道家批判的对象。“法”是道家的统治工具,“法治”是通向无为而治的唯一途径。《黄老帛书》对此处的“法”有明确界定:“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这一界定明确了法的两项主要功能:正得失和明曲直。*陈鼓应先生将此句译为:“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页。)在这一句中,法是“引得失”和“明曲直”二者的主语。陈先生误将绳墨当作明曲直的主语,又无端增加了事物一词,致使这一翻译含混不清。“得失”和“曲直”都是就人而言,“得失”是从权利角度明确某些人得到什么而某些人又失去什么;“曲直”则指法从规范人的行为方面明确了哪些行为是可以做的,哪些行为是不可以做的。在诉讼过程中,违背了法的一方是“曲”,将会失去某些依照法本来不属于他的利益;反之,遵守了法的一方是“直”,将会得到依照法应该属于他的某些利益。作者对法的这一界定已经具备了现代法的基本特征。
“道生法”之法虽与儒家之“礼”同为社会规范,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异。《黄老帛书》又指出:“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法一经制定就具有权威性和普遍的约束力,连“生法者”也不能违背,这更说明此处的“法”正是和“礼”相对而言的法律意义上的法,而非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规范。《管子·心术上》曰:“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明确指出礼的制作依据的是人情,而法源出于道,二者无论从来源、功能还是特征上都存在差异,这说明他对于礼、法的本质差异有明确的意识。
其次,黄老道家“道生法”的原则绝非“以道家的哲学为法家政论法理作论证”[8]217。中国哲学经常用“体—用”模式来分析客观对象,就特定的对象而言,有其体则必有其用,无其体必无其用,体异则用异,体同则用同。从道家形而上学体系推导出来的只能是道家的政治理论,从法家形而上学体系推导出来的只能是法家的政治理论,当然法家有无形而上学体系又另当别论。道家之体如何能有法家之用?梁启超说:“法家最大缺点,在立法权不能正本清源,彼宗固力言君主当‘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力言人君‘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然问法何自出?谁实制之?则仍曰君主而已。夫法之立与废,不过一事实中之两面。立法权在何人,则废法权即在其人,此理论上当然之结果也。”[9]148而这一“法家最大缺点”也是法家和黄老道家的根本区别所在。黄老道家明确提出“道生法”,以之作为其“道法体系”的首要原则,说明其“法”并非单纯君主意志的体现,而是道的具体化,道才是法的最终根据。
再次,黄老道家以“道法体系”为通向老子理想中无为而治政治秩序的工具和途径。在老子那里,法是和“无为”原则相悖的,因为现实社会中的法都出自君主的个人意志,是与人性相违背的。黄老道家通过对“法治”和“无为而治”的双向调整实现了“法治”和“无为而治”这两种“治道”模式之间的沟通。一方面,黄老道家利用“因”这一概念对“无为”作了更具积极意义的改造。黄老道家的“无为”和老庄“堕肢体,黜聪明”之“无为”的区别就在于“因”观念的引进。“因”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原则,其具体内容可以从认识论和实践哲学两个方面来分析。从认识论上讲,“因”强调认识过程中的客观性原则,即主体在认识过程中要去除主观成见,尽量原原本本地反映对象的客观状况和规律,达到对对象客观、全面的认识。从实践哲学上讲,“因”有凭借、依靠、遵循等意义,指人的实践活动必有所取法,有所依遁。“因”观念的引进丰富了道家的“无为”理论,使其更具理论的融摄性,亦更具可操作性。治理国家本是“有为”,“无为”之所以能够和“治”联系起来其原因也在于此。具体而言,通过“因”观念的引进,老子“无为而治”的实质转变为“因道而治”,简言之即“道治”。另一方面,黄老道家以“法”为“道”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化,以“法治”为“道治”之实现途径,完成了对“法治”的改造。“法”作为统治工具,本非法家一家的专利,事实上,先秦各家,包括儒家都不曾绝对地排斥“法”。黄老道家通过“道生法”的途径,将抽象的“道”转化为具体的“法”。借用西方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区别,在“道生法”命题中,“法”即实证法,作为人类社会运行规则的“道”即自然法。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理性、道德的观念往往纠缠在一起,儒家的“天”、道家的“道”所承载的就是这种复合而非单一性的意义,但“道生法”的思路与西方自然法学派是一致的。通过这一改造,法治成为“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的实质性内容和达到理想的“无为而治”的途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先秦政治哲学话语的核心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天命”到“天道”,再到“道”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推动者是道家而非儒家。在先秦道家的两派中,黄老一派关注现实政治,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与儒家的“德礼体系”相对的“道法体系”来完成道家“治道”的整体建构,并成为先秦政治哲学话语转变的重要推动者。
[1]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 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代思想史[M].北京:三联书店,2009.
[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 龙大轩.道与中国法律传统[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5] 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6] 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7]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8] 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