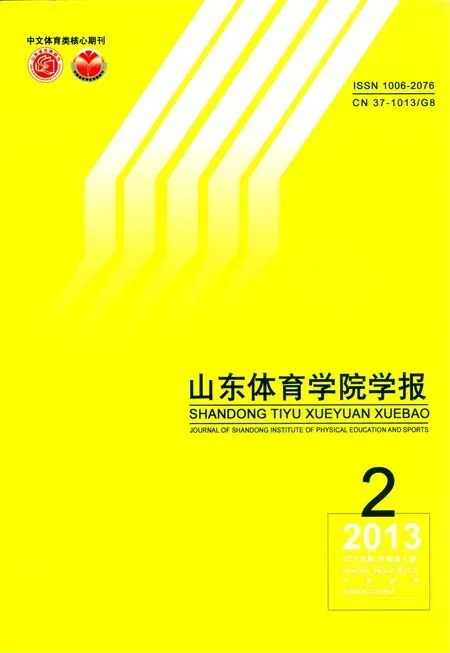赛艇运动员专项体能研究进展
韩 炜,叶国雄,韩海涛
赛艇运动是一项以有氧供能为主、强调力量耐力素质的体能主导类项目。在2 000 米赛艇比赛中,运动员依靠四肢和躯干肌群的力量共同协调工作,重复依次完成提桨入水、拉桨、按桨和推桨等一系列相关动作,通过桨叶划水使船艇前进[1]。全程大约耗时5 分30 秒~8 分,运动员平均以每桨686~882 牛顿的力划210~240 桨,桨频在32~38 桨/分,有氧供能比例在75%~80%之间,无氧供能比例在20%~25%之间。赛艇运动的项目特征决定了体能训练在赛艇运动训练实践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综观当今世界赛艇运动强国,都非常重视运动员的体能训练。专项体能是运动员能否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关键因素。专项体能是指与专项训练及特殊的比赛任务紧密联系的,运动员为圆满完成特定的训练比赛任务而必须具备的特殊体能要求[2]。目前,针对赛艇运动员专项体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项身体形态、有氧和无氧代谢能力、专项素质以及划行技术对专项体能的影响四个方面,上述四者的有机结合是赛艇运动员获得优异成绩的有效保障。
1 赛艇运动员专项身体形态特征
身体形态是决定运动员是否适合从事某项竞技运动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长年的专项化训练塑造了运动员独特的专项化形态特征。从赛艇运动员的外形看,体型大的运动员往往在比赛中占有更有利的位置。一般情况下,公开级运动员身材高大健壮、肩宽、臂长、肌肉发达而匀称且体脂较低,而轻量级运动员在体重限制的范围内也要求身材尽量高大,这些外形特征对加大划频和划长都十分有利[3-4]。Hahn[5]的研究表明,与普通人群相比,优秀赛艇运动员身材高大,下肢较长,臂长与身高比要高于平均水平;与一般运动员相比,优秀男子运动员身材更高,体重更重,上、下肢更长,同时,体脂%更低,髋部较窄,臂围较大;而优秀女子运动员和一般运动员在所有形态学指标上均无显著性差异。Misigo JM 等[6]的研究发现,优秀划船运动员皮下脂肪少、四肢围度特别是上肢围度及体重和瘦体重大。Hagerman[7]发现近30年来(1964年~1992年),优秀赛艇运动员的身高、体重几乎没有变化,而体脂%却下降了,世界级男轻选手体脂百分比平均在5%~7%、女轻选手体脂百分比在15%以下。我国2000年奥运会国家赛艇队集训队员的体脂%分别是:女重组17.55%、男重组11.40%、女轻组14.48%、男轻组10.63%[8],与美国奥运会集训队相比,我国男、女赛艇重量级选手的体脂百分比分别高2.74% 和2.70%,因此在体质量分别大4.0 公斤和4.6 公斤的情况下,瘦体质量几乎与美国选手相等。因而,降低运动员的体脂%、提高瘦体重,是提高我国赛艇运动员运动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罗马尼亚的约·格里果里察教授提出摸高、臂长、坐肩高、坐腿长、肩宽、蹲超、蹲拉距等指标可作为赛艇项目的典型形态指标,周琦年[9]和梁瑾[10]曾分别采用上述指标对我国赛艇运动员的形态学特点进行研究。张长青[11]则找出了反映我国男子赛艇运动员最重要的专项形态学指标,包括呼气末胸围、吸气末胸围、体重、上臂紧张围、上臂放松围和肩宽。这些指标对于赛艇运动员的选材、个体技术的优化、设计与评定有直接作用。
上述研究均以定性描述和常用的形态定量指标测量分析为主,应用派生指数则可进一步反映各指标间的比例关系、体形特点和相对水平等,而这恰恰是目前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目前仅有曹景伟等有过相关研究报道。曹景伟等[12]通过对16 项身体指数的研究后指出,克托莱指数、大腿围指数和身高胸围指数可有效地反映中国优秀女子赛艇运动员的形态水平,且中国优秀女子赛艇公开级和轻量级运动员的身体指数在总体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但目前还未见有对我国优秀男子赛艇运动员身体指数的相关研究。
2 赛艇运动员有氧代谢能力与专项耐力
有氧代谢能力特指机体依赖能源物质的有氧氧化所提供的能量维持体力,完成运动负荷的能力,是人体从事日常生活、劳动、工作和学习的主要供能支持系统,也是评价人体健康水平的主要标志和依据。对赛艇运动员有氧代谢能力的评价主要是围绕着机体的摄氧能力和利用氧能力两个方面展开。许多研究表明最大摄氧量(VO2max)和无氧阈(AT)是评价赛艇运动员有氧能力的重要指标,而以无氧阈强度进行训练是赛艇运动员提高有氧能力的重要手段。
作为以有氧代谢供能占主导的赛艇项目,其运动成绩与最大摄氧量关系密切。Cosgrove 等[13]采用2 000 米测功仪成绩与赛艇运动员的多项生理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专项成绩与VO2max 和廋体重的相关系数r=0.85,呈高度相关,应用逐步回归分析后发现,VO2max 是预测成绩最好的单个指标。通过对国内外赛艇运动员VO2max 基本数值的对比后发现,我国男子赛艇运动员与国外优秀男子赛艇运动员的VO2max 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而我国女子赛艇运动员的VO2max 水平则与国外优秀女子赛艇运动员相差无几,甚至超过了国外运动员的标准,这与我国赛艇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中的运动成绩情况较为相符。虽然VO2max 大小主要取决于遗传,但经过系统训练的运动员仍可提高15%~20%[14]。Hagerman[15]以9 名美国国家赛艇队队员为研究对象,对其赛季与非赛季的训练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与非赛季相比,赛季中赛艇运动员的VO2max 显著增加,绝对值从5.09 L/min 增加到6.01 L/min,相对值则从56.5 ml/kg/min增加到69.1 ml/kg/min,最大功率增长了14%。与最大摄氧量相比,有更多学者认为用无氧阈判定有氧能力可能更准确[16]。耐力项目的运动成绩和AT 水平密切相关,相关系数r 可达到0.89,比VO2max 与运动成绩之间的相关程度更高(r=0.64)[17-19]。通过系统训练,无氧阈值可显著提高。Steinacker 等[20]对德国国家青年队一个训练周期的乳酸阈值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后发现,运动员的乳酸阈值通常在上量训练阶段下降,而在减量恢复期上升,且运动成绩也会提高。杜忠林[21]的研究表明,要想使乳酸阈功率显著增加,4 个月以上的有氧训练才明显,2 个月的有氧训练影响不明显。盛蕾[22]发现经过4 个月训练后,赛艇运动员的乳酸阈显著增加了20%。国内外许多针对赛艇项目运动训练的研究都指出,无氧阈值在运动训练中是一个重要指标,无氧阈训练是高水平运动员广泛采用的训练手段之一。哈格曼指出,优秀赛艇运动员的无氧阈训练强度通常能够达到最大摄氧量的85%~89%,因而,赛艇运动员应该要不断地进行无氧阈强度的训练以提高氧的利用率。
在赛艇比赛中,专项耐力与一般有氧耐力相比与运动成绩的相关性更高,一般有氧耐力高的运动员,在赛艇训练和比赛中所体现的专项耐力并不一定好,但一般有氧耐力较低的运动员,其专项耐力多数较差。因此,在赛艇训练中,既要高度重视专项耐力的训练,又不能放松一般有氧基础的提高。但是,一般与专项耐力对专项成绩的不同作用并不能决定它们在训练中的负荷比例,也就是说不能因为专项耐力的核心角色而加大它的训练份额,优异的专项耐力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一般耐力基础之上[23]。研究表明,优秀赛艇运动员的训练特点就是70%~80%的水上训练都是采用氧利用2(血乳酸水平小于2 mmol/L)和氧利用1(血乳酸水平在2~4 mmol/L)的有氧耐力训练[24]。即使在竞赛期,有氧训练仍占总训练量的70%,血乳酸浓度在4~8 mmol/L 的有氧—无氧训练占到接近25%,剩余的5%才完全是血乳酸浓度高于8 mmol/L 的无氧训练[25]。
3 赛艇运动员无氧代谢能力与专项速度
无氧代谢能力是指运动中人体肌肉的无氧代谢供能系统提供ATP 的极限能力,它表示肌肉在磷酸原和糖酵解供能条件下的做功能力[26]。赛艇虽是一项以有氧代谢供能为主的运动项目,但是无氧供能能力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糖酵解供能能力在起航和冲刺阶段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运动后最大血乳酸值既表示机体对乳酸的最大耐受能力,又反映了机体无氧酵解供能的最大能力。研究表明,在2 000 米模拟比赛后,欧洲优秀运动员的血乳酸水平可达到15.24±3.30 mmol/L[27]。在测功仪上进行2 000 米模拟比赛后,欧洲优秀运动员的血乳酸水平可达到16.11±1.77 mmol/L,有的队员甚至超过18 mmol/L[28]。而反观我国运动员,全国冠军选手比赛后的血乳酸值为10.27±2.41 mmol/L,6 min 最大功测试后的血乳酸值为11.99±3.30 mmol/L[29]。Niels 等[30]在研究中指出,在赛艇模拟比赛中,90%的乳酸是在第一分钟内产生的,第二分钟达到最高值并一直保持在一个高的稳定值直至比赛结束,因此运动员必须在耐受体内高乳酸浓度的情况下做功,像赛艇这种在完成相当于最大摄氧量水平的长达几分钟的运动中,运动员在途中维持的极量有氧强度越高,到达终点的血乳酸浓度愈大,其运动成绩也就越好。上述结果提示,我国运动员与世界级优秀赛艇运动员相比成绩有很大差距,运动后血乳酸浓度也较低,说明我国运动员的有氧和无氧代谢能力均较差,因此,在大力提高运动员的有氧能力时,也需要提高运动员的糖酵解能力,特别是在比赛期应加强最大乳酸水平的训练和耐乳酸能力的训练。采用传统的Wingate 无氧试验也可以对赛艇运动员的无氧代谢能力进行评价。测试指标中对赛艇运动员意义较大的是反映赛艇运动员爆发力的最大功量和反映速度耐力的平均功量。丁宁伟对江苏男子赛艇运动员的Wingate 测试表明,12 名公开级选手的最大功量为1049.9±109.0 W,平均功量为785.0±72.2 W;轻量级选手的最大功量为970.6±56.2 W,平均功量为700.5±24.8 W[31]。鉴于赛艇运动中无氧代谢供能以糖酵解为主,有研究认为将Wingate 无氧试验的运动时间延长至60 秒可以较好地反映赛艇运动员的无氧能力,特别是乳酸性无氧能力[32]。但目前仅有许帆等有相关报道,其测试结果表明我国运动员的60 秒无氧功成绩远低于罗马尼亚优秀赛艇运动员标准。此外,测功仪五桨最大功率测试和20 秒全力拉桨距离两个指标是实践中常用的反映赛艇运动员无氧代谢能力的指标[33]。
Mader 等[34]指出,赛艇运动员冬季86%~94%的训练和夏季70%~77%的训练都是血乳酸水平低于2 mmol/L 的非强烈训练,这样血乳酸水平低于4 mmol/L 的训练就占到了全年训练的93%~99%,因而他们质疑高强度训练对赛艇成绩提高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无氧酵解的输出功率是有氧代谢的2 倍,因而无氧酵解能力强的运动员就能表现出更高的速度(输出功率),而且研究表明,对于较低水平的运动员,低强度训练可以实现有氧能力的提高,但当训练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只有大强度训练才能实现此目的[35]。提高VO2max 的最佳方法是强度为90%~100%VO2max的速度划和间歇训练。因此,在比赛期,应加强最大乳酸水平训练与乳酸耐受力训练以提高赛艇运动员的速度耐力。可见,建立在无氧代谢能力基础上的赛艇专项速度素质是赛艇运动员提高成绩所必需的,赛艇运动员要想划得更快,就需要一个高无氧功率下的高VO2max[36]。
4 赛艇运动员的专项力量
力量素质对赛艇运动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力量素质的改善,既可以提高运动员在有氧强度训练时每一个周期动作的效果,以克服传统有氧训练强度低的缺点和提高有氧训练质量的目的,还可以改善每一个周期动作的实效性,促进运动技术的改进[23]。此外,根据流体力学原理:在水中随着运动速度的增加,水流阻力与船速的平方成正比[37]。因此,赛艇运动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力量素质才能划得更快。
虽然赛艇比赛的冠军并不总是力量最大的选手,但是大力量至少是取得优异成绩的一个开端。Hartmann[38]通过Gjessing 赛艇测功仪对赛艇运动员进行5桨和10 桨最大能力拉桨测试后发现,男子的5 桨和10 桨最大峰值力量和最大功率分别为1 350 牛和3 230瓦;女子的5 桨和10 桨最大峰值力量分别为1 020牛和1 860 瓦。此外,赛艇运动员还需要快速力量保证每一桨迅速地完成水下拉桨动作,更需要很好的力量耐力以尽可能保持贯穿全程的速度。在2 000米比赛中,运动员需要以平均686~882 牛的力划210~240 桨。研究发现,运动员约需40%的最大划船力量才能够维持这种肌肉耐力水平[39]。在实际训练中,卧拉、卧推、负重蹲等手段常用来评价赛艇运动员的最大力量,采用最大力量40%~50%的负荷记录完成动作的次数以评价运动员的力量耐力水平。
从训练的适应原理来看,肌肉力量主要通过负重抗阻训练得到提高。采用陆上杠铃负重力量训练是提高运动员力量水平的主要方式。但是,关于赛艇运动员是否需要陆上力量训练或者说陆上力量训练是否有益于水上运动成绩的提高尚存有争议。有文献报道,世界上大多数的赛艇训练计划,均组合了几种系统的力量训练模式,并构成各自完整的训练计划。但是,这些计划中力量训练的相对量相差很大,其中有一些非常成功的训练计划甚至几乎没有室内的基础力量训练安排。即使在同一个国家队中,这种差异也是存在的[40]。从我国赛艇训练实践看,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各地方队,对于陆上力量训练还是非常重视的。众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各种力量素质的训练方法和手段。张孝斌等[41]在分析划船运动项目特点基础上,给出了划船运动员的最大力量、速度力量和力量耐力的训练方法。王治华等[42]指出要使专项力量达到较高水平就应根据参与拉桨的原动肌工作条件和工作性质,采用相应的训练方法和手段,包括陆上徒手或持器械的力量练习、赛艇测功仪的训练、陆上练习架的训练和水上阻力划。韩红升[43]依据赛艇运动专项力量发展的训练需要,将专项力量训练分为陆上杠铃、水上训练、测功仪训练三种方法,并给出了各种训练方法的组数、次数、间歇时间、负荷大小等信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先进的生物力学仪器也作为辅助训练手段应用到赛艇运动员的陆上力量训练中。王旭红等[44]采用神经肌肉电刺激仪对女子赛艇运动员的腰背肌力量进行了实验研究,取得了较好效果。易名农等[45]设计了一套赛艇运动员上肢专项力量练习器,解决了运动员后半桨拉桨力量不够、高度不够等问题。清华大学的欧阳波等[46]设计了国内第一套可用于赛艇专项力量训练的系统,除了能够完成对专项力量的科学训练,还可以对专项技术进行训练。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有时陆上力量素质提高了,而水上成绩却并没有增长,相反会影响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成绩,即陆上训练所获得的力量能力没有能够很好地转移到水中去。因此,如何将力量房中的杠铃训练与赛艇专项技术相结合,使神经—肌肉系统通过负重抗阻训练形成符合赛艇专项技术所需要的力量能力,即发展运动员的专项力量,是赛艇项目陆上力量训练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5 赛艇运动员的划船技术
赛艇运动是一项人、船、桨、水相互结合的项目,除了运动员本身的专项运动能力和器材的好坏外,运动员驾驭船艇的能力,即划船技术对运动成绩也有着重要的影响。Ulrich Hartmann 曾说过,“如果没有赛艇技术,超乎常人的身体能力和完美的身体形态也毫无用处。”因而,赛艇运动员的专项体能是取得优异成绩的保证,而专项体能必须要通过运动员良好的划船技术方能得以体现。影响赛艇划船技术的因素众多。Clara 等[47]从生物力学角度,对影响理想赛艇技术的因素进行过文献综述。本部分主要是从技术风格与身体姿势、肢体发力顺序两个角度进行阐述。
5.1 技术风格与划船姿势
赛艇是一项周期性运动,其技术动作呈周期性重复。加拿大的Peter Klavora 于1976年首先分析了三种主导1974~1976年赛坛的划艇模式,分别是前民主德国(DDR)技术风格、亚当(Adam)技术风格和罗森博格(Rosenberg)技术风格[48]。之后,Valery Klavora[49]又提出格林柯(Grinko)技术风格,并根据发力时间(腿和躯干同时发力或接续发力)和拉桨用力特征(强调腿部用力和强调躯干用力)将这四种技术风格区分开来。从发力时间角度分析,由于腿与躯干的接续工作,卢森博格风格和格林柯风格通常能够产生更高的峰值力量和功率值,而且由于卢森博格风格更强调躯干的摆动,相较于格林柯风格它能够产生更大的峰值力量,因而也被认为是最有力的技术风格,但这两种技术风格的桨叶推进效率较低。前民主德国风格和亚当风格要求腿与躯干同时发力,桨叶推进效率较高,但其峰值力量和功率值较低。从拉桨用力特征角度分析,由于亚当风格和格林柯风格强调腿部蹬伸,因而力量激发快,很快就可以达到力量峰值。这使得船艇的最初加速度提高,提升了拉桨的瞬时结构,使得拉桨更有效。而卢森博格风格和前民主德国风格更强调躯干摆动,由于更多地动用了大肌群,如臀肌、最长肌,因而能够产生更大的力量。但是,由于这些肌群本身是维持人体姿势的慢肌,因而它们与躯干肌群无法快速产生峰值力量,通常在拉桨中段力量才能达到峰值,从而使得拉桨的瞬时结构不是太有效。
四种技术风格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着眼于如何最大化利用身体特征获得最佳的船艇推进效率,各有千秋,也各有优缺点。德国的Theo Körner[50]基于如何优化运动员的体能表现和效率提出了较优的划桨姿势:1)拉桨初期身体应十分前倾,倾角约60~70 度,膝盖张角应适度压缩,但不宜到极限位置;2)起始拉桨后腿和躯干应同步运动;3)腿部施力应与长的上体摆动相结合,手臂施力应当起始于手掌约与膝盖同高的时候;4)腿与躯干应保持最大运动直到能够稳定不断地增加强力的手臂推动为止;5)手臂必须全力施力到下肋骨处为止;6)在桨叶脱离水面而手掌带着桨柄摆动之后,躯干不再弯曲并以舒适受控的方式贴着座位,这些动作适宜的同步性确保了运动员重量的自由后移,从而使艇平稳前进。然而,在现实赛艇运动中,并不存在与上述描述完全统一的技术模式,大多数桨手都根据自身的身体形态特点和肌肉组织特征选择适合自身的技术风格[51]。
5.2 肢体发力顺序特征
从划桨技术动作的发力情况和顺序看,赛艇划桨动作涉及了四肢和躯干的绝大部分肌群。有研究表明,人体约有70%的肌群参与了做功,下肢爆发力是赛艇的直接动力,而躯干和上肢起传导和支撑的作用[52]。运动员要充分利用全身各主要肌群的力量,腿、腹、腰、背、肩、手臂等依次协调、连贯、有节奏地进行划桨动作方能产生最佳的做功效果。因此,了解赛艇运动员的主要用力肌群及工作特征,对提高运动员的专项体能水平,加强专项力量训练的针对性有重要作用。
5.2.1 拉桨阶段肢体发力顺序
拉桨是动作周期中的动力阶段,是技术的关键。拉桨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伸腿,以伸膝肌群开始,主要由大腿前部的股四头肌完成;第二个阶段是伸髋,它几乎与伸腿动作同时完成,主要由大腿后部的腘绳肌和臀大肌完成;第三个阶段是伸躯干,主要通过下背部的竖脊肌完成;最后一个阶段是手臂的拉桨动作,主要工作肌群是上背部的背阔肌、大圆肌、三角肌、手臂的肱二头肌,斜方肌上部肌束、斜方肌中部肌束以及菱形肌等较大的肩部回旋肌起辅助作用。任喜平等[53]研究发现,拉桨阶段运动员身体各关节最大角速度出现顺序为:膝关节→髋关节→躯干→肘关节→腕关节,发力顺序遵循大环节肌群带动小环节肌群发力的原则。Lamb[54]对拉桨阶段身体各主要关节角速度对桨叶向前推进速度的贡献率进行了研究,人体各环节在拉桨不同阶段均同时参与工作,但在拉桨初期,小腿角速度贡献率最高,达到76%;而随着桨手向船头移动,躯干角速度的贡献率迅速增大至接近70%;到拉桨后段,上肢力量贡献率增加至接近40%,保证桨叶做出快速且有效的推进力后迅速出水。
5.2.2 回桨阶段肢体发力顺序
回桨阶段是运动员拉桨用力完毕、肌肉协调放松的阶段,也是为下一个周期拉桨做准备的阶段。对于回桨阶段人体发力顺序的研究不多。任喜平等[53]曾对2007年世锦赛赛艇女子单人双桨运动员回桨阶段身体各关节的角速度进行了研究,发现运动员各关节最大角速度出现的顺序有所差异。但作者指出回桨阶段机体各关节最大角速度出现的合理顺序应为:腕关节→肘关节→肩关节→躯干→髋关节→膝关节,且肩关节、肘关节和躯干最大角速度几乎同时到达为最佳。上肢发力并非大关节带动小关节,而是中小关节(腕、肘关节)先活动,然后大关节(肩关节和肩带)才活动。
6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对赛艇专项体能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主要集中在专项身体形态、有氧和无氧代谢能力、专项运动素质以及运动员划船技术与专项体能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在赛艇训练实践和比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及今后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1)对赛艇运动员(特别是男子赛艇运动员)专项体能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2)对赛艇有氧训练、无氧训练和混合供能训练的合理分配、搭配比例和转换的研究;3)对赛艇运动员专项力量素质训练方法与手段的研究;4)赛艇运动员陆上专项力量训练器材的研制与开发研究;5)灵敏、协调、柔韧等“软素质”训练对提高赛艇运动成绩的研究。随着对赛艇专项体能特点的进一步深入理解和探究,未来的研究趋势应当是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如将运动生物力学指标纳入赛艇运动员专项体能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不同划船姿势和用力方式对赛艇运动员能量消耗差异性的研究、赛艇专项体能辅助训练器材的研发等。总之,继续加强体能基础理论,尤其是专项体能训练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仍将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赛艇运动训练领域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1]冯连世,冯美云,冯炜权.优秀运动员身体机能评定方法[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281.
[2]袁运平.运动员体能与专项体能特征的研究[J].体育科学,2004,24(9):51.
[3]Pavle Mikulic.Anthropometric and Physiological Profiles of Rowers of Varying Ages and Ranks[J].Kinesiology,2008,40(1):80 -88.
[4]Secher NH,Vaage O.Rowing Performance,A Mathematical Model Based on Analysis of Body Dimensions as Exemplified by Body Weight[J].Eur J Appl Physiol,1983,52:88 -93.
[5]Hahn A.Identif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Talent in Australian Rowing[J].Excel,1990,6(3):5 -11.
[6]Misigo JM,et al.Characteristics of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Status of Rayakers and Canoeists[J].Sports Med Phy Fit(IT),1992,32(1):45 -50.
[7]Hagerman FC.Applied Physiology of Rowing[J].Sports Med,1984,1(4):303 -326.
[8]杜忠林.中国国家赛艇运动员身体成分的分析[J].湖北体育科技,2003,22(4):457.
[9]周琦年.赛艇运动员若干选材指标的探讨[J].浙江体育科学,1987(8):53 -56.
[10]梁瑾.女子公开级赛艇选手若干形态指标的比较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1992(3):55 -58.
[11]张长青.我国男子赛艇运动员的身体形态指标研究[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8,24(5):64 -66.
[12]曹景伟,罗智,鲍勇,等.中国优秀女子赛艇运动员身体指数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26(3):347 -350.
[13]Cosgrove MJ,Wilson J,Watt 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ected Physiological Variables of Rowers and Rowing Performance as Determined by A 2000m Ergometer Test[J].Sports Sci,1999,17:845 -852.
[14]Brooks,GA.Anaerobic threshold:review of the concept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Med Sci Sports Exrec,1985,17:22 -31.
[15]Hagerman FC,Staron RS.Seasonal Variables among Physiological Variables in Elite Oarsmen[J].Can J Appl Sport Sci,1983,98(3):143 -148.
[16]王凤阳.关于无氧阈概念与机制的探讨[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02,2l(l):110 -112.
[17]Hagberg JM.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ndurance performance as studied in competitive race walkers[J].Med Sci Sports Exer,1983,15(2):287 -289.
[18]Foehrenbach R.Die Ausdauertie Stungsfaehigkeit Deutscher Spitzenathletinner Mit Wettkampfstrecken Vom Sprint Bis Zum[M].Marathonlaufsport:Leistung und Gesudheit.Kongrens Deutsch Sportaeztekongress Koeln,1982:555 -562.
[19]Tanaka.Relationship of anaerobic threshold and onset of blood lactate accumulation with endurance performance,zur[J].Appl Physiol,1983,(52):51 -56.
[20]曾凡星,丁轶建,彭希记.优秀男子赛艇运动员的训练效果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28(3).
[21]杜忠林,王武韶,顾军,等.优秀赛艇运动员无氧阈增长幅度的分析[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00,19(1):92 -95.
[22]盛蕾.正常训练对划船运动员通气阈的影响[J].体育科学,1987,7(2):52.
[23]陈小平.当代运动训练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136,112 -142.
[24]Jensen K,Nielsen T.High Altitude Does Not Increase Maximum Oxygen Uptake or Work Capacity at Sea Level in Rowers[J].Scand J Med Sci Sport,1993,3:56 -62.
[25]Nielsen T,Daigneault T,Smith M.FISA Coaching Development Programme Course[M].Lausanne:Fisa,1993:13 -18.
[26]浦钧宗.Wingate 无氧试验的进展[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1989,8(2):96 -99.
[27]Secher NH.Physiological and Biomechanical Aspects of Rowing Implications for Training[J].Sports Med,1993,15(1):24 -42.
[28]Hagerman FC,Connors MC,Gault JA.Energy Expenditure During Simulated Rowing[J].J Appl Physiol,1978,45(1):87 -93.
[29]杜忠林,顾军,李荣华,等.不同划船训练手段的血乳酸值分析[J].湖北体育科技,1998(4):19 -24.
[30]Niels H,Secher NH.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Aspects of Rowing[J].Sports Medicine,1993,15(1):24 -42.
[31]丁宁伟,等.赛艇运动员专项能力的研究[R].江苏省体科所,2001.
[32]许帆,等.赛艇运动员无氧功能的研究[J].国家体委体育科学研究所学报,1990,3(1):33 -37.
[33]李诚志.教练员训练指南[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937 -971.
[34]Mader A,Hartmann A,Hollmann W.Einflueins Hhentrainings auf die Kardiopulmonale Leistungsf higkert in Meeresh he,dargestellt am Beispiel der Deutschen Ruder-Nationalmannschaft,in Hollmann W.(ed):Zentrale Themen der Sportmedizin.Berlin:Heidelberg,Springer,1986:276 -290.
[35]孙小华,张晓.赛艇运动员有氧能力的测试[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6(2):68 -71.
[36]Volker Nolte.赛艇——划得更快的科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65.
[37]Martin TP,Bernfield YS.Effect of Stroke Rate on Velocity of a Rowing Shell[J].Med Sci Sports Exerc,1980,12(4):250-256.
[38]Hartmann U,Mader A,Wasser K.Peak Force,Velocity,and Power During Five and Ten Maximal Rowing Ergometer Strokes by World Class Female and Male Rowers[J].Int J Sports Med,1993(9):42 -45.
[39]Ed McNeely,竞技性赛艇运动员的力量训练目标[J].张海洋,林辉杰,译.中国体育教练员,2006(4):64.
[40]中国赛艇协会官方网站.赛艇运动员的专项力量训练[OL].http://www.rowing.org.cn/teamchina/science/ 204 -06-02/37323.html.
[41]张孝斌,张军.划船运动力量素质训练的探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37(4):72 -73.
[42]王治华,丁攀.赛艇双桨技术动作的解剖学分析及专项力量训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40(7):57.
[43]韩红升.论赛艇运动员专项力量训练[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4,38(6):108 -109.
[44]王旭红,蒋健.应用神经肌肉电刺激技术发展女子赛艇运动员腰背肌力量[J].浙江体育科学,1992,14(4):18 -21.
[45]易名农,郑伟涛,韩久瑞.赛艇运动员上肢专项力量练习器的研制及应用[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1,35(4):97 -99.
[46]欧阳波,王培勇,沈杜,等.陆上赛艇专项力量训练系统的研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39(2):32 -36.
[47]Clara S,Patria AH.Towards an Ideal Rowing Technique for Performance:The Contributions from Biomechanics[J].Sports Med,2004,34(12):825 -848.
[48]张清,叶国雄.中国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教材(赛艇)[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203.
[49]Valery Kleshnev.Rowing Biomechanics[EB/OL].http://www.biorow.com/Papers_files/ 2006%20Rowing%20Biomechanics.pdf,2006.
[50]佘振苏,周明德,陈军,等.赛艇运动的训练及技术研究进展[M].北京大学湍流与复杂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赛艇运动科研组编译(内部资料).2006.
[51]Kleshnev V,Kleshnev I.Dependence of Rowing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on Motor Coordination of the Main Body Segments[J].J Sports Sci,1998,16(5):418 -419.
[52]拉里·克格曼.赛艇的力量训练原则[J].李建新,译.中国赛艇,1990(2).
[53]任喜平,潘慧炬.优秀女子赛艇运动员划桨动作的运动学特征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2009,45(1):98 -101,132.
[54]Lamb DH.A Kinematic Comparison of Ergometer and On -water Rowing[J].Am J Sports Med,1989,17(3):367 -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