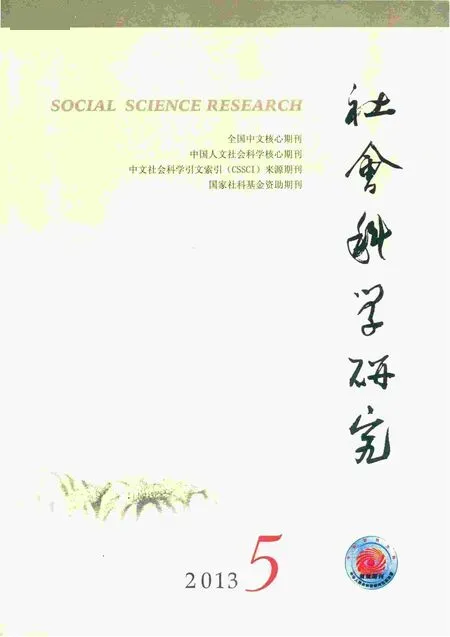历史唯物主义 “思想”与 “现实”关系的解释学分析
刘 李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旨在批判新黑格尔主义者和费尔巴哈。在他们看来,新黑格尔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错误地理解了思想与现实的关系。这一错误主要表现为:新黑格尔主义者将思想、观念确立为现实的本质和现实运动的根本动力,并认为通过改造思想、观念 (宗教的、政治与法的)即可根本地改造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对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做出了全新理解和阐释。这样的阐释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系统的表述。
在这次系统表述中,“思想”与“现实”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关键词,而两者关系问题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最宏大和最基本的主题。说它“宏大”,是因为对这一关系的阐释内在包含了对其他诸种重要关系的阐释;说它“基本”,是因为这种阐释集中表现了马克思最基本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立场。这也使得这种关系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基本主题。
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对思想与现实关系的阐释,理论界主要有这样两种观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知识社会学观点。前者认为,马克思的阐释是从本体论 (谁决定谁)和认识论 (是否正确反映)方面对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关系的分析;后者则认为,马克思的阐释是对思想生产的一般社会学条件和过程的经验研究。在我们看来,上述两种观点都没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作为“具体整体”来把握,都没能深入分析“思想”现象的意义结构,因而无法准确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对思想与现实关系的阐释。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尝试从一种特定的解释学视角来透视马克思对两者关系的阐释,以期更准确地把握这种阐释。
一、作为解释对象的“思想”
我们知道,解释学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多个阶段,但这些阶段实质上并不是连续的,而是分别对应着指向解释问题的不同进路。与之相应,“解释学” (hermeneutics)这一概念也是多义的且无法相互融贯。在《诠释学》一书中,帕尔默曾归纳了“解释学”的六种定义,分别是:(1)圣经注释的理论;(2)一般的语文学方法论;(3)所有的语言理解之科学;(4)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5)存在和存在论的理解之现象学;(6)既是恢复性的又是反偶像崇拜的诠释体系。〔1〕这六种定义分别对应着透视解释问题的不同理论视角,代表着考察解释学的不同立场。这就提出两个问题:当我们说要从解释学的视角或立场上透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之关系时,这种解释学是何种意义上的解释学?从这样的视角去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题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
我们采取的解释学进路是第六种意义上的解释学。这种意义上的解释学是保罗·利科提出来的;选择这种视角的合法性可以从保罗·利科对马克思思想的看法中得到保障。不同于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保罗·利科在定义解释学时,将对文本的解释视为最核心的规定性要素,而在他那里,文本是指“象征符号” (symbol)或“多义的符号”。象征符号是指“任何意指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个直接的、原初的和字面的意义附加地指示另一个间接的、从属的、形象化的意义,后一种意义只有通过前一种意义才能被领悟。这种对双重意义上的表达进行限定便确切地构成了解释学领域”。〔2〕与之相关,“我打算赋予解释与象征符号一样的外延。我们将说,解释是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在于对隐藏在表面意义中的意义加以辨读,在于展开包含在字面意指中的意指层次,……哪里有多重意义,哪里就有解释,意义的多重性也正是在解释中变得明显起来。”〔3〕
按照保罗·利科的理解,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不是单义而是多义的符号,即它不仅有着表面的连贯一致的意义,同时还具有更深层的但被表面意义掩蔽的意义。解释就是透过表面的意义揭示深层的意义,而解释学就是在解释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规范和理论体系的综合。这种意义上的解释和解释学是“怀疑的训练”,是揭露伪装、祛除神秘、打破偶像、重建“真实”的理论实践。
有哪些思想或思想家可以代表这样的解释学呢?保罗·利科认为,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思想是这种解释学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示例。这三个人物“都扮演着怀疑的主角,扮演着面具的撕裂者”,并且,这种怀疑深刻到使“整个哲学规划都被触及和受到质疑”。〔4〕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说法意在强调:这几位思想家都发现了看似自明现象的多重意义结构,并着力于不断深入地揭示现象的隐蔽意义,而这样的理论实践产生出一种新的思想类型,即保罗·利科意义上的解释学。
保罗·利科的观点绝不只是个例。后现代主义的杰出思想家福柯同样将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相提并论,并从解释学的理论立场考查他们思想的共通之处。在一篇名为《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的文章中,他认为,这三位思想家“改变了符号的性质,变更了通常可能用来解释符号的方式”。〔5〕因而,“十九世纪,特别是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再次为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的可能性,他们重新建立起一种解释学的可能性。”〔6〕
保罗·利科和福柯关于马克思思想的观点为我们选择这种解释学视角的理论合法性做了辩护。并且,通过更深入的分析将表明,要想把握马克思对“思想”与“现实”这种关系的阐释,这样的视角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须的。这种分析将揭示:历史唯物主义中“思想”实质上等同于保罗·利科所说的作为解释对象的“象征符号”;历史唯物主义对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分析实质上就是以“现实”为根据对作为解释对象的“思想”之解释。
我们首要面对的问题是:“思想”如何成为“象征符号”,亦即成为被解释的对象?对于探究“思想”如何成为“象征符号”,重要的并不是对思想概念的分析,而是对思想现象之意义结构的形式分析。因此,重要的不是厘清“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是明确“思想”现象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架构中所处的层面或位置;明确这一层面上的事实与其他层面上的事实之关系。这些关系深刻关联着思想现象的意义结构。
如何把握这些关系并最终把握思想现象的意义结构呢?我们可以先从形式的角度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架的典型特征和结构。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理论结构的“层级性”。马克思将对立、冲突、斗争视为基本而普遍的事实。这种对立不是概念或命题间的逻辑意义上的对立,而是实存性力量的对立。对立关系作为具有最强张力的结构关系,倾向于不断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对立关系。这种转化实质上是一种构造。作为一种构造,它使得被构成的关系相对于构成性的关系成为“表层的”事实,以此类推,从而形成理论空间的“深度性”。层层转化的对立关系又使得“深度”层层增加。因而,层级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形式特征。
另一方面,实存性力量的对立使得“伪装”成为力量表现自身的普遍形式。处于对立关系中的力表现为服务于斗争,而不是纯粹的为表现而表现。对于这种表现,马克思强调它们普遍具有伪装、歪曲、自我掩蔽的形式特征,即对立关系中力的表现同时也是伪装和自我掩蔽。伪装和自我掩蔽并非源于个人的有意识的动机,而是超出个人的力量借助于人的活动所实现。
从上述两方面我们看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中,每一层级的现象都由下一层级的对立力量所构成并表现深层力量;并且,这种表现并不是直接的自明的表现,而是同时作为伪装的表现,即深层的力量和力量关系在借助表层现象表现自身的同时也借助它们掩蔽自身。从解释学的角度看,表层现象就具有了双重意义结构:一层是表层意义或无意义,另一层是深层意义。表层意义或无意义作为“虚假”的意义乃是对深层的“真正”意义的掩蔽。
正是这样的意义结构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表层现象”成为保罗·利科意义上的“象征符号”,成为福柯所说“被改变了性质的符号”。“解释”的任务由此产生。“解释”是对现象所表现但同时又掩蔽了的力量和力量关系的揭示;是对力量的伪装形式的分析;是重建表层现象及其表面意义被构成的过程与机制。我们看到,正是这样的“解释”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保罗·利科和福柯谈到的新型解释学。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结构中,相对于其下层级的现象而言,每个层级的现象都是这种性质的“符号”。由于思想、观念、意识处于这一结构的最表层,它们成为其下一层级的力量与力量关系的表现与伪装形式,成为“真正意义”最为深刻和丰富的“象征符号”。从解释学的角度上,这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思想只能作为解释对象而存在,不同于思想但以思想为伪装的“非思想之物”则构成解释的根据;只能通过后者去说明前者,而不是相反。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非思想之物”正是马克思所说的“现实”。
二、作为解释根据的“现实”
“现实”(Actuality)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概念之一。站在解释学的立场,马克思对一切有待解释的现象的阐释,即对其掩蔽意义的揭示,都是通过 (并只能通过)对“现实”之结构的深入分析来实现的。当以思想为解释对象时,这样的分析正是对思想与现实之关系的揭示。马克思如何规定这一概念呢?在我们看来,他依循对“现实”的一般规定,把“现实”看作“非思想性的存在”;在一般的规定前提上,他在深层的意义上将“现实”规定为“具体整体”。
一般来说,“现实”是指并非幻想或思想的存在,现实之物对立于“思想”、“表象”等,指独立于并外在于思想的客观实存。〔7〕马克思接受了现实内涵的一般规定。正如他自己谈到的那样:“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8〕“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9〕
在这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段落中,“现实”首先应被理解为“非思想性的存在”。但除此之外,在马克思那里,“现实”还有进一步的规定。这种规定在哲学史上亦有很深的渊源,具体说,它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对“现实”概念的规定一脉相承。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现实”(actuality)和“实现”(actualisation)被交替使用。两者都对应于“潜能”(potency),“都是指不同种类的潜能的满足或实现。在亚里士多德对本体变化的讨论中,现实或实现等同于形式,有时等同于质料和形式的组合物,即已经赋予形式予质料的事物。”〔10〕“现实”是潜能经由 “活动” (activity)的“实现”。黑格尔认为:“现实是本质和实存或内部和外部所直接形成的统一。现实事物的表现就是现实事物本身,所以现实事物在表现中同样还是本质的东西,而且只有在具有直接的、外部的实存时,才是本质的东西。”〔11〕显而易见,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现实”概念的规定内在相通。他们都认为:现实之物不是直接的实存之物,而是实现其“潜能”或符合其“本质”的实存之物;现实作为“实现”是某种“活动”或“运动”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对“现实”的理解深刻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也同样认为现实之物不是直接给予的实存之物或实存之物的集合,而是符合或实现其“本质”的实存之物,并且,“实现”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区别也非常明显。马克思并没有把“本质”理解为“实体”、“形式”或一物区别于他物的内在规定性,而是理解为构成事物并与事物一体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不是思想范畴间的辩证关系,而是实存力量间的对立关系。
对于马克思来说,事物本身就是被掩盖起来的社会关系。比如,作为劳动者的人、商品、资本、货币、机器,实质上都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构成物。只有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它们才是其自身。不仅如此,构成事物的关系也是被更深刻的关系所构成。更为重要的是,事物与关系的关系、关系之间的关系是内在而非外在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从存有的方面来看,事物的本质并不限于构成并支配它的直接关系,而是同时包含支配着关系的关系。因而,事物真正和完全的本质乃是诸种关系构成的“整体”。从认识的方面看,任何被直接给予的事物只是一个马克思所说的处于“混沌整体”中的“混沌表象”。只有深入分析这个表象所掩盖的诸种关系之后,事物才获得清晰的规定,直接的实存之物才能成为现实之物。同时,这个整体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从而成为“具体整体”。
原则上,作为“具体整体”的现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和唯一的研究对象。当我们得到这样的现实概念时,思想与现实之关系问题才获得一个得以展开的理论平台,并真正地、完整地呈现出来。但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简要分析马克思的对“本质”和“现象”的看法中蕴含的解释学意义。
马克思仍然坚持本质与现象的区分和内在联系,并认为这是一切科学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但如上所述,“本质”已经不是内在的、自在的形式,而是实存力量的对立关系,进而是作为“现实”的对立关系整体。与本质概念的变化相应,“现象”的意义结构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或黑格尔眼中的现象。现象固然仍是表现本质的现象,但同时亦是对本质的掩蔽。我们同样以《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诸经济学范畴的分析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资本、货币、商品、机器、劳动者、资本家实质上都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12〕这就是说,作为本质的关系与物结合并作为物而出现,但物的形态却又是对关系的颠倒和掩蔽。
不仅物与构成性关系的关系是这样,关系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因而,当我们从解释学的视角去看时,物与构成物的关系都成为象征符号,而现实这个整体则成为象征符号的层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上一层级的现象都是下一层级现象伪装的表现形式。这与我们通过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构架得到的结论一致。这种一致不是偶然的,因为“现实”之结构与以“现实”为认识对象的理论之结构具有必然的同构性。
基于上述分析,历史唯物主义中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呈现出来了。两者的关系直接表现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因为思想直接表现为现实的一部分。而当我们从解释学的角度去审视这种“部分——整体”关系时,它就转化为解释对象和解释根据的关系。由于整体内部关系的对立性质,作为部分的“思想”成为待解释的象征符号,而整体 (现实)作为思想“真正意义”的隐蔽源泉成为解释的根据;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反映——被反映”关系,而是被层层掩蔽和扭曲了的“表现——被表现”关系。这意味着:思想与现实关系的性质不是认识论性质而是解释学性质。马克思分析这种关系的目的不是追问思想是否为真,而是追问思想的隐含意义;分析不是对思想的证实或证伪,而是对思想隐含意义的阐释。
经由上述总结,我们从解释学视角大体刻画了思想与现实关系的性质。以下我们借助类比对以思想为对象的解释活动进行更具体的分析,借以充实和深化对两者关系的理解。
三、通过类比对“思想”与“现实”关系的进一步分析
我们选择解释学上的一个经典范例,即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作为参照对象来分析马克思的解释活动所包含的要点。选择这种参照的合法性在于两位思想家具有解释学上的“家族相似”。除了保罗·利科和福柯,齐泽克也认识到这种相似性。他认为,精神分析的解释对象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对象都是作为“症候”(symptom,也译为“征兆”或“象征”,同保罗·利科的“象征符号”实质上是一致的)的同一类现象,并且,“马克思的阐释程序和弗洛伊德的阐释程序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13〕以下我们从逻辑起点、解释程序、解释活动的动态性等方面具体展开弗洛伊德对梦的阐释与马克思对思想之阐释的类比。
首先,从逻辑起点看,将梦确立为解释对象是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逻辑起点;将思想确立为解释对象是马克思思想解释的逻辑起点。弗洛伊德认为,梦具有意义但意义被掩盖在看似无意义的形式之下。如果梦只被看作无意义的混乱表象,或梦的意义直接明白地呈现出来,就不会存在对梦的解释。马克思认为,思想 (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是“对现实内容的歪曲、颠倒的反映”、“幻想”、“想象”,但思想的真正意义恰恰掩盖在这样的表象之下。如果思想仅仅只是幻想或想象,或思想的真正意义直接明白地呈现出来,就不会存在对思想的解释。
其次,从解释程序来看,弗洛伊德对梦的解释与马克思对思想的解释是大体同构的。对弗洛伊德来说,显梦内容是分析的直接材料,也是最有意义的材料,它内在包含着现实与心理的内容与对这些内容的歪曲形式和机制。释梦者必须首先进入显梦内容并借助自由联想来扩充它,以便为更深入地分析建立必要的前提。同样,在马克思那里,思想内在包含着现实内容与这一内容的歪曲形式和机制。要把握特定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应当首先深入特定的思想内容中去,并借助某种方式扩展这种内容,建立思想内容与被扭曲的现实内容的关联。
在弗洛伊德那里,对显梦内容的扩展主要表现为对诸种伪装形式 (如以部分代替整体、暗喻、意象化、象征化等)的分析和破除,实存的现实与心理内容正是经由这些形式转变为显梦并在显梦中隐藏自身。马克思同样谈到了思想伪装的诸种形式,比如“普遍化”、“神秘化”等,现实内容正是经由这些形式转化为思想并被隐藏在思想中。因而,对思想内容的扩展也同样表现为对诸种伪装形式的分析与破除。
对弗洛伊德来说,重建梦内容与现实和心理内容的关联是重要的一步,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基础上分析这些内容为何要以歪曲或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利用自由联想重建的显梦与现实内容的关联仍然只是表层的关联,必须借助于对深层关系的分析来进一步解释这种表层关联存在的条件、必然性与其指向的潜意识目的。同样,对马克思而言,解释不止于重建思想与其现实内容间被扭曲和掩蔽的关联,而是要进一步分析支配着扭曲和掩蔽的更深层的力量与力量关系,完整地说明这种关联的条件、必然性和更深层目的。
更深入的分析使弗洛伊德发现了潜意识欲望与压抑性力量的对立关系和使这种关系得以可能的更深层对立关系,后者说明了表层关系存在的必然性及其深层意义。在马克思那里也是如此。原则上,对特定思想的阐释要求不断深入作为“具体整体”的现实,层层深入地分析诸对立关系,使思想的意义更深刻和系统。
最后,从解释活动的动态性来看,一方面,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来说,解释都是与解释对象的较量。在弗洛伊德那里,对梦 (及神经症)的解释不是一种纯粹的认知活动,而是作为一种现实力量与造就并隐含在梦 (与神经症)之下的活跃力量进行较量;解释像是一场持久的拉锯战。在马克思那里,解释同样不是纯粹静观式的认识,而是一种实践活动。对思想 (尤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解释乃是解释者所代表的力量与思想所代表的力量之较量。
另一方面,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来说,解释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解释对象 (梦、神经症与思想)的意义并非稳定不变,因为以之为伪装和工具的力量与力量关系变动不居。当解释对象被新的力量关系所构成和支配时,就需要被重新解释。
上述类比展示了以思想为解释对象时马克思的解释程序及解释活动包含的要点,从中我们看到了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动态方面及这种关系包含的要点。正是基于解释学视角,这些内容才系统地呈现出来。这就提出两个问题:基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立场是否也能准确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对思想与现实关系的阐释?较之解释学视角,它们是否具有理论优越性?两个问题答案都是否定的。
正统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后者被认为是前者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与之相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题 (思想与现实关系问题)变成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并且,问题被从本体论和认识论 (正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的方面进行规定,成为“谁决定谁”和“社会意识是否正确反映社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将思想与现实关系问题转换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否合法呢?如果正统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原本意义上使用“社会存在”概念,这种转换是合法的。但是,它将“社会”视为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另一个领域,将“存在”规定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相应地,“社会存在”就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之物;社会存在构成的整体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因而,问题的转换变成对问题的非法歪曲。
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失误还在于:它所确立的问题形式使其无法全面系统地把握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实质和要点。对于本体论意义上“谁决定谁”的问题,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这里,一方面,“决定”的提法意在标示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即“谁离开谁可以存在”;另一方面,“反作用”的提法隐含地将思想看作外在于现实的实存性力量。但是,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提问“谁离开谁可以存在”是不恰当的,因为思想是现实的必然表现和它的一部分;作为“表现”,思想也不是一种外在于现实的实存性力量,它具有力量只是它被现实力量支配的假象。
同样,对于把握思想与现实之关系而言,正统马克思主义基于认识论立场谈论社会意识是否正确反映社会存在也是不得要领。我们已经说明,思想与现实关系不是认识论性质的关系。无论是否正确反映了现实,思想都是“象征符号”,在其表面的意义下总是存在深层意义。比如,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正确地”反映了现实,但它并不因此不再是解释的对象,因为“正确反映”得以可能同样是现实内部的深层对立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表征,在没有分析这种变化之前,这一思想的深层意义恰恰被“正确反映现实”所掩蔽,从而仍是一个“混沌的表象”。
知识社会学也重视马克思对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分析,并将马克思视为重要的思想先驱。但一般而言,作为一种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经验科学,知识社会学无法理解和接受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概念。在它看来,经验现象不是具有本质的实存,经验的总和也不构成一个具体整体。同样,思想也不具有什么“深层意义”,只是实存的经验现象而已。相应地,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上,马克思所揭示的思想与现实的内在关系变成相互外在的经验现象间可以 (并必须)用实证方法确定的相关性。显然,这样的理解方式也没有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实质。
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之失误从另一个方面确证了解释学视角的优越性。它也再次提示我们:对于把握马克思的阐释来说,确立恰当的理论视角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视角决定了能看到什么以及看不到什么;决定了赋予对象什么样的性质与结构;决定了针对对象所确立的提问方式和问题;最终,它决定了我们能否真正把握对象。
〔1〕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M〕.商务印书馆,2012.50-51.
〔2〕〔3〕〔4〕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选〔M〕.商务印书馆,2008.13,13,121.
〔5〕〔6〕汪民安,陈礼国编.尼采的幽灵〔J〕.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99,99.
〔7〕布鲁格编注.西洋哲学辞典〔M〕.国立编译馆、先知出版社,1975.33-34.
〔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65.22,29.
〔10〕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M〕.人民出版社,2001.22.
〔11〕黑格尔.逻辑学:哲学全书·第一部分〔M〕.人民出版社,2002.263-264.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人民出版社,1965.232-233.
〔13〕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