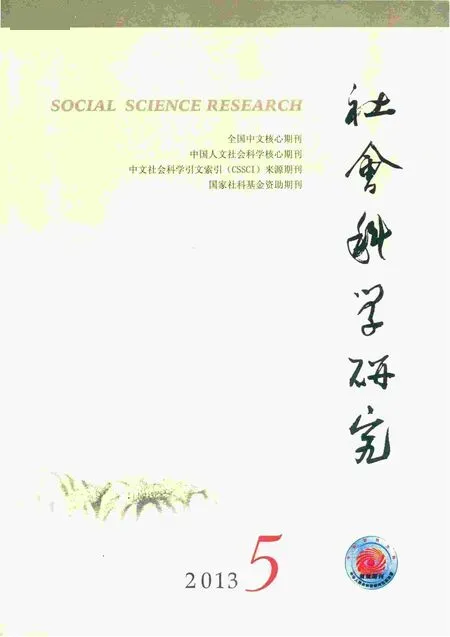公共供求场域中的行政权力:配置方式、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
黄建洪
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是公共行政中的关键环节。超越于传统静态工具观的认知,将其放置于公共场域的复杂活动之中予以动态性地考量,行政权力本身的客观性与资源性,以及行政权力使用的合价值性与合目的性之统一的公共性要求与实践性愿景便呈现了出来。在一个社会民众利益诉求多元分化且持续高涨的时代,寻求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就需要高度关注行政权力的行动身份、配置方式、运行机制及其发展趋势,从而展拓和塑成行政的公共价值与实践力量。
一、公共供求的三重论域与行政权力
实际上,与惯常的认识不同的是,行政权力并非始终处于一种一次性给定和受动性运行的权能状态之中。这是因为,行政权力始终都处于与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的持续能量互动与调试之中,深受公共能量场中公共供求波动变迁的影响和制约,同时其自身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发展出来的行政自主性也对权力的运行状态与绩效呈现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论域一:公共供求关联性与行政权力。公共行政是讲求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动态平衡的科学。作为公共能量场中关于价值权威性分配和有序实现的交互活动〔1〕,其绩效高低受制于行政权力对公共供求关联性的把握程度。从公共需求引发的行政实践看,公共供求在四个方面与行政权力关系密切:一是在秩序与发展方面。由于行政权力大量卷入到民众生产生活的众多细节之中,因而它的配置与运行便深度地塑造着微观的公共交往秩序,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制度发挥形塑和建构作用。因此,行政权力是创造公共绩效的能量基础。二是在效率与公平方面。面对治理资源有限的客观约束,治理效率的提高与公平价值的实现,以及消除效率与公平张力,有赖于对行政权力的配置运行做出适应性调试并确保行政权力作用的适度发挥。三是在结构与功能方面。公共供给的核心在于在合理辨识公共需求的基础上组织和整合公共资源,实现治理结构的优化,从而整体提升治理功能。这离不开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规划与调配使用。四是在信度与效度方面。具有公共可信度和公共有效性的行政权力配置和运行,需要体现出权力实践的亲民性与服务力,即以政府为中心的公共治理结构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进行有效率的均衡供给。在此过程中,若公共供给过量或不足,都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与低效率,从而引发公共事务的荒芜、损害民众利益。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公共供给的显著不均衡与行政权力配置、运行之间的明显不匹配。譬如,转型期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的凸显,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政府在具体的微观经济领域出现管得过多、过宽和过细的宿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加剧的态势。这表明,行政权力如何有效捕捉到切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公共需求,以规范的制度化方式供给相应公共管理和服务,并循序克服越位、错位、缺位等低效甚至“无为”状态,对于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发展则举足轻重。
论域二:政府职能重心位移与行政权力。政府职能与行政权力之间互为表里。从历时关系演进的角度看,社会生活中实际形成了三类彼此适应的行政范式与社会形态,即统治行政与依附性社会、管理行政与弥散性社会以及服务行政与自主性社会。〔2〕前者以土地为资源进行政治统治;中者以经济事务管理为使命和依托明示规则进行治理;后者则以公民导向和社会本位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职能重心从统治向管理和服务持续位移,不是个别阶层或集团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经济社会变迁内驱力所产生的客观要求。〔3〕依据这种政府职能重心位移原理可知,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4〕,势必引发对行政权力实践价值与作用机制的更新和调整,以及对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利间的交往范围与合作方式进行重新规划设计,这意味着行政范式与公共事务治理机制的重大变化。以行政回应于社会公共需求,就需要在以社会发育来厘定行政职能边界、以公共性引导公共决策等方面重新思考行政权力的配置运行。伴随着行政范式的服务化转变,选择性地进行政府职能的弱化、强化或转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域三:治理工具选择组合与行政权力。宏观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之间的互动变化,引发了对新治理结构和更高治理效能的渴求,从而对以政府自我治理和政府社会治理为中轴的公共治理提出了挑战。从刚性统治到效率管理、再到公平服务成为不可阻止的行政发展趋势。基于行政权力配置的客观状况与职能实现的需要,治理工具的大规模更新便如火如荼地推展开来。作为结构化的集体行动,治理工具 (或被称之为政府“箭袋”里的“箭”〔5〕)是与公共事务领域相关的社会主体持续互动的一种制度化的信任行动模式,其目的在于解决公共问题。〔6〕在行政服务化的整体趋势下,大量采用市场化、工商化与社会化的治理工具来运行行政权力,与社会中的公司企业、社会团体乃至公民个人进行持续合作。在各国的民营化和市场化行政改革探索中,灵活使用政府付费、合同外包、特许经营、产权交易、绩效管理等市场、工商技术〔7〕,正逐步实现政府支配资源的最小化、市场支配资源的最大化。与此同时,社区参与、志愿者模式和合作治理等社会化技术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在有别于传统政治社会高度同质化与一体化的新层次上,呈现出了基于分化的高级一体化,即治理的互融、互助与互利,因而公共事务的公共治理形态也就更为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二、公共供求过程中的资源性存在:认知行政权力
行政权力是将行政理念转换成为具体实践、进而实现行政愿景的关键资源和支配力量。但在认知上,有两个“迷思”需要厘清:一是将行政权力本身理解为一种道德性存在。即将其使用效应的社会评价当作本质加以归并,并不能够清楚判明行政权力的客观性。行政权力本身属于“器”而不是“道”,这种“器”只有与它的使用者结合起来并为某种特定利益结构服务的时候,其“面向”才能得以划定。可见,作为一种资源性的存在,行政权力为谁掌握与服务于谁才是问题的关键。二是将行政权力理解为治理能力。作为一种势能,行政权力的存在只表明它具有了为一定利益立场服务的可能性,至于此番利益的公共性究竟如何、其服务后的社会评价究竟怎样,则取决于权力实践的方向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吻合程度。以“公共”面目出现的权力运作,只有得到了公共利益的确证才能被认定为具有公共有效性。可见,公共行政之事,从来都不是行政系统可以单方面自我确证的事,而应是一个尊重现代社会利益条件下动态持续的公共选择。
依据上述认知,行政权力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基于公共行政的治理价值,行政权力是促成公共价值权威性分配的主导力量。实践中,社会行动秩序与普遍价值持续地受到来自于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外围”支配构架的公共治理结构的塑造和控制,行政权力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威性资源。其二,基于公共行政的管理价值,行政权力是贯穿于公共政策过程的支配力量。无论是公共议题转换成为政府议程,还是行政方案的择优、合法化、分解执行、政策修正乃至政策监控、政策评估以及政策终结,都离不开行政权力的全程参与。但其参与的范围、程度与力度不同,对于公共绩效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第三,基于公共行政的技术价值,行政权力是弥漫于具体行政管理诸环节中的管制性力量。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保障、发展效率还是社会公平,无一不受到来自行政权力的系统规制。
作为处理信息和保持控制的系列活动,行政权力是公共行政的生命线。〔8〕无论是根据作用维度的权力观〔9〕,还是 “意志论”和“结构主义”(权力是非人格化的社会“结构”的产物)的权力观,都需要解决在公共能量场中权力在何种状况下才是真正有效的问题。公共治理结构不仅需要知道什么应该发生、什么正在发生,而且有办法知道在二者之间有一定差距时使后者与前者保持一致。在国家越发成为一种理性的行动力量受到控制和约束之时,其日常运行最为频繁的行政权力不得不朝向规范化与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在回应民众与日俱增的公共需求背景下的“行政超载”困惑〔10〕和“行政国家”的发展。〔11〕在执行法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过程中,行政权力主体就必须遵循权力主体法定性与权力客体普遍性的原则,从而确保行政权力得到合理、高效的配置使用,以保护公共利益。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在公共场域中行政权力具有如下三重显著特征:
其一,从根本性质上讲,行政权力具有阶级性、关系性和社会性。所谓阶级性,是指国家政治时代行政权力是特定主导阶级的权力。在一个资源总体有限的背景下,权力的赋予和行使都会展现出力量支配性和利益排他性。关系性,意指行政权力是通过一系列的权力关系得以实现的。一方面,它需要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分配权力;另一方面,它还需要在权力系统内部实行纵向和横向的分权与制衡,通过国家结构形式和政治体系结构来对行政进行确权、赋权、督权。所谓社会性,指相对于民众权利而言,行政权力是派生于人民主权的治理权,具有显著的工具性。作为一种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恶”,它必须受制于且服务于社会权利,因此就需要构建有限行政与有效行政,以便能够有效回应民众的权益诉求。
其二,从职能发展角度看,行政权力同时具有统治性、管理性和服务性。尽管三种属性兼而有之,但从实践发展来看,服务行政取代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客观上成为公共行政发展的总体趋势。“行政是现代政治的心脏”〔12〕,掌握行政权威而形成秩序可控、利益稳定的统治格局,是公共行政的第一课题。但同时,“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3〕这表明,行政权力的管理服务价值极为重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倡导离散权威、多中心决策和服务的治理主义 (替代宪政主义和管理主义)不断兴起,更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的服务型政府浮出水面,如何更有效率和更加节约成本地服务成为政府改革的主题。
其三,从利益取向角度论看,行政权力具有公共性、自主性和自利性。为“虚幻共同体”〔14〕国家的执行工具,行政权力具有一定的利益超然性,即它必须通过提供一定数量的公共物品来形成统治、服务社会。但同时,作为整体的政府由各层级、各条线的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组成,存在着行使行政权力的政府和官僚对于国家整体利益、社会众意的某种偏离、甚至违背的情况,即自主地决策和执行。对于政府,可称之为政府自主性;对于公务群体,可以称为官僚自主性。〔15〕但在行动方向和利益结构与公共利益具有重合性的治理领域,行政权力的自由裁量能够成为促进制度创新和绩效创造的积极力量,而当它的决策立场与利益获取失去法律约束时,则会演变成为掠夺性力量,表现出明显的自利性。
由是观之,从分权角度论看,权力场中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不可或缺;以合法性角度而言,人民同意是合法政治行政秩序建构的基础。为此,为回应来自社会的公共需求,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需要在“有限”与“有效”的双重维度上展开,前者涉及到民主行政的基本精神,后者则关系到效能行政的实践原则。
三、行政权力的配置方式
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公共选择过程,行政权力配置是指通过特定程序和方式对公共场域进行权威能量供给,以促使行政主体能够有充足的公共权力资源对公共事务进行合法、高效的管理和服务。行政权力配置量的大小、行使范围的宽窄及其治理工具的选择,均需要放置在以市场机制力量与社会自治能力所设定的公共需求场域中来判断。而行政权力的受配主体即行政主体,它们是根据国家明示规则进行公共管理与服务活动的行动者。在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浪潮中,持续分权和放松规制这些新的确权路径就使得公共组织与非公共组织、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在合作治理的技术更新中获得了行政权力行使的新规定性。概括起来,常见的行政权力配置方式或机制有三:
第一,法律配置。这是行政权力配置的最基本方式,即通过宪法和法律实现行政权力的分配。一般而言,通过立法机关立法方式来配置现代政府的行政权力,这是通例,即人们所常说的“权力法定”原则〔16〕以及权力适量原则来确权赋能。这一配置方式意味着,任何行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其权力的来源都是依据明确的程序,对其权力的行使和监督也自然应纳入法治的轨道。在不同的政治体制、政府体制下,行政权力的配置差异明显。〔17〕在西方,尽管存在着议会制模式下立法机关的行政权配置,总统制模式中依宪法规定和定期大选的行政权配置,以及混合模式 (半总统制与委员会制)下的总统民选及总统任命总理配置、众议院选举委员会的集体行政等多种方式,但最高行政权和地方行政权力的配置一般均依据于宪法和政府组织法等法律法规在权力精英层面进行定期选举,日常性的行政管理权限则依照政务岗位设置与职能确立来完成。在我国,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的国务院行使国家行政权,各级地方人大对地方各层级政府进行行政赋权。〔18〕不论在哪级政府中,以组织层面享有的行政管理权限,则是经由宪法、国务院及地方政府组织法等法律进行权威性配置。
第二,授权配置。通过政府系统内部力量的调整,以达到配置公共事务管理权力的目的。最常见的行政权力配置方式包括两类:一是逐级授权。为实现行政权力结构性分配和功能性分配,较高层次的行政主体授权下级行政主体以一定的责任和管理权限,使下级在上级的监控下获得某种自主行使的权力。逐级授权可分为多种形式,例如上级向下级发布工作指示可采用充分授权,不充分授权则适用于重大公共事项或执行任务,为强化政务执行子系统之间的彼此牵制可选取制约授权,在完成具有多阶段的同一项任务时进行弹性授权。二是权力下放。根据公共事务的需要,行政权力系统内部自上而下地进行职责、权力与利益的调整。在单一制国家内,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的权力下放,是权力系统内部的改革和调整。譬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20世纪末期至今的日本地方分权化改革〔19〕以及英国地方政府的“半自治”实践等〔20〕,都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改革的鲜活案例。在复合制国家,联邦政府 (如美国)的改革客观上也存在向州和社会放权的可能,但无论是程序规范,或是权能数量的下放转移,都受到严格约束。
第三,社会配置。指通过向私人领域、向市场、社会转移权力和寻求合作的方式来配置行政权力。一方面,向社会转移权力来配置行政权力。通过国家向社会、政府向公民转移权力以促进社会自治,有利于地方社会获得来自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放松规制等途径转移而来的权力。以政府组织为主导的公共管理部门便获得了一种核心的职能规定性,即以基于市场机制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确定政府权力的范围、数量以及相应财政配给,进而对于政府工具的选择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寻求与社会合作治理来配置行政权力。即通过市场化、工商化和社会化等治理技术的优化组合,以更多参与、更高效率、更多节约和更为透明的方式改革政府,驱使政府权力成为更为适宜的公共服务力量。例如,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注重对工商管理技术的运用,引入竞争机制和顾客导向进行管理改革〔21〕;同时,美国的“重塑政府运动”、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方式和市场机制促进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此外,德国的“苗条国家”、荷兰的“地方治理模式”以及法国、瑞典等国的政府改革,也都有类似的效能化特征。
从公共供求的互动角度看,行政权力配置具有四重实践价值:一是确立权威。公共治理中的行动结构是一个持续开放但并非是绝对均衡的“中心—外围”梯度权威秩序结构,其间政府权力要吸纳、引领、支配和导控社会相关事务主体的治理参与,其前提是政府具有足够、适度的行政力量。权力配置过程则恰好是树立这一行动权威的过程。二是输送资源。公共秩序的建构和公共利益的发展,一般可以通过权力驱动、利益驱动和问题驱动等多种方式进行。但究其质里,它都是一个对公共能量场内的公共资源进行特定方式的分配和使用的过程;但同时,需要克服越级行政授权导致的指令紊乱、权威耗损与能量散溢〔22〕。后现代国家结构中,政府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的扩张性配置使用所引发的“大政府”治理,就始终面临着约束官僚、节约成本和提升绩效的种种压力,为此应对行政碎片化的整体性治理受到重视。〔23〕在后发政治驱动型的现代化中国〔24〕,在转型期以持续的经济分权和中央对地方授权来进行的治理资源配置,则集中体现在通过具有丰富弹性的“改革权”强力驱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三是建制机制。行政权力的配置过程,实质上正是公共治理机制的建制和运转过程。法律配置、权力下放与社会配置方式在宏观上互相需要、彼此耦合,从而有利于政府减少人格化治理、增强治理的制度化水平。四是优化工具。通过行政权力的社会配置方式,市场化与工商化政府治理工具得以大量导入和优化组合,用企业家精神改造公营部门、用市场机制形塑公共市场、用顾客导向和效能原则涤荡陈腐的文牍主义与官僚气息,正深刻地改变着公共场域权力与权利之间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方式。
四、行政权力的运行机制
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是指从动态方面规范权力运行的过程,包括决策、执行、监督、协调和控制等运行环节以及对政务系统中人、财、物、信息等资源的支配方式。〔25〕从行政过程这一动态角度看,需要建制起行政权力运行的稳定化、全息态与规范性机制,以确保行政权能资源的合理整合与高效利用,从而为保障和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创造条件。
其一,面向社会主体的价值机制。行政权力的核心目标是为公众、为社会服务。作为人民主权实现方式之一的行政权力,是治权的一种,其价值依归就是“以人为本”,因而就需要以公共理性的精神来进行民主治理。〔26〕一方面,其运行需要符合民主的价值。即在行政权力体系内部,要有赋权的公开与透明,不论是高层行政权力的定期更替还是事务性行政权力的授权治理,都需要满足民主参与和合作治理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其运行需要符合法治的价值。法治是人民权益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障。确保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规范有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杜绝敷衍塞责和权力腐败。民主与法治是一种思维习惯,一种管理方式,更是一种治理机制。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27〕作为公权力,行政权力的运行必须考虑到效率与民主、权威与制度的统一,增强权力的公正性与透明度。
其二,准确高效传馈的信息机制。信息是政府的神经〔28〕,它构成衔接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与公共事务界面之间运作的纽带。譬如,公共政策过程中,对大众关心的各类社会问题进行凝练、使之由公众议程转变成为政策议程,以及初拟出各种政策方案并依据程序进行方案择优,都离不开对公共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利用;与此同时,在政策周期中还普遍地存在着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政策再决策以及政策终止等复杂环节,都离不开及时准确的信息保障。在一个日渐开放的政策决策与执行环境之中,科学、高效的信息机制有助于通过广泛获取社会各类信息而助益于行政决策、行政组织和行政领导,这对于提高公共政策质量和公共事务治理水平至关重要。从民众参与的角度讲,准确、高效的信息传输与反馈机制的建立运行,有助于公民获取政务信息、增进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合作,从而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这对于提高行政管理过程的透明度、提高公众对公共管理与服务参与度、提升政策对象对决策执行的配合度,从而化解政策风险、降低治理成本,均有积极推动作用。
其三,纵横双向沟通的协调机制。政务活动是涉及多层级、多部门和多问题领域的复杂活动。因此,就始终面临着如何将科层化的权能构成与弥散性的资源分布有机地整合起来,通过合理规划、管理和调配,使公共事务治理能够既经济节约又行动高效的问题。此外,在治理不可预期性增强与发展风险日渐增多的背景下,行政协调的危机治理作用更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确保政府层级之间和部门之间运转协调、配合良好、进行协同治理角度讲,行政协调是现时代极为重要的治理机制和管理方式。从协调的方向看,行政权力协调包括:纵向协调,涉及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协调,表现为不同政府层级之间的职权、责任与利益协调,中央部委与省 (市)对口线上的协调较为普遍;横向协调,是指同一政权层级中的协调,既包括行政与立法、司法之间的协调衔接,又大量涉及行政决策、执行与监督方面的协调。从协调的方式讲,针对于行政权力系统内外环境的协调,方法各有不同。对于与系统外的协调,包括信息反馈、行政参与、手段调整等方式;对于行政系统内部,则主要通过会议、组织、民主决策等方式来完成。
其四,复合强化作用的激励机制。权力运行的激励,涉及到选取何种内容和以何种强度予以实施这两个维度问题。这是因为,对于总体上以工具性为主要特征的行政权力行使,既要解决其效率问题——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又要促使其有鲜明的价值导向——使之成为保障和服务于公共利益发展、尤其是民众对发展成本均衡承担、对发展受益公正享有。这是从正向角度对行政权力进行导控的实际表现。一方面,激励内容引导着行政权力的运行方向。如若仅以满足上级权力考核为目标,则往往会导致大量的“唯上”现象,进而刺激出治理中大量短期的显性绩效行为。因此,强调注重对法制环境塑造、市场机制建设、生态质量提供和民生服务供给等方面的权力激励,将有利于发展出具有公共性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另一方面,激励强度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具有约束力。权力行使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难以摆脱自我利益的衡量。在这种格局下,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与其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效益的日渐下滑形成鲜明对比,行政权力扭曲运行几乎就不可避免。着眼于长远发展,就需要通过新的利益结构设置,以形成多领域的激励结构,以此来优化行政权力的管理运行。
其五,立体监督控制的约束机制。“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9〕人不是天使,因此需要政府;而统治政府的不是天使,因此需要分权与制衡。〔30〕这便回应到公共行政的一个核心命题上来,即如何在有效行政与有限行政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链接机制和风险防范的“防火墙”。一则,有效政府需要受到系统性的监控,确保其成为促进公共利益的能动力量,否则仅有效率考量而失却对其进行价值规约,则会放纵其成为暴虐专横的“恶”;二则,需要建立有限政府,进行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合理划分,以社会权利制约政府权力〔31〕;三则,需要建立起依法行政的政府,用权力制约权力〔32〕,通过不断发展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控制机制来确保其公共性。为此,对行政权力的立体监控,有效行政与有限行政的动态平衡,还必须来自政府的自律与来自社会的他律有机结合的制度建设上来。前者如倡导公共行政伦理、建立起完备的行政内部监控制度来约束行政权力。后者则需要通过国家制度来防止权力滥用,确立责任追究、国家赔偿制度,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权利救济方式来确保行政权力行使的主体合法、职权合法与程序合法,强化制度性硬约束与文化性软约束的复合作用机制。
五、行政权力配置运行的发展趋势
权力配置过程说到底是公共选择过程,而权力机制运行过程则是作为公共资源的行政权力由势能转换成为动能以实现公共绩效的过程。这两个维度的过程性衔接互动直接影响着公共行政的实践绩效。从整体来看,以公共供求平衡和公共利益发展为基本导向的行政权力配置运行会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一是行政权力配置运行的民主化。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民主行政是对政府良心的探索和治疗”〔33〕,关键则在于行政权力资源配置与使用的民主化程度,其民主衡量尺度在于公众以各种方式参与权力过程的广度与深度。〔34〕作为公共治理的核心资源,其配置运行需要充分重视来自社会群体和市场机制的力量。以政治民主来促进公共治理体制的持续变革,使其更具有开放性与吸纳度。通过扩大公民参与来确保行政权力配置运行的公共性,譬如授权配置过程中的民意表达、民权监督等就有利于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在国家型政府、行政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变的大趋势下〔35〕,行政权能的管理最终还是需要落实到民主化权力配置和开放性的权力运行上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原则,建立起对公共权力的整套规划、训导、指挥和控制体系。民主化的行政权能实践,有助于以体制的力量、规则化的渠道和理性的方式化解公共紧张和社会矛盾,实现体系内外沟通的优化和交往的理性化,减小发展阻力,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促进社会稳定协调发展。
二是行政权力配置运行的法治化。“公共行政就是公法的明细而且系统的执行活动”。〔36〕从制度机制建设角度讲,行政权能的配置运行实践,需要将公共治理中的确权和用权行为规范化,通过一系列的改进措施使之纳入明示、稳定预期的制度轨道。基于行政科学发展的基本态势,我们认为,行政权力实践的法治化需要过好三道关:一是分权的规范化关。不断调整行政与社会、行政与市场、行政与公民的权力与权利边界,这些持续性的改革行为必须经受住民主程序与法律规则的检验和拷问;二是参与的制度化关。为避免因参与渠道狭窄、参与机制不畅以及参与表达低效等问题而引发的非制度化参与和社会疏离、甚至对抗,需要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有效地纳入到民众意愿与政策议程之间的实质性互动关系之中,构建多元主体供给机制和多层次供给模式,确保治理的整合力与超越性;三是监督的效能化关。行政权力的配置过程本身就是重要公共资源的配置形式之一,其运行过程便是以各种形式对社会资源进行汲取、支配、使用和控制的过程,二者都容易出现因官员和社会成员持续逐利而导致的腐败问题。
三是行政权力配置运行的效能化。与传统静态治理的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治理需要对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治理结构进行不断调整,以应对持续高涨的公共需求所施加的治理压力。效能化的行政权力配置运行需要关注:一是行政权能的调整运行需要围绕公共供求的动态均衡来展开。即以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实际发展需要来确定行政权力的实践定位与目标。二是要明确行政权力配置运行的政府职能重心。政府职能重心位移重心理论给人们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以服务行政为基本行政范式进行行政改革已经成为有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持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冲突、增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可靠路径。三是大力使用以市场化工具为主的治理工具来提升政府能力,发展调控-监管能力、汲取-分配能力、合作-发展能力、整合-平衡能力等功能性能力群。〔37〕采取市场化方式,进行分权与整合来重组机构、节约组织资源、激活政府权能来达成效能目标;通过管理技术如全面质量管理、标杆管理、目标管理、成本控制、政府合同和公共物品的社会化供给方式来强化政府能力;以及通过人力资源改革来实现效能化,以科学的绩效评估来优化行政管理方式。
四是行政权力配置的服务化。规范管理基础上更多的服务而非简单的刚性统治,业已成为公共行政话语的风向标和公共行政精神释放的具体表现。为此,服务行政需要关注:其一,行政权力价值的服务性。社会权利是公共行政的导师,这解决了“服务谁”的问题。否则,便不会有真正的公共行政。其二,行政权力的作用重心在于创造公共治理机制。行政权力需要在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促使政府行政、市场机制与社会自治之间形成合力。因此,需要克服主体排斥以及机制替代的错误倾向,进行开放性的合作治理。而如何通过具有针对性的权能配置和运行实践,重视社会力量的有效利用和公共服务社会化〔38〕,来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至为关键。其三,行政权力配置运行的绩效评价需要回归到对公共需求的回应性与服务性上来。在坚持顾客导向和导入服务标准化的基础上,采用新的治理手段和服务工具以改造公共管理与服务流程,有利于权力服务效能的持续优化。
〔1〕〔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0.
〔2〕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5-6.
〔3〕施雪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J〕.社会科学,2010,(2).
〔4〕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12,(5).
〔5〕〔美〕戴维·奥斯本,等.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周敦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9.
〔6〕Lester M.Salamon,The Tools of Government: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7〕陈振明.政府工具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5.
〔8〕〔美〕诺顿·朗.权力和行政管理〔A〕.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 (上册)〔C〕.李方,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11.
〔9〕〔英〕戴维·米勒,等.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Z〕.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41-642.
〔10〕〔美〕乔尔·阿伯巴奇,等.两种人:官僚与政客〔M〕.陶远华,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2.
〔11〕Dwight Waldo,The Administration State: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2nd ed.New York:Holmes& Meier Publishers,1984.
〔12〕夏书章.行政学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1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3.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15〕Niskanan,William A.A reflection on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Blais,Andre& Stephane Dion.(Eds.).The budget-maximizing bureaucrat:Appraisals and evidence.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1,p.22.
〔16〕郭济.政府权力运筹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1.
〔17〕卓越.比较政府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9-38.
〔18〕马明华.公民参与视域中公共行政的法律控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19〕万鹏飞,白智立.日本地方政府法选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17.
〔20〕〔英〕戴维·威尔逊,克里斯·盖姆.英国地方政府〔M〕.张勇,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1.
〔2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1-102.
〔22〕施雪华,曹丽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特征、问题与改革〔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6).
〔23〕〔英〕佩里·希克斯,等.迈向整体性治理:新的改革议程〔M〕.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02.37-38.
〔24〕胡伟.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中国因素〔N〕.文汇报.2008-12-13.
〔25〕郭济.政府权力运筹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8-181.
〔26〕Fred D’Agostino,Gerald F.Gaus,Introduction:Public Reason:Why,What and Can It Be?.From Public Reason.Fred D’Agostino& Gerald F.Gaus,ed(s),Dartmouth: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98.
〔27〕〔美〕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6.
〔28〕Deutsch·K·W.The Nerves of Government:model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New York:Free Press,1963.pp.1-5.
〔29〕〔英〕阿克顿.自由的历史〔M〕.王天成,等译.译序.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
〔30〕〔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C〕.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64.
〔3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良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0.
〔3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54.
〔33〕孔繁斌.认真对待民主行政——对中国行政管理体制自我认同的一项分析〔J〕.公共管理研究,2011,(1).
〔34〕〔美〕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
〔35〕顾平安.政府发展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52.
〔36〕〔美〕托马斯·W.威尔逊.行政学之研究〔J〕.李方译.国外政治学,1987,(6).
〔37〕黄建洪.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能力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选择〔J〕.社会科学研究,2010,(4).
〔38〕〔美〕丹尼尔·耶金,等.制高点——创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M〕.殷宏,等译.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529-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