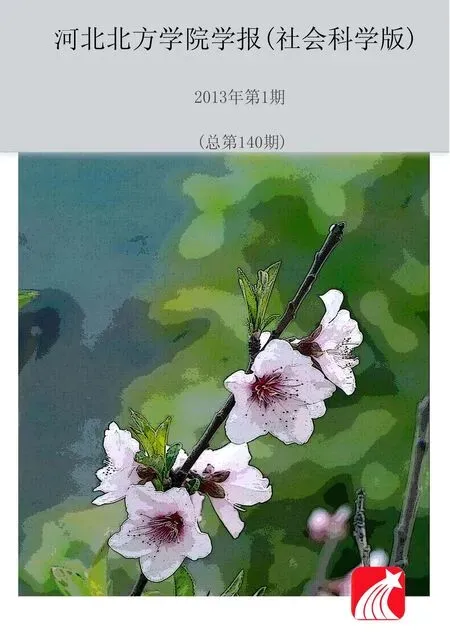《罗生门》的两个中译本比较
师 彩 霞
(河北北方学院 文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罗生门》的两个中译本比较
师 彩 霞
(河北北方学院 文学院,河北 张家口 075000)
对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罗生门》的两个中译本进行比较,通过对比两个译本相同的地方,说明文学翻译不能离开原文,它是“不逾矩”的;通过对比两个译本不同的地方,说明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它是包含了作家的主体性的。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不逾矩”;再创作;主体性
《罗生门》是日本近代新思潮派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也是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短篇之一。从鲁迅开始到现在,中国很多的译者都介绍过它。以下主要对楼适夷译本(以下简称楼本)和文洁若的译本(以下简称文本)进行比较和分析,希望能借此进一步明确文学翻译的本质,把握处理好翻译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为建立中国文学的翻译理论提供一点思考。
一、两个译本的相同之处
在思想内容上,《罗生门》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描述了平安朝末期一个仆役被生存所逼做了盗贼的故事,表现了他从弱者到强者的心理历程。通过这个故事,反映了现实社会利己主义的盛行,解释了人生的无可奈何。对此两位翻译家是没有什么异义的。所以,两个译本在内容构思、结构安排、形象塑造、语言基调、小说行文格调的灰色阴冷方面都没有差异。这些相同之处的存在,体现了翻译过程中“信”的标准和原则,这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而“信”包括原作的内容和形式及形式中的风格。译作是依附于原作而存在的,翻译不能离开原著,必须在原著设定的界限里进行,即钱钟书所说的“不逾矩”。施康强认为:“这个矩,一是不能脱离原文,二是原文是文学作品,翻成了中文,也必须是一部文学作品。‘不逾矩’即严复的‘信’,就是‘不倍本文’,要尊重原文,不能越过它。”[1]11叶君健也认为,“作者有他的作品替他说话,我们做翻译,要了解原作者的感受,只能从他的作品的字面上去推测,去领悟字里行间所蕴涵的精神和意义。这说明翻译是不能不以原作为依据的”[2]19。李芒也强调:“翻译必须以再现原作为原则。”[2]20
二、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两个译本在表达过程中的差异
(一)翻译的过程中所用语言不同
文洁若的译本多用书面词语,用词极讲究,有些甚至不常见,而楼适夷的译本用语则较通俗普遍。如文本中的“鸱尾”,楼本中用“门楼”表达;文本中的“雕甍”,楼本中用“飞檐”表达;文本中的“薅头发”,楼本中用“拔头发”表达;文本中的“七磴石阶”,楼本中用“七级台阶”表达;文本中的“强弩”,楼本中用“弹弓”表达;文本中的“孑然一身”,楼本中用“除他以外,没有别人”表达;文本中的“弃置不顾”,楼本中用“无人来管”表达;文本中的“白发老妪”,楼本中用“老婆子”表达;文本中的“眺望落雨”,楼本中用“等雨停下来”表达;文本中的“嗅觉剥夺殆尽”,楼本中用“夺去了他的嗅觉”表达;文本中的“部位”,楼本中用“部分”表达;文本中的“思忖”,楼本中用“想”表达;文本中的“踱”,楼本中用“走”表达;文本中的“映入眼帘”,楼本中用“发现”表达。这仅是一些词语上的比较。另外,还有一些句子表达的不同。如文本中“太阳西坠后,人人都感到毛骨悚然,不敢越雷池一步”[3],楼本中的表达是“一到夕阳西下,气象阴森,谁也不上这里来了”[4];文本中“雨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把刷刷的雨声聚拢过来。薄暮使天空逐渐低垂下来,抬头一看,门楼顶那斜伸出去的雕甍,正支撑着沉甸甸的乌云”[3],楼本中的表达是“雨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飒飒地打过来,黄昏渐渐压到头顶,抬头望望门楼顶上斜出的飞檐上正挑起一朵沉重的暗云”[4];文本中的仆役说“我不是什么典使衙门里的官吏,而是刚刚从这门楼下经过的旅人。所以不会有把你捆起来发落之类的事。你只要告诉我这般时辰在门楼上干什么来着就行”[3],楼本中的表达是“我不是巡捕厅的差人,是经过这门下的行路人,不会拿绳子捆你的。只消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门楼上,到底干什么”[4];文本中“仆役甩开老妪,抽冷子拔刀出鞘,将利刃的钢青色闪现在她眼前”[3],楼本中的表达是“家将摔开老婆子,拔刀出鞘,举起来晃了一晃”[4];文本中“倘若择手段就只有饿死在板心泥墙角下或路旁的土上。然后被拖到这座门楼上,像狗一样遗弃拉倒”[3];楼本中的表达是“要择手段便只有饿死在街头的垃圾堆里,然后像狗一样,被人拖到这门上扔掉”[4];文本中“京城的傍晚阴冷,冷得恨不能来上一只火钵才好”[3],楼本中的表达是“夜间的京城已冷得需要烤火了”[4];文本中“老妪的生死完全任凭自己的意志所摆布。而后,这种意识使迄今熊熊燃烧的心头那憎恶之怒火不知不觉冷却了。只剩下圆满地完成一件工作时那种安详的得意与满足”[3],楼本中的表达是“家将意识到老婆子的死活已全操在自己手上,刚才火似的怒气,便渐渐冷却了,只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4]。从以上对比完全可以看出两个译本语言风格的不同。文本用语显得文气十足,不符合文化水平低的仆人身份,达则达矣,雅则过矣,笔者认为不易被一般的读者接受。而楼本用语则流畅优美,达雅兼顾,笔者认为更易被一般的读者接受。这种译语差别的存在,笔者认为就涉及到翻译的“雅”的标准与原则。关于此,李芒曾说:“‘雅’与否和‘雅’的程度,在文学作品中多有高低和浓淡之别。一律求之以雅,就可能在尺度上出现不够准确的偏向。”[5]31郭宏安对“雅”的阐释是:“如果一提雅,就以为是‘汉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没有道理的,其说可攻,攻之可破。然而,可否换一种理解呢?以‘文学性’解‘雅’。有人问:‘原文如不雅,译文何雅之有?’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对立中对‘雅’字作孤立的语言层次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学层次上看,情况就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则其字词语汇的运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学性,俗亦有文学性,雅俗之对立消失在文学性之中。离开了文学性,雅自雅,俗自俗,始终停留在语言层次的分别上,其实只是一堆未经运用的语言材料。我们翻译的是文学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语言材料去对付。如此则译文自可以雅对雅,以俗应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如同在原作中一样,译文语言层次上的雅俗对立亦消失于语境层次上的统一之中。如此解‘雅’,则‘雅’在文学翻译中断乎不可少。”[2]15笔者认为,文学翻译中的“雅”应该是优美的文学性的语言。
(二)理解差异造成的表达不同
这在两个译本中主要有4处。第一处是在对仆役脸的描写上。文本中说仆役右颊上是颗“大粉刺”,而楼本中说是一个“大肿包”。在原文中,作者很留意仆役脸上的这个特点,小说中先后有4次说到仆役总在摸着它。笔者认为译为大肿包比较合适。脸上长个粉刺对仆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要是因生活所迫去偷、去抢,而被人打起了肿包那就要紧了,说明仆役的生存已受到威胁,必须加以解决。第二处是在小说最后,仆役要剥老婆子的衣服时,文本中说他揪住了老妪项后的头发,楼本中说他抓住老婆子的大襟。笔者认为应译为抓住大襟准确,因为仆役就准备要抢老婆子的衣服了,所以他下意识会去抓别人的衣服。第三处是当仆役爬上梯子看到门楼上的火光,文本中说好像有人在东一下、西一下地拨着火,而楼本中说火光这儿那儿地在移动。笔者认为楼本准确,因为老婆子正在找有头发的尸体,肯定在拿着火把动。第四处是老婆子衣服的颜色。文本中译为黄褐色,楼本中译为棕色,笔者未读过原著,不知哪一个准确,只好提出这一点,请教于懂日文者。这些不同之处的存在,说明翻译家们对原作的理解过程是个不断学习、不断领悟、不断深入的过程。叶君健认为,“译者在理解原文的阶段,在揣度与领悟原作当时的意义的过程中,就受到他本人的人生修养、文化知识水平和艺术欣赏趣味等因素的限制,他所达到的理解程度,就不一定完全与原作的本意相吻合”[2]18。这实际上是指出了译者作为阐释主体所存在的局限性。对原文的理解和阐释,不是一个译者一次就能彻底完成的。尤其是艺术个性强的原作,往往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一代又一代译者不断去挖掘。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一部作品可以同时拥有多个译本,或者不同的时代会不断出现新的译本。
其他差异如文洁若的译本有注释,楼适夷的译本无注释。这是由于文本中出现了一些带有文化色彩的词汇,需要解释才能被一般读者理解,如市女笠、乌帽子等。这些注释的标注加大了译文的文化含量,使译文很丰富。而楼本用语本就通俗,也无需解释。此外,还有数词使用上的差异。文本中数词的表达很明确。而楼本却较模糊。
对同一部作品,译者不同,出现以上的差异充分说明了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它不只是一种语言的转换,它是包含了作家的主体性的,是有个性存在的。文学翻译的风格很复杂,它既有原著作家的风格,又有文学翻译家的风格,是两者加起来形成的风格。而正确传达原著的风格是翻译家首要的任务。原著作家的风格只有一个,而文学翻译家10个人就有10种风格。因此,一种原著,尤其是名著,应该容许有不止一个译者来译,让读者自由选择他所喜爱的译本。杨武能说:“译家失去了个性,不能发挥主体作用,何来文学,何来艺术,何来创作?果真如此,文学翻译岂不仅只剩下了技能和技巧,充其量只可称作一项技艺活动;译家岂不真成了译匠,有朝一日完全可能被机器所代替!”[2]24叶君健先生认为: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再解释”的过程:一部作品,在岁月演变过程中,在不同译者的笔下,可以被染上不同的颜色,呈现不同的面貌,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翻译不是‘复制’,它确实有‘再创造’的一面”[2]19。
从以上对《罗生门》两个中译本的比较可知,正因为不同的译本包含着不同的译者的个性,才造成不同译本差异的存在,使得不同译本的存在大有必要。一方面,不同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阅读不同的译本;另一方面,对译者来说,不同的译本可使其更深刻地理解原作,发现译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正确理解原著,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好的译本,并不断总结翻译经验,逐步繁荣翻译理论。
[1] 许钧,罗新璋,施康强,等.谈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A].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C].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 许钧.传统与创新——代引言[A].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C].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3]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文洁若,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
[4] 芥川龙之介.罗生门[M].楼适夷,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8.
[5] 李芒,许钧.翻译再现原作的再创作[A].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C].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白晨)
ComparisonbetweenTwoChineseTranslationsofRashomon
SHI Cai-xi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ebei North University,Zhangjiakou,Hebei 075000,China)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Ryunosuke Akutagawa’s masterpieceRashomon.The similarities show that literary translation cannot go away from the original text and it cannot “go beyond the truth”.The differences reveal that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re-creation and it must contai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Ryunosuke Akutagawa;Rashomon;not going beyond the truth;re-creation;subjectivity
I 0-03
A
2095-462X(2013)01-0024-03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4.C.20130109.1026.018.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3-01-09 10:26

师彩霞(1971-),女,河北康保人,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西方文学与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