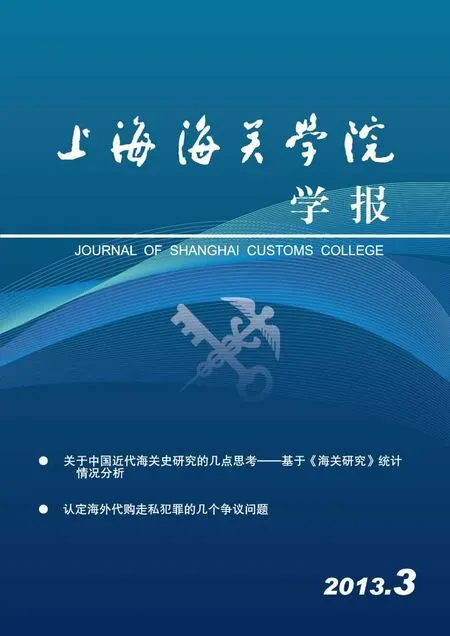外交保护与国际组织职能保护的比较分析
殷 敏
根据传统理论,国家对于在国外的本国国民行使外交保护,是国家基于属人管辖权而产生的一种权利,是国家的主权权利,因此外交保护也就是国家的主权行为。*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国家一经接受对本国国民的案件行使外交保护,就不是作为私人的代理人行使私人对东道国的请求权,而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行使国家本身的国际法上的权利。然而,对于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来说,除了本国可以对其行使外交保护权外,其所在的国际组织是否具有独立的赔偿请求权,这也就是国际组织对其工作人员的职能保护,它对传统国际法提出了挑战。
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委员会在就外交保护专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几次提到了国际组织的职能保护。但是关键问题是该问题是否应当放在外交保护的条款草案中来解决?如果是,又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加以解决,以及如何解决?委员会据此提出了若干条款草案,试图涵盖这一特殊关系引发的所有问题,*A/CN.4/538,p.8.下文将探讨外交保护与国际组织职能保护两者的关系。
一、国际组织职能保护的概念
梁西教授的《国际组织法(总论)》中认为:“从法学角度来解释:国际组织是国家间进行多边合作的一种法律形式。”*梁西:《国际组织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在该定义中所提及的“国际组织”,是从(国际)法的角度着眼的,因此它仅指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GO),即“若干国家(政府)为特定目的以条约建立的各种常设机构”,*同注③,第4页。这也是狭义的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广义上,国际组织可以包括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也认为:“国际组织即为政府间之组织。”*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一)(壬)规定:“称‘国际组织’者,谓政府间之组织。”
一般来说,国际组织的职能保护是指政府间组织对其工作人员的保护。*A/CN.4/538,p.8.此处关于国际组织职能保护的定义中的国际组织显然也只限于政府间国际组织,所以本文所研究的国际组织的职能保护就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其工作人员的职能保护。它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在国际组织内,通过建立行政法庭*一般来讲,国际组织的行政法庭是由本组织的权力机关设立的,并不是一个咨询机关或辅助机关,而是一个具有独立裁判权的国际司法机关。其职能仅限于处理组织系统内部机构与职员间的内部纠纷,例如有关任命、雇佣合同以及退职、退休和其他福利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其职能具有专门性,管辖范围具有特定性,在行政法庭的诉讼中,原告只能是受雇佣的国际组织工作人员,被告却总是以行政首长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由此观之,国际行政法庭与审理国际间诉讼的国际法院是不同的。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大会在1949年设立的联合国行政法庭。根据有关规定,联合国的职员在内部投诉程序已经全部使用后,便可向行政法庭起诉。行政法庭在接受案件并进行审理后作出的判决具有约束力。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法院起到审查行政法庭作出的判决的上诉法院的作用。比如,1955年联合国大会修订了国际法院规约,根据规约的规定,诉讼当事者任何一方,可在法庭作出裁决后的三十天内提出异议,将案件提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是有拘束力的,咨询意见一经发表,秘书长可使咨询意见付诸实施,或者要求行政法庭进行复审,作出与咨询意见相一致的新裁决。尽管如此,在国际实践中只发生了几起向国际法院上诉的案件,例如,1972年联合国行政法庭158号判决审查案、1981年联合国行政法庭273号判决审查案和1984年联合国行政法庭333号判决审查案,等等。http://www.icj-cij.org/icjwww/idecisions.htm,2005年8月18日访问。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对外方面则是通过国际组织独立地对其职员行使类似于外交保护的方式来实现。*由于对外方面可能与外交保护发生冲突和重叠,所以这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对于国际组织职能保护的对内方面本文将不作赘述。
二、国际法院1949年损害赔偿咨询意见——国际组织职能保护的实践问题
1948年9月间,联合国派往巴勒斯坦作为调停员的意大利人贝尔纳多特在执行职务中在耶路撒冷被犹太族恐怖主义团体暗杀。当时以色列国已经成立,但尚未加入联合国,出事地点耶路撒冷处在该国控制之下。联合国在对贝尔纳多特的家属给予抚恤金后,意图向对该暗杀行为负责任的以色列政府要求赔偿。但是,由于这种要求在国际法上究竟有无理由尚存疑问,联合国大会遂于1948年12月3日做出一项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此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就此案在其1949年损害赔偿咨询意见中认定,联合国是一个“国际人”,即“是国际法的主体,能够拥有国际权利和义务,并有通过提出国际赔偿要求而维护其权利的行为能力。”*国际法院:执行联合国公务时受损害的赔偿咨询意见,《194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79页。法院提出的理由是:为了使工作人员能够很好地履行职责,工作人员必须感觉到本组织已保证要向他提供这种保护,而且这一保证是可以信赖的。为了确保工作人员的独立性,以及本组织本身的相应独立性,该工作人员在其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必再依赖本组织提供的保护之外的任何其他保护(当然,其所在的国家理应给予的更直接和迅速的保护除外),这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他应当不必依赖自己国家的保护。因为如果他不得不依赖自己国家的保护,就很可能有损于其独立性,有悖于《联合国宪章》第100条*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100条:(1)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之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对本组织负责;(2)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之专属国际性,决不设法影响其责任之履行。规定的原则。最后,不管该工作人员属于一个强国还是一个弱国;不管他的国家受国际活动的影响程度如何;也不管该国是否赞同该工作人员的任务,该工作人员都应当知道,他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受到本组织的保护,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这名工作人员是无国籍者,那么这种保证就更有必要。
“通过审视本组织的职能特点及其工作人员任务的性质可以清楚看出,本组织对其工作人员进行某种程度职能保护行为的能力,是《联合国宪章》中的必要意旨所赋予的。”*同注④,第183-184页。
法院最后主张:“若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责时受到损害并且涉及某会员国的责任,那么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有权对负有责任的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政府提出国际求偿,以便联合国〔和〕……受害人或与其有关的其他享有权利者所受的损害能够得到赔偿。”*国际法院:执行联合国公务时受损害的赔偿咨询意见,《194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87页。可见,上述咨询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似已综合地吸收了国际组织法律人格学说中的“约章授权论”*“约章授权论”,认为只有在组织约章中明确赋予国际组织以国际人格的情况下,这种法律人格才存在,按这种观点推论,凡没有在组织约章中明确规定的国际组织,不得享有国际人格,这无异于否认了现今国际组织的大部分不具有国际人格。因为在实践中,通过组织约章明确授予国际人格的情况始终是少数例外,而不是一种规则。与“隐含权力论”*“隐含权力论”,认为联合国除有宪章所明确规定的权力外,按宪章含义得行使为执行其职能所必需享有的隐含权力。例如,联合国对其工作人员得行使外交保护权;联合国大会有权设立行政法院(其裁判对联合国本身有拘束力)等等。两种主张的某些合理因素。
这个案例就从实践上引发了国际组织职能保护和外交保护的关系问题。但两者的区别是什么?联系又是什么?发生冲突时,如何解决?下文将结合国际法委员会在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第四部分的相关条款来试图阐明因这一关系引发的所有问题。
三、国际组织职能保护与外交保护的区别
《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23条规定:“这些条款*这些条款指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概不影响一国际组织对受到一国国际非法行为损害的工作人员行使保护*即是指国际组织对其工作人员的职能保护。的权利。”*A/CN.4/538.从这一条款中可以看出,外交保护与国际组织职能保护是有区别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目的不同
外交保护的目的是确保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受到损害后能够获得赔偿,其依据的原则是,对国民的损害即是对国家本身的一种损害;而职能保护是一个国际组织通过确保对工作人员的尊重来促进其运作效率的一种方法。
鉴于这种区别,国际法委员会和联大第六委员会*2002年和2003年,第六委员会代表在关于国际法委报告的辩论中发言时表明了这一点。认为,一个国际组织对其工作人员的保护不属于关于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内容。
(二)研究范围不同
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上一个传统的概念,它的研究范围比较成熟和稳定;而在职能保护方面,有许多问题有待回答,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国际组织的哪些工作人员有资格获得保护?*M.J.L.Hardy,“Claims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spect of Injuries to their Agents”,(1962)37 BYIL 516,p.522-523.对哪些国际组织适用?是仅适用于联合国,还是适用于所有的政府间组织?是否仅适用于在履行公务过程中所受的损害?*See M.J.L.Hardy,supra note 5,p.521、523.一个国际组织是否有保护其工作人员的义务?*《国际法案件汇编》(1970年),第301页。受损害的工作人员是否必须首先用尽当地补救办法?*M.J.L.Hardy,“Claims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spect of Injuries to their Agents”,(1962)37 BYIL 516,p.526.能否针对受损害的工作人员的国籍国提出职能保护?*国际法院在损害赔偿案中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执行联合国公务时受损害的赔偿咨询意见,《194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86页。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外交保护所不能解决的。另外,国际组织职能保护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很难找出这方面任何明确的习惯国际做法。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国际组织的职能保护应采取独立立法,确定其特殊的规则。
四、国际组织职能保护与外交保护的冲突
《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25条规定:“这些条款概不影响一国对在一国际组织工作的本国国民〔在该组织不能或不愿为此人行使职能保护时〕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A/CN.4/538.
虽然我们认为国际组织对其工作人员的职能保护不属于外交保护直接研究的范围,但是一个主权国家可否对其在一个国际组织工作的本国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问题显然属于本研究的范畴。从国际法委员会*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号》(A/57/10),第118至149段。和联大第六委员会的辩论*2002年和2003年在第六委员会就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时,有人表示支持审议这项专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一)冲突的出现
国际法院在答复损害赔偿案咨询意见时,从一开始就确认,对联合国工作人员(并非被告国的国民)的损害可造成“国家外交保护权与国际组织的职能保护权之间出现竞争。”*国际法院:执行联合国公务时受损害的赔偿咨询意见,《194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85页。“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法律规则说明何者优先,或强求国家或国际组织不要提出国际求偿。法院不能理解有关各方为何不能凭借诚信和常识找出解决办法,而对于该国际组织与其会员国,法院提请会员国有义务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5款‘尽力予以协助’。”*《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5款:“各会员国对于联合国依本宪章规定而采取之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各会员国对该国不得给予协助。”
具体来说,“可通过一项一般的公约或针对每一个特定案件签署协议,减少或消除国际组织与国籍国之间出现竞争的风险。毫无疑问,国际惯例到一定时候将会形成,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家已经在本国国民为国际组织执行任务而受损害时显示出了找出务实解决办法的合理的合作意向。”*同注④,第185-186页。
法院接着谈到工作人员为被告国国民时可能出现的问题。法院就此提出: “一国不为本国国民针对将此人视为自己本国国民的国家行使保护的通常惯例,在此不能作为有意义的先例。”事实上,该组织采取行动的依据并非受害人的国籍,而是他作为该组织工作人员的地位。因此,被求偿国将此人视为本国国民与否无关紧要,因为国籍问题对可否受理求偿没有关系。
多重求偿并不构成一个严重问题。法院在损害赔偿咨询意见中指出,*同注④,第186页。这并非新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各国际法庭在处理涉及双重国籍国民的相竞外交保护权利要求方面已有经验。这方面适用的重要原则是,不应由被告国重复支付损害赔偿——这项原则已得到法院*同注④,第186页。的认可。因此并无充足理由说明为何要将多重求偿列入有关职能保护与外交保护相竞求偿的条款中。
(二)冲突的解决
1.确定职能保护的适用范围
解决职能保护与外交保护冲突的最有效、最明确的办法无非是订立准则,明确规定职能保护可适用于哪种工作人员,并进一步确定有资格获得此类保护的职能特征。这样可以将职能保护局限在明确划定的界限内。只有处于界限内的个人和行动才有资格获得职能保护,而界限以外的个人和行动只有资格获得外交保护。这样就可以消除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使其得到调和。但实践中,按此界限对这两种制度进行明确区分并非易事。
国际法院在上述损害赔偿咨询意见中的裁决没有就此专题给予明确指导。关于谁是工作人员的问题,法院指出,“非常宽泛地理解‘工作人员’一词,也就是说此人是该组织的一个机关委托履行或协助履行它的一项职能的任何人,不管是否向他支付薪酬,也不管是否予以长期雇用——简而言之,就是该组织通过其发挥作用的任何人。”*国际法院:执行联合国公务时受损害的赔偿咨询意见,《194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77页。在损害赔偿咨询意见中,Azevedo法官在他的单独意见中强调,对“工作人员”一词可作不同解释。他认为,“工作人员”包括该组织直接任命的任何国籍的官员或专家,但不包括会员国的代表或在顾及国籍的情况下任命的专家。*同注①,第195页、218页。根据这种解释,“工作人员”是否包括联合国直接任命的任何国籍的特别报告员,但不包括大会在地域分配作为一种相关因素的选举中选出的国际法委员会成员?这个问题表明了“工作人员”一词所具有的不确定性。
关于哪类职能应予保护的问题,必须回顾,在该损害赔偿咨询意见中,法院关心的是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直接受到的损害。Kerno博士在为联合国争辩时对这一点作了强调。他着重指出,联合国并没有要求为其官员取得支持求偿的一般权利,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对于因公受到的损害的有限权利。*《国际法院诉状》,1949年,第65页。法院所考虑的仅仅是工作人员的公务:“该组织可能认为需要、而且事实上已经认为需要委派其工作人员在世界的动乱地区执行重要任务。许多任务从其本质来看,会使工作人员遇到一般人不会遭遇到的非同寻常的危险。”*同注①,第183页。综上,可将法院的意见理解为下列主张的依据,即联合国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受到损害时拥有保护权,但这不包括在从事一些私人活动时受到损害的情况。不过,这项意见没有考虑到公务的外部界限。
但是对属于执行公务范围内的行为的限制问题也有很大争议性。例如,如果一工作人员的房东因其不缴房租气愤不已,冲进他的联合国办公室向他开枪,联合国可否行使职能保护?如果房东在家里将他打死,情况是否不同?职能保护的范围是否涵盖联合国官员在带薪假期所受的损害?这种情形是否包括执行特派任务的联合国官员在餐馆遭到反对所在国政府、但并不反对联合国的恐怖主义分子杀害的情况?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国际法院在该咨询意见中提出,“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就对其工作人员造成的损害提出赔偿要求时,赔偿要求只能以违反了对联合国承担的义务为依据。”
鉴于“工作人员”一词的含义和公务范围不确定,如草拟一项条款,大意是:一国际组织可对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受到的损害行使职能保护,而此人受到的所有其他损害属于外交保护的范围,这样做似乎不够明智。*大韩民国代表2003年在第六委员会提出了大意如此的提议(A/C.6/58/SR.16,第81段)。但这样一项条款不仅会由于不确定原因而存在漏洞,而且它还会侵入职能保护领域,而一般认为职能保护应当属于另一项研究的范畴。
2.协商解决
国际法委员会也可以通过一项条款,将括号中认为职能保护优先的文字删除,仅确认职能保护也是一种可能时国家有权行使的外交保护。这样做将符合国际法院在损害赔偿咨询意见*国际法院:执行联合国公务时受损害的赔偿咨询意见,《1949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85、188页。中采取的态度,即“没有任何法律规则指定一种‘索赔要求’对另一种享有优先地位”,应由有关各方依靠“诚信和常识”,通过谈判和协议调和相竞的求偿。
这种务实态度*2003年第六委员会就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时,德国代表提出了一项纳入优先原则的务实建议: “对于工作人员的国籍国和该组织之间相竞外交保护权的冲突问题,应采用务实做法。德国认为,由于外交保护涉及到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权利,决定性标准应当是国际不法行为主要针对有关组织还是工作人员的国籍国。但是,如受损害最深的一方不能或不愿行使外交保护,则受损害较轻的一方,无论它是组织还是国家,都应有权行使外交保护权”(A/C.6/58/SR.14,第61段)。有一定可取之处,因为在实践中,相竞求偿是通过谈判加以调和的,而且目前尚没有有记录的案例表明国际组织与国籍国之间可能的冲突已演变为现实。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若在两者之间不订立优先原则,那么这项条款对现有法律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内容,它只是在重述显而易见的情形,事实上可以全部删除。
3.发生冲突时,职能保护优先
使相竞赔偿要求相调和的第三种办法是在职能保护与外交保护两者相冲突时,优先考虑职能保护。Clyde Eagleton是这一观点的首要倡导者,他在1950年《海牙讲义集》*Clyde Eaglet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Law of Responsibility, vol.76,(1950), Recueil des Cours ,p.361-363.中,提出了优先考虑联合国赔偿要求的理由:
(1)联合国必须能保护自己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只是因为联合国才要冒受伤害的风险,因此联合国应承担保护工作人员的责任。该组织必须能向其潜在的雇员表明它愿意提供保护,而且这种保护不能留给国籍国,因国籍国并非始终愿意或能够提供有效的保护。
(2)鉴于所涉的费用、国籍国可能不熟悉案情,以及可能损害与被告国的关系等原因,国籍国往往不愿坚持求偿,“如果能解除这一负担,可能更感到高兴”。
(3)被告国、特别是被告的小国,往往喜欢同联合国而不是另外一个国家(尤其是更强大或蛮横的国家)打交道。
(4)工作人员本人总是希望由联合国而不是其国籍国求偿。往往不清楚国籍国是否会行使外交保护,也不清楚如果行使的话,鉴于政治上的考虑,国籍国将在何种程度上支持个人的求偿案。此外,特别是小国无法发挥像联合国那样的政治影响力,或得到同等程度的公众注意和同情。
(5)《联合国宪章》第100条规定,联合国工作人员效忠该组织,不得接受其国籍国的指示。有鉴于此,工作人员与联合国之间的联系比与其国籍国的联系更紧密、更相关。
(6)国际法要求对官员的保护应比对私人的保护更尽责。为此原因,受损害的个人往往愿意让联合国而不是自己的国家提出赔偿要求。
(7)联合国“是比其任何部分都重要的一个整体”。因此,以《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联合国宪章》第103条: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类推,联合国的利益在与会员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联合国的利益应得到优先考虑。
Eagleton提出的联合国可优先提出赔偿要求的论点确实有某些道理,但是这些论点是否同样适用于其他国际组织尚不明确,因为这些论点有一些所依据的是《联合国宪章》这部比通常建立国际组织的条约更高一级的法律。此外,联合国在实践中也没有实行优先原则的佐证。尽管如此,《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25条括号部分列有国际组织保护工作人员的权利要求优先的原则。括号中文字的效力是使国际组织有机会先对不法行为国家提出行使职能保护的权利要求,但该组织往往由于若干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例如,“工作人员”可能不具备受保护的资格;损害行为可能发生在执行公务范围以外;该组织的章程可能在一般情况下或针对某一案情不承认职能保护等等。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作人员国籍国决定给予外交保护,则国籍国的剩余权利就会生效。
五、一点补充和说明——关于一国针对一国际组织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
《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24条规定:“这些条款概不影响一国针对一国际组织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A/CN.4/538.
1962年,Jean Pierre Ritter写道,“国家可否代表国民针对国际组织行使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中探讨得最少的领域。*“La Protection diplomatique à l’égard d’un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e”,(1962) 8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p.454-455.(转引自A/CN.4/538)四十年后,Karel Wellens评论说,Ritter的看法“今天仍适用,因为这方面的国家实践非常罕见,判例法也没有明确处理行使这种权利是否可行的问题。”*Karel Wellens,Remedies again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74.
因此,这个问题在实践上的研究价值并不大,但从理论上来说,它显然是一个与外交保护有关的专题,但它似乎属于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研究范畴,因为其主要涉及归因、责任和赔偿等问题。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最好是在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研究中审议这一事项,而不需要在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中加以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