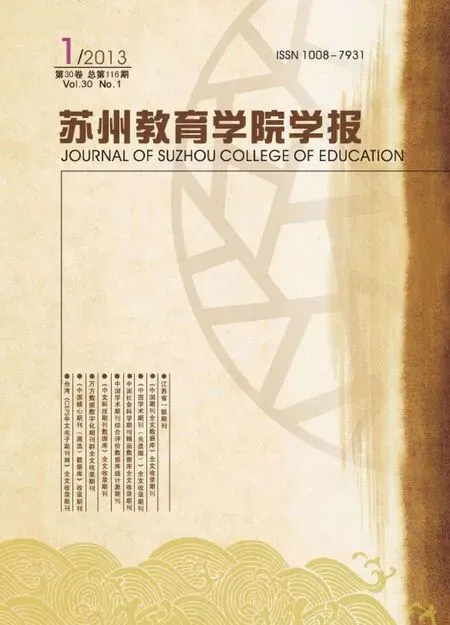先秦两汉文献中伍子胥故事及其形象流变
熊贤品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伍子胥是先秦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对于其形象的演变,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多为一些演变的梳理,而未注意到“忠孝”等社会观念的变迁对伍子胥故事的影响,且一些新发现的材料也未被运用。本文试就这些问题略抒己见。
一
先秦文献中关于伍子胥的记载较为简略,主要见于《左传》《国语》《楚辞》及先秦诸子的书中。如《左传·昭公二十年》通过费无极的叙述从侧面表现了伍子胥的军事才能:
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1]610
其后,又从正面记载了伍子胥对于军事策略的见解,《左传·昭公三十年》曰:
吴子问于伍员曰:“……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1]662
上述记载,肯定了伍子胥的见解对吴国军事上强大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左传》哀公元年和哀公十一年中,还记载了伍子胥进谏夫差反对与越讲和及伐齐而不被采纳的故事,这些都表明了伍子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卓越才华。《国语》中所记有关伍子胥的内容与《左传》大体相同,只是在《吴语》篇中对比记载了吴王的刚愎自用与伍子胥的刚烈:
夫差将死,使人说于子胥曰:“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遂自杀。[2]
表现了伍子胥的忠诚、刚烈,从而凸显出伍子胥担忧国家前途的忠臣形象。
先秦诸子著作中另有一些关于伍子胥的记载,使伍子胥的故事及形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韩非子》一书,如《韩非子·说林上》:
子胥出走,边侯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侯因释之。[3]190
这一故事为《左传》《国语》所无,它展现了一个机智而富于才能的军事将领形象。此外,《吕氏春秋·孟冬纪·异宝》的记载,则充分刻画了伍子胥的仁义形象:
伍员亡……解其剑以予丈人……丈人不肯受……伍员过于吴,使人求之江上则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4]
《楚辞·九章·悲回风》记载了伍子胥是死于江上:
浮江淮以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
出土文献中也有关于伍子胥的记载,如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第9至第11简曰:
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遇与不遇,天也。[5]
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简五《鬼神之明》曰:
及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6]
顾颉刚先生曾指出,先秦时期的“圣”主要指能力上的突出,并不具备后世的道德意义。[7]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材料,反映了时人充分肯定伍子胥的突出才华及对其不能得到君主任用的反思。
在秦汉时期文献的记载中,伍子胥的故事及形象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以《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最为重要。《史记》所载伍子胥的故事情节进一步完善,对伍子胥的形象有较为丰富的刻画,成功地塑造了伍子胥的“烈丈夫”形象,体现出坚忍、刚烈等鲜明的特点。司马迁还对比了白公胜与伍子胥复仇的不同:白公胜在面对仇敌而不能复仇时,转移怨气而大开杀戒,不能等待时机以求报,甚至有迁怒之嫌,以至于最后事败身亡;而伍子胥在最初游说吴王伐楚被驳回时,就隐居于野而等待机会。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8]
在《越绝书》中伍子胥的忠义形象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而在《吴越春秋》中则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位集文武双全和忠孝节烈于一身的神化英雄。[9]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伍子胥还被当做水神来祭祀,如《史记·伍子胥列传》:
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8]
《越绝书》卷十四有伍子胥死后变为水仙的描写:
胥死之后,吴王闻,以为妖言,甚咎子胥……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10]
《吴越春秋》中的记载更加典型:
(越军)入胥门,来至六七里,望吴南城,见伍子胥头,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越军大惧……范蠡、文种乃稽颡肉袒,拜谢子胥,愿乞假道。[11]
这种变化应该与吴越地区多湖泊有关。早期吴越先民大体以自然性水神为崇拜对象,而从汉代开始将伍子胥作为水神来祭祀,表明其时吴越地区人们的信仰状态逐渐由自然神崇拜转向人格神崇拜。[12]
二
“伍子胥故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颇有影响的叙事传统,相关内容从先秦文献到明清戏曲中一直延续不断。如上所述,其中一些基本因素及其变化已经见于先秦两汉文献的记载中,而这一变化,笔者认为主要与如下两个方面有关。
其一,“孝亲”与“血亲复仇”。先秦时人们认为应当孝亲,因此不仅重视孝祭已故祖先,也善待长辈。如《多父盘》曰:
用锡屯录受介福,用及孝妇娌氏百子千孙……多父其孝子作其宝盘,子子孙孙永宝用。
此外,在一定程度上,先秦时期人们认为如有家仇则必须复仇。统治者对于作为伦理道德义务的“血亲复仇”也给予宽赦。《礼记·檀弓上》载:
子夏问于孔子:“居父母子仇如何?”夫子曰:“寝苫,枕干,弗与共天下也。遇之市曹,不反兵而斗”。曰:“请问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陪其后。”[13]
这里阐发了对不同的“血亲复仇”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表明了当时人们对“血亲复仇”的推崇。
其二,“忠孝”冲突。先秦至于两汉时期,“忠”的内涵及其与“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先秦时期“孝”的观念更为突出,虽然传世的先秦文献中的“忠”见于《左传》等一些书籍,而出土文献中所见的“忠”则不见于春秋以前,故“忠”的观念可能较为晚出。先秦时期 “忠” 的观念与后世有所不同,从传世文献来看,此时期“忠”的观念较为广泛,如《论语》中的 “忠”,泛指待人接物的基本之道;而《左传》中的“忠”则有对民负责、守官尽职等内容。从出土文献可以看出,“忠字在战国时期金文及玺印文里始见……‘忠’的语义概念是在战国时期才产生的。‘忠’字由本义内心适中,引申为秉公忘私尽力效力,又引申出对君长尽心忠诚,并由此发展成为道德意义的‘忠’的观念。”[14]
在先秦时期,君臣关系相对平等,《论语·八佾》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就强调了忠君是相对的,是在“君使臣以礼”的前提下进行的。《孟子·离娄下》载,孟子曾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中晏子也曾对齐景公说过:“今君临民若寇仇,见善若避热,乱政而危贤,必逆于众,而诛虐于下,恐及于身。”这些都表明,先秦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后世并不完全一样。
先秦两汉时期的思想家大都认可伍子胥“忠”的精神。《荀子·大略》曰:“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鹖冠子·备知第十三》曰:“比干、子胥好忠谏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史记·张仪列传》记载了陈轸对伍子胥的评价:“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但从秦汉时期开始,随着中央专制政治的加强,狭义的“忠”即指忠于君主。因此,在先秦时期舍“忠”就“孝”之事较多,而从秦汉开始则多舍“孝”就“忠”之事。[15]随着时代的变迁,原本蕴涵于伍子胥故事中并不明显的“忠孝”冲突却在汉代开始凸显,使得秦汉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再像先秦时候那样忽略这一问题:一方面是伍子胥富于才能和忠诚而不被任用,使其显得悲壮;同时又必须合理解释作为“烈丈夫”的伍子胥的“鞭尸”之事。《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均记载了其“鞭尸”故事。对此,后世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或以为是鞭坟,或否定“鞭尸”和“鞭坟”两说。[16]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楚国之败是由于其国君的暴虐,《春秋繁露·王道》即曰:
楚平王行无度,杀伍子胥父兄……吴王非之。举兵加楚,大败之……贪暴之所致也。[17]
《公羊传·定公四年》载:
曰:“事君犹事父也,此其为可以复仇奈何?”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旬,古之道也。”[18]
可见,时人认为替受冤枉的亲人复仇是应尽之责,不应受到惩罚,从而许可了这一复仇行为。在这里,“忠”和“孝”得到了合一。这表明在秦汉大一统局面下,“忠” “孝”不可避免对立的问题日益需要加以合理解释,而这一时期又恰巧处在专制权力的初期阶段,“忠”尚未能全面超越“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伍子胥的故事成了一个具有强烈冲突而又被合理解释的特例。
此外,以伍子胥为代表的忠臣进谏而不被采用,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难题,这在《庄子·盗跖》中被称为 “忠之祸”:
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19]
《韩非子·人主》以伍子胥为例,强调了君主应该能任贤,避免“忠之祸”的发生:
故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奚时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为人臣非不忠,而说非不当也,然不免于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贤智之言,而蔽于愚不肖之患也。[3]586
由此可见,伍子胥故事也表达了古代忠臣呼唤明主进而得到重用的思想,这亦是伍子胥悲剧故事的意义所在。
[1]左丘明.左传今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左丘明.国语[M].焦杰,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145.
[3]陈维礼,张桂兰,王月清.《韩非子》译注[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4]吕氏春秋[M]//齐豫生,夏于全.中国古典名著.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50.
[5]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145.
[6]马承源.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16.
[7]顾颉刚.顾颉刚经典文存[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35.
[8]司马迁.史记[M].易行,孙嘉镇,校订.北京:线装书局,2006:293.
[9]曹林娣.论《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形象塑造[J].中国文学研究,2003(3):31-33.
[10]张仲清.越绝书校注[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335.
[11]赵晔.吴越春秋[M].徐天祜,音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66.
[12]蔡丰明.吴越地区的水神信仰[M]//越文化与水环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8.
[13]陈澔.礼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0.
[14]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阐释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39.
[15]岳庆平.中国的家与国[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104.
[16]张君.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3):74-77.
[17]阎丽.董子春秋繁露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61.
[18]齐豫生.春秋公羊传[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133.
[19]庄子[M].韩维志,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