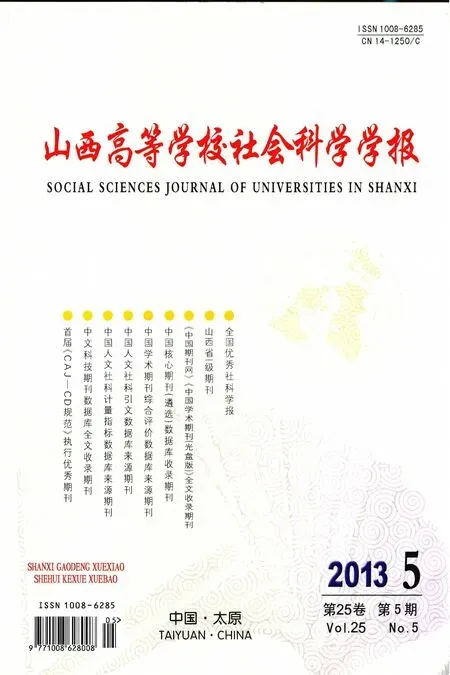论《桃花扇》侯李爱情结局的处理得失
胡伟栋
(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清代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是明清戏曲的压卷之作,最后的结局,是侯方域和李香君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种种磨难后,偶然重逢,本应是破镜重圆,扇缘再续,偕老白头的一对有情人,却因张瑶星道士喝斥,双双入道。这种结局,一直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论者多以以偏概全的观点或褒或贬。对于《桃花扇》的结局,我们应该客观、全面地分析孔尚任这样安排的得失及原因。
一
悲剧结局打破中国文学传统的大团圆模式,具有开拓意义。《桃花扇》原批中谈到:“离合之情,兴亡之感,融洽一处,细细归结,最散、最整、最幻、最实、最曲迂、最直截,此灵山一会是人天大道场,而观者必使生旦同堂拜舞乃为团圆,何其小家子样也!”[1]这段话表达孔尚任对戏曲小说传统的大团圆模式的反对。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2]胡适也曾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结局。”[3]翻开元杂剧的历史,就连《窦娥冤》《赵氏孤儿》这样最具有代表性的悲剧作品,结尾为了满足观众大团圆心理,都带有光明的尾巴。《窦娥冤》中的窦娥冤情得以昭雪,坏人最终被绳之以法,这种结局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冲淡了悲剧效果。《赵氏孤儿》中的孤儿长大后报仇雪恨,奸佞也最终被诛,正义战胜邪恶,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但其中包含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思想,使得作品悲剧震撼力大打折扣。即使《牡丹亭》《长生殿》这样的名作,也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因为它们的结尾都带有“大团圆”的色彩。《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为情死而复生,柳梦梅考中状元,皇帝下旨完婚,爱情终获胜利。《长生殿》中李杨二人跨越了生死,精诚不散,至月宫团圆,终成连理。以这种虚幻荒诞的结局补偿观众期待的团圆心理,终究是缺乏彻底的悲剧意识。
《桃花扇》的最后结局是侯李经历了离乱之后,邂逅在栖霞山下,团圆之际,张道士断然喝问:“两个痴虫,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父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4]285这一番话,说得侯李“冷汗淋漓,如梦初醒”[4]285,最终二人双双入道。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孔尚任安排这样的结局,就是把爱的希望与价值生生地剥夺,给人一种彻底无望的感觉,给那些苟活者以当头棒喝,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展现出敢于创新的精神与气魄,令人耳目一新。
二
悲剧结局符合创作主旨,深化了主题,升华了爱情,加深了全剧的悲剧意蕴。孔尚任为什么安排这样的悲剧结局?根本的原因是由其创作主旨决定的。《桃花扇》中《试一出·先声》中说:“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4]2,要使得人们“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4]1作者用“借”和“写”,道出了侯李爱情只是个表象,是一条副线,南明王朝的兴亡之感才是深层次要表达的,是创作主旨。也就是说,作者以侯李悲欢离合的爱情为依托,牵带出种种政治矛盾以及所引发的斗争,反映出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复杂的矛盾斗争,引发出了南明王朝兴亡的全过程,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就沿着侯李爱情这个载体展开并逐步体现。南明王朝的结局决定了侯李爱情必然是以悲剧收场,这两者应该是相一致的。倘使安排侯李团圆,就淡化了亡国之痛的感受,与全剧所要表现的主题出现了矛盾。因此其结局借用张道士的喝问使得侯李二人幡然醒悟,双双入道,那血染的桃花扇本是侯李爱情永恒的象征,却顷刻间裂扇掷地,从此情缘断绝。二人以情殉国的勇气着实震撼人心,令人痛彻心扉,这样的悲剧结局强化了作品主旨的同时,也使得爱情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是一种因国弃情的自觉爱情意识,这也深化了全剧的悲剧意蕴,提升了作品的内涵,使得作品产生了超越时代的永恒魅力,因而在文学殿堂大放异彩。
三
悲剧结局的突兀性影响舞台演出效果。肯定悲剧结局的价值,并不代表以张道士的当头棒喝使得二人分离这样的安排是无懈可击的。戏曲作品最终是要在舞台演出的,从舞台演出效果来说,以这样的方式来收场,是观众难以接受的。诚然,作者表达兴亡之感是主线,但是毕竟是以侯、李二人悲欢离合的爱情为线索来贯穿的。观众在演出现场首先的感情关注焦点就是侯李爱情,无论是视觉上、心理上都是沿着侯李二人悲欢离合而起起伏伏的,而兴亡之感往往是过后深层次思考的问题。当情节跌宕起伏,长时间铺垫了二人历尽艰辛、思念着彼此,终于相遇于栖霞山白云庵,二人喜出望外,诉不尽的离情别绪,团圆顺理成章。突然间风云变幻,张道士走下法坛,撕碎维系两人的爱情信物——桃花扇,三言两语的喝斥,二人同时悟破,决然转身,断绝俗世的爱恋。这种草率的、不合常理的结局,让观众情绪突然遇阻,期待已久的感情无法得到宣泄,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困顿,致使他们对剧作产生疑惑。所以,从舞台演出的效果来说,安排这样突兀的结局,很难让人信服。与孔尚任同时期的顾天石改写的《南桃花扇》使男女主人公重逢后重温旧梦,以团圆结局。乾隆年间无名氏的《桃花扇》平话中,侯李二人庵中相遇,抱头痛哭,然后一起漂泊,最终隐居终南山。这样的结局一方面不符合孔尚任的创作意图,另一方面也落入俗套。我们也并非主张要写成大团圆的结局来满足观众。但是,至少可以证明这两个作者都看出了孔尚任剧作结局的舞台效果有不合理之处。
四
悲剧结局的突兀性与情节发展存在矛盾。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其来,倏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6]7双双入道的结局,确实是独辟蹊径,但这样的结局与情节的发展存在着矛盾。孔尚任在之前情节的铺垫中给观众造成了一种看似男女主人公必然要团圆的各种因素,在离散的岁月里,爱情成为二人精神的寄托,甚至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理由。香君守楼待郎君,为拒嫁田仰,不惜以头抢地,血溅诗扇,后又诚托昆生寻侯郎,忠贞不渝。方域手抚血扇,思念恋人。侯李从始至终对爱情非常渴望,丝毫没有入道的迹象。最后的结局却陡转急下,主人公在外力的作用下双双入道。情节的团圆因素与结局的突然入道,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矛盾,这种矛盾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使其感染力大打折扣。假如前面的情节铺垫没有团圆的因素,二人始终没有重逢,最终不得完聚,这样的悲剧虽然不能满足中国人普遍喜好团圆的心理,但是接受性肯定要好于人为斧凿的痕迹。
五
悲剧结局的突兀性有违人物自身性格的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物自身性格发展是需要有内驱力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入道是需要个体看破红尘的结果。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谈到《桃花扇》时说:“……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2]这段话是说侯李双双入道,并非真正的通过自身悟道而解脱。王国维的这个观点是很令人认同的。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两个人离散的岁月里,侯方域收到李香君寄来的诗扇后,一直坚持苦苦寻找所爱之人的下落,李香君也是以寻找侯方域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双方的心态可谓是积极入世,不管经历多少磨难,始终不放弃希望,对俗世的爱恋刻骨铭心,丝毫看不出有看破红尘之意。而结尾处,张瑶星突然出现,三言两语,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作者在此处夸大了宗教的作用,是不可取的,更重要的是用外力破坏的作用代替了人物性格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就连侯方域还反驳道:“从来男女室家,人之大伦,离合悲欢,情有所钟,先生如何禁得?”[4]285
艺术作品中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往往不受作家的控制,有内在的发展变化规律,而作家经常因为各种因素安排一个不符合人物性格命运发展的结局。现代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大陆写的《十八春》,后在美国期间改为《半生缘》,二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结局的处理上。《十八春》最后男女主人公投身新时期东北建设的政治色彩,淡化了爱情悲剧;而《半生缘》结局改为男女主人公邂逅,以一句平淡的“我们回不去了”而终止,又像两条平行线一样行走在不同的人生路上,生离等同于死别。这样的结局是作者的本意,也更符合人物性格命运的发展。反观《桃花扇》结局,显然是作者为了强化主旨而刻意安排了有违人物性格发展的结局,是存在不足之处的,我们应该客观对待。
再伟大的作品,也不会尽善尽美的,或多或少都有些“瑕疵”。《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遗失问题,一直是红学界争论的话题,金圣叹腰斩《水浒》也是看到了其结局的不合理之处。《桃花扇》侯李爱情结局,孔尚任处理成最终双双入道的悲剧,从整体上、宏观上看,打破生旦团圆的传统模式,具有开拓意义,贯彻了其创作主旨,深化了主题,表现了自觉的爱情意识,加深了悲剧意蕴,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虽说瑕不掩瑜,但突兀外力的介入而造成的悲剧,有其失误性的一面,使人难以信服,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这才符合文学批评的精神。
[1]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931.
[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红楼梦》之美学上价值[M]//王国维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10.
[3]胡 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M]//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61.
[4](清)孔尚任.桃花扇[M].唐松波,校注.北京:金盾出版社,2008.
[5]鲁 迅.坟[M]//鲁迅自编文集.北京:北京未名社初版,1927:203.
[6](清)孔尚任.桃花扇[M].贾炳文,任爱玲,评注.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10.
——从《桃花扇》序文看孔尚任创作心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