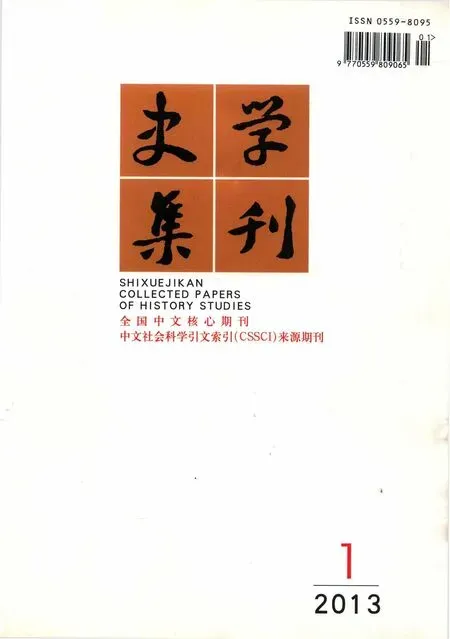古典史学的“现代”遗产——对古典史学与“史学现代化”问题相连接的思考
史海波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在对历史沉积下来的各种现实问题的反思中去探研域外文明,便不失古史研究的现代意义。现今,不论是在我们自身的智力操练和努力中,还是在政治、道德和教育方面的困境中,我们依然能从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中深受益处。①[英]G.E.R.劳埃德著,钮卫星译:《古代世界的现代思考》,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西方古典史学,是西方史学的发源之处,古典史学的优良特质,是西方史学长桥的坚实桥墩。一直到历史学引以为骄傲的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依然在“科学”的角度继承和强化古典史学的某些特定模式。
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实则异常繁杂而艰巨:在社会历次转型之后,古典史学留给现代化史学的到底是怎样一笔遗产?虽然众多研究历史哲学或者现当代史学的著述,多将渊源追溯到古典时代,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找到一个兼顾整体与细节的成熟答案。②在古典史学与现代史学的连接上,最值得参考的著作莫过于A.莫米格里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所著《现代史学的古典根基》(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但是作者着重探讨了古代史学自身的相互影响、衍生等古代史学自身的问题,对史学某些共性特征和理论问题关注不够,部分论断也缺乏缜密的逻辑分析。而类似于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的相关分析,又多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对于古典史学的细节无暇顾及。这里,我们首先要预想的不应该是答案本身,而是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可能要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首先是古典史学自身的特质。古典史学特质的确定性,应该在一种“比较”的意义上来定位。如果以较为原始而杂乱的古代近东的历史记录为背景,古希腊史学的优越性便凸显出来。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年代记,多彰显神祇权威和帝王伟业,其宗教与皇室特征一目了然。而最为不可取的,是亚述君王的各种年代记以及相关浮雕铭刻,其中常以对敌方残酷杀戮与侮辱为记述或刻画要务,诵读者只感其血腥与恐怖,无从思考其公允与客观。整体而言,古代近东各国,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念,其相关“历史”记录,更无严格意义上的体系与分类。
古希腊史学,在城邦体制化、民主化以及海外殖民运动的催促下,从一场声势巨大的知识革命当中诞生出来。到希罗多德那里,古希腊史学已有如下明显特性:历史记述的是人事,并且要在人类社会内部寻找事件的原因,历史记述有了固定的体裁。其中,可以在“现代化”史学意义上提及的,主要是古典史学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念和理性的批判方法。由于人本主义史观问题将在“文艺复兴”的相关分析中继续深入,此处,我们先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侧重于对后者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古希腊罗马史学是一个前后相继的整体,而且在理性认识和批判特性上,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后来的波利比乌斯乃至于卢基阿努斯,古典史学也体现了历史认识上的共性。
希罗多德善于提出诸多问题并津津乐道于各种有趣的传闻,这显然是在效仿自己的前辈荷马、赫卡泰戊斯等。但是其《历史》的开篇词已经别具动机:一是保存人类的功业,使其免受时间的破坏,二是记载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为此两种目的,进行“探询”已不可避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希罗多德赋予“历史”一词以真正的内涵。在转述了流行于腓尼基人和波斯人中间的关于战争缘起于希腊人和亚洲人之间互相劫掠妇女的传闻之后,希罗多德并没有直接判断它们的真伪,但是他表示出:宁愿依靠个人的知识来指出到底是谁事实上首先向希腊人寻滋闹事。①[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他实际上认为那些传闻没有一个值得相信。而接下来对战争原因的探询,比较漫长而富于理智,虽然他把笔锋游移在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和波斯等民族的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中,但是希罗多德从来没有在这些枝节旁生的叙述中偏离对战争原因的探询。另外,希罗多德也没有迷失在他所津津乐道的“传闻”当中。希罗多德所能使用的资料,更多的是一种“证词”,这种证词有目击者的证词,也有道听途说的证词 (传闻),对于这些证词,希罗多德制定了适用于全书的原则:如果读者是个轻信的人,便可以相信那些传闻,但是他不会为读者去判定真假。实际上,希罗多德在能够实施判断的地方,并不犹豫,直陈己见。在有些地方,他为了达到保存人类功业的目的,把关于同一事件的几种证词都收录下来。他甚至为了核实一些传闻的真实性去做实地的探询考察。
如果说希罗多德的这种对“证词”的批判方法还很幼稚,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几乎与希罗多德相对立而又极为成熟的意见:至于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各种事情,我认为在叙述它们的时候我的责任是不相信任何一个偶然的消息提供者的话,也不相信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情。我列举的事件,无论是我亲自参与的还是从其他与此有关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都经过了对每一细微末节精心备至的审核。②[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18页。这种要求近乎于苛刻,而且我们也有理由对修昔底德能否完全落实这一原则提出质疑。但是不论如何,修昔底德以一种超常的理智控制着战史的每一个角落:详尽的历史史实、精确的军需数字、细致的条约条款、事件背后的经济因素、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抽象不变的人性,还有风格雷同的演说词等等。我们感到,他不单在运用着理性批判的原则,还在进行一种庞大的理性建构。他的理性建构不单表现在对史实的处理上,还表现在对自身感情的控制上。在战争的第二年,他自己身染瘟疫,这种瘟疫给人带来极大痛苦并且几乎没有生存的几率。公元前424年安菲波利斯失陷,他被指控为驰援不利并被判处流亡海外20年。这些痛处,修昔底德只是用最简短而不带任何感情的文字一带而过。修昔底德便是用这种理性和批判,去书写一部旨在垂诸久远的信史。
修昔底德的历史理性与批判,基本代表了古典时代史学的最高水准。古希腊历史的这些认识方法,虽然还不成熟,但却指明了整个西方历史认识发展中不可回避的要求,即以一种有效的规则、模式或者理论来接受、揭示历史,并最终指导生活。③陈新:《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从这种意义上,古典史学影响的不是哪一个时期的哪一代史家,而是整个西方史学。
其次是古典史学和现代史学是如何承接的。这里面首先应该明确西方史学现代化的时间断限问题。“现代史”在西方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史学现代化自身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不是有“后现代史学”这个名词出现,我们只能认为史学现代化的进程依然继续。史学被赋予现代性的品质的过程是漫长的,我们不应该把眼光局限于18、19世纪。虽然启蒙时代对待文艺复兴复古大旗的态度也不是十分尊重,但是史学现代化的轨道的确毫无疑问地承接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陈迹。
A.莫米格利亚诺在其《传统与古典史学家》一文中,提出古典历史撰述的遗产之一就是如何根据传统来面对变迁。④参阅 Arnaldo Momigliano,“Tradition and the Classical Historian Author,”History and Theory,vol.11(1972),pp.279 -293。但是我们很难界定这种影响是否超越了古典时代。还有一种情况也需注意,即便我们知道古典史学具有精神特征的统一性,但是由于古典史学自身和诸多层面的知识相混杂,我们很难估算这些作品在后世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比如塔西陀的著述,或许我们很难想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利用了塔西陀在政治角度的叙述的特性,⑤参阅 Arnaldo Momigliano,“Tacitus in Renaissance Political Thought,”Classical Philology,vol.74(1979),pp.72 -74。而不是他赖以成名的犀利文风和道德垂询。除了文艺复兴之外,这些在后世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古典”,是否具有一种可以总结的特征?这种特征是否具有进步的现代意义?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关注和细化。从一般的情况看,我们可以在如下问题上确定古典史学和现代史学之间存在着承接关系:
1.古典著作对后世史学有体裁上的影响。传记这种体裁和关注人类“整体”事业的历史著作相比,更容易被改造利用,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传记的写作一直未有中断。只是这种影响为“史学现代化”增添的色彩有限,此处暂不多论。
2.博学派及其先驱者为历史走上专业化和科学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博学派在文艺复兴时期存在着更早的先驱者,最为著名的是洛伦佐·瓦拉,他对《君士坦丁赠礼》这份文件进行了颇有意义的证伪。实际上,除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人文主义学者对古典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以及考辨之外,博学派存在着更为古老的先辈,在中世纪,9世纪时期那温纳的阿格内卢斯写成《教皇本纪》,还有稍晚时期曼兹伯里著有《格莱斯顿教会古迹考》。这些著作,都是建立在对过去的文献和古迹的搜寻整理的基础之上。在罗马历史上,内战的动荡使一些学者到古代去寻找依托,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便有古物学家诺比里奥,搜求往昔关于国家要务以及执政官纪年的历书,汇编成册并公诸于世。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更是功不可没,而从根源上讲,希罗多德之前的那些散文记事家,可以算作最早的古物学家了。
当然,我们这里没有将文献学和考古学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只是在博学好古这个层面上把古代和现代连接起来。前代所有人的努力,才有可能为博学派把历史学改造成科学的主张和实践提供更为坚实的资料以及理论准备。
3.人文主义思想对古典人本主义的继承和发扬。文艺复兴时期有修辞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布鲁尼、奎恰尔迪尼,还有政治学派,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和中世纪的历史编纂相比,他们所著历史的最大进步之处便是又把“人”塑造为历史的主体。这种打着古典大旗的人文主义思潮,是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的有力思想武器。但是这种人文主义思潮,经过中世纪的沉积,面向着新兴资本主义的呼唤,已经被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赋予了和古典的人本观念不同的内涵。古典时代的体现在历史著作中的人性不变论、历史循环模式、“世界”历史眼界等问题,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编纂中自然有了不同的取向。而且,“人”作为历史主体问题,给后来的历史本体论遗留了一个课题,实证主义所创立的西方正统史学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当成是单一项度的政治人,这样,历史中“精英”便主宰了历史。正如帕雷托所言:历史是贵族的坟场!年鉴学派开始对此发动诘难,费弗尔强调了历史研究的“不是个别的人,重复一遍,绝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人类社会,是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①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
我们站在现代化的角度考察古典史学,不应该割断历史的发展,也不应该只关注古典遗产的优越性。我们可以反向考虑古典史学的缺陷,这种缺陷是否在社会转型当中得到了一种修正并作用于现代?中世纪时期所确立的线性时间观念和人类“整体”观念可以作为例证来分析。另外,史学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来自古代的促进因素,是不是超越了史学的范畴,哲学作为古希腊影响西方的最大遗产,完全可以作用于后来诸多层面的思想。这样,历史哲学便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巨大任务。我们所要时刻保持清醒关注的,便是古典的遗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史学现代化产生作用的多角度性。经过时代的多次转折,这种作用绝非直接,却异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