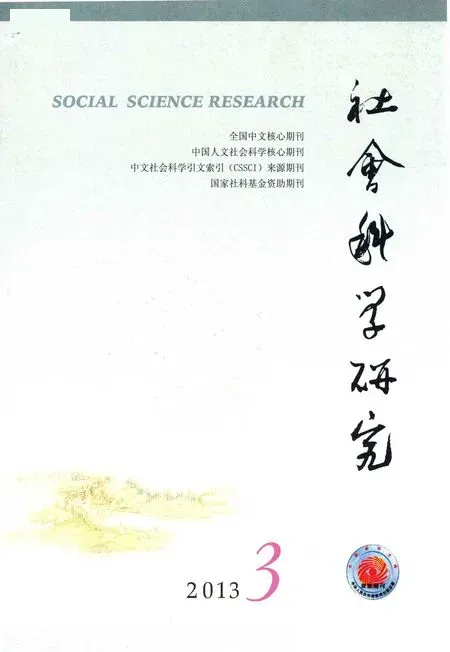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
常德荣
“士”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是参与国家管理和文明传承的特殊人群。南宋中期以后,数量庞大的中下层士人成为士的主要构成。他们逐渐由社会的中心走向边缘,从中央走向地方,从而游离于政治,活跃于“江湖”,士人群体发生深刻分化。①学界对南宋士人之分化已有注意,如王水照先生《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便有论及。伴随士人分化出现的游士、隐士诗人成为此期诗坛的重要主体,其诗学活动改变了宋诗的风貌。从士人分化这一角度考察南宋中后期诗坛,可从文化层面把握推动此期诗学演变的内在动因。
一、仕途拥塞引发士人的价值观新变
宋代是一个成熟的科举社会,科举是宋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所谓“朝廷取士舍科举之外无他法,士子进身舍科举之外无他涂”。〔1〕宋代庞大的士人群体,某种角度说正是科举制度所催生的。然而这一制度在南宋中期以后却出现了严重问题,锁院、糊名、誊录等规制形同虚设,各种舞弊行为迅速蔓延,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这引起当时官员的极大关注,《宋会要辑稿·选举》中保存了大量揭露科举弊病的奏疏,南宋人的文集中也有众多涉及这一问题的史料。科举制度的腐坏使士人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失去了改变社会地位的可能。醇厚学子很难脱颖而出,以至“远方孤寒,至有通榜无名者”〔2〕。时人对通身腐坏的科举制度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夺精失营者,莫科举之为累”〔3〕,有人则高呼取消科举重新实行荐举制。
从理论上说,科举对所有士人都是开放的、平等的,但实际上,能否参加科举、能否中第受诸多外在因素的限制。其中是否有雄厚经济实力做后盾,便是普遍性的制约因素。南宋大儒真德秀因为家贫筹集不到足够的费用,所以第一次赶考时“囊衣笈书,疾走不敢停。至都,则已惫矣”。第二次赶考时得到民间互助组织“过省会”及亲友的馈赠,才“舍徒而车,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试,遂中选焉”。〔4〕虽然没有明说经济上的拮据影响了科举“成绩”,但其言外之意显然包含了这层意思。参加科举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中第之后的各种应酬开支更是巨大。李昴英宝庆二年 (1226)中第后接连写了五通家书,除第一封专为报喜外,其余四封说的主要事项便是在京的各种应酬及其花费,其《第二家书》中所涉及的开支名目竟达13项之多。〔5〕以至他所带的盘缠不能应付,不得不向人借钱。可以想见,经济方面的原因在当时限制了相当数量的士人,使他们的入仕之路更加曲折。
入仕途径的异常拥塞,引发文士观念悄然改变。传统士人多强调对道义的秉持,羞于言利,耻于为商、为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信条,然而这种观念南宋中期以后却加速裂变。士人不再将入仕为官作为唯一人生准则,在他们看来凡是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都可心安理得地接受。士人观念上的新变在袁采《袁氏世范》中体现得集中且明显,此书为“家训”类著作,著述目的是教育子女如何为人处世以便使家族兴旺,因而书中所论不是即兴而发的随意说教,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思想观念。其卷中云: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仕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资,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6〕
袁采为士大夫 (即官员)子弟指出了多种立身门径。传统士人读书目的在于通过掌握“道”而实现其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袁采这里说的只有“能习进士业者”才符合这一要求,而“不能习进士业者”则失去了士的政治品格和思想品格,与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已有不同。而更具突破性的思想是:如果不能读书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皆可作为“士大夫之子弟”的选择。也就是说,凡是可以养家糊口的事业士大夫子弟均可为之,士人可以从事农、工、商、艺人之业,反之,这些人也可以成为士。《袁氏世范》成书之后,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发挥了实际影响。姚勉《孺人墓志铭》记其同年程澥的妻子谭氏“诵《袁氏世范》甚习”〔7〕;胡次焱在与人议论有关“过房”的问题时,《袁氏世范》中的观点也作为重要论据而被引用。〔8〕由此可见,《袁氏世范》中的观念得到了南宋中后期士人的广泛认可,其所代表的是一种普遍的思想,是对当时士人生活的总结与指导。观念的新变在当时学者大儒身上也有表现。陆九渊的重要弟子杨简,在富阳为官时援引“商人肥家”子弟入学,以至“文理稍稍即收之”,引导这些工商之人成为习文传道之士。〔9〕这些由工商入儒之人进一步改变了士人群体的构成,使工商与儒士之间建立起“良性”的沟通与循环,反过来深化了士人观念的新变。
这种观念新变对士人群体的影响,时人即已敏锐发觉。欧阳守道《回包宏斋书》说:
大率士列四民之上。而古之士由农出,农之气习淳良。后之士杂出于工、商、异类矣。又降而下,有出于吏胥、游末矣。名则士也,气习则士而工、士而商、士而异类、士而吏胥、士而游末也。人品既卑陋而不可移,气习又熏蒸而不可涤,而充塞人间,谓之多士,亦何以责学术于此等辈哉!〔10〕
“学术”即“道术”,“亦何以责学术于此等辈”即不能将传道的责任寄希望于此辈。欧阳氏对士人群体的这一变化是极为悲观的,但这却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①清代沈垚在《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落帆楼文集》卷24)中有一段与欧阳氏相近的议论,他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这段文字为治史者多所征引,然从欧阳守道这篇书信可知,中国士人的这种变化在南宋时即已凸显并为人所觉察。
二、士人阶层分化带来诗坛结构变动
古人一般将社会阶层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南宋中期以后这种四分法已不能准确反映当时的阶层状况。淳祐四年 (1244),阳枋“分教广安”〔11〕,时值广安大旱,他作《广安旱代赵守榜文》。阳枋在此文中将当时的社会阶层分为九类,包括士大夫、胥吏、士、农、工、商、游手、军、释道,对他们的各自职分均有界定。〔12〕由榜文可知,士大夫是指地方官府中的官员,也是科举出身或荫补入仕的士;吏胥的来源当是未能中第的地方士人,他们占有一定的行政资源,又有着丰富的地方“人脉”,多世故老辣,与知识传播往往格格不入,为正统士人所鄙视;士则是饱读诗书之人,他们或正在科举的独木桥上努力,争取成为“士大夫”,或已在科场败下阵来,成为地方上的知识人,他们在地方虽然没有行政方面的权力,却有教化民风的责任。榜文告诫士人“毋盘游,毋逸乐,毋言尧舜而行市人,毋外衣冠而中木石”。“毋盘游”说明士人有游的风气,表明他们与游士、游手、游末关系密切;“毋言尧舜而行市人,毋外衣冠而中木石”说明士人之中存在价值观念破裂的情况,也即上文所说的士人观念发生变化。“榜文”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公文,阳枋在榜文中对社会各成员的分类,应当说代表了一种官方认识,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阶层的构成情况。其中“士大夫”和“士”都属于士的范畴,是不同层次的士。政府公文将其明确区别对待,正是士人阶层发生严重分化的表现,即在朝之士与在野之士间的鸿沟已经确立。另外,吏胥实际上也是由士转化而来,可以看作士人分化的一种形态。这里的游手与欧阳守道《回包宏斋书》所说游末当为同一指称,是从士人群体分离出来的一类“闲杂”人员,其游动性和不稳定性尤为突出。也就是说,除了军与释道这两个阶层之外,新增的其他三个阶层均与士有着疏密不等的关系,是士人分化的具体形态。阳枋对各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仅是不同人员所应担负的社会职能,若从士人的谋生手段、人生经历等角度考虑,则当时士人的分化更为复杂。
士人身份的多样化和士人群体的层级化,对南宋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批士人疏离政治,导致士人群体呈现出从中央到地方的流动态势。杜範在《车隘轩闲居录序》中针对其家乡浙江黄岩的士人群体总结说:“俊秀能文之士”能够博得功名者“百不一二”,大部分只能“陆沉约处,首白衣褐”。〔13〕这些寒士中的一部分涌入“江湖”,过着四处奔波的游士生活。还有一部分则“闭门挟策,隐几著书,矻矻穷年”,选择了隐居耕读的生活。杜範指出的这一文化现象,绝不限于黄岩一地,而是南宋中后期的普遍问题。由此形成南宋中后期相对稳定的游士诗人群体与隐士诗人群体,他们如繁星一般点缀东南一隅,深刻影响了南宋的文化风气和文化格局,南宋诗坛结构因之发生变动。
何梦桂《清溪吟课序》说:“士非阨于山林,逸于湖海,与夫失志于朝廷之上,而窜逐遐荒者,不暇于诗。”〔14〕阨于山林、逸于湖海之人,生活状态非游即隐。窜逐遐荒之人,心境和活动也近于隐。其言论虽不免绝对,但反映了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一种实际状况:诗坛人员构成发生改变,游士诗人、隐士诗人成为重要主体,诗坛重心分散于地方。
对于南宋中期以后的诗坛,人们习惯上关注的重点是江湖诗人,而江湖诗人的主体正是因士人分化而形成的游士。考察游士诗人的生平经历,可概括为两种模式,一是:少有大志——蹭蹬科场——绝意仕进——游历江湖——寂寞终身。如,刘过“少有志节,以功业自许,博学经史百氏之文,通古今治乱之略”〔15〕,然而多次应举无果,感叹“科名付诸公,老矣吾归休” (《归耕》)。二是:少有大志——幸而入仕——沉浮下僚——出入江湖——寂寞终身。如叶茵入仕后“十年不调”(《参选有感》),最后“不慕荣利,萧散自放”,成为“江湖间诗人”。〔16〕这两种模式正是士人分化在个体命运上的呈现。这些游士诗人虽小有名气,但难称大家,人们对其文学价值的评价也不高。然而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力量,一种士与工、商等其他社会阶层相交融的文化趋向。江湖诗歌的平民意识、个人化情趣,都是这种文化趋向的表露。
相对于游士诗人,人们对南宋中后期的隐士诗人极其缺乏认识。隐士群体同游士群体一样,都是士人加剧分化的产物,是南宋中后期诗坛的重要构成。隐士虽然屏迹乡间、山林,但他们的文化活动并没有停止,往往主导着地方上的文化事务,这也是南宋隐士群体的显著特征。退隐地方的士人之间多有频繁的诗学交往,进而形成小型诗人群体,这在两浙、闽、赣地区尤为普遍。像永嘉薛师石,他“终身隐约,不求人知”,王绰《薛瓜庐墓志铭》指出在薛氏周围有十余位同样乡居的诗人,他们之间相互唱和、形成一个群体,使“永嘉视昔之江西几似矣”。〔17〕又如,福建邵武以严羽、严仁、严参为主,“邑人上官阆风、吴潜夫、朱力庵、吴半山、黄则山”为羽翼,也形成了一个隐士诗人群体,在他们的活动下闽中地区唐风盛传。〔18〕再如,以王汶为中心的黄岩“三王”,也是这种隐士诗人群体。〔19〕这些地方性隐士诗人群落,其影响多限于地方,没有发展成引领时代风气的洪流。然而他们的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和繁荣了南宋诗坛,使诗坛的重心分散于地方,增加了诗学活动的广度和密度。
游士诗人与隐士诗人作为群体始终占据南宋中后期诗坛的重要阵地,然而作为个体,却表现出流动性与交互性。在经济原因、求名欲望、家庭观念、江湖多舛等因素的影响下,作为个体的游士诗人或隐士诗人其身份往往发生转变,或厌倦江湖归隐地方,或步入江湖变身游士,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种身份上的转换,活跃了中下层社会的诗学,增强了游士、隐士诗人的诗坛主体地位,也使诗学重心进一步分散于地方。
三、士人群体异动诱导“宋调”流变
南宋中后期士人之加剧分化,促使游士、隐士群体成为诗坛重要力量,同时也推动了“宋调”的演变。杨载《诗法家数》将诗之“书事”概括为:“大而国事,小而家事、身事、心事。”〔20〕游士、隐士诗人所思索的问题由国家社会收缩为个人家庭,其诗歌在国事上虽有所缺失,却在家事、身事、心事上用力尤深。因之,诗歌风貌发生变化。
吴乔《答万季埜诗问》说:“宋人不可轻也。宋诗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个人。”〔21〕这是说宋诗具有一种生活的真实性,是诗人现实生活的艺术展现。不过,宋诗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这个“人”并不相同。东坡诗表现出的是一位倜傥的豪士,山谷诗表现出的是一位深沉的文士,而南宋中后期游士、隐士作品表现出的则是普普通通的贫士。他们没有苏东坡的才情,缺少黄山谷的学力,多数人“足迹游历不过数郡,无名山大川以豁荡心胸。所与唱和者不过同官丞簿数人,相与怨老嗟卑。又鲜耆宿硕儒以开拓学识”,其诗歌也就“边幅稍狭,比兴稍浅”。〔22〕艰辛的生活,以及长期与中下层人民的接触,使他们将普通人的七情六欲表现得尤为真实彻底。作品中的情感与平民更加贴近,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则很不同。“赣之隐者”〔23〕萧澥写有《寇中逃山》二首,记录了逃难时的惊慌情景。他并不从大处着眼,也不议论匪寇发生的社会根源和影响,而是从自身感受落笔,写逃难时的胆颤心惊。其中“心破胆寒无处著,风枝露叶亦惊疑”,“婴孩底苦不解事,偏是怕时方始啼”两联写得十分形象贴切。这类诗歌反映出的个人形象与宋元话本中描写的人物十分接近,是文学“平民化”的一种体现。这种平民化的情感在游士、隐士作品中随处可见,是其诗歌的重要特征,与士大夫诗歌对比鲜明。如欧阳修《大热二首》与戴复古《大热五首》,题材相同,诗体均为五古,但诗作表现出的情味迥异。以二人第一首作品为例,戴诗开篇直入诗题,写得很具体,“大窑”的比喻也十分通俗。欧诗则从四时物理入题,显示出作者的眼界与修养,措辞也典雅稳重。戴诗接下来都是从实处落笔,言语通俗。欧诗则写自己的浪漫想象,与戴诗的处处落实不同。二人作品一直接,一婉转;一通俗,一典雅。游士、隐士诗作不同于正统士大夫的别样风韵,在这种对比中可以十分清晰地显露。
游士、隐士诗歌的这种风韵可概括为“率直”,其突出表现是诗歌情感的愈加日常化、平民化,诗歌语言的愈加通俗化、生活化。传统士大夫诗学崇尚含蓄与比兴寄托,对这种率直风格很难认同。故而,历代评论家对此期宋诗多持批评态度,或目之为“酸馅”,或视之为“猥杂”。但这是游士、隐士诗人不同于传统士大夫诗歌的独特艺术样式,将其置于诗歌发展史来看,有其积极的意义。
除了率直之外,游士、隐士诗歌还有一种“轻清”的倾向。作为士人分化结果的游士、隐士诗人,他们的作品很少关注重大社会问题,而热衷于对一己之感和自然景物的咏唱,诗作内容也就趋向单薄。诗歌中往往缺少“感慨”,而只有“吟咏”,风味或幽淡、或轻巧、或闲澹、或清润,融会成“轻清”的总体特征。如薛师石诗歌多写友情、闲情、幽情,曹豳《瓜庐集跋》说:“余读四灵诗,爱其清而不枯,淡而有味。及观瓜庐诗,则清而又清,淡而益淡。”〔24〕宋末韦安居《梅磵诗话》评论了多位游士、隐士的作品,他所使用的词语如“不尘腐”、“有新意”、语意“洒落”、“语意清新”、“颇有意味”、“警策可喜”等,均与轻清指向相同。翁方纲《石洲诗话》也对多位游士、隐士诗人有所评论,其措辞:“不俗”、“风致”、“清高”、“秀韵”等,也同样指向“清”这一审美特征。可见前人对游士、隐士诗歌的这一风格倾向已有所认同。
轻清风格的形成是此期士人主观追求的结果。宋代诗学在审美上对“格”特别重视,“格”是宋代诗学“弘扬至大至刚、充实完善的人格力量”〔25〕的审美表现。但“格”这一标准至南宋中后期却不再被人强调,“清”则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清”是一个有着多种指向性的美学概念,它通常与其他词语结合,形成新的美学范畴,如清健、清奇、清远、清婉、清新、清丽等〔26〕。但游士、隐士诗人之“清”绝无清健、清奇这种指向。他们的“清”是将“格”中“气”与“力”的成分涤除,进而加入“雅致”、“绝俗”等内涵,更多地指向清润、清婉、清新、清丽,典型表现便是“轻清”。这在刘克庄的诗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他为时人作的《王与义诗序》、《真仁夫诗卷序》、《王元度诗序》等序文均标举“诗贵轻清”的理论。
诗学审美上的尚清还与此期中下层士人群体中流行的清高意识相表里。游士、隐士诗人多政治上不得志,生活上不如意。穷困潦倒的生活,使他们在心理上对世俗世界产生了逆反,形成清高的群体性格。苏泂有一首关于重阳节的诗,其题为“闲居复遇重九,悠然兴怀,颇谓此节特宜于贫,盖富贵者不知若是之清美也。因赋唐律呈同社”。认为重九是迁客骚人、贫寒雅士的节日,富贵之人难以体会到此节的“清美”,这是对贫寒生活方式的被迫认同,也是对世俗世界的一种反拨。李涛《诗社中有赴补者》说:“有诗千首可成名,万户侯封亦可轻。自是高标凌富贵,肯随余子逐恩荣。君游璧水甘芳饵,仆为铨衡上玉京。水镜兰坡各求第,诗盟似未十分清。”因为诗社中有人应第求官,也即步入世俗,所以认为“诗盟似未十分清”。他们的理想是以“高标凌富贵”,而非“逐恩荣”,表现出贫寒之士的倨傲。游士、隐士诗人的这种清高意识与审美上的尚清理论相融合,共同促成诗作清轻之风格。
率直轻清是士人群体加剧分化这一文化现象在创作风格上的映现,与当时理学诗人群的创作特点明显不同,〔27〕从而形成风格上的对比与互补。游士、隐士的这一诗学倾向是南宋中后期宋调变衍的一种表征,构成宋诗发展流程上的重要一环,同时也为元初诗学的建立和演变划定了“基调”。
〔1〕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4528.
〔2〕刘宰.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A〕.漫塘集:卷13〔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刘辰翁.丁守廉墓志铭〔A〕.须溪集:卷7〔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真德秀.万桂社规约序〔A〕.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7〔M〕.四部丛刊本.
〔5〕李昴英.文溪集:卷20〔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袁采.袁氏世范:卷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姚勉.谭氏孺人墓志铭〔A〕.雪坡集:卷50〔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胡次焱.论过房〔A〕.梅岩文集:卷5〔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钱时.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A〕.杨简.慈湖遗书·“附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欧阳守道:回包宏斋书〔A〕.巽斋文集:卷5〔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阳少箕.纪年录〔A〕.阳枋.字溪集:卷12〔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阳枋.广安旱代赵守榜文〔A〕.字溪集:卷9〔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杜範.车隘轩闲居录序〔A〕.清献集:卷16〔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何梦桂.清溪吟课序〔A〕.潜斋集:卷5〔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殷奎.昆山复刘改之先生墓事状〔A〕.强斋集:卷3〔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293〔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王绰.薛瓜庐墓志铭〔A〕.薛师石.瓜庐集:卷尾〔M〕.上海:古书流通处1921年印“汲古阁景宋钞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本.
〔18〕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39〔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嘉靖太平县志:卷6〔M〕.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Z〕.上海:上海书店,1986.
〔20〕杨载.诗法家数〔A〕.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728.
〔21〕吴乔.答万季埜诗问〔A〕.丁福宝.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7.
〔2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1372.
〔23〕陈起.江湖后集:卷15〔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曹豳.瓜庐集跋〔A〕.薛师石.瓜庐集:卷末〔M〕.
〔25〕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7.287.
〔26〕蒋寅.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A〕.中国社会科学〔J〕.2000,(1).
〔27〕常德荣.理学世俗化与南宋中后期诗坛〔A〕.文学评论〔J〕.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