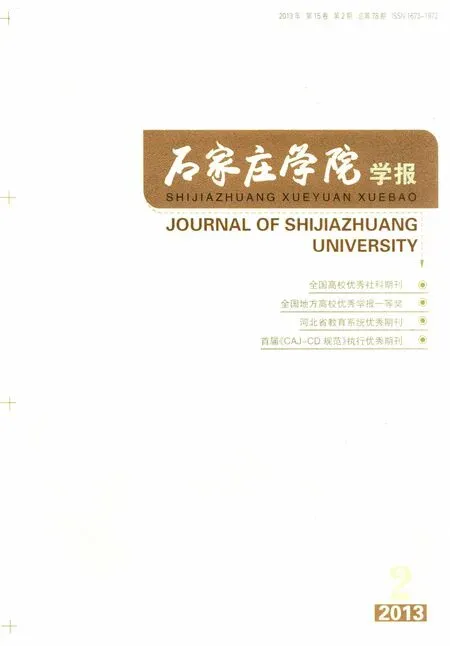自由心证与排除合理怀疑关系再诠释
郭 旭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一、刑事诉讼事实判断——证据自由心证
事实认定无误是法院作出正确判决的前提,确定事实之基础在于对证据的处理和运用。刑事诉讼进入到法院审判之后,庭审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即是对证据证明力有无及其大小的判断。为了保障诉讼活动的稳定、有序进行,各国法律大抵都规定了相关的规则,比如美国的证据相关性与可采性规定,德国的证据禁止等。通常情况下,法律避免对某类或某项证据的证明力 (weight)的强弱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是交由对事实进行裁判的裁判者自行确定,即证据自由心证制度。
自由心证是指证据的取舍及证明力的大小及其如何运用,法律不作预先规定,而是由法官秉诸“良心”“理性”自由判断,形成内心确信,从而对案件事实作出结论。[1]50“法院于事实之真伪,虽有判断之自由,然亦非可率尔以从事,法律之所期待着,审判官恒为富于学识经验之人,其判断事实必能依经验定则而为之,如依经验定则而行,自无专横之弊,故敢舍法定证据主义而采自由心证主义者。”[2]244自由心证制度被认为是对法定证据制度进行批判的产物。法定证据制度固然更能凸显刑事诉讼实现国家权力、惩罚犯罪的价值和目标,但也造成了对于“法定”证据的过分追求,不仅导致诉讼效率低下,也滋生了伴随证据获取而导致刑讯逼供行为,对被追者人权造成侵犯,严重影响了诉讼的正当性基础。
(一)自由心证在两大法系的表现
自由心证制度是诉讼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结果,在两大法系之中均已形成了固定的表述,但是由于诉讼模式不尽相同,在侧重点方面就各有特色。在陪审团审判为主导的英美法系国家,自由心证侧重于对陪审团的指示(jury instruction);而在大陆法系参审制的法庭组成机制下,陪审员同法官对事实作出认定,因此,自由心证就直接表现为法官在认定事实上的充分自由。
1.英美法系中的自由心证——美国
美国的刑事诉讼庭审大多有陪审团的参与,负责对案件的事实部分进行认定。陪审团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法律训练,因此在他们对事实进行裁定之前,法官通常会作出以下几方面指示(jury charge):陪审团的职责和义务;与案件有关的法律;由证据引起的争议;解释有关法律术语的确切含义。除此之外,许多州授权法官对证据作出评论,但是一些州却禁止这样做。[3]80证据的评论,包括证据的关联性和可采性等方面,甚至可以对证据证明力的大小进行概括说明,但是即便法律允许法官作出此类评论,该评论也不是必须遵守,陪审员仍旧可以依照自己心中的“确信”作出裁决。陪审团有权不顾法律与证据对明显有罪的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①Spark&Hanson v.United States,156 U.S.51 (1895).陪审团对事实认定的评议一概秘密进行。在联邦法院系统,陪审团作出的裁决必须全体一致通过。①《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1条。经过长时间讨论而无法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会导致陪审团僵局(dead jury),必须另行组成陪审团进行审理,这种绝不妥协的方式,也保证了心证获得的“自由”性,不仅不受到法律的限制,也不应该受到其他陪审员意见的左右。
2.大陆法系中的自由心证——法国
较美国对于陪审团的指示而言,法国关于自由心证制度规定得更为具体。“法律不过问法官形成自我确信的理由,法律也不为法官规定某种规则并让他们依赖这种规则去认定某项证据是否完备,是否充分。法律只要求法官平心静气、集中精神、自行思考、自行决定,本着诚实,本着良心,依其理智,寻找针对被告及其辩护理由所提出之证据产生的印象。法律只向法官提出一个概括了法官全部职权范围的问题:你已有内心确信之决定吗?”[4]46-47此处的“法官”不仅包括职业法官,也包括参与到诉讼过程中作为陪审员的相关人员。
(二)自由心证的前提——证据排除制度
自由心证只是解决证据证明力有无及其大小的问题,而且根据“自由”的原则,无法对最后“心证”的形成进行一个文本性的分析。②通常情况下,如果在仅有法官进行审判的场合,判决中必须说明判决的理由;但是在有陪审团进行审判的场合,对于案件的事实部分的认定,只需记载陪审团最后表决的情况,并不需要给出如同前者一般详细的分析论证。因此,法庭必须对证据的相关性、可采性事先进行说明,以保证陪审员在认定事实时不会受到不相关或者非法证据的影响。
审前证据开示和庭审认证、质证是保证无关或非法证据得以排除在心证形成之外的两种重要手段。前者主要将控方手中掌握的所有证据,包括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展示给辩方,辩方可以针对证据的合法性与相关性提出质疑,要求法官裁定排除,也可以要求持续开示,形成了诸如传闻证据规则、排除规则等实用规则;后者主要是对证据的可采性,也就是证明力的大小进行质疑,包括补强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等等。“证据禁止法则形成自由心证的外在界限,已经因此而排除的证据,法官不得任其有证据价值而采为裁判之基础。”[5]356
正是由于以上制度的设计,使得一部分证据在庭审之前已经被排除在外,而那些能够进入陪审团视野的证据,也必须在法庭上进行充分论辩和交叉讯问之后,才能成为事实认定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经过两道程序被法庭所采纳有证明力的证据,对陪审员而言,也仅为参考,对事实的判定完全在自由理性下形成。
(三)自由心证的补充——证据法定效力制度
毋庸置疑,自由心证可能会导致诉讼效率低下、案件事实认定不统一等问题,因此,赋予特定证据法定证明力作为自由心证制度的补充,很有必要。一方面减少了陪审团对于该类证据的心证形成时间,另一方面也能够确保在实体认定上的一致性,即“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在承认法官(陪审团)对证据价值凭理性和良知进行评判的制度下,证据规则实际上是法律约束法官广泛裁量权的最后防线。[6]比如,在美国,对于普通证人不够格提供有效意见的事项,陪审团不能任意无视未遭到反驳的专家意见,否则其定罪裁决可能因缺乏证据支持而被宣布无效;在法国,法律规定,除非以书证或者人证提出相反的证据,有关违警罪的笔录具有证明效力。虽然这些证据被赋予了法定效力,但与法定证据制度还是有很大区别。法定证据制度要求被告人被定罪量刑的依据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而作为自由心证补充,被赋予法定效力的证据不能成为定罪的唯一因素,还需要其他证据的佐证。“易言之,法官必须在现有的证据提出之情况下为自由心证,不能离开现有的证据而为自由心证,因此在此严格财政体系之下,纵法律未对法官之心证形成任何限制,但法官之心证形成自然受此严格采证体系之影响。”[7]424-425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据的被采用是一方面,但是运用证据得出被告人有罪的裁定(verdict)却又是另一方面。通过证据开示、法庭质证而进入陪审团视野形成心证的证据,最终能否认定被追诉人应该承担刑罚,还需要完成另一项技术性的活动,即将各种可能存在的合理怀疑予以排除。
(一)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的角度上通常理解为对事实进行判断的法官(或陪审员)要形成被告人有罪这一结论需要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基于刑罚惩罚的严厉性和谦抑性,在证明标准上的反映便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毫无疑问,这是在局外人进行事后审判的刑事诉讼活动中,人类认识水平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在大陆法系的表述是“内心确信”,联合国相关文件的表述是“没有其他可能解释的余地(no room for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facts)”①“no room for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facts”是联合国《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文件中对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的要求,但是死刑案件亦属于刑事案件的范畴,所以笔者将该标准也一并列入讨论。,[8]三者虽然在词语运用上有所不同,但内涵却大致相近。只有在满足该标准之后,陪审员才能作出有罪判决的裁定,否则,无罪推定应该贯穿整个诉讼程序的始终。②美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无罪推定,但无罪推定被一向视为是一个宪法原则。见In re Winship,397 U.S.358(1970).
(二)合理怀疑
所谓合理,亦即其怀疑须有理由,而非纯处于想像或幻想之怀疑。[9]395合理怀疑“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决以达到内心确信的程度”③《加利福尼亚刑法典》第1 096条。。这段表述是在谈论何为合理怀疑时经常被引用的观点,但却也未能明确说明哪一种或者哪一类怀疑就是合理的,概念解释中的“内心确信”实际上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另一方面,从而陷入了循环解释的窠臼。
不过,该段文字至少扩充了对于合理怀疑的认识:在适用主体上,为参加法庭事实认定的陪审员;在适用阶段上,是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比较考虑之后;而要达到的程度,则是形成“内心确信”;在内容上,是一种实在的、诚实的、为良心所驱使的怀疑。[10]323实际上,英美法系也在通过判例不断地丰富和充实关于合理怀疑的相关表述,④1947年英国著名法官丹宁(Denning)勋爵对于合理怀疑的解释是:“在判决被告人有罪以前,案件事实应当达到真实性的程度,该真实性程度不必要达到完全肯定性的程度,但是必须具有高度的可能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并不意味着连怀疑的影子都必须排除掉,如果允许幻想的可能性妨碍司法的过程,法律就不能有效地保护社会。如果证据如此强而有力,以至于某人的利益只有遥远的可能性,‘当然这是可能的,但却是丝毫不能证明的’,就应当予以驳回。因为案件事实已经得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当然任何缺乏这种程度的证明都是不充分的。”1954年霍兰诉美国案中,合理怀疑被界定为:“你们大家在生活中面对非常严肃和重要的事情时愿意据此采取行动……合理怀疑是一种导致人们在行动上产生犹豫的怀疑……而不是人们愿意据此采取行动的怀疑。”[11]试图给这个本身模糊的概念进行阐释。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国家、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对排除合理怀疑的界定都有很大差异。[12]
(三)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何种程度的怀疑能够认定被告人无罪,或者说,在多大程度的可能性下,能够认定被告人确实有罪而需要接受惩罚?笔者不妄想能够给出具体的说明,“排除合理怀疑”已经是对其含义较为简练的界定。反面论证法固然可以排除部分情况,比如50%的可能性必然不能定罪,因为这个程度甚至连 “优势证据”的标准都没有达到,但是在解决诸如90%甚至98%的可能性之情况下却是无能为力,更何况何为50%也难以界定清楚。
运用一个在讨论中经常提及的案例:“监狱里一共有50名犯人。在一场监狱暴动中有一名狱警被杀死,而根据摄像头记录的信息,仅有一名身形模糊的犯人没有参加暴动。所有的犯人都声称自己是摄像机记录的那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犯人是那个无辜者的可能性仅为2%,但却毫无疑问地构成了合理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给任何一个罪犯定罪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对合理怀疑的程度进行量化,不仅毫无必要,也是行不通的。排除合理怀疑,其价值在于彰显行使国家权力追诉犯罪实施刑罚的过程中的谨慎和细致,更多的是一种“标杆性”的作用,而其程度及内涵,就应该在具体的案件中把握与分析。
(四)排除合理怀疑的对象和主体
要认定被告人确实为犯罪人需承担刑罚惩罚,在证明标准上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该标准的适用对象并非仅是定罪的结论本身,而是应该扩大到满足该罪的各个构成要件要素上。比如对能够判处死刑的“第一级谋杀罪”的认定,对合理怀疑的排除就不应该只是对结论的确定,还应该对相应的各类要素诸如“预谋”“杀人行为”等的确定。同样的,排除合理怀疑的主体虽然是独立的个人(陪审员),但是有罪裁定(verdict)的作出,必须是整个陪审团全体的一致结论,或者大多数人的一致结论。⑤在美国,联邦法院的有罪裁决的作出必须经过陪审团一致决定,但是在有些州并不要求该一致性,也可以是特殊多数;英国则是先要求一致同意,若不能达成则可以延长两小时作出裁定,此时可以是不少于10人的特殊多数决定。
只有如此规定,才能保证在最大可能的情况下实现对被追诉者的保护。错误的追诉的恶果远远比放走一个有罪之人影响要更为恶劣,因此“如果我们用一种不正义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那么这种不正义是可以容忍的”[13]28。根据罗尔斯(Rawls)关于程序正义的观点,刑事诉讼程序是一个“不完善的程序”,即便严格按照法律的预设方式规定进行操作,也不能保证判决的绝对正确性。但是,通过提高和严格证明标准、证明过程的方式,能够保证在同等认识水平下判决的可接受性,而这种可接受性就成为了刑事判决的正当性之基础。
三、自由心证下的合理怀疑
自由心证与排除合理怀疑,乍看之下,两者一个为事实判断的过程和方法,一个为证明标准即有罪认定需要达到的程度,似乎毫无联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笔者认为,合理怀疑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经验性,而该怀疑能够对进入陪审团视野的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产生二次影响甚至将之排除,但这种排除具有暂时性,一旦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此种怀疑是不存在或者不合理的,那么被排除的证据之效力就得以恢复。从这种角度上来讲,合理怀疑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证据的排除规则,其依据并非是证据没有满足某种法定的形式性要件,而是作为事实裁定者——陪审员的经验和逻辑理性,“自由心证主义必须是合理的心证主义和科学的心证主义”[14]314。
(一)作为事实裁判者的陪审团
陪审员选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法官审理的偏见与局限(judicial lottery)。“每个人都应当由同他地位同等的人来裁判。这是最有益的法律。因为,在那些关系公民自由和幸福的地方,不应该让煽动不平等的那些感情作怪。走运者看着不幸者的优越感,下等人看待上等人的嫉恨心,都不能从事这种裁判。然而,当犯罪侵犯的是第三者时,法官就应该一半是与犯罪地位同等的人,一半是与受害者地位同等的人,这样,那些改变包括无意中改变事物面目的各个私人的利益得以平衡,这时候,发言的便只是法律和真相。”[15]20美国联邦法院也承认陪审团享有作出无罪裁断的无可争议的权力,即使这一裁断违背法律或证据。①United States v.Moylan,417 F.2d 1002,1006(4th Cir.1969),cert,Denied,397 U.S.910 (1970).
经过法学系统培训的法官在法律适用的处理上经验丰富,但是在确定案件事实的问题上却未必比身为“门外汉”(lay person)的陪审员做得更好,原因在于法官作为法律职业者可能存在的思维定式和特别的喜恶。陪审员代表的广泛性,其他姑且不论,在人数上就有压倒性的优势,在事实的认定上就更能够接近“真相”,也更能为被追诉人接受。
(二)作为经验规则的合理怀疑
合理怀疑产生于陪审员对生活的认知,是每个陪审员通过自己人生阅历系统化、逻辑化之后的主观反映。不同的人就同一证据可能产生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陪审团评议的秘密性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可以推知评议室里发生的必然是一场说服与被说服的论辩。比如常带眼镜的人在睛明穴处就会留下较深的印记,视力正常之人通常很难知晓;火车轰鸣而过的声音到底有多响,经过之时可以听到多大的声音,也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有所了解,等等。这些问题在陪审团的讨论中并非没有存在的可能,虽然其中大部分显而易见的争论在法庭质证阶段就可以被睿智的控辩双方排除出去。来自各行各业身份各异的陪审员,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对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进行理性分析,考虑的范围远远大于作为律师或者检察官的法律工作者,对证据提出质疑,对定罪的结论提出合理怀疑。通常说来,一个口若悬河的怀疑者的质疑效果远远比一个唯唯诺诺的怀疑者的嘟囔要好得多,但这涉及到说话的方式与艺术,本文不作详细讨论。
(三)传统的证据排除规则
提及证据排除规则,传统证据法理论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意见规则等内容往往成为众多学者优先讨论与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只是证据排除规则的一小部分,是对证据可采性或者证明力的判断,若是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关联性判断也应该纳入证据排除的范畴。
1.关联性(证据能力)判断
证据被认为是与法院即将作出判决的案件有关的证明材料,因此,对案件的关联性便成为了上述材料能够成为证据的首要前提。《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对相关证据的定义是: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该证据的存在能够对于最后存争议事实认定的可能性趋势加强或者减弱。②原文为:Federal Rule of Evidence:401 “Relevant evidence” means evidence having any tendency to make the existence of any fact that is of consequenc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ction more probable or less probable than it would be without the evidence.笔者将其翻译为:“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该证据的存在能够对于最后存争议事实认定的可能性趋势加强或者减弱。”因此,在对证据进行初步判断的时候,首先是分析其内容是否与待证案件本身有关,即进行实体性考察,对其形式及获得手段与途径倒可以先搁置一旁,没有关联性的证据必然没有可采性。
2.可采性(证明力)判断
在自由心证制度的影响之下,法律不对证据的证明力有无及其大小作出明确规定,而交由事实裁判官根据自己的理性进行逻辑判断。但是,法律却为能够进入事实裁判官视野的证据设定了相关的条件,最大程度减少不相关或者不可采的证据影响陪审员心证形成的可能。
事实上,在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特别是在指控有罪而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控辩双方的所举证人之证词必然是相互矛盾的。控方所有证据旨在证明被告人的行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需要受到刑罚惩罚,辩方却总能够举出与之相对的抗辩理由,因此,在逻辑上来讲,两方的证据本身就是值得质疑的,在符合相关的程序性和形式要求的情况下,双方提供的证据都具有可采性,而差别在于其证明力大小在陪审团成员中的印象。无罪推定原则基础上的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并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为陪审团最终心证的形成提供了相应的指引。
3.传统证据排除的价值
毫无疑问,传统证据排除规则是总结诉讼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成果,对于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及诉讼程序的正义具有重大意义。具体说来,关联性规则能够节省司法时间,提高诉讼效率,而可采性规则,有的是为了保障程序的正当性,比如排除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对“毒树之果”的排除(当然也存在大量的例外情况);有的是为了保障控辩双方的质证权利,体现追求实体真实的理念,比如传闻证据规则;有的是为了保障心证形成的合理性,比如意见规则和专家证人意见规则,等等。
(四)作为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怀疑
传统的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能解决陪审团在评议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就同一份证据而言,在具备关联性和可采性之后,在陪审员的心证形成过程中仍旧可以不予采用,或者即使纳入考虑的范围,也可以作出证明力极低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证据排除理论无法发挥作用,因为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传统理论指导之下的证据排除,仅仅只是证据采纳的前阶段,法律并没有规定经过法庭质证的证据就理应具有什么样的证明力而必须被采纳并据此作出判决;陪审员根据自由理性及合理怀疑形成“心证”时对于进入视野证据的价值判断,才是证据排除的最终阶段。笔者认为,传统的证据排除规则与作为证据排除规则的合理怀疑,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排除内涵的差异。传统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排除,如上文所述,是由于证据不满足法律规定的最低实体或者形式要件,若是不予排除,则会徒增诉讼压力或者导致程序不公的问题;后者排除的目的并不是考虑采用该证据的外部影响或后果,而是在自由心证指导下基于案件事实的合理怀疑,对证据材料主观的、经验性的排除。
第二,排除作用的差异。被传统规则排除的证据,无论是缺失了实体或者程序合法性的任何一个要件,均不产生证明力,不仅在本案中无法采用,在以后对该案的司法处理中也不得采用;①笔者在此处想要表达的是被传统规则排除的证据在事实认定程序中的不可采性,但是在量刑程序中,比如品格证据、重复行为证据等通常在事实判断中因缺乏关联性而被排除的证据却可以被采用。基于合理怀疑而排除的证据,并不是对证据本身的否认,而是对该具有证明力的证据材料的选择性忽视,其作用不仅是针对单一的有罪证据,足以对抗所有能够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也就是说,只要存有合理换衣,那么就能够忽视其他证据(主要是有罪证据)的相关效力。
第三,排除理由的差异。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中,通过法官对案件的审判而逐渐发展出了相当多的证据规则,其中有证据排除规则,也有排除规则的例外,传统的排除理由包括但不限于非法证据(狭义)、品格证据、意见证据、传闻证据等;而后者,从字面上理解,排除的理由就是合理怀疑,只要存在合理怀疑,陪审员就可以排除所有认定有罪的证据。对合理怀疑的界定,笔者在上文已经作出,顾不赘述。
第四,排除效果的差异。证据材料被传统证据规则排除之后,对于所有的事实裁判者,都不得作为作出有罪认定的依据,或者根本就应该被阻隔在陪审员的视野之外。但是,由于法律职业者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仍会有部分证据不可避免地通过传统证据排除相关规则的认证,在形式上就具备了法律上的证明力。在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则之下,证据即使经过了法庭审判,进入到了陪审团评议的环节,陪审员能够根据生活经历、人生阅历,发现证据之间的疑点予以排除。这种排除不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每个陪审员对于证据的评价不尽相同,被一个陪审员认为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在另一个陪审员看来却可能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
第五,事后救济的差异。根据美国刑事诉讼的上诉规则,通常情况下,上诉人不得就事实问题作出的裁决提出异议。但是被告人可以以在审判中错误地采纳了不应采纳的证据,或者排除了不该排除的证据为由,请求上诉法院裁判原判决。而对于陪审团作出的有罪或者无罪的事实裁定,不能成为上诉的理由,并且之后也不能对该评议活动进行调查。在有陪审团参与审判的情况下,法院在判决中对于事实认定的论述无需详细,仅需记录票数和最后结果即可。因此,控辩双方并不能够了解每个陪审员对证据最后的认定情况,故也无法提出相关的救济申请,这也是自由心证所应该涵括的内容。
四、结论
刑事诉讼承担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从刑事诉讼法设置目的的角度上分析,人权保障的价值位阶甚至还要高于追诉犯罪。在此基础之上,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每个被追诉人在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就应该被当作无罪之人看待。鉴于刑事惩罚的谦抑性、严厉性甚至不可恢复性,法律对刑事案件设定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是人类认识水平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
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的争点就在于证据材料能否足以说服事实裁判者形成内心确信或者排除合理怀疑。为了规范双方的行为,即使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均确立了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但是对于那些能够提交到法庭的证据都设定了相关的限制,即传统的证据排除规则,将与案件事实无关或者由于程序上违法、不可采纳的证据排除在陪审员心证形成的过程之外。
经过质证而进入陪审员视野的证据,即便在形式上已经具备了法律效力,若是存在合理怀疑的余地,裁判者也可以不依其而形成心证,当然,笔者也同意这并非常态。在陪审团评议阶段中对于证据的排除,基于其秘密性,不会有文字记录,也不会受到事后审查,是陪审员的主观经验经过理性分析之后的外化,是一种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外界可以从评议作出有罪或者无罪之结果推知一二。这种怀疑可能是由一个人对一份或多份证据提出,在经过评议之后可能会将该种怀疑传递给其他陪审员,如果全体一致同意这种怀疑,那么就可以作出无罪裁定,也就排除了在心证形成过程中所有“有罪证据”的适用;如果有人质疑这种怀疑的合理性,那么就会是一场持久的论辩,可能导致“悬案陪审团”的出现,即审判无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该次即将被宣布无效的审判中,“有罪证据”的适用亦被排除,被告人依然无罪。
[1]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外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石志泉,杨建华.民事诉讼法释义[M].台北:三民书局,1987.
[3]卞建林,刘玫.外国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4][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5]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宋英辉,吴宏耀.外国证据规则的立法及发展[J].人民检察,2001,(3):58-61.
[7]蔡墩铭.刑事证据法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8]杨宇冠.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与程序要求[J].人民检察,2008,(8):22-25.
[9]李学登.证据法比较研究[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
[10]樊崇义.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1]彭海青.简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J].学术论坛,2004,(4):175-178.
[12]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J].中国法学,2003,(2):150-160.
[13]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4][日]土本武司.日本刑事诉讼法要义[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15][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