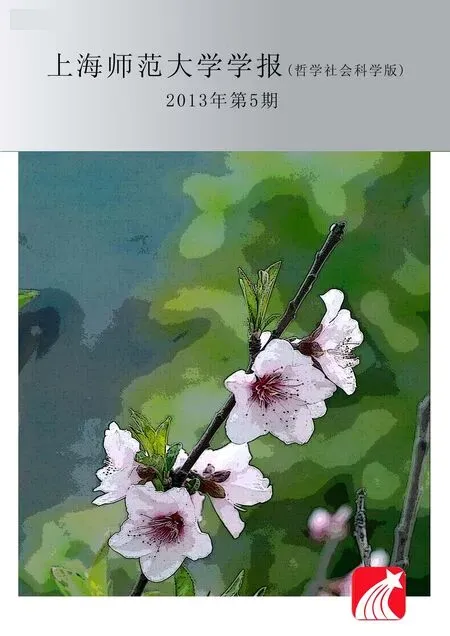唐代“岳牧举”及相关问题考辨
陈 飞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唐代“岳牧举”是一个既具体又宽泛的问题,很多文人和文学与之有关,在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与地位也很重要。由于问题比较复杂及学者的关注不多等原因,文献记载和学术论著多不详明,本文拟就此稍作探讨。
一
文献关于唐代“岳牧举”的记载不大容易辨别,本文采用“以纲带目”的方法为其分类:“纲”主要是从“主—客”关系上着眼,因为“岳牧举”实质上是一种人才举荐制度,涉及到举荐者和被举荐者双方,前者属“主体”,后者属“客体”,双方结成特定关系共同完成其活动,故具纲领性。“目”主要是从其特征和细节着眼的,它们从属并充实上述关系。两者结合,以期“纲举目张”之效,当然这样的分类是相对的。
总的说来,唐代“岳牧举”属“非常之举”,具有很强的制举性质。①《新唐书·选举志》载:“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太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②这段记述涉及到唐代制举的诸多问题,这里可注意三点:一是制举是以天子名义进行的旨在选取“非常之才”的制度;二是制举虽有临时性且名目繁多,但也有相对稳定的科目和考试程式,这些可称之为“通常制举”;三是有些特殊情况(如天子巡狩、行幸、封禅之类)下的人才选取,虽不在通常制举之列,但具有制举的性质和特点,可称之为“特殊制举”。唐代的“岳牧举”有的属于通常制举,有的属于特殊制举。
二
从“主—客”关系上说,唐代“岳牧举”主要有两类:
甲:“岳牧”举,即由“岳牧”举荐特定人才。
《册府元龟》载:
(高宗)麟德元年七月丁未朔诏: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实,有事于岱宗。所司详求茂典,以从折衷;其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诸王十月集东都;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天下诸州,明扬才彦,或销声幽薮,或藏器下僚,并随岳牧举送。③
此诏是麟德元年(664)为准备麟德三年的泰山封禅之事而发,内容除了要求有关部门明确典章礼仪、各类参与人员集按时集中之外,还明令“天下诸州”推选“才彦”,“并随岳牧举送”,因而便有了“岳牧举”。然则这里的“岳牧”与“诸州都督、刺史”实为同一类人员,既是封禅大典的出席者,又负有举荐和送达人才的使命,于是“岳牧”和“才彦”便形成“主—客”关系。
这样的“岳牧举”并非偶见,《通典》载:
(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封祀于泰山……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台之前坛,高祖神尧皇帝配享焉。辛卯,享皇地祇于社首之泰折坛,睿宗大圣真皇帝配。壬申,上御朝觐之帐殿,大备陈布。文武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咸在位。④
这里记载了玄宗开元十三年(725)的封禅活动,其中“御朝觐之帐殿”接见有关人士为其节目之一。在被接见的各类人员中有“岳牧举贤良”,亦即由各地“岳牧”举送而来的“贤良”人选,于是也有“岳牧举”。
以上两例“岳牧举”均与封禅活动相关,不同的是前例出现在诏文中,是将要实行而尚未实行的“岳牧举”;后例出现在封禅现场,是已经送达(尚未考试,详下)的“岳牧举”。值得注意的是,玄宗于事后发布《赦书》说其封禅是“遂奉遵高祖、太宗之业,宪章乾封之典,时迈东土,柴告岱岳……”⑤所谓“乾封之典”,便是前例所言高宗封禅泰山之典,因封禅后改元乾封,故曰“乾封之典”。⑥由此可知玄宗的封禅是对高宗封禅的效仿,而高宗的封禅则是对太宗的效仿。《唐会要》载:
(太宗)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诏曰:“……可以贞观二十二载仲春之月,式遵故实,有事于泰山。诸内外具僚、岳牧卿士,既相敦喻,将事告成。各罄乃心,无亏政道。恪居职务,以协时雍。所司宜与缙绅先生、载笔圆冠之士详求通典,裁其折中,深加严敬,称朕意焉。仍令天下诸州,明扬侧陋。其有学艺优洽,文蔚翰林,政术甄明,才膺国器者,并宜总集泰山。庶令作赋掷金,不韫天庭之掞;被褐怀玉,无溺屠钓之间。务得英奇,当加不次也。”⑦
将此与上引高宗麟德元年诏两相比观,不难看出两者的诸多相似:都是为将要举行的封禅而预作安排;都是指示在作好相关典礼准备的同时,要求“天下诸州”举荐人才并送达泰山。显然高宗的封禅(包括“岳牧举”)其实是对太宗封禅的遵循。
然则唐代“岳牧举”并非始于高宗,也非始于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实际上早在贞观十五年的《访求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中,就有“可令天下诸州搜扬所部,士庶之内,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具以名闻,限来年二月总集泰山”⑧的要求,其中虽然没有明言“岳牧”或“都督、刺史”,但“天下诸州”其实就是指诸州都督、刺史或“岳牧”,显然这也是因封禅而伴随的“岳牧举”,不过这次封禅因故并未举行。此外如《唐会要》载:“永淳二年七月庚申,诏以今年十月有事于嵩岳,宜令礼官、学士等审定仪注,务展诚敬。仍令天下岳牧及京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有孝行、儒学、文武之士”。⑨这也是为预备封禅而发的诏制,除了地点改在嵩岳外,其他事项安排略如以上诸例,其中也有“岳牧举”。
这些事例表明,唐代天子在封禅的同时伴有举贤活动似已成为惯例,而且在表述上都明显使用“岳牧”的指称。其中两例的“岳牧”与“举”字相连构成“岳牧举”,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科目名称,但其实不是,而是说由“岳牧”来“举”人才,只是“举”字正好与“岳牧”相连而已,“岳牧举”只是着眼于举主的概指和简称。根据上引《新唐书·选举志》所言,封禅所伴随的这种举贤活动并不属于通常制举,但具有制举的性质和特点,属特殊制举。应当指出的是,并非只有封禅才伴有“岳牧举”,其他如即位⑩、改元、南郊、上尊号等,也多伴有类似活动,甚至可以说举贤已成为唐代重大典礼的经常性内容,其中往往有“岳牧举”(但不一定明显使用“岳牧”的表述)。
乙:举“岳牧”,即举荐“岳牧”型人才。
《旧唐书》载:
员半千,本名余庆,晋州临汾人……上元初,应八科举,授武陟尉……寻又应岳牧举。高宗御武成殿,召诸州举人,亲问曰:“兵书所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也?”半千越次而进曰……高宗甚嗟赏之。及对策,擢为上第。
《新唐书》的记载略同:“员半千……凡举八科,皆中。……调武陟尉……俄举岳牧,高宗御武成殿,问:‘兵家有三阵,何谓邪’?众未对,半千进曰:‘臣闻……’帝曰:‘善’。既对策,擢高第。”由此可知:员半千应“岳牧举”及第应在高宗上元元年(674)以后,与上述麟德三年的“岳牧举”并非一事,情形和性质也有所不同。《玉海》于《唐制举·制举科目图》题下记云:“永隆元年,御武成殿,问岳牧举人,员半千对。”《太平御览》云:“《唐书》……又曰:高宗御武成殿,亲试制举人,问之曰……”皆将其作为通常制举来记述。当然此次“岳牧举”看上去也有些“特别”之处,就是高宗的“亲问”。《通典》云:“其制诏举人,不有常科,皆标其目而搜扬之。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试已,糊其名于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可知天子“亲临”考试原本就是唐代制举的常情,但那是指笔试对策,而高宗的这次“亲问”则是在正式考试之前接见参试人员临时增加的口头提问,员半千的对策也是口头的,此属“口策”,虽然博得高宗的赞赏,但员半千的“擢高第”还是要通过其后的正规考试(笔试对策),故又有“既对策,擢高第”之说,所以这次“岳牧举”仍属通常制举。
这里的“岳牧举”还可能是一个具体科目名称。《旧唐书》本传用“应八科举……又应岳牧举”的表述,是将“八科举”与“岳牧举”并列,“事”属同类。而在“应……举”的结构中,“……”即为(制举)科目。《新唐书》本传用“凡举八科……俄举岳牧”表述,其并列之义同上,而“举……科(岳牧)”的结构更有特别显示其所“举”为科目之意,是谓员半千参加科目名为“岳牧举”的制举考试而获得“举”(及第)。《玉海》于《唐岳牧举》题下记云:“《旧纪》调露元年十一月甲寅,临轩试应‘岳牧举’人。”注云:“员半千举‘岳牧’,髙宗御武成殿,问兵家三阵,对策擢髙第。”这里的“试应‘岳牧举’人”的表述亦有特别显示科目之意:高宗所“试”者为应“岳牧举”科目之“人”也,员半千应此科目考试而中“举”,故注云“举‘岳牧’”。《册府元龟》在《贡举部》的《科目》门下记:“永隆元年,岳牧举。”小注云:“武陟县尉员(贺)半千及第。”《唐会要》在《制科举》门下按年列述制举科目及其及第者,中有:“永隆元年,岳牧举,武陟县尉员半千及第……”凡此皆可证其“岳牧举”为通常制举科目。然则若此“岳牧举”确为一个制举科目,则属唐人(高宗)首创,意在选取特定的人才,其“特定”之处在于具备“岳牧”的素质和能力,可以胜任“岳牧”之官职,也可以说是“岳牧”型人才。当然这里的“具备”和“胜任”有现在时和将来时两种可能:有的现在就可以出任“岳牧”,有的则是将来的“岳牧”人选。员半千属于后者,《新唐书》本传又载:“会诏择牧守,除棣州刺史。复入弘文馆为学士。武三思用事,以贤见忌,出豪、蕲二州刺史。半千不专任吏,常以文雅粉泽,故所至礼化大行。”看来员半千后来果然成为一个好“岳牧”,高宗的这次“岳牧举”亦可谓举得其人矣。
三
“岳牧”有虚实之分,据载黄帝时已有“力牧”之举,尧舜时已设“岳牧”之官。《尚书》载:“(周成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孔安国传云:“道尧舜考古以建百官,内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国之长。上下相维,外内咸治。”孔颖达疏云:“‘百揆’,揆度百事,为群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内典四时之政,外主太岳之事,立四人也……‘牧’,一州之长;‘侯伯’,五国之长,各监其所部之国。外内置官,各有所掌,众政惟以协和,万邦所以皆安也。”“岳”、“牧”作为官职名号可谓古已有之。“四岳”职兼内外,掌“四时”、“山岳”;而“牧”作为“一州之长”专掌“外”(地方)事。《通典》云:“四岳,分主四方诸侯者也。……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国之长。”《国语》韦昭注云:“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为诸侯伯。”大致说来,“四岳”作为官号,原本职兼内外,后来“外”的部分逐渐加重,成为诸侯的“主”和“伯”;而“牧”一直为“外”官,并主要定位于“州长”。上述“岳”、“牧”多为实指,秦汉以降,逐渐“虚”化,一方面很少使用“岳”、“牧”之官名,另一方面多用其代称(郡)守、尉、太守、刺史、总管、都督之类。相对说来,称“牧”者居多,称“岳”者渐少。唐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唐六典》载:“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各一人,从二品。”注云:“……皇朝又置雍州牧。洛州初为都督府,及置都,亦为牧。开元初,复为京兆、河南尹。”《通典》载:“大唐武德元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而雍州置牧。至神龙二年二月,分天下为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至景云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开元十年省,十七年复置。二十二年,改置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至德之后,改采访使为观察,观察皆并领都团练使。其僚属随事增置。分天下为四十余道,大者十余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区域为制。诸道增减不恒,使名沿革不一,举其职例,则皆古之刺史云。)。”又载:“乾元中,又置都统使,监总管诸道,或领三道,或领五道,皆古方岳牧伯之任也。”可见“牧”在唐代作为实际官号,大抵仅用于京兆、河南、太原以及雍州、洛州等“王畿”之地,而且时间不长。至于“岳”,《唐六典》虽有“五岳、四渎,令各一人,正九品上”的记载,但此处的“岳令”为下层小官,与上述“四岳”之“岳”不可相提并论,大体可以说唐代并没有实际上的“岳”之官名。
虽然没有“岳牧”的官职名号,但不能没有相应的职能之实。唐代与“古方岳牧伯之任”相当的官职有都督、刺史、巡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节度使、都团练使、都统使、屯田使等等。易言之,唐人所谓的“岳牧”,一般是对如此等等官职名号的代称和概指,而杜佑“皆古之刺史”之说则提示“刺史”为唐代“岳牧”的主体和代表。然则“刺史”所代表的“岳牧”可概称“高级地方长官”,至于“高级”到何等程度,可据刺史的品级约略推知。唐代的上州、中州、下州刺史的品级分别为从三品、正四品上和正四品下,据此可将“正四品下”作为“高级”的大致下限。上引永淳二年七月诏文云“仍令天下岳牧及京官五品以上各举所知……”是将“天下岳牧”与“京官五品以上”相提并论,既表明“岳牧”不在“京官”之列,属于地方长官,亦表明两者在品级上大致相当。虽然看上去“岳牧”的“正四品下”略高于京官的“五品”,但考虑到唐人“重内轻外”的一般情况,京官的“五品”与外官的“正四品下”亦可大体相当,甚至以六品京官出任刺史还被视为“用崇岳牧之任”。
既然“岳牧”可以作为“高级地方长官”的代称,那么在特定的语境下,两者便可以相互“置换”,这样前述甲、乙两类“岳牧举”的“岳牧”便可以置换为“高级地方长官”,于是形成两类置换了的“岳牧举”:
甲1:“高级地方长官”举人才。
《唐六典》载:
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掌清肃邦畿,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谕五教。每岁一巡属县,观风俗,问百姓,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部内有笃学异能,闻于乡闾者,举而进之……
这里的“京兆、河南、太原牧及都督、刺史”皆属高级地方长官,也是实际上的“岳牧”,举进“部内”贤才既是其职责和义务,则其举进活动亦可称为“岳牧”举。这种职责和义务写入典章,表明这样的“岳牧举”具有经常性。
除了这种经常性的举进,还有很多诏制性的举荐,诸如:
唐高祖武德五年诏:……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
(太宗)贞观十一年四月诏:……宜令河北淮南诸州长官于所部之内精加访采……
高宗(祖)以贞观二十三年即位,九月诏曰:……京司长官、上都督府及上州各举二人;中、下州刺史各举一人……
(龙朔)三年八月诏:内外官五品以上各举……
上元三年闰三月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都督、刺史,各举所知一人。
永隆元年十二月诏:县令、刺史、御史、员外郎、太子舍人、司仪郎、左右史、文武五品以上清要、近侍及宿卫之官,并令举所知一人。
(玄宗)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制:内外八品已下官及草泽间有学业精博,蔚为儒道,文词雅丽,通于政术,为众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长官,精加搜择,具以奏荐。
开元二十七年正月令:诸州刺史举德行尤异、不求闻达者,许乘传赴京。
(肃宗)乾元三年闰四月御明凤门诏: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员官,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一人……
(敬宗)长庆四年即位,三月壬子赦书: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人师,详娴吏理达于教化,军谋宏远材任边将者,委常参官并诸道节度、观察使、诸州刺史,各举所知……
在以上诸例中,往往将“京官五品以上”和“诸州都督、刺史”作为举荐“主体”相提并论,或称“内外官五品以上”,可证上文关于“高级”程度的推测为通常情况。这些都督、刺史或五品以上外官亦可用“岳牧”来代称,因而他们的举荐活动皆可视为“岳牧举”。
乙1:举“高级地方长官”型人才。
《册府元龟》载:
(仪凤)三年十二月诏:京文武职事三品以上官每年各举所知:或才蕴廊庙,器均瑚琏,体王佐之嘉猷,资公辅之宏量;或奇谋异算,决胜千里;或投石拔距,勇冠三军;或謇谔忠亮,志存规弼;或绳违纠恶,不避权豪;或威惠仁明,堪居牧守之重;或公正廉直,足膺令长之任。咸宜搜访,具录封进。朕当详览,量加奖擢。
这里的“或……或……”,既是一系列的“制目”,也是天子所欲取、官员所须举的各类人才特点和类型。从“客体”看,其中“威惠仁明,堪居牧守之重”与“公正廉直,足膺令长之任”,可谓专为地方长官型人才而设:“牧守”更高级,应为都督、刺史之类;“令长”相对低些,应为县令之类。这里的“牧守”与“岳牧”仅一字之异,几乎与举“岳牧”的表述无异。
类似的例子也不少,诸如:
(景龙)三年三月,令内外五品以上举堪任刺史、县令者。
太极元年二月,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举才堪将军及边州都督、刺史一人。
开元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礼毕,诏曰:……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学究天人之际,知勇堪将帅之选,政能当牧宰之举者,五品以上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举一人。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诏:……其内外官,有亲伯叔及兄弟并子侄中,灼然有才术异能、风标节行、通闲政理、据资历堪充刺史、县令者,各任以名荐。
天宝元年正月一日改元,诏曰:……其京文武官五品以上、清资官并郎官,据资历人才堪为刺史者,各任封状自举。
肃宗至德元年七月即位于灵武,诏:有直言极谏,才能牧宰,文词博达,武艺绝伦,孝悌力田,沉沦草泽,委所在长官闻奏(荐);诣阙自陈者,亦听。
上元二(十)年九月赦书:每除京官五品以上正员清望官及郎中、御史、诸州刺史,皆令推荐一两人以自代,仍具录行能闻奏,观其所举,以行殿最。
广德二年正月丙午诏:常(尝)参官各举所知堪任宪官、谏官、儒官、刺史、县令者。
(大历)八年正月诏:京官三品已上郎官、御史,每年各举一人堪任刺史、县令者。
(大历)十二年七月诏:尚书、御史大夫、左右丞、侍郎,各举堪任刺史者以闻。
(贞元)四年正月诏:诸色有清白政术堪任刺史、县令,常参官各举所知,朕当亲自策试之。
宪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委内外官各举所,知当亲策试。
这里的举荐情形及对象(客体)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含有刺史、都督、牧宰之类。其中“刺史”的出现尤为频繁,可见朝廷对此类人才的特别重视与亟切需求。然则这些对象也都可以称作“岳牧”。
四
以上四类“岳牧举”实际上是两个大类:一类是由甲到甲1,即由“岳牧”举荐人才到“高级地方长官”举荐人才,后者其实是对前者的“置换”和“推广”;另一类是由乙到乙1,即由举荐“岳牧”型人才到举荐“高级地方长官”型人才,后者同样也对前者的“置换”和“推广”。因此也可将两者合起来,统称“岳牧举人才”和“举岳牧人才”。然则其间还有一些细微差异:一是直接而单纯地使用“岳牧举”或“岳牧”的表称,此可谓完全代称;二是没有使用“岳牧举”或“岳牧”的表称,而是直接点出官职名号,如刺史、都督之类,此可谓完全指实;三是使用“牧”、“牧守”、“牧宰”、“州牧”、“方牧”之类的表称,此可谓不完全代称(也可谓“不完全指实”);四是如“其名最著”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四科的名目表述,既没有使用“岳牧”或“牧守”之类,也没有点出官职名称,但其所标明的举荐对象中包含有“岳牧”型人才,此可称之为隐性指称。
这些细微差异既体现了唐代“岳牧举”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说明所有关于“岳牧举”的分类都是相对的,不应将其绝对化。由于“主—客”双方的变化,还会出现一些“特别”情况,如开元二十三年诏“五品以上清官及军将、都督、刺史”各举“政能当牧宰之举者”,其“主体”中有都督、刺史,是属“岳牧”;其“客体”为牧宰,亦为“岳牧”,可谓是“岳牧举岳牧”,故在分类上既可以归入“岳牧举荐人才”,也可以归入“举荐岳牧人才”。又如上引(肃宗上元)“二(十)年九月诏:每除京官五品以上正员清望官及郎中、御史、诸州刺史,皆令推荐一两人以自代。仍具录行能闻奏,观其所举,以行殿最”。“诸州刺史”举人自代就等于举荐“诸州刺史”,也就是“岳牧举岳牧”,在归类上也可两属。
相对说来,甲、乙两类“岳牧举”更加“名副其实”,是“岳牧举”的基本类型,也可以说是狭义的“岳牧举”。尤其乙类,以制举的名义和制度,设置具体的“岳牧举”科目,考试选取“岳牧”型人才,是更加典型的“岳牧举”。而甲类“岳牧举”则是一种举荐活动,而不是科目名称,但其过程中含有考试环节,其具体的科目及其考试、录取等如同制举,故属特殊制举。其“特殊”之处主要在于:与封禅等重大活动相伴,举荐“主体”为“岳牧”,而且其举荐“客体”不一定是“岳牧”型人才。至于甲1、乙1两类,既是甲、乙两类的推广,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或宽泛的“岳牧举”。总的看来,前两类“岳牧举”在唐代前期(大抵以“安史之乱”为界)比较活跃,这主要是由于此期天下相对太平,封禅之类活动比较频繁,制举的科目亦颇丰富多样;后期由于天下多事,封禅之类的大典不多,尤其是制举科目渐趋稳定,各种类型(包括“岳牧”型)的人才大抵皆“包含”在几个主要科目之中,如“列为定科”的四个科目,其“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两个科目主要是为“岳牧”行人才而设,于是后两类“岳牧举”便经常可见。
由以上讨论可知,唐代的“岳牧举”所涉及的人员范围较广、层次跨度较大,故很多文人与文学之有关,然其情况亦颇复杂,文献记载和学者论述往往不够详明和准确,这里不妨略举几例:如《文苑英华》卷四七三载颜师古《策贤良问五道》,此应系为贞观十六年封禅而伴随的“岳牧举”而作,是现存唐代最早的“岳牧举”试策(策问)文本。虽然这次封禅因故未能实际施行,颜氏的策问也可能并未付诸考试,但此可证当时已(预备)有“贤良”考试,故其“贤良”便具有科目的意味。而在(贞观十五年为此次封禅而发的)《访求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中有“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的表述,又可知“贤良”(或“贤良方正”)似乎并不是其最终的科目名称,其下还会有更具体的分类科目。这些情况,文献(如《文苑英华》、《全唐文》等)在收录颜氏策问文时并未有说明,而《登科记考》未载其文。
又如《文苑英华》卷四七三之《卷目》中有《策神岳举问》一道,但卷内仅标其题而未载其文,题后单行大字注云:“此篇所答策载四百八十卷《贤良方正科》,策问随策,今不重出,止存其名”。检同书卷四百八十,其“卷目”有《贤良方正科策二道》,卷内首题《贤良方正科策》,题下双行小字注云:“神龙二年。”其下先载策问文,文后单行大字注云:“此题四百七十三卷重出,前已削去。注意:同为一作。”其后载对策文,署名“苏晋”。据此可知,前之“神岳举”与后之“贤良方正科”实为“一作”——系同一科目同一次(场)考试的策问,其科目的完整表述应为“封禅神岳所举贤良方正科”,也属于封禅所伴随的“岳牧举”。然则这里的“神岳举”与“贤良方正科”不是同名异称,而是从属关系,亦即后者是前者的实际考试和录取的科目名称,故不宜将其分别标题,这样容易使人误会为两个科目。《唐会要·制科举》载:“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愔、卢绚、张文成、褚璆、成廙业、郭隆、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贞、张敬及第。”随后又载:“二年,‘才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瓌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泚、卢怡、吕恂及第”。后一个“二年”未标年号。如果其事亦属神龙二年,则“才膺管乐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经邦科”与“贤良方正科”很可能都是此番“岳牧举”下的具体科目。然而《登科记考》却将“才膺管乐科”张大求等及第与“才高位下科”冯万石等及第记于神龙二年(706),将“才堪经邦科”张九龄等及第与“贤良方正科”苏晋等及第记于神龙三年,并据《文苑英华》录苏晋对策文,却于其“神龙二年”之说弃而不取,亦未说明“神岳举”事,未详何据?这样没有了“封禅”背景,容易使人误以为是与封禅无关的通常制举。
此前还有一次“神岳举”,《资治通鉴》载:“(万岁通天元年)腊月,甲戌,太后发神都;甲申,封神岳;赦天下,改元万岁登封……”注云:“后以嵩山为神岳。”《文苑英华》卷四八一《卷目·方正》门下有《贤良方正(止)策五道》之目,然卷内题作《应封神岳举对贤良方正策三道》,下载策问文及崔沔对策文三道,题下双行小字注云“神功元年”;其后又载《重试一道》策问文及其对策文,未署对策人姓名;其后又有《神岳举贤良方正策》一题,题下双行小注云“策(册)问阙”,其对策文署名“袁映”,其下小注云“未审何年”。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既云“册问阙”,则知袁映所对之“神岳举”与崔沔所对之“封神岳举”不是同一策问,既非一事,可暂不论。二是崔沔对策所谓之“应封神岳举”应即《通鉴》所谓之“封神岳”所伴随之“举”贤活动,亦即“岳牧举”;故其“贤良方正”应属此“岳牧举”下的具体科目。三是既云(袁映所对策)“未审何年”,则知崔沔对策之“神功元年”为已“审”矣。这就是说,崔沔对策科目所属之“岳牧举”的考试时间是在神功元年(697)。而《登科记考》却将其事记于天册万岁二年,显然是欠准确的,这不仅是因为《文苑英华》已注明“神功元年”,还因为天册万岁元年(695)腊月以封神岳而改元万岁登封,故实际上并没有“天册万岁二年”。《登科记考》又于“贤良方正科”之及第人中首列“崔沔”之名,考云:“……颜鲁公《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公讳沔,字若冲,博陵安平人。年二十四,举乡贡进士。考功郎李迥秀器异之,曰:“王佐才也。”遂擢高第。其年举贤良方正,对策数公,独居第一,而兄浑亦在甲科。典试官梁载言、陈子昂叹曰:“虽公孙、晁、郄不及也。”’《文苑英华》以崔沔对策为神功元年。按封神岳在丙申年,不应以次年方策应神岳举人。且《陋室铭》明言对策对策为二十四岁事,沔卒于开元二十七年,年六十七,推之丙申年,适二十四岁。是《文苑英华》误,今改正。”一般说来,封禅所伴随的“岳牧举”通常要在封禅之后举行考试,这“之后”需要一定的时间,如玄宗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封禅泰山,其“岳牧举”考试在十四年十月,中间将近一年。从实际情况考虑,封禅之后,要有一个车驾还都(京)、处理积压要务、选定主考官员并安排考试事务等的过程;同时应试者也须回到都城,稍作安顿和准备,况且崔沔在(同年)此前还有“举乡贡进士”的过程。实际上这次封禅的次年三月即改元万岁通天,第二年的九月又改元神功,故自万岁登封元年到神功元年也就不到一年,故“次年(神功元年)方策应神岳举人”不是“不应”,而是在情理之中,可能性很大。而《文苑英华》所注“神功元年”当有其据,应属不误,徐松的“改正”并不正确。然则这次“岳牧举”之“贤良方正科”的实际考试时间不会早于万岁登封元年。
又如《登科记考》于麟德元年下记有“销声幽薮科”,及第人为“严善思”;又记有“藏器下僚科”,及第人为“平贞昚”。实际上“销声幽薮”和“藏器下僚”只是麟德元年诏文中的“制目”,此诏既是为麟德三年的封禅而发,诏中又明言“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实,有事于岱宗”,“销声幽薮”、“藏器下僚”(人选),“并随岳牧举送”,则这两个“制目”的实际施行与其人应试“擢第”,都应是两年后亦即麟德三年(实为乾封元年)之事,故不宜系于麟德元年。同书麟德三年下记有“幽素科”,其下所列及第人中有“王勃”之名,并考云:“《旧书·文苑传》:‘王勃年未及冠,应幽素举及第’……”这里的“幽素科”应即麟德元年封禅诏中“销声幽薮”的实际施行科目(“试目”和“第目”),两者同属“岳牧举”,其考试和录取应在改元乾封以后。这些情况和关系,两家似未甚留意。又,《新唐书·王勃传》载:“麟德初,刘祥道巡行关内,勃上书自陈,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此说为《唐才子传》等所本,然不免有些含混。由于麟德三年正月初即改元乾封,麟德实际上只有两年,故此“麟德初”应是指麟德元年。但若说麟德元年刘祥道表荐王勃或有可能,若说王勃的“对策高第”也在是年便欠准确,因为王勃“对策高第”只能在封禅之后的乾封元年。《册府元龟·科目》载:“乾封元年:幽素科(苏瑰、解琬、苗神客、格辅元、徐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可知高宗封禅后确有考试,其科目确为“幽素科”,此即王勃所应者,实为此次“岳牧举”下的一个科。而《册府元龟》、《唐会要》于此科及第人中皆未载王勃,《登科记考》将其补入麟德三年(乾封元年)为是,然其所记麟德元年的“销声幽薮科”严善思及第和“藏器下僚科”平贞昚及第之事亦当移入是年。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虽将《登科记考》的麟德三年改作乾封元年,但并未就其麟德元年所记加以改正。又据前人研究增补“岳牧举”科目与及第人明崇俨。据《旧唐书·明崇俨传》:《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明崇俨传》:“乾封初,应封岳举,授黄安丞。”可知明崇俨所应之“封岳举”就是高宗麟德元年所诏、乾封元年所举行(封禅而伴随)的“岳牧举”考试,属于甲类“岳牧举”,其具体考试和录取的科目为“幽素科”。因此不宜将“岳牧举”列为科目,明崇俨实际上是“幽素科”及第,应将其名列于此科之下。
以上只是略举其例,其他相关问题尚多,拟另文考述,这里就不多及了。
唐代“岳牧举”的大致情况略如上述,在结束本文之前,还想说一点“题外话”。《册府元龟》云:“自《舜典》所载,盖十有二牧,以讫于周,重方伯连帅之任,秦置郡守,汉仍其制。或郡或国,错峙于四封;曰守曰相,咸(釐)于兆姓。专制千里,其为威重可知矣。故推择之际,未尝轻焉。乃有密迩都邑,俯介戎貊,或豪猾恣横,或寇攘为孽,至乃干戈甫定,水旱相仍,罢(羸)赖其(共)惠绥,强暴资其式遏,由是选循良之器,求真干之用,分符以往,专城而居,足以为王庙之藩屏,黔民之师长者矣。”又云:“昔汉宣帝云:与吾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夫一圻之地,千乘之赋,上承于王庙,下熙于民务,有刑辟之政,有军旅之事,所谓生民休戚之所属,王室安危之所渐。故得其人则成治,非其材则受弊。至乃仁慈以流声,清白以飞誉,礼让以化俗,公正以御物,不慑于威权,不溺于荣利,此良吏之最也。巽愞以取容,依阿以附势,殖货以厚己,苛刻以求名,不畏于简书,不恤于惸弱,此奸吏之首也。”又云:“居岳牧之任,为万夫之长,风化攸系,品庶式瞻”。总之“岳牧”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国家的存亡、天下的治乱、民风的淳浇,是支撑和维系天下的重要群体,其作用和地位不言而喻,故历代帝王无不慎重其选,而唐代尤有过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不仅频繁地举行“岳牧”举荐人才和举荐“岳牧”人才的活动,还将其制度化和公开化:一方面通过典章、诏令等使之成为经常性的责任和义务,并纳入“殿最”,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将其纳入制举,悬为科目,进行公开的考试选拔。这样既扩大了取才范围,也增加了公平性和公正性,从而培养和选拔了大量的“岳牧”人才。“大唐盛世”的造成,特别是几经“磨难”仍能复归承平,延祚三百,流誉后世,“岳牧”可谓与有力焉,其间意义亦堪深思而长想。
注释:
①唐代取士是一个大的制度系统,其中“常科”和“制举”是两个主要次级系统,前者包括明经、进士等一系列经常性科目;后者具有临时性,先后使用过的科目名称有近百个。详见拙著《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按:本文所涉及的制举问题,均参见此书,以下不再注明。又,本文所引用文献材料,出处相同者仅于首次引用时详细注出,其后则从略。
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169-1170页。按:本文所引文献标点有未当者(如此处原作“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均随手改正,恕不一一说明。
③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三六《帝王部》之《封禅》二,中华书局影明本,1960年,第393页。
④杜佑:《通典》卷五十四《礼》十四《吉》十三《封禅》,中华书局王文锦等点校本,1988年,第1520-1521页。
⑤详见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六十六《典礼》之《封禅》之《开元十三年东封赦书》,中华书局重印商务印书馆本,2008年,第371页。
⑥刘昫:《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车驾至泰山顿。是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帝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飨;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辛未,御降禅坛。壬申,御朝觐坛受朝贺。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元年。”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89页。
⑦王溥:《唐会要》卷七《封禅》,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聚珍版排印本,1955年,第93-94页。
⑧《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政事》之《举荐》上《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可令天下诸州,搜扬所部,士庶之内,或识达公方、学综今古、廉洁正直,可以经国佐时;或孝悌淳笃、节义昭显、始终不移,可以敦风励俗;或儒术通明,学堪师范;或文章秀异,才足著述,并宜荐举,具以名闻,限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庶独往之夫,不遗于板筑;藏器之士,方升于廊庙。务得奇伟,称朕意焉。”第518页。按:文后双行小字注云,“贞观十五年六月”。《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贞观十五年)夏四月辛卯,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详定仪制……六月戊申,诏天下诸州,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丙辰,停封泰山,避正殿以思咎,命食减膳。”据此可知此诏是为准备封禅泰山而发。
⑨《唐会要》卷七《封禅》,第103页。
⑩《唐大诏令集》卷二《帝王》之《即位赦》上《穆宗即位赦》:“……其择刺史、县令,宜委门下、中书、尚书省、御史台官,有所谙知,即具闻奏。”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