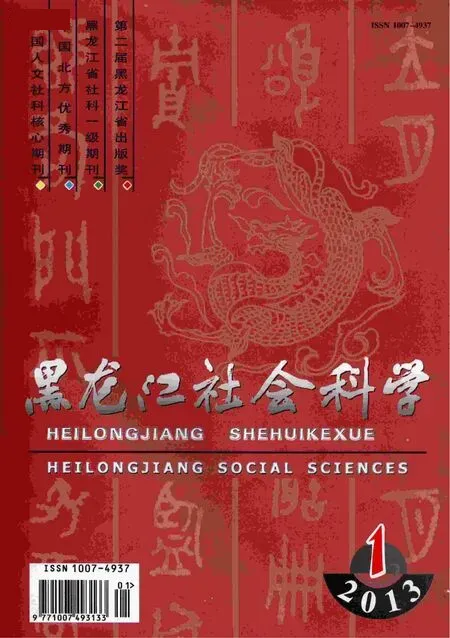齐桓公伐戎救燕及其相关问题——以经史为双重审查视角
彭 华
(四川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成都 610064)
齐桓公北伐山戎以救燕是春秋时期的一件大事,先秦两汉载籍于此多有记载;但是,此事尚有待发之覆。而关于齐桓公得胜归来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关于“齐侯来献戎捷”的评价,历来多有不同看法;于此,亦有进行考辨的必要。另外,通过对史实的还原、评价的梳理,尚可“以小见大”,从而考见齐、鲁、燕三国的文化差异及其国家化风格。
一、史学:齐桓公伐戎救燕史实的还原
周朝之时,曾经有过两个燕国,一个是姬姓的燕国(北燕),一个是姞姓的燕国(南燕)。本文所说的燕国,指的是姬姓燕国。
统观燕国八百余年的历史,总体上呈现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国运长久。史书云,“(燕国)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史记·燕召公世家》)。二是国力弱小。史书云,“燕固弱国,不足畏也”(《战国策·赵策二》),“燕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史记·燕召公世家》)。三是民族杂居。史书云,“燕北有东胡、山戎”(《史记·匈奴列传》);燕易王自云,“寡人蛮夷辟处”(《战国策·燕策一》)。
春秋时期,山戎曾经强盛一时,兵锋南向,孤竹、令支一度成为山戎的“与国”,①《国语·齐语》韦昭注:“二国(令支、孤竹),山戎之与也。”燕国也经常遭受山戎的掳掠和骚扰。周平王东迁雒邑以后六十五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史记·匈奴列传》)。
关于齐桓公北伐山戎、解救燕国一事,本文的考证重点有二:一是事件发生的时间,二是历史过程的还原。
关于齐桓公伐戎救燕事件发生的时间,史籍的记载多有歧义;或作公元前664年,或作公元前663年。《春秋》及其“三传”系年于鲁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史记·燕召公世家》系年于燕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4年);今人黄朴民从此说[1]。《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系年于燕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3年),《齐太公世家》系年于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年);今人陈恩林从此说[2]。
笔者认为,以上典籍所记录的时间均不算误,但均不准确。确切而言,齐桓公之北伐山戎,当始于公元前664年冬,终于公元前663年春。换句话说,《春秋》、《左传》和《史记》诸篇所记,各言其一,皆有可取之处。《春秋》庄公三十年明言,本年,“齐人伐山戎”;《左传》接着解说道,“冬,(齐、鲁)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次年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春秋》庄公三十一年)。由此可以看出,《春秋》和《左传》将齐桓公伐戎救燕的时间叙述很清楚,准确点明这是一次跨年度的行动(冬往春返)。清人高士奇和今人赵逵夫、方朝晖从此说[3]。
《史记》对此事的记载在时间上前后矛盾;于此,我们恐怕只能以“互文见义”视之,而不能简单责怪太史公。顺便指出,《韩非子·说林上》说“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虽然大致道出战事跨年这一事实,但“春”、“冬”二字恰好颠倒。遗憾的是,诸家校注者均未注意这一点。
关于齐桓公伐戎救燕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借助先秦两汉载籍予以还原。
相对而言,《春秋》、《左传》、《史记》对此事的记载都很简略,而《战国策》和《说苑》的记载则要详细得多。《太平御览》卷四五〇引《战国策》:“又曰: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助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又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覇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以不进周公之庙也。桓公乃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明年,起兵伐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此之谓也。”(《说苑·权谋》的文字,与《战国策》完全相同,显然系因袭所致)
这段文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它客观而真切地揭示了历史的一个隐曲,即齐桓公意欲联合鲁国出兵北上伐戎救燕,但结果得到的是鲁国的空头诺言,故为后来的“齐侯来献戎捷”埋下了伏笔。②宋人赵鹏飞云:“鲁济之遇,齐侯谋伐山戎也,公辞不能,故明年齐侯来献戎捷。”(《春秋经筌》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顺便说明:本文所引古籍,尤其是两汉以后的经学著作,所用版本多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免繁琐和节省篇幅,行文省略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字样。鲁国自知理亏,故在次年齐国的“伐莒”行动中倾力相助,从而缓和了两国的紧张关系。
齐桓公北伐山戎,行军千里,深入蛮夷之地,费时费力,历尽艰辛。至卑耳之溪时,曾经一度迷路,幸赖“老马识途”,才走出迷谷(《管子·小问》)。冬去春来,最终才击败山戎。之后,齐桓公又“刜令支,斩孤竹”,一路扫荡,声势大震,“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国语·齐语》),直至“三匡天子而九合诸侯”(《管子·戒篇》)。
为了答谢齐桓公的深情厚谊,燕庄公一路陪送齐桓公南下归国;但就在不知不觉之间,队伍已经跨出燕境而入于齐地。深明大义的齐桓公不愿违背礼制,“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之地与燕。临别之时,齐桓公又叮嘱燕庄公,“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使燕复修召公之法”;诸侯听说齐桓公如此深明大义,“皆从齐”(《史记·齐太公世家》,另见《史记·燕召公世家》、《新书·春秋》)。齐桓公和燕庄公的分手之地,就在所谓“燕留”城,“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地与燕,因筑城,故名燕留”(《史记·燕召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燕留故城,在今河北省东南部沧县一带,当地还有“盟亭”。《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五云:“盟亭,《郡国志》云:‘长芦县有盟亭,即燕、齐之界。’”
综合以上古籍所载,可以将该事件完整而真实的历史过程钩稽如下:公元前664年冬,势力强大的山戎南下侵燕,燕国告急,随即向强齐求救;齐桓公意欲联合鲁国共同进兵而北上救燕,故于是年冬与鲁庄公“遇于鲁济”,共谋伐戎大事,得到了鲁国的口头承诺;但当齐国一切准备就绪以后,鲁庄公却出尔反尔,“许助之而不行”;于是,齐国只好独自北上伐戎救燕;齐国经过辛苦的跋涉和艰难的激战以后,方于次年春天取得胜利;燕庄公陪送齐桓公南下归国,不知不觉而入于齐地,深明礼义的齐桓公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之地与燕;齐桓公班师回朝,本欲“移兵于鲁”,后为管仲劝止;但齐桓公尚觉意犹未尽,于是特意至鲁献捷,故经书有“齐侯来献戎捷”之谓。
北伐山戎一事,齐桓公一直引以为傲;直到公元前651年葵丘(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北)之会时,还念念不忘此事,“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史记·封禅书》)而玉成桓公大事者,管仲实有大力焉。于此,孔子大加赞誉:“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于此,孟子亦是赞誉有加,“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下》)。
二、经学:关于“齐侯来献戎捷”的评论
在正式梳理古人关于“齐侯来献戎捷”的评价之前,必须先解决文本问题。即究竟是“齐侯来献戎捷”,还是“齐人来献戎捷”;或者说,究竟是齐桓公亲自来“献戎捷”,还是派人来“献戎捷”。虽然二者仅有一字之别,①历代经学家认为,《春秋》笔法严谨,一字即寓褒贬之意(“以一字为褒贬”)。于此,可参看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晋范宁《春秋穀梁传序》、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征圣》等。但与评价有密切关系。②明人朱朝瑛云:“伐戎,则称人以抑之;献捷,则称爵以愧之。《春秋》有互起以见义者,此类是也。摠一齐侯也,于后称爵,则知前之称人为贬辞。前既称人以贬,则知后之称爵,亦非美辞。”(《读春秋略记》卷三)
《春秋》庄公三十一年的文本如下:“六月,齐侯来献戎捷。”《春秋》三传的文本高度一致,均作“齐侯来献戎捷”。由此可以看出,经书于此并无异文。
但是,部分后世学人认为当做“齐人来献戎捷”。元人吴澄《春秋纂言》卷三云:“‘侯’字,当从赵氏作‘人’。齐之将伐戎也,尝与鲁庄遇于鲁济以谋之,伐而得胜,故使人献捷于鲁,以嘉其谋之中也。”所云“赵氏”,当即唐人赵匡。明人朱睦?《五经稽疑》卷四云:“陆氏曰:当为齐人,文误。按上文,伐戎则人,安得献捷则侯乎?”所云“陆氏”,当即唐人陆淳。
赵、陆二氏的这一说法,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宋人吕大圭指出:“或者又以为,伐山戎当书齐侯,献捷当书齐人,交互致误,则又改易经文而难以为据。愚谓,经凡称人者,皆略辞;用兵而非有大役者,皆称人。今山戎之役,其齐侯乎,其将卑师少乎?愚不得而知也。以僖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之辞观之,则伐北戎为齐侯亲往,伐山戎为将卑师少,于义可通。不然,一齐侯也,前伐山戎则称人,后伐北戎则称侯,前后自异,谁能晓之?”(《吕氏春秋或问》卷十)元人赵汸于此亦有辩驳,“说者谓齐侯实使人来,非也。若使人来,当书齐人;若其卿来,当书名氏。《春秋》以礼法修辞。苟非齐侯身来成礼,安敢直书齐侯来乎?史乱名实,应不至此”(《春秋属辞》卷五)。吕大圭、赵汸的驳斥甚有理,“改易经文”的做法实不足取,更不可信。
后人对于“齐侯来献戎捷”的评价,大致可以一分为三:一者认为齐桓公此举实属“非礼”;二者认为齐桓公此举在于“尊鲁”,或者说齐桓公实则“知礼”;三者认为齐桓公和鲁庄公均属“非礼”。
1.齐桓公“非礼”说
《左传》庄公三十一年认为,齐桓公此举实属“非礼”,“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晋人杜预于此的解释是,“以警惧夷狄。虽夷狄俘,犹不以相遗”(《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杜预注);“《传例》曰:诸侯不相遗俘。捷,获也。献,奉上之辞。齐侯以献捷礼来,故书以示过”(《春秋》庄公三十一年杜预注)。唐人孔颖达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持论与杜预相同(《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唐孔颖达疏)。
《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认为,齐桓公此举的目的在于“威我(鲁)也”,“齐,大国也。曷为亲来献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获而过也”。《公羊传》虽然没有径直斥责齐桓公此举“非礼”,而仅用“威我”二字予以评骘;但体会其用语之深意,所持之论实则近于“非礼”说。此中微言大义,汉人何休独具只眼,“据齐未尝朝鲁,以威恐怖鲁也”,“不书威鲁者,耻不能为齐所忌难,见轻侮也”,“刺齐桓憍慢恃盈,非所以就霸功也”(《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何休注)。
赞同《公羊传》和何休此说者,有宋人孙觉、家铉翁等。孙氏云,“《春秋》齐侯用兵皆贬称人,于此献捷显言齐侯者,盖齐大鲁小,齐于鲁无所畏惮。若言齐人,则是微者无疑也;特书其爵,以见齐威之罪。齐威伯者,不务德以绥诸侯,而专恃兵革,远以伐戎,已有过矣;又因过鲁,以其伐戎之所得夸示诸侯,以自矜大,因使之威服焉。《春秋》诛齐威矜功威鲁之罪,故特书之曰‘齐侯来献戎捷’也”(《孙氏春秋经解》卷四)。家氏云,“合(《左传》、《公羊》)二说而观,乃见《春秋》之意。齐为霸,伐戎有功,当躬献之于王,以展职分之常。今乃以俘获分遗诸侯,此不过欲威示同盟之国,失其所以为霸之道矣。此齐侯使人献捷于鲁,书齐侯来献,卑之也”(《春秋集传详说》卷七)。
两汉以降,齐桓公“非礼”说居于主流地位。①明人王樵不同意《公羊传》的评价:“今按:齐鲁方睦,何威我之有。旗获过我,又妄说也。”(《春秋辑传》卷三)但是,持此说者实属凤毛麟角,不足以摇撼主流评价。宋人孙复、刘敞、胡安国、苏辙、陈深、崔子方、高闶、李明复、叶梦得等,元人俞皋等,明人湛若水、熊过等,皆持此说,并且认为这是对齐桓公的“讥”(讥讽)、“贬”(贬斥)、“抑”(贬抑),是齐桓公“慢上”。
刘敞云:“《春秋》书献捷者,二齐侯来献戎捷,书曰齐侯,罪其矜功伐劳,斥言其爵也。”(《刘氏春秋传》卷六)胡安国云:“齐伐山戎以其所得,躬来夸示,书‘来献’者,抑之也。”(《胡氏春秋传》卷九)陈深云:“《左氏传》,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献者,下奉上之辞。齐侯伐山戎得捷,志气骄溢,不顾失礼,躬来夸示于鲁。圣笔书来献者,盖抑之也。”(《读春秋编》卷三)崔子方云:“彼云卫俘,俘囚也;此言戎捷,然则捷不独俘矣,献卑者之事也。齐侯为覇主而亲献捷于我,非所宜献也。其有警于我乎?故月之以见讥献捷例。”(《崔氏春秋经解》卷三)高闶云:“圣人书曰来献者,抑之也。始伐称人,此称其爵者。方其伐戎过我,固已贬之,此献捷而称人,则疑若?者,故特书其爵,以诛齐侯矜功、威鲁之罪。此《春秋》大公之义也。”(《高氏春秋集注》卷十二)湛若水云:“愚谓,今戎捷不以献于王,是之谓慢上。”(《春秋正传》卷十)
2.齐桓公“知礼”“尊鲁”说
《穀梁传》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捷。齐侯来献捷者,内齐侯也。不言使,内与同,不言使也。”所谓“内齐侯”、“内与同”,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汉人何休概括的《春秋》书法的“三科九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隐公元年》徐彦疏)。因此,晋人范宁有“尊鲁”之谓,“献,下奉上之辞也。《春秋》尊鲁,故曰献”(《穀梁传》庄公三十一年范宁注)。在范宁之前,汉人郑玄已有“尊鲁”之谓:“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则曰献,通行曰馈。《春秋》曰:‘齐侯来献戎捷,尊鲁也。’”(《周礼注疏》卷六郑玄注)
其后,宋人魏了翁、明人髙攀龙、清人惠士奇皆持“尊鲁”说。魏氏云:“《春秋》曰:齐侯来献戎捷,尊鲁也。……齐侯来献戎捷。齐大于鲁,言来献,明尊之,则曰献;未必要卑于尊,乃得言献。”(《鹤山集》卷一百七)髙氏云:“诸侯不相遗俘献者,下奉上之词。齐侯亲来,卑词,尊鲁,故据其所称之实,而谓之献也。”(《春秋孔义》卷三)惠氏云:“齐侯来献戎捷,礼欤?曰:礼也。左氏曷为谓之非礼?左氏以为非礼者,言当献于王,不当献于鲁。献于王不书献,于鲁则书之。曰来献者,尊宗国也。”(《惠氏春秋说》卷五)
换句话说,既然齐桓公此举在于“尊鲁”,故齐桓公可谓“知礼”也。宋人张大亨持论即如此,并且在立论时糅合了何休“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齐桓之霸也,以德不以力,以功不以势;会则亲接四国之微者,伐则请师于天子;会王世子则不敢主其会,尊王世子则不敢与之盟。可谓知礼矣!……齐桓之伐山戎,盖以卫中国也;齐桓之献戎捷,盖以抚诸侯也。伐戎,小事也;卫中国,大功也。献捷,小失也;抚诸侯,大德也。……宋襄一会而虐鄫滕之君,晋文一战而分曹卫之地,君子比其德而计其功,则齐桓之礼可以无愧矣”(《春秋通训》卷三)。在明人卓尔康看来,“齐侯来献戎捷”是为了与鲁修好,“齐侯已伯矣,曷为亲来献捷,与公为好也”(《春秋辩义》卷七)。
3.齐桓公鲁庄公“非礼”说
持此说者,有宋人戴溪、张洽和元人程端学等。戴氏云:“齐侯亲来献捷,非威我也。鲁济之谋,庄公与焉。捷获而过我,因归功于鲁云尔。敌忾献功,诸侯事天子之礼也。鲁与齐,皆失之。”(《春秋讲义》卷一下)张氏云:“愚案:献者,下奉上之辞。观笔削之旨,则齐桓之恃功而不知礼,鲁不当纳而轻受之,其罪皆可见矣。”(《张氏春秋集注》卷三)元人程端学赞同张氏之说(《春秋本义》卷八)。
通过上文的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出,前二说的“正统”论色彩极其浓厚;惟因其囿于“正统”观念,故未能将“齐侯来献戎捷”的症结点明。相对而言,第三说更加客观、更加深入;但其立论的理据依然是“正统”论,仍然未能脱“正统”论之窠臼。易言之,若欲对“齐侯来献戎捷”予以合情、合理、合时的评价,必须有机结合史学的材料与经学的评说,从而审视之、通观之。于此,今人陈寅恪和贺麟所倡导和践履的“同情的理解”,堪称无上法宝、不二法门[4]。
要想合理评价“齐侯来献戎捷”、“同情理解”齐桓公此举,必须首先立足于史实;换句话说,首先应以史实为依据,如此方可客观审视经学诸说。揆诸史实,可以发现,齐桓公之所以“来献戎捷”,是因为前一年尝与鲁庄公遇于鲁济,共商谋伐戎救燕大事;但让齐桓公颇感不快的是,鲁庄公虽然口头答应出兵,但最终未能兑现诺言;鲁庄公出尔反尔、自食其言,结果让齐桓公抓住了把柄。于是,次年便出现了“齐侯来献戎捷”一幕。此中隐曲,宋人沈棐了然于胸,“三十一年书齐侯来献戎捷者,所以愧鲁也”(《春秋比事》卷三)一个“愧”字,可谓画龙点睛。准此,我们可以说,“齐侯来献戎捷”显示了齐桓公光明磊落的一面;因此,孔子对齐桓公的评价是“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当然,我们在“同情理解”齐桓公其人及其“献戎捷”之举时,也有必要指出,“齐侯来献戎捷”并非无可非议。作为一国之君的齐桓公和作为辅弼大臣的管仲如此而为,确实有其考虑不周之处,其气量也未免显得狭小了一些。就后者而言,孔子曾经发表过“管仲之器小哉”的感叹(《论语·八佾》),宋人黄仲炎亦有“齐侯之器小矣”的喟叹(《春秋通说》卷三)。就前者而言,宋人洪咨夔尝为“齐侯来献戎捷”深深惋惜,“使齐移所献鲁者,躬擐甲胄,献之天子之庭,天子大合乐而受之功,与方叔召虎相颉颃矣。惜乎,夷吾智不及此”(《洪氏春秋说》卷八)。更进一步而论,“就周朝国家自身的发展而言,像齐桓公这样的霸主的出现,是周朝国家制度化出现紊乱的标志”[5]。
三、文化:齐鲁燕之文化差异与国家化风格
关于齐、鲁、燕三国的文化差异与国家化风格,我们既可以“分而视之”,也可以“合而观之”;换言之,文化差异与国家化风格实际上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彼此影响着对方。
就齐、鲁、燕三国的国家化而言,三国均系西周初年的封国,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一条相同的道路。即以周王朝为典型的成熟的蓝本,①谢维扬先生认为,商朝和周朝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期”(《中国早期国家》,第381-458 页)。在制度建设上模仿周王朝中央政府;唯因建国者身份的不同、所处地域的差异以及周边环境的互异,致使三国在国家化风格上各具特色,而其文化风貌亦是异彩纷呈。兹事体大,本处仅略道其一(文化差异)。
我曾经指出,在西周之时,如何处理周之封国与土著居民(古族与古国)的关系,当时至少产生过两种模式:一种以鲁国为代表,“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即注重硬性的移风易俗;一种以齐国为代表,“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即注重软性的因风就俗。就燕国而言,当以后一种为主(但也并不排除武力的使用)[6]173。因为处理模式不同,故其后世之发展亦自不同,而其文化风貌亦颇多悬殊。
先以齐国为例。王晖曾经指出,齐太公封于齐地之后,“因其俗,简其礼”,大大地简化了华夏君臣之礼,用以适应东夷地区的习俗。也正是这种因地制宜的文化政策,使齐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同时也造成了齐礼不同于周礼的现象,因此齐国非礼之举甚多[7]。
再以燕国为例。燕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以下三支:姬燕文化、殷商文化、土著文化。这三种文化在燕地既互相冲撞,又互相融合,最后形成了既有别于中原华夏文化、又不同于北方土著文化的燕地文化。当然,以燕国为代表的周文化系统,仍然是燕地文化的主体[6]272-281。
又以齐鲁之别为例。孔子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齐国和鲁国的礼乐制度,相对于“道”(周道)而言已经渐次等而下之。而孔子最向往、最崇拜的文化是周文化(西周文化),亦即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而形成的“周礼”、“周道”,这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文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1]黄朴民.中国军事通史:第2 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181.
[2]陈恩林.中国春秋战国军事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
[3][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9:189,191;赵逵夫.先秦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51;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M].济南:齐鲁书社,2001:58-59,89-90.
[4]彭华.“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J].孔孟学报(台北),2012,90.
[5]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462.
[6]彭华.燕国史稿[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7]王晖.从齐礼、夷礼与周礼之别看周原甲骨属性[J].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4);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北京:中华书局,200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