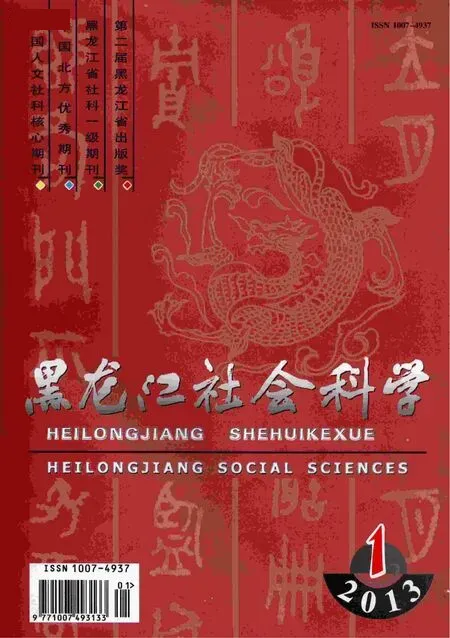冷战与英国小说创作
陈 兵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23)
“冷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47年至1991年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对峙状况。冷战的起因很复杂,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冷战不是哪一个事件或者哪一项决定的产物,而是苏联和西方在意识形态和利益方面根本性冲突造成的结果[1]。1946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美国时发表的“铁幕”演说可以认为是冷战的预言。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正式提出“对苏联发动冷战以遏止共产主义”,成为冷战正式打响的标志。此后1949年以美国为首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方面则于1955年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剑拔弩张,长期对峙。尽管冷战时期除了一些地区性冲突外,北约和华约没有直接进行全面的对抗,但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世界处于核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国际形势长期紧张。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进行民主改革,这种对峙才渐趋缓和。后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失败,苏联于1991年解体,冷战也随之结束。
英国人在二战后期曾一度谋求与美苏一起在战后主宰世界。无奈大英帝国在二战中遭受重创,此时实力大减,已经无力与美苏争雄。因此冷战开始后很快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格局,而英国只能做美国的小兄弟,帮助其摇旗呐喊。这不能不使英国人产生深深的失落感。特别是二战后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进一步削弱了英国的实力。当时英国著名诗人奥登的长诗《焦虑时代》(1947)就是这种失落和焦虑感的表达。冷战初期,英国小说创作中弥漫着悲观主义的情绪和对共产主义苏联的强烈敌意。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经济复苏,社会比较繁荣稳定,才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乐观情绪。而随着冷战的升级,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使得间谍小说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通俗文学类型,其中的“007”系列间谍小说的风行既反映了国际政治风云,也体现了英国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的回归。与此同时,冷战期间笼罩全球的核战争阴影又促使不少作家利用科幻小说的形式来研究人性,探讨人类的未来。
一、对共产主义苏联的拒斥
在英国争霸世界的过程中,俄国一直是它的一个重要对手。19世纪中期英国和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及其在中亚的争夺等都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广泛关注。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就多次在自己的作品里将俄国描述成英国的敌人。另一方面,英国有悠久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因此对苏联高度集权的共产主义制度怀着高度的戒备和憎恶。当德国法西斯被击败之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迥然不同的共产主义制度就成为西方国家政治心理挥之不去的新的梦魇。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斯大林政府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大清洗运动更是使得很多原本同情苏联的西方知识分子感到幻灭。这一点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如下事实里:1949年英国国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编辑出版《失败的上帝》一书,记述了路易斯·费舍尔、安德莱·纪德、亚瑟·凯斯特勒、依格纳西欧·希罗尼、斯蒂芬·斯彭德和理查德·赖特等六个曾是共产主义者的欧美著名作家、记者放弃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这本书在当时的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实际上属于冷战中意识形态之战的组成部分。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也表现在当时的英国小说创作中。
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戒备和拒斥在当时的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作品里表现得最为明显。奥威尔信奉民主社会主义,起初对共产主义持同情态度。他曾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作为志愿者赶赴那里参战,支持共和政府,但后来共和政府内部的派系纷争使其对集权主义产生了极大的恐怖,而共产主义在其眼里也成为集权主义团体。其名作《动物农场》(1945)和《一九八四》(1948)就是对集权主义的抨击。一般认为,《动物农场》是二战后第一部英国小说[2]278。这部小说以动物寓言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农场上的动物如何在猪的组织下反抗人类的压迫,赶走了主人,成立了各种动物均平等共处的自治组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公猪“拿破仑”为首的动物领袖们逐渐萌发了特权思想,它们追求享乐,为此不惜篡改先前的革命思想,欺压其他动物,直到最后这些特权动物们甚至与它们推翻的人类进行合作,一起来欺压其他动物。这部作品里有明显的对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影射和攻击。比如,那个发起革命的老公猪“老少校”明显指代列宁,而强横霸道的公猪“拿破仑”则无疑影射斯大林。刷在墙上、后来被“拿破仑”等随意涂改的革命标语则是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形象演绎。奥威尔自己在1947年3月为《动物农场》的乌克兰文版写的序言中就明确说明此书的情节部分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同时说明自己1937年在西班牙参战的经历使得他体会到了苏联极权主义的可怕及其宣传对西方的蒙蔽,因此从西班牙回来后他要写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3]。
奥威尔对集权主义的攻击在《一九八四》中表现得更加突出。这是部反乌托邦科幻小说,时间设定在1984年。小说描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温斯顿·史密斯在“大洋国”里的遭遇。“大洋国”是个高度集权主义的国度,有统一的政党、严密的政治组织和原则,一切以党首“老大哥”的马首是瞻。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体制的严密监管和控制之下,一言一行均无任何自由可言,甚至连人们的思想也受到思想警察的操控。温斯顿在这令人窒息的国度里曾经试图反抗,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奥威尔通过对温斯顿观察、质疑、反抗到最后完全屈服的过程的细致描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集权主义统治的残酷和灭绝人性。
《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奥威尔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攻击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许多经历了德国法西斯集权统治和斯大林大清洗运动的西方人对集权主义制度产生了高度的戒备和拒斥心理。
冷战初期除了奥威尔的作品外,还有其他一些作家发表了攻击共产主义苏联的作品。如前述的亚瑟·凯斯特勒曾加入过共产党,但后来也反对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和集权主义,他写过不少反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其于1940年出版的小说《中午的黑暗》,以政治大清洗为背景,通过一个名叫鲁巴肖夫的老布尔什维克含冤入狱的经历表达了对集权主义恐怖统治的厌恶。这部作品后来在1951年被改编成戏剧,在纽约上演,受到好评,获得了纽约剧评家奖。1998年此书在美国现代图书馆推选的“20世纪最好的100 部英语小说”中名列第八。
此外,当时英国著名作家伊夫林·沃在二战后创作的“荣誉之剑三部曲”(《军人》,1952;《军官和绅士》,1955;《无条件投降》,1961)也间接攻击了苏联政权。这几部小说被认为是关于二战最杰出的小说作品,它们以自己的战争经历为基础,描述了一个怀有正义感的英国老派贵族对于这场战争的失望。但是,尽管几部小说的主题在于抨击当时英国政治上的尔虞我诈,传统道德的堕落,号称正义战争的荒诞,却也表现了一定的冷战思维。比如小说将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视为集权主义的联盟,是西方公开的敌人。由此出发,小说将英苏在二战时的结盟视为对政治正义的背叛,原本针对希特勒纳粹主义的“圣战”被玷污[2]285。显然,“荣誉之剑三部曲”表达的是英国保守人士对苏联及共产主义的疑惧。而当代英国女小说家丽贝卡·韦斯特的长篇小说《鸟儿坠落》(1966)则通过一个英裔俄国姑娘的遭遇描写了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意识形态分裂问题,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争议。
总的来说,上述拒斥共产主义苏联的小说作品既表达了这些作家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冷战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必须加以明确。
二、对东西方暗战的关注
冷战期间国际局势波诡云谲,间谍活动非常频繁。而英苏这对传统的老对手之间更是一直间谍战不断。仅以二战后论,就有1945年至1950年初的“剑桥间谍案”;1960—1971年27 名苏联外交官遭到英国驱逐;1971年又有105 名驻英苏联外交官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遭到英国驱逐。频繁的间谍活动也促成了间谍小说的繁荣。间谍小说在英国历史悠久,一般认为以威廉·勒克的《一八九七年英国之战》(1893)或罗伯特·奇尔德斯的《沙滩之谜》(1903)为诞生的标志[4]138。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基姆》(1901)也描述了英国和俄国的情报部门在印度边境进行间谍战的情形。约翰·布肯的间谍小说名作《三十九级台阶》(1915)等更是名闻遐迩。此后间谍小说虽然历经沉浮,却一直在英国通俗文学中绵延不绝。间谍小说往往以国际争端为背景,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展开间谍故事情节,主题则往往涉及爱国主义或个人的信仰。冷战时期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显然是间谍小说发展的沃土。
冷战初期,英国间谍小说以埃里克·安布勒和格雷厄姆·格林的间谍小说为代表。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作品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为传统的间谍小说增加了关注个人利益和社会正义,重视对道德和忠诚问题的探讨等主题,促进了间谍小说的发展。其中安布勒写于二战前的间谍小说如《迪米特里奥斯的假面具》(1939)等表现出左倾思想倾向,抨击国际资本主义势力。而其二战后的小说则站在弱小民族和国家一边,谴责超级大国的争霸给世界带来的威胁和罪恶。其《审判德尔切夫》(1947)、《希尔默遗产》(1953)、《武器通道》(1959)等都表达了类似的主题。与安布勒相比,格林在其作品中则更重视对道德、忠诚等人性问题的探讨。格林将自己的作品分为“娱乐小说”和“严肃小说”,但实际上有时很难将其作品归类,比如其间谍小说名作《沉静的美国人》(1955)、《我们在哈瓦那的人》(1958)、《人性的因素》(1978)等既属于间谍小说,又因为对人性和道德的深度探索被认为是严肃小说。格林曾经做过特工,熟悉其中的很多奥秘,因此写起间谍小说来得心应手。上述间谍小说既惊险刺激,又表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个人的渺小以及人性的弱点,内涵非常丰富。中国著名学者王佐良先生曾评价说:“在格林撰写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并不是艾略特诗作中那种一片干旱的荒原,而是一个被评论家称作‘格林之原’的世界,一个有多种信仰,多种性格,多种经历的人组成的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精神世界。”[5]
冷战时期最受欢迎的间谍小说家当数伊恩·弗莱明。这位二战期间英国海军情报局的得力干将战后在自己情报生涯的基础上创作了一系列以代号为007 的特工詹姆斯·邦德为主人公的间谍小说,如《豪华赌场》(1953)、《来自俄罗斯的爱情》(1957)、《金手指》(1959)、《为了女王陛下的特殊使命》(1963)等。这些小说大受欢迎,很多都被搬上了银幕,在全世界风靡一时。甚至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还有詹姆斯·邦德恭请女王出席的场面。007 系列小说具有典型的娱乐小说元素:俊男靓女、具有异国情调的场景、富丽堂皇的宴会、艳遇以及这些光鲜色彩掩盖下的凶杀和钩心斗角。而特工们的坚韧顽强和强烈的责任感就展现在这些衣香鬓影和觥筹交错之中。故事构思巧妙,细节逼真,很好地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融合在一起。007 系列间谍小说的畅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民众对大英帝国往日荣光的怀念,特别是邦德的神勇和机智无疑再次激发了英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如果说弗莱明的007 系列使得间谍小说发展成为一种极受欢迎的通俗文学,那么约翰·勒卡雷和莱恩·戴顿则以深刻的主题、精湛的艺术技巧和优美准确的语言将间谍小说发展到新的高度。勒卡雷真名是戴维·康维尔,如前辈格雷厄姆·格林一样,他也做过英国特工,而且从小就与其专横的父亲斗智斗勇而养成了“双重间谍”的性格。这些都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勒卡雷的第一部间谍小说是《打给死者的电话》(1961),其时他还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他于1963年出版的《来自冷战世界的间谍》大受欢迎,于是勒卡雷脱离特工生涯,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勒卡雷的小说不仅以圈内人的身份展现冷战期间间谍战的种种内情,也以疑虑和厌恶的笔调表达间谍活动中爱国主义观念的异化,人性的扭曲、道德的堕落等等。“你知道,我们都一样,这真是个笑话”。勒卡雷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样说道,反映出战后各国情报部门的活动都一样堕落,从而使得其间谍小说获得了一种思想的深度[2]429。其1965年的《镜子战争》就是对整个间谍世界的深度探讨。此后他的间谍小说三部曲《补锅匠、裁缝、士兵和间谍》(1974)、《可敬的学童》(1977)和《一个完美的间谍》(1986)对上述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莱恩·戴顿的首部间谍小说《伊普客雷斯档案》(1962)描写一位无名英雄参与营救一位被绑架的生化学家,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缺陷,受到广泛的欢迎。此后他创作了多部间谍小说。《被淹的马》(1963)被很多评者认为是其最优秀的作品,而《豪华坟墓》(1967)也以细节的真实和对人物的精心刻画受到读者的好评。其后的三部曲《柏林游戏》(1983)、《墨西哥同伙》(1984)和《伦敦对手》(1985)也显示出不俗的实力。尽管戴顿的小说有时情节过于复杂,描写过于琐碎,但总体而言,他的创作想象力丰富、细节描绘真实、人物形象鲜活,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勒卡雷和戴顿的间谍小说不仅继承了奇尔德斯和布肯等前辈的间谍小说传统,还从格林和凯斯特勒等作家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发展了间谍小说的文学性和严肃主题,使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作为通俗文学的间谍小说,成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
除了勒卡雷和戴顿的间谍小说外,20世纪80年代还有一些小说家如弗雷德里克·福赛斯和肯·福利特等将历史传奇和间谍小说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秘史”模式,表现职业间谍的敬业精神。
朱利安·西蒙斯在1972年曾断言,间谍小说已经走到尽头,在天才作家弗莱明、勒卡雷和戴顿之后不会再有辉煌[4]165。这个结论可能下得过早。因为冷战时期的国际风云变幻的因素仍然存在,间谍小说还有生长的土壤,因此上述作家之后间谍小说依然繁荣,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核战争阴影下的人性反思
英国文化人长期以来一直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经历过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他们更是注重对人性和道德的探索。1948年,英国当时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出版《伟大的传统》一书,通过对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等著名作家的研究,指出英国文学中存在着一个重视人性和道德探索的传统。《伟大的传统》出版于冷战开始后的第二年,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此书与冷战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但在刚刚经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版此书,显然有在礼崩乐坏之后重建人文道德的意图,体现了利维斯这样的文化精英对人类未来的忧思。
这种忧思无疑也和冷战期间潜在的核战争危险有关。在二战末期,美国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基本上毁灭了这两个城市。原子弹的可怕威力使不少有识之士对人类的未来心生疑惧,特别是很多人已经在战争中见识了人性的扭曲和丑恶。冷战期间,美苏尽管没有进行直接的全面对抗,但全球各地小规模战争和地区性冲突不断,背后基本上都有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子。而且两国一直公开进行军备竞赛,双方都储备了足够毁灭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甚至将军备竞赛发展到外太空。国际形势如此紧张,一旦失控,毁灭全球的核战争就有可能爆发。可以说,自冷战以来,全世界都处在核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而英国失去了大英帝国的雄风之后,又成为孤悬海外的小岛,不安全感分外强烈。因此冷战期间不少英国作家以悲观主义的基调表现对核战争和未来人类命运的担心。
冷战初期英国著名作家和科学家C.P.斯诺的小说就表现了这种主题。其小说《新人》(1954)描述了科学家在面临学术和权力分歧时的道德困境,同时也反映了英国科技界对核战争的恐惧心理。故事结尾核物理学家马丁主动放弃原子弹研制,表明了斯诺对研制和使用核武器的否定态度。而《权力通道》(1964)则以冷战为背景,描写了英国社会高层的权力斗争,其中也涉及核武器竞赛和核战争,表现了作家对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高度关注。
也许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能够代表冷战初期英国作家对冷战和核战争阴影背景下的人性反思。戈尔丁参加过二战,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以及在战争中人性的扭曲。其首部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蝇王》(1954)更是以其战争的背景和对人性的深度探索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小说借用了英国19世纪中期著名历险小说《珊瑚岛》(1857)的少年海岛历险形式,但却一反《珊瑚岛》对英国人自身文明的自信,表现了在失去文明约束后人性的扭曲和堕落。故事开始时战争爆发,一群英国少年儿童搭乘飞机撤离,但飞机被炮火击中,众人流落荒岛。故事结尾,这些已沦落为野蛮人、自相残杀的儿童终于得救,但前来救助他们的是一艘驶往远方执行任务的巡洋舰。故事结尾,小说主人公拉尔夫“他失声痛哭: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为忠实而有头脑的朋友猪崽子坠落惨死而悲泣”[6]。整部小说的外在叙述框架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是核战争),加上小说本身的“人性恶”主题,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人性和战争的反思。戈尔丁的小说创作对后来的英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选出1945年以来英国50 位最伟大的作家,戈尔丁名列第三。
对核战阴影下人性的反思更多地反映在当时的科幻小说中。英国科幻小说源远流长,利用科幻小说表现严肃主题的传统也很悠久,20世纪初英国现实主义三杰之一的H.G.威尔斯就写了一系列科幻小说来探索英国社会和人性。二战后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冷战的需要促使各国大力发展尖端军事技术。科技的繁荣促进了科幻小说的发展。同时由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不少科幻作家也在科幻小说中表现对人性的反思。约翰·温代姆的《吃人三叶草的一天》(1951)描写在流星雨和吃人三叶草的肆虐下伦敦的末日景象,而这些流星雨和三叶草则极有可能是苏联研制的太空和生物武器。《海妖醒来》(1953)则描述了外太空生物对地球的入侵,而在这危难时刻处于冷战中的几个大国却依然不能同心协力,共抗外来侵略,反而互相猜疑,差点引发核战争。这些小说中明显流露出一种对苏联的敌意和对处于核战争阴影下的人类未来的担忧。类似的焦虑不安情绪在约翰·克里斯托弗的小说中也有表现,如其《小草之死》(1956)也描写了与《吃人三叶草的一天》类似的末日景象,而其科幻三部曲《白色的群山》(1967)、《金和铅的城市》(1968)和《火塘》(1968)也通过描写外来三脚机器怪对地球的征服表现了一种焦虑感。女作家克里斯汀·布鲁克-罗斯也在其小说《外面》(1964)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描述了一场核战争后世界满目疮痍的恐怖景象,发人深省。而克里斯托弗·普利斯特在《为变黑的岛作赋格曲》(1972)也描述了未来在核辐射背景下,成千上万的非洲难民涌入“变黑的岛”英国,引起日趋剧烈的种族纠纷,社会一片混乱。有意思的是,普利斯特写了不少科幻小说,还得过科幻文学奖,却不承认自己写的是科幻小说,因为他觉得科幻小说大都很肤浅,而他的作品却具有深意[7]。1960年代英国“新浪潮运动”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J.G.巴拉德在其“灾难三部曲”《沉没的世界》(1962)、《燃烧的世界》(1964)、《结晶的世界》(1966)里以悲观主义的笔调描写人类在冰川融化淹没世界、全球旱灾引发大火、宇宙结晶化等弥天大灾前挣扎求存的惨状,表现出冷战背景下对人类未来潜在灾难的恐惧。1984年,巴拉德出版半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该小说以二战后期为背景,描写二战期间一个住在中国上海的英国少年与父母失散后住进了日本的平民集中营,在那里体验和见证了战争中的饥饿、死亡和其他种种暴行,也知道了原子弹轰炸长崎的消息,是1980年代英国最有影响的小说之一,获得了英国《卫报》的小说奖。考虑到英国与日本俱为岛国,这部小说的热销明显表现了英国普通平民在核战争阴影下的疑惧和不安全感。
这里有必要提及安格斯·威尔逊和多丽丝·莱辛。这两位都是当代英国重要作家,写过许多严肃文学作品。但他们也运用科幻小说形式表现自己对处于核战争阴影下的人类未来的思考。威尔逊的《动物园的老人们》(1961)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时间设定在1970—1973年间。小说中的伦敦动物园无疑是英国社会的缩影,故事通过管理动物园的几个老人之间的权力争斗以及动物园里人与动物间的冲突表现了当时在核战争威胁下英国无序混乱的景象,哀叹英国昔日辉煌不再。这部小说涵盖了冷战期间英国小说创作的各种主题,特别是“战争导致人性退化”的主题[8]913。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风格和主题都经历了不少变化。其《幸存者回忆录》(1974)是反乌托邦小说,描述了一场无名灾难之后伦敦的残破和沉沦景象。而其1980年代的科幻小说《南船座的老人星》(1979—1983)五部曲则在外太空的广阔背景下描述第三次世界大战后三个星际帝国争斗的故事,明显具有讽喻色彩,表明作家对人类未来的担忧。有评者指出莱辛的小说内容丰富,涵盖多种主题,也深刻反映了冷战初期欧洲的文化气候[8]937。
二战之后的英国小说创作延续了战前的强劲势头,发展良好,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等纷纷粉墨登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英国小说家们一如既往地关注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的变化,同时参与社会的价值建构,针砭时弊,探索人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半个世纪的冷战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施展其才华的舞台。在冷战之初一些英国作家在其创作中表达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疑惧。随着冷战的升级,国际局势日益复杂,间谍小说开始繁荣,很多英国作家通过间谍小说表达对国际局势的理解和对爱国主义、人性、道德等观念的思索。与此同时,核战争阴影笼罩全球,许多英国作家秉承英国文学注重人性和道德探索的良好传统,通过科幻小说等艺术形式表现了对人性的堕落和对人类未来的忧思。冷战期间的英国小说创作既反映了当时的国际争斗和社会变化,又带有鲜明的英国特色,是当代英国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1]约翰·W·梅森.冷战[M].余家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
[2]Malcolm Bradbury.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3]董乐山.奥威尔文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01-106.
[4]黄禄善、刘培骧.英美通俗小说概述[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7.
[5]王佐良,周珏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667.
[6]威廉·戈尔丁.蝇王[M].龚志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01.
[7]刘文荣.当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334.
[8]John Richetti.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