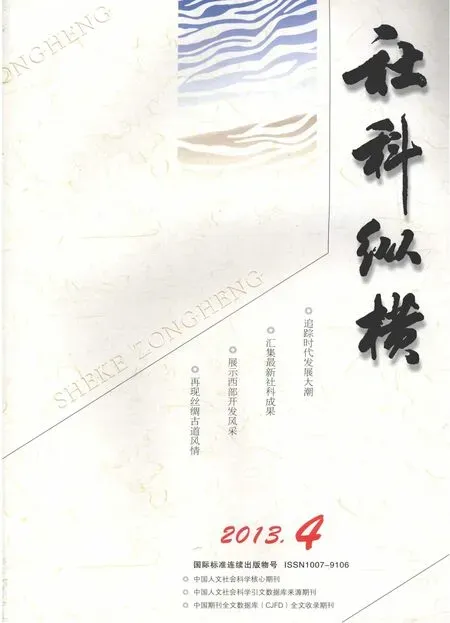突厥语中的汉语借词
王新青
(新疆大学语言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8)
众所周知,欧洲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强调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研究的同时,也谈到了语言的外部要素,例如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殖民统治、国家政府的行政法令、教会、学校、文学语言、相邻地域等对语言的内部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属于语言发展的外部要素[1](P43-44),这些外部要素对语言产生影响的直接结果就是语言中的借词。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E.萨丕尔(Edward Sapir)关于借词也有这样的阐述:“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与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或敌对的……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2](P43-44)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语言在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与外界产生一定的联系和交往,文化的交流必然会对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语言相互之间的借用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
1929年前苏联巴泽雷克墓葬中发现的物品,其中中国精美的丝织品和绣有凤凰图案的茧绸、漆器以及“山”字纹青铜镜震惊了世界[3](P55)。中亚出土的此类物品大约属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之间。说明汉语借词很早就被借入到中亚语言之中。这些借词多保留在公元7—10世纪的鄂尔浑—叶尼塞时期的古代突厥文碑铭及回鹘文突厥语文献中。
baxsi义为“巫师、师傅”,借自于汉语的“博士”。“博”为宕摄、开口、帮母、铎韵、補各切、一等入声字,其古音为:bak;所以“博士”的古音在古代突厥语作baxsi,义为:师傅,该词见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例如:
我做了师傅(baxsi)应该为弟子们做的事情,当你们明智的眼睛明亮之时,你们不要把我忘记[4](P246)。
现代乌兹别克语作baxsi,义为:①民间说唱艺人②巫师,巫医。③预言者;现代哈萨克语作baqsi,义为:①女巫婆。②巫师,巫医。③萨满;现代吉尔吉斯语作baksi,义为:巫师,巫医;现代土库曼语作bagsi,义为:民间说唱艺人;现代土耳其语作baksi,义为:①观察者。②预言家,巫师;现代波斯语作baxsi,义为:军事长官,博学的;现代蒙古语作bags,义为:教师,教员,老师,导师,师傅[5](P109);现代满语作 baksi,义为:学者,儒者[6](P458)。汉语“博士”用时音变为baxsi;现代中亚诸语言中仍有保留,只是根据各自的语言特点略作音变;波斯语在对中亚语言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反过来从中亚语言中借用了这个汉语借词;蒙古在征服中亚的同时,也从中亚语言中转借了这个汉语借词bags;满语又从蒙古语中再次转借这个汉语借词baksi。
ba··g,义为:伯,伯克,老爷,大人,有的突厥人男性人名后缀加该词,以示尊敬。该词借自于汉语的“伯”,“伯”为梗摄、开口、帮母、陌韵、博陌切、入声二等字,其古音为:bok,其义表示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的第三等爵位“伯”。该词被突厥语借用为ba··g,保留在古代突厥语碑铭中:ba··g,义为:匐,官员;并被保留在古代突厥语文献中,义为“伯”、“伯克”等,如:
11.然安康,有一块细布(和)
12.箩筐请你查收,你从艾得古·依干手中取吧
13.我们伯(ba··g)·末思达干的信
14.请交库温僧人[7](P139-140)
该词在古代突厥语中有时表示“头目”、“官儿”,如:
有四个夜叉来到跟前,其中一个握着大鞭子,另一个拿着绳索,第三个手持夹子,第四个是一位身着蓝衣骑在马上的头目(ba··g)。[8](P225)
在唐代史籍中,ba··g一词的惯用对音词是“匐”[9]。元代音译为“别”、“伯”、“卑”、“毕”等[10](P321)。该词至今仍然保留在中亚突厥语中,现代乌兹别克语作бек,义为:①爵位的称号。②中亚官职。③多用于男性人名之后,表示尊敬;现代哈萨克语作бек,义为:贵族,封建主;现代吉尔吉斯语作①仅次于可汗的王公贵族②部落酋长,首领③多用于男性人名之后,表示尊敬;现代土耳其语作bek,义为:观察员,监督官;现代蒙古语作bag,义为:蒙古行政区基层单位,相当于“乡”。显然,中亚诸语言借用了汉语的“伯”这个词,蒙古语又从中亚语言中转借了汉语的这个借词。上述这些语言均保留了汉语”伯”的古入声韵尾[-k],从中可以反映出古汉语的一些语音面貌。
bit-i-[biti],义为:写、书写,该词借自汉语的“笔”。“笔”为臻摄、开口、帮母、质韵、鄙密切、入声三等字,古音拟为bit。古代突厥语受汉语影响,借用了这个汉语借词,例如:
有一个名叫居道的人由于杀死了许多生灵,因悔恨而发愿要将唤作《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经典全部抄写(bititi),以乞求幸福[8](P236-237)。
在突厥语社会经济文书中也经常出现该汉语借词,如:
16.该手印是我证人艾山·不花的。
17.我喀里姆杜亲自书写了(bititim)该文书。[11](P120)
蒙古也借用了这个汉语借词,蒙古语动词作bicex,义为:写,书写,记录。bitig,突厥语义为:信、书、文书,该词是由借自古汉语的“笔”的同根词bit-i-“写、书写”构成的。例如:
24.托合里利写了(该文书)。这个图章是我萨比的。
25.(这是)从萨比处买土地之文书(bitigi)。[11](P49)
蒙古语借用了汉语的这个借词,蒙古语名词作 bicig,义为:文字,文献,书,文件,证件;满语也借用了汉语这个借词,满语作bithe,义为:书,书札,文[6](P460)。
此外,中亚突厥语当中还有汉语sangun,义为:将军,该词借自汉语的“将军”一词。“将”为宕摄、开口、精母、阳韵、即良切、三等平声,“军”古音为臻摄、合口、见母、文韵、举云切、三等平声字,sangun“将军”一词见于缪勒于1913年发表的《吐鲁番出土的二则木杵铭文》中:
优婆塞俱录·伊难奇沙州将军(sangun)。我们二人从那些通晓佛经的、智慧的师傅们那里听说了如下的话语:“如果有任何一个人……”。[12](P177-178)
总而言之,中亚突厥语言中仍然保留了一些非伊斯兰教方面的汉语借词,使我们透过这些借词,依稀窥见中亚古代多元文化的影子,这些借词是历史上中亚多种语言、多元文化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历史见证。本文通过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蒙古语、满语等文献资料,论述了突厥语中的汉语借词,这些汉语借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汉语借词在古代的语音面貌。本文在此仅对其中的几个汉语借词做了论述。由于篇幅所限,突厥语中其他的汉语借词就不在此一一赘述,若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学者予以惠教。
[1][瑞]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2004.
[2][美]爱德华·萨皮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商务印书馆,2003.
[3]王治来.中亚史纲[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4]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鹘文献寓言语言研究[M].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5]新蒙汉词典.编委会.新蒙汉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
[6]季永海.满语语法[M].民族出版社,1984.
[7]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M].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139-140.
[8]杨富学.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M].民族出版社,2007.
[9]F·Hirth:“Nachworte zur Inschriften des Tonju kuk”,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der Mongolei,St.Petersburg 1899,S.107.
[10]韩儒林.穹庐集.突厥官号考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1]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M].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
[12]F.W.K.Müller,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rufanfunden,APAW,1915,S.3~13.;杨富学.回鹘之佛教[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7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