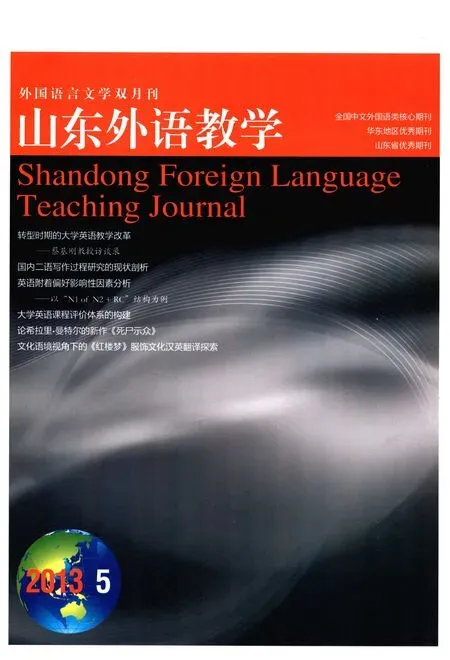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伦理思考
——论达雷尔小说《阿芙罗狄特的反抗》
徐彬,刘禹
(1.大连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伦理思考
——论达雷尔小说《阿芙罗狄特的反抗》
徐彬1、2,刘禹1
(1.大连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44;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通过《阿芙罗狄特的反抗》劳伦斯·达雷尔实现了对后现代消费文化在虚拟小说世界中的构拟与批判。小说中梅林公司建立的全球范围内的商业帝国是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微缩景观。通过对发明者、公司、产品和消费者之间复杂伦理关系的描述,达雷尔为读者提出了一系列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的伦理真空和伦理危机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达雷尔意在指出:消费者个人层面上理性意志的觉醒和有德、有志且处于权力阶层的“有机知识分子们”果敢、正确的伦理判断和伦理选择,才是遏制后现代消费文化中人们的“兽性因子”,回归“人性因子”的有效途径。
后现代消费文化;伦理;劳伦斯·达雷尔;《阿芙罗狄蒂的反抗》
英国著名现当代小说家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的“双层小说”(double-decker novel)《阿芙罗狄特的反抗》(The Revolt of Aphrodite)包含《彼时》(Tunc,1968)和《永不》(Nunquam,1970)两部小说。英美文学评论界对这两部小说的评论褒贬不一。《时代周刊》(Time)、《新闻周刊》(Newsweek)和《观察报》(Observer)对达雷尔精致的语言和精巧的故事情节赞叹不已,其中不乏文学大师和批评家,如:安格斯·威尔逊(Angus Wilson)和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等人的溢美之词。然而有些评论家并不看好这部作品,他们认为《阿芙罗狄特的反抗》偏离了《亚历山大四重奏》(The Alexandria Quartet)的创作风格,无法与《亚历山大四重奏》同日而语,达雷尔该作品的艺术和社会价值也因此被诸多评论家所忽视。
《阿芙罗狄特的反抗》中,达雷尔以梅林公司的全球商业帝国为原型构拟了一个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的世界图景,为读者阐释了以伦理主体的缺失和异化为外现的伦理真空的成因。在此基础上,达雷尔指出隐藏于后现代社会“消费快感”之后的是人类“兽性因子”激发下的非理性消费欲望。发明家费利克斯对“人性因子”的理性回归受到与公司签订的契约的限制而无法实现。费利克斯两种伦理身份:“浮士德博士”和“普罗米修斯”的并存与矛盾冲突使其深陷伦理危机之中。为了解决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的伦理失范问题,小说主人公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和费利克斯分别从个人层面和“有机知识分子”的权力层面对公司进行了反抗。达雷尔在小说中阐释的这种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伦理觉醒与实践正是作者本人留给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的读者们的有益启示。
1.0 梅林公司与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伦理真空
赫布迪齐(Dick Hebdige)将后现代生活比作“另一个星球上的生活”(转引自Zylinska,2005:40),言外之意面对全新的生存环境,人们丧失了对传统伦理规范的把握,变得无所适从;斯莱克(Jennifer Slack)和惠特(LauriteWhitt)指出:“后现代主义指的是一种道德困惑和所有价值的贬值状态。”(同上:31)在《阿芙罗狄特的反抗》中,达雷尔以小见大将梅林公司设定为后现代消费文化的缩影,为读者绘制了一幅伦理真空的图谱。达雷尔虚拟的小说世界就是梅林公司统治下伦理失范的“另一个星球”,公司既是这个星球的主宰者又是伦理真空的制造者,伦理真空主要体现在伦理主体的消失和异化两方面。
达雷尔笔下的梅林公司如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91)中描述的那样,是跨国资本主义扩张的具象,是造成多个小说主人公“主体之死”的动因。(詹明信,2013:328)梅林公司分别以西方(英国的伦敦)和东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为中心,像巨大的资本章鱼一样迅速发展成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跨国企业集团。然而与规模的无限制扩大相并存的却是公司领导人的缺失(the absence of leader),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伦理主体的消失。
达雷尔用“梅林”给小说中的科技公司命名旨在取得反讽的批判效果。公司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为前提预设”(费瑟斯通,2000:18)的金钱至上的后现代消费文化的缩影。梅林是英格兰及威尔士神话中的睿智机敏、法力强大,能预知未来的传奇魔法师(Briggs,1976:440)。在亚瑟王的传说故事中,梅林是正义力量的化身,在他的帮助下亚瑟王登上英格兰的王位,领导圆桌骑士统一了不列颠群岛。然而小说中以“梅林”命名的科技公司却好似魔鬼撒旦,它的执行总裁朱利安则是撒旦爪牙梅菲斯托费勒斯(Mephistopheles)的化身,他们的联合旨在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以刺激消费为手段,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帝国。朱利安曾借路德(Luther)的观点,揭露了“公司”的魔鬼本质,“他[路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撒旦用以统治世界的力量来源。撒旦的王国从本质上讲是资本主义的——我们都是恶魔的财产,他[路德]在谴责现存社会制度时说‘金钱是魔鬼的语言,与上帝以神圣的语言创造世间万物一样,魔鬼以金钱为语言创造了这个世界’”。(Durrell,1990b:177)
公司创始人和后继领导者已被置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境地,人作为伦理规约制定者的身份被公司剥夺。公司创始人梅林(Merlin)病逝后,朱利安(Julian)接替他成为从未露面的公司领导人(faceless leader)。公司仿佛一个不受控制、独立运行的有机生命体,正如朱利安在电话中批评费利克斯(Felix Charlock)时所说的那样:“公司早已超出缔造者们——梅林、乔卡斯(Jocas)和我的掌控:我们不过是它的前辈罢了。现在公司能自我延续,按照自身设定好的轨迹运行,你我都无法左右它。”(Durrell,1990a:286)。公司运行的伦理道德监管也因此陷入真空,如,公司在费利克斯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发明的镶纳纤维(sodium-tipped filament)给公司另一名科学家马钱特(Marchant)使用去生产枪炮瞄准器。发明专利被公司剥夺,产品的应用是否符合伦理规约已超出发明者本人的掌控。
公司缔造者梅林为了招募天才发明家加入公司,无情地践踏了父女间的亲缘伦理关系。梅林从女儿守护神的父亲角色异化为夺取女儿贞操与幸福的恶魔。梅林的养子朱利安与亲生女儿贝妮蒂特(Benedicta)青梅竹马。为了阻止二人的结合,让他们各自为公司所用,梅林命令手下人阉割了朱利安,轮奸了贝妮蒂特。梅林任命朱利安为公司继承人,把女儿调教成以美色诱引发明家们加盟公司的“诱饵”,并先后与不同的发明者结婚。
费利克斯便是众多“上当受骗”的发明者中的一员。费利克斯与贝妮蒂特第一次见面时,贝妮蒂特正在哄诱、训练刚捕获的猎鹰。凯克文斯基(Donald P.Kaczvinsky)指出:言语之间,贝妮蒂特实际上将费利克斯与手上的猎鹰相提并论。在贝妮蒂特的诱引下,费利克斯分别与梅林公司和贝妮蒂特签订了工作与婚姻的双重契约,成为受制于公司的“猎鹰”。(Kaczvinsky,1994:67)朱利安和费利克斯沦为梅林公司的傀儡,而贝妮蒂特从梅林的女儿——梅林商业王国里的公主,降格为公司利益链条上不可或缺的“性奴隶”,公司生产之初所必须消耗的“原材料”。
公司还通过特殊的“洗脑”方式完成了对费利克斯伦理主体的异化,失去记忆的费利克斯丧失了伦理判断的能力,心甘情愿地为公司服务。小说《彼时》结尾,试图逃离公司的费利克斯被公司抓捕后送到公司位于保尔豪斯(Paulhaus)专门收治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疗养院。费利克斯大脑记忆中枢的一小部分被外科医生切除。就这样费利克斯被强制进行了“洗脑”,一觉醒来,费利克斯甚至连自己写在日记封面上的名字都认不出来了,“床头放着一本绿色的日记,或许这能提供线索?上面写着别人的名字费利克斯·夏洛克(Felix Ch.)。……一连好几个月的日记内容都被人撕掉了。消失了!消失的月份,消失的日子”。(Durrell,1990b:11)费利克斯变成“一个没有影子的人,就像没有表盘的钟表”。(同上:12)从《彼时》结束到《永不》开始,费利克斯对公司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洗脑”后的他是最值得信任的、最有责任心的成员。
罗宾逊(Jeremy Robinson)指出《阿芙罗狄特的反抗》“凸显了20世纪中后期自我身份危机、文化衰落、道德下滑等主题”。(Robinson,1989:143)如从微观视角出发,以公司为切入点,不难发现引发上述论题的核心应该是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公司制度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被人格化了的公司把商业版图的扩张和追求经济效益设定为公司成员必须服从的“终极伦理旨归”,消除了人对公司的领导与伦理监管,扭曲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伦理关系,公司制度下的人最终陷入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伦理真空之中。
2.0 契约关系、“消费快感”与伦理身份危机
费利克斯与梅林公司之间存在着类似浮士德博士与魔鬼撒旦之间的契约关系,为了换取公司物质(科学研究设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上的支持,费利克斯身上的“兽性因子”战胜了“人性因子”。(聂珍钊,2011:6)加入公司后,两种因子之间的斗争关系发生了逆转,然而费利克斯对向善的“人性因子”的伦理选择却被契约的牢笼囚困。费利克斯因无法实现伦理选择,重塑伦理身份而深陷危机之中。
在梅林公司提供的一系列“消费快感”(费瑟斯通,2000:19)面前,费利克斯迷失了自我。未加入“公司”前,费利克斯已经对“公司”充满了如浮士德博士对魔鬼撒旦般的笃信。“南去的列车上,我(费利克斯)大声朗读着《泰晤士报》的市场报告专栏,听起来像是在读圣经里的赞美诗,胸中充满对梅林公司的忠诚与热爱。”(Durrell,1990a:20-21)在被朋友问及为何与梅林公司签合同时,费利克斯回忆说:“那时我眼里满是名誉、爱情和随之而来的巨额资产。我对自己说‘是的’,听到自己沙哑的嗓音我吃了一惊。‘是的,我的确是个傻瓜,但我必须在合同上签字’。”(同上:147)新婚之际的费利克斯面对隆重、奢华的婚庆场面感叹说:“不是我在说话,上帝啊。我不过是我身处文化的代言人罢了。”(同上:173)费利克斯身上存在着“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为了实现“消费快感”费利克斯与公司签订了浮士德博士般出卖灵魂的契约。“浮士德精神”内含“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这两种伦理选择因子。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The Fall of theWest)中指出:“浮士德精神”是近代欧洲人为了改造社会而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等领域展现出的进取精神。(转引自Fischer,1989:32-34)“浮士德精神”体现了一种张力的延伸、精神的释放和无限进取的开拓精神,这恰好是“人性因子”的美好写照,因为“人性因子指的是人类从野蛮(savagery)向文明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能够导致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聂珍钊,2011:6)与此同时,浮士德精神中还包涵着“为追逐知识、财富和权力而不惜向魔鬼出卖灵魂的恶的精神”。(吴晓江,2009:1)在浮士德精神指引下费利克斯伦理精神中的“兽性因子”战胜了“人性因子”,对善的追求降格为兽欲的满足,如聂珍钊教授所说:“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因为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成为有理性的人。”(聂珍钊,2011:6)
契约关系中的费利克斯在批判后现代消费文化的同时展示出较为清晰的伦理判断。费利克斯已经认识到“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差别的消弥,向后现代文化的转轨,给知识分子带来一种特别的威胁”。(费瑟斯通,2000:81)费利克斯对贝妮蒂特“消费狂”的心理疾病作出诊断,即:漫无目的的狂欢化消费让贝妮蒂特整日无所事事,消费成为她生活的全部,消费的停止即是她生命的终结,这是造成她周期性“脑疲劳”(brain-fag)和精神不济的主要原因。(Durrell,1990a:251)以自己发明的超级电脑亚伯(Abel)为例,费利克斯指出后现代消费文化的负面效应已显露无疑,因为亚伯作为一台机器已具备了预知未来、通晓古今文史的能力,相比之下沉溺于大众消费中的人“不过是核糖核酸的残留[RNA遗传信息的载体],不是吗?然而,亚伯却表现出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同上:13)费利克斯以物讽人,机器的智能“人化”与人的消费活动“机器化”形成鲜明反差,后现代社会中的异化消费对贝妮蒂特和费利克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乃至人类文明已构成了威胁。
费利克斯伦理危机的导火索源自契约之争和专利所有权之争;在契约约束力面前,费利克斯却显得束手无策。为“梅林”公司工作多年后,费利克斯希望将一项简单的发明无偿送给大众使用,却遭到公司执行总裁朱利安的断然拒绝。朱利安的回答是:“很高兴在你还没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先来跟我商量。该如何解释呢?即便这发明一文不值,它也还是公司的财产和恩惠——梅林公司的专利。”(Durrell,1990a:283)随后,费利克斯以辞职相威胁,朱利安拿出了他与公司签订的为期20年的合同。谈及合同期限,费利克斯不寒而栗,这让他联想起浮士德博士与魔鬼撒旦签订的为期24年的灵魂契约。
值得注意的是费利克斯兼具“浮士德博士”和“普罗米修斯”的双重伦理身份,其中隐含着与之相对应的多条“伦理线”(ethical line),如,费利克斯实践“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的伦理线等,“伦理线串连或并连”在一起便形成伦理节。(聂珍钊,2010:20)小说中引起费利克斯产生伦理困惑的伦理节有二,它们分别是与公司签订的合同(契约)和专利所有权。为了实现“消费快感”费利克斯签订了契约,费利克斯在享受公司提供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发现自己的发明专利权被公司剥夺。费利克斯为人类谋福利的“普罗米修斯”的伦理身份在与公司间的契约之争和专利所有权之争中凸显出来。虽然费利克斯良心发现,“浮士德博士”内心的“人性因子”被再次唤醒,但他依旧受制于契约,无法按照自己的道德良心支配自己的发明。在逃跑和将发明免费送给大众的努力被公司阻止后,费利克斯像被捆绑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一样被囚禁在公司的疗养院里。
科斯诺斯基(Frank Kersnowski)认为主人公费利克斯是达雷尔在小说世界里虚拟道德法庭上的“被告”,而读者则是“绅士陪审团”,有裁决费利克斯是否有罪的道德审判权。(Kersnowski,1990:138)上述论述不无道理,然而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和达雷尔伦理思想代言人的费利克斯在“道德法庭”上的角色并不固定,而是游离于“被告”和“原告”两种角色之间。作为“被告”的费利克斯崇尚“消费快感”,在“浮士德精神”中的“兽性因子”作用下遵循享乐主义伦理原则;作为“原告”的费利克斯有“普罗米修斯”一样崇高的道德情怀,控诉的是以公司为代表的后现代消费文化对人类伦理价值造成的负面影响。费利克斯介于两种角色之间的不确定性恰是其受契约束缚而欲罢不能的伦理危机的外在反映。
3.0 “阿芙罗狄特”的反抗:后现代消费文化下的伦理启示
如上文所述,发明者、公司、商品三者的有机组合激发出人类“兽性因子”中的自由意志,表现为消费文化下自然欲望的满足。后现代消费文化迎合、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并通过诸多方式将其无限放大。在《阿芙罗狄特的反抗》中,达雷尔为读者绘制了一条明晰的后现代消费文化链:产品发明者(费利克斯)——产品生产者、后现代消费文化主导者(梅林公司)——产品(以艾俄兰斯为例)——媒体(电影、广告)——产品消费者(大众)。通过对艾俄兰斯类人机器人的自杀式反抗和费利克斯烧毁公司合同存放档案室等事件的描述,达雷尔从产品和发明者两个层面出发挑战了公司在消费文化中的霸权地位,解构了上述消费文化链,为人们回归理性消费伦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达雷尔将女主人公艾俄兰斯比作古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特,小说《阿芙罗狄特的反抗》因以艾俄兰斯为原型制造出的类人机器人的自杀式反抗而得名。如鲍德里亚所说,“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消费的已不是物品,而是符号”(转引自罗钢,2003:38),以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审美客体或形象出现的艾俄兰斯以及此后的类人机器人已成为维系公司经济命脉的消费“符号”。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的自杀终结了自身作为商品化了的消费“符号”的存在,实现了作为人的艾俄兰斯伦理回归的欲求。
梅林公司掌握并充分利用了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商品“符号化”特点,即:“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响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费瑟斯通,2000:166)艾俄兰斯经公司包装、媒体宣传从流落街头的妓女华丽转身为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然而究其本质,她不过是公司利用广告、影视媒体制造出来的消费“符号”。公司将艾俄兰斯形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与审美功能与公司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其成为公司产品的文化代言人,最终达到以文化、审美展示的方式促进公司产品销售的目的。艾俄兰斯是双重消费的受害者,第一重消费源于自身,第二重消费源自公司和大众,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前提条件。凯克文斯基指出艾俄兰斯的消费价值在于她的“荧屏意象”(screen image),“艾俄兰斯能俘获后现代社会大众对美好事物的幻想,让他们与美保持联系”。(Kaczvinsky,1994: 70)艾俄兰斯消费欲望的达成以她的消费价值为基础。美貌是其消费价值的源泉。为确保自身作为公司商品被消费的价值和消费欲望得到满足,艾俄兰斯意图通过液体石蜡丰胸的方式维持美丽形象,结果却是反受其害。液体石蜡丰胸是艾俄兰斯致死的原因,这无疑是对后现代消费文化中为了消费而消费的伦理观的强有力反讽,也是后现代消费文化下“人性因子”之理性意志泯灭的挽歌。
透过艾俄兰斯的案例,达雷尔向我们揭示了后现代消费文化“兽化”于人的残酷事实,即:在强大的物欲、消费欲驱使下,艾俄兰斯丧失了理性,成为任公司摆布的消费机器;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的自杀式反抗却是对人性的回归。妓女艾俄兰斯作为电影明星的生是与自身消费欲望的妥协,她的死是为此而付出的高额代价。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的“生”虽然短暂,但贯穿始终的却是“她”对“被消费”的、“符号化”了的生存状态的抵抗。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以自杀终结了作为人的艾俄兰斯“兽性因子”中不可控的自由意志,恢复了“人性因子”中的理性意志。在此,达雷尔给读者的启示是:与作为人的艾俄兰斯相比,类人机器人更具有人的品性。
然而“阿芙罗狄特的反抗”并未就此结束,因为后现代消费文化中“艾俄兰斯的形象和肉体可被再造和买卖”。(Kaczvinsky,1994:73)尽管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与公司领导者朱利安同归于尽,但公司依然运行如故。达雷尔并不满足于主人公个人层面上对后现代消费文化苍白无力的伦理反抗,他认为对后现代消费文化链的解构才是彻底消除伦理真空和伦理危机的有效手段。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的反抗失败后,产品发明者费利克斯的反抗成为解构后现代消费文化链,恢复人们消费理性的必经之路。费利克斯取代死去的朱利安成为总裁后,决定将对公司的反抗进行到底,把储存公司合同的文件室付之一炬,断绝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员工与公司之间的契约关系。“逃离”、“囚禁”和“反抗”这一系列行动勾勒出小说中费利克斯追求自由与真、善、美的伦理主线。
费利克斯从发明者,即:受公司奴役的“无机知识分子”到当权者,即:有伦理判断能力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转变反映出更高层面(社会领导层)上“人性因子”的伦理回归。费利克斯的“逃离”和辞职威胁与他建造的类人机器人的自杀式反抗一样对公司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此时的反抗还未上升到权利和决策层的高度。如何将个人的理性意志注入后现代消费伦理的形塑之中,是达雷尔在小说中为读者提出和解决的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伦理问题。
《知识分子论》中,萨义德曾提到:“葛兰西相信有机的知识分子主动参与社会,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努力去改变众人的心意、拓展市场”,他们有“获取潜在顾客的首肯、赢得赞同、引导消费者或选民的意见”的能力。(萨义德,2007: 12)如前文所述,被“洗脑”后的费利克斯不过是无条件为公司利益服务的傀儡,而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的自杀式反抗重又点燃了费利克斯内心业已熄灭了的“人性因子”中理性意志的火焰。费利克斯焚烧文件室的行动在切断了以公司为中心的后现代消费文化链的同时,彰显了有智慧、有良知的“有机知识分子”以理性意志遏制非理性生产与消费的决心,因此对处于权利阶层的“有机知识分子”“人性因子”的伦理呼吁是达雷尔呈现于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伦理启示。
综上所述,达雷尔为读者展现了后现代消费文化下伦理真空的成因、表现及其严重后果。消费欲望刺激下“兽性因子”与“人性因子”矛盾斗争中主人公的人格分裂和伦理身份的危机。消费欲望原本是人类本能的自由意志的体现,然而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下人们的消费欲望非但没有得到理性控制,却被以公司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放大和利用。达雷尔给身处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我们提出了是“按理所需”还是“按欲所需”;是继续沉沦还是奋起反抗的伦理选择的迫切要求,如《阿芙罗狄特的反抗》中两部小说的书名《彼时》和《永不》所示,“不是现在就是永不——因为我们是人,应该具有选择命运的权利。选择的时间就是现在”。(Durrell,1990b:285)小说主人公类人机器人艾俄兰斯和费利克斯分别在后现代消费文化链的产品和发明者两个环节上的伦理反抗为我们揭示了逃离伦理真空和重塑伦理身份的有效途径。尽管达雷尔在小说结尾为读者描绘了一副类似“乌托邦”式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但作者警醒、启示读者的意图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主人公费利克斯身上闪现着的不仅是“有机知识分子”“人性因子”的光辉,还有一种改良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下的伦理判断和伦理选择的摧枯拉朽的理性力量。
[1]Briggs,K.M.An Encyclopedia of Fairies,Hobgoblins,Brownies,Boogies,and Other Supernatural Creatures[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6.
[2]Durrell,L.Tunc[M].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90a.
[3]Durrell,L.Nunquam[M].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90b.
[4]Fischer,K.P.History and Prophecy:Oswald Spengler and the Decline of theWest[M].New York:P.Lang,1989.
[5]Kaczvinsky,D.P.“Bringing Him to the Lure”:Postmodern society and themodern artist’s“felix culpa”in Durrell’s“Tunc/Nunquam”[J].South Atlantic Review,1994,59(4):63-76.
[6]Kersnowski,F.Authorial conscience in Tunc and Nunquam[A].In M.H.Begnal(ed.).On Miracle Ground Essays on the Fiction of Lawrence Durrell[C].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133-139.
[7]Robinson,J.Love,culture,and poetry[A].In F.L.Kersnowski(ed.).Into the Labyrinth Essays on the Art of Lawrence Durrell[C].London:UMI Research Press,1989.141-150.
[8]Zylinska,J.The Ethics of Cultural Studies[M].London: Continuum,2005.
[9]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0]罗钢.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述评(上)[J].国外理论动态,2003,(5):6-42.
[1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1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6):1-13.
[13]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4]吴晓江.浮士德精神与西方科技文化[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5):1-8.
[1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二版)[M].陈清侨,严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Ethical Reflections on Postmodern Consumption Culture:On Durrell’s Novel The Revolt of Aphrodite
XU Bin1、2,LIU Yu1
(1.School of Applied English,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116044,China; 2.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Through The Revolt of Aphrodite Law rence Durrell has reconstructed and criticized the postmodern consumption culture in a virtual world of the novel.The global commercial empire established by Merlin Group is a miniature of postmodern consumption culture.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comp licated ethical relations among inventor,com pany,p roduct and consumer,Durrell raises a series of urgent questions such as ethical vacuum and ethical crisis.Durrell intends to argue that the awakening of rational will on an individual level and the decisive correct ethical judgment and choice made by“Organic Intellectuals”with sound ethical conscience and aspiration on an authoritative level are the ways in which man’s“animal factor”in postmodern consum ption cu lture is contained and man’s“human factor”is effectively regained.
postmodern consumption culture;ethics;Law rence Durrell;The Revolt of Aphrodite
I106
A
1002-2643(2013)05-0093-05
2013-01-3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劳伦斯·达雷尔研究”(项目编号:13CWW018)、第53批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伦理选择与价值评判——劳伦斯·达雷尔研究”(项目编号:2013M53171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项目编号:12&ZD172)的阶段性成果。
徐彬(1976-),男,山东莱芜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大连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现当代英美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刘禹(1976-),女,辽宁大连人,大连外国语大学应用英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英语教学研究。